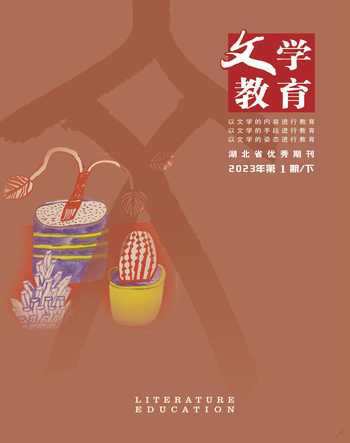《項鏈》中的馬蒂爾德及女性社會規訓性
孟亞璇
內容摘要:學界對法國著名作家莫泊桑短篇小說《項鏈》的內涵以及其中的女主人公瑪蒂爾德形象的解讀呈現出了多元化的趨勢。學界已經從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階級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基于本體象征文本探析以及基于女主人公馬蒂爾德性格的哲學分析,對《項鏈》的文本內部及文本外部均進行了詳實而深入的探究。本文試圖在社會規約的范疇探究《項鏈》中體現的對于女主人公馬蒂爾德以及與其境遇類似的女性潛在的社會規訓傾向性。
關鍵詞:莫泊桑 《項鏈》 馬蒂爾德 社會規訓性
居伊·德·莫泊桑是19世紀法國小說家、作家,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被譽為“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善于捕捉生活的本質,從平常人視而不見的日常平淡生活中挖掘出生命和生活的本質意義與美學價值的內涵,極大的豐富了文學的母題。以凡人小事作為題材,以短篇小說為主要創作形式,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分析、提煉和概括的做法,對生活抱著旁觀的態度,以冷靜的描摹來掩蓋作家對現實的分析,是莫泊桑在文學題材和體裁上的突破。其名作有《項鏈》、《羊脂球》、《俊友》等。《項鏈》是法國作家莫泊桑創作的短篇小說,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最初刊載于1884年2月14日的《高盧報》(Les Gaulois),以其極具莫泊桑風格的大逆轉結局而聞名。故事講述崇尚上流社會的女子瑪蒂爾德(Mathilde),年輕時總是夢想自己擁有珠光寶氣并受人欣羨,但成年后仍舊一無所有,并嫁給了一個只會一味討她歡喜,在教育部當低階文員的洛瓦塞爾(Loisel)。一天丈夫爭取到了供職教育部舉辦晚會的一封請柬。在機會面前,瑪蒂爾德卻因沒有服飾十分懊惱。丈夫把原本要存下來買來福槍的錢給她買了華麗的晚裝,但她還是想要珠寶首飾。因為沒有錢,丈夫讓她找她以前的同學珍娜(Jeanne)借點兒首飾。她有幸借到了最眩目的寶石項鏈,也的確令她占盡晚會的風頭,不料隨后項鏈就丟了。瑪蒂爾德和丈夫傾家蕩產的拿出積蓄并借債湊夠三萬六千法郎買來新項鏈還給珍娜。隨后數年里,她和丈夫勤儉節約,辛苦勞作償清債務。瑪蒂爾德在極樂公園撞見了珍娜,并告訴了她項鏈丟失后買新項鏈奉還的事情。珍娜聽完非常驚異的說,那串項鏈其實只是價值五百法郎的贗品[1]。
《項鏈》中莫泊桑對于洛瓦塞爾一家遭遇的冷靜描摹使得此短篇小說有著極大的解讀和研究空間。首先便是女性主義的解讀,比如有學者就十九世紀后期法國女性的權益和兩性平等方面切入,研究當時法國廣大中產階級女性的生存和婚姻狀況以及女性意識的覺醒程度,并得出結論道當時的法國婦女們“看似有所改觀的生存狀況和有所覺醒的女性意識背后依然是獨立人格、平等夫妻關系、婚姻自主權、外出就業權、財產支配權的缺失,女性原本低下的地位并沒有因為婦女運動的風起云涌而發生實質性的改變。”[2]有學者從《項鏈》的結構藝術巧思和本體象征方面進行研究,將洛瓦塞爾一家從借項鏈,戴項鏈炫耀,丟項鏈和通過勞動賠償項鏈……這樣層層遞進的結構,結合女主人公的遭遇把人的個性與共性結合起來,從局部對故事的象征意義進行闡釋,并得出結論“項鏈”既是人性的虛榮卻又能夠激發人性對于誠信與勞動的向往,同時還蘊含了“人物命運和人生哲理的本體象征”[3]的戲劇化事件。還有學者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利用“人格結構理論來解讀瑪蒂爾德的人格裂變,以此重構瑪蒂爾德這一藝術形象”[4],而馬蒂爾德也“完成了從自我焦慮到生存危機、從道德拯救走向人格升華的人格裂變過程[5]。”除此之外還有眾多學者從階級審判角度,辛辣的指出《項鏈》中體現的階級壓迫和上層階級即資產階級和舊貴族的虛榮[6]。
以上眾多學者的研究和多元化解讀豐富了《項鏈》的內涵,而筆者也試圖通過新的理論來解讀此短篇小說中的后現代性。雖然莫泊桑是知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但縱觀其作品,那難免不發現后現代性的蛛絲馬跡;并且,后現代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思維方式,“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二十世紀60年代后期出現于西方的社會文化思潮,最初崛起于建筑和文學領域,后來迅速擴展到藝術、哲學、社會學、歷史學、語言學等人文和精神科學領域”[7],雖然后現代主義思潮有著一定的懷疑主義,否定主義和虛無主義立場,但不可否認其給我們“提供了觀察視角的變換”[8]這種全新視角的改變能讓我們對一些“熟視無睹、已經被當做‘自然(nature)的東西,進行一番再審視,而發現它們其實是‘文化(culture)”[9]。
米歇爾·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打過一個比方,“一個建筑物不再僅僅是為了被人觀賞(如宮殿的浮華)或是為了觀看外面的空間(如堡壘的設計), 而是為了便于對內進行清晰而細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舉一動都彰明較著。”[10]這里的“建筑”據福柯即為監獄,作為國家這個階級統治的載體[11],監獄在福柯的筆下是社會權力對于被統治者的“規訓”工具,通過監獄,“控制他們的行為,便于對他們恰當地發揮權力的影響,有助于了解他們,改變他們”[12]。而這種規訓也并不僅僅存在于監獄當中,它滲透入社會的各個層面,其中就包括規訓書寫。筆者不討論莫泊桑是否在作品中故意進行規訓書寫以宣揚其自己認為理性的價值觀,但無論作者是有意或者無意,社會的規約性也一定會滲透到作者的作品當中并體現出來蛛絲馬跡。故本文從福柯的社會規約理論入手,從“監視(surveillance)”、“等級劃分”、“規范(norm)”和“檢查”四方面入手,探討《項鏈》體現的社會規約性。
監視、等級劃分、規范與檢查:
米歇爾·福柯在其《權利與規訓:監獄的誕生》一書中提到“‘規訓既不會等同于一種體制也不會等同于一種機構。它是一種權力類型,一種行使權力的軌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術、程序、應用層次、目標。”[13]福柯以監獄、學校、軍營和官僚文書機構為例深入講解了規訓的機制。在監獄中,監獄長無時不刻不在監察被安排在一排排單人監房中的犯人;他們會給每個犯人劃分等級鑒別品質并設立獎懲,聽話的犯人適當減刑而屢教不改的慣犯則加重懲罰;并且在貫穿整個的過程中時不時進行高度程式化的例行檢查以加深,通過檢查“顯示了被視為客體對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對象化”[14],在這種實踐中權力關系將會異常顯著,正如閱兵中,士兵和軍隊及政府領導者的關系一般。
“被降低了身份地位的人”
福柯在權力層面的宏觀監視講的是權力中心為了控制被統治者而進行的“分層的、持續的、切實的監督”[15],而落實到個人層面,必然是權力主體對于客體的俯視,這種自上而下的俯視無疑會對被監視的個體產生極大的精神壓力并且產生焦慮情緒。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監督,規訓權力變成一種“內在”體系”[16],使得被監視者雖然在體系內,但自己卻不自知,由此一來,監視所造成的嚴重精神壓力就會表現出異化的特征,而被異化的人,則會絞盡腦汁逃離這個階層。正如《項鏈》的女主人公馬蒂爾德一樣,她“長得面目姣好,風韻迷人”[17],然而卻出生在一個普通的職員家庭,沒有什么家底和遺產也沒有高貴的嫁妝可以讓她高攀富貴之門,于是“她不得不聽人擺布,嫁給了教育部的一個小科員”[18]。那么所謂的監視者在哪兒呢,這就不得不提到馬蒂爾德對于自己的認知以及當時的法國社會狀況。
馬蒂爾德雖身為小職員家庭的普通妻子,卻妄想著有一天能夠登上大雅之堂,她總感覺自己“像一個被降低了身份地位的人一樣,為此,她感到委屈不平”[19]。雖人們對自己的認知有著個體差異性,但不可否認的是一定的社會歷史狀況條件下的權力滲透影響會對人造成更大的影響,正如權力是“一種復雜的、自動的和匿名的”[20]。在《項鏈》出生之時法國正在如火如荼的經歷工業革命,大量的工業資產階級和借助機器工業發達的部分舊貴族與勞動人民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但是底層的勞動人民以及落魄貴族仍然有著一定的上升空間,其中文中就提到了女性的漂亮容顏就是她們的珍貴財富[21],正如此小說提到“她們的美麗、她們的風度、她們的魅力就是她們的出身和門第。而單憑她們天生的聰慧、她們自然的優雅和她們機智的頭腦,就足以使這些平民百姓家的姑娘和最高貴的婦人平起平坐。”[22]她們的姿色,就是她們階級躍遷的手段。而這也成為了新興工業資產階級打著愛情的名義向下兼容落魄貴族為自己的家族貼金的絕佳手段,由此看來,似乎是一個雙贏的策略,但同時這也是一段權力的敘事,也是文中上層階級對馬蒂爾德和其境遇類似之人的審視,此審視,即使滲透著權力意志的監視。
但是對于只有小職員家庭出身且已經嫁給了另一個小職員洛瓦塞爾的馬蒂爾德來說,以上這個滲透著經濟和家族社會地位的權力敘事的“雙贏”的策略,儼然成為了面容姣好的馬蒂爾德的一個高壓監視者,這個監視者不斷地捶打著馬蒂爾德,使她認為自己“感到委屈不平”[23],因為當她“覺得自己生來就是應該享受各種考究、豪華的生活”[24],這個監視不停地將馬蒂爾德異化于她所在的階層,憋屈的不滿促使她整日沉迷幻想,妄想不勞而獲得逃離這個小職員之家,與達官顯貴同宴共舞、共進晚餐。可是命運卻給她開了個玩笑,當馬蒂爾德看著自己家“簡陋的住室、寒磣的墻壁、破損的椅凳、難看的衣衫”[25],她想到的是“四壁蒙著古色古香的絲綢的大客廳,夢想著那些上面陳放著珍奇擺設的精致家具;還有那種經過精心布置的、香氣沁人的小客廳”[26];當他丈夫揭開大湯碗并喊著“‘哎呀,多好吃的牛肉蔬菜濃湯啊!”[27],她遐想著“精美的晚餐……那些盛在高貴器皿里的美味佳肴……鱒魚肉或者松雞翅膀……向她獻媚的娓娓情話”[28]得英俊男友。她沒有珠寶衣裝金銀首飾,但她卻覺得自己生來就是為了享受這些東西得,她希望自己被別人喜愛,被別人羨慕,被別人欽佩著,但每當她見到自己有錢的同學,面對來自于她目光,她會感到“極大地痛苦,既傷心又懊惱,既悲哀又絕望,甚至要一連難過上好幾天”[29]。這種極大痛苦的來源就是社會層面的監管,換一句話說,就是來自于文中“有錢人”的審視,這種金錢審視將馬蒂爾德排除在她想要融入的圈子之外,妄圖跨入而無力的現實不斷侵襲著馬蒂爾德,逼迫她做出無妄的舉動,由點開始,這個滲透著權力意志的審視,即監視是她曾經的女同學,擴展到面,即是她妄圖成為其中一員的“有錢人”或上層階級。
“你叫我穿什么衣服到這種場合去?”
小說的張力和矛盾在馬蒂爾德的丈夫洛瓦塞爾得意洋洋得拿回來一個大信封開始逐漸上升,那是一張教育部長邀請他們家去大廈參加舞會和晚宴得請柬,這一張請柬使得馬蒂爾德離她想融入上層社會圈子得夢想更進了一步,然而這張請柬并沒有使得馬蒂爾德欣喜若狂,反而使她氣洶洶而悶悶不樂,“‘你叫我穿什么衣服到這種場合去?”[30],馬蒂爾德氣勢洶洶。為何在馬蒂爾德得到機會之后卻憂郁了并且更加的焦慮?在這里,參加此等上層階級得宴會隱含著對于等級的劃分,等級既是“標示出差距,劃分出品質、技巧和能力的等級”[31]也是“進行懲罰和獎勵”[32]得手段。這種等級的劃分促成了一種紀律性和表演性,作為教育部晚宴得舉辦者,他們擁有這個國家的的教育話語權力和一定得經濟權力,他們是馬蒂爾德心中上層階級得代表,他們穿著富麗堂皇、光彩奪目,珠光寶飾錦衣玉食渾然天成,反觀馬蒂爾德,當她質問自己丈夫她應該穿何衣服而去時,丈夫只得“結結巴巴地說:‘你去戲院穿的那套衣服呢?依我看,那一套就不錯嘛……”[33],這套衣服,還有之后馬蒂爾德索要得珠寶首飾,就是一張進入晚宴得“入場券”,是一個等級劃分得符號,沒有華服首飾,就無法被認同無法融入到這個價層,也就無法應邀去參加舞會,因為不會被認可;而有了這一切,參加舞會就顯得從容了許多。在這里雖然可以將馬蒂爾德得行為解釋為愛慕虛榮和崇拜奢華,但是脫離社會權利滲透得社會監視和與其相呼應得等級劃分尺度,顯然是有失偏頗得。
總之,以華服首飾為代表的“入場券”,作為等級劃分得工具以“‘賦予價值的度量”[34],馬蒂爾德和其代表的人亦或接收亦或排斥于更上一個社會階層。而用于劃分等級的工具,或者是標準,即為前文提到的“規范”,當華服首飾廣泛應用于等級劃分時,其就會自動變為“自18世紀以來,已與其它力量——律法、圣經、傳統結合起來”[35]得“規范”的力量,而在文中,這一刻華服首飾成為了馬蒂爾德心目中理所應當的“傳統”。
而在規訓過程的核心,“‘檢查顯示了被視為客體對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對象化。權力關系和認識關系的強行介入在檢查中異常醒目”[36],當馬蒂爾德穿上他丈夫省掉買獵槍的錢而籌買的漂亮裙子,戴上從她同學福雷斯蒂埃太太那里借過來的“黑緞子的小盒子里發現一串富麗堂皇、光彩奪目的鉆石項鏈”,她在教育部晚會上“一舉獲得成功。她的美貌壓倒了所有在場的女人。她豐姿綽約,儀態嫻雅,臉上始終帶著迷人的微笑,她快樂得簡直要發瘋了。所有男人的眼睛都盯著她,他們打聽她的名字,想方設法和她結識。部長辦公室的每個隨員都希望跟她一起跳舞”[37],甚至連教育部長都注意到了她。在晚會上馬蒂爾德異常醒目,但更加醒目的是周圍人群的反應,他們為馬蒂爾德容貌的癲狂,恰是默默的對于馬蒂爾德躋身入與他們同等階層(哪怕僅僅一夜)的檢查。
“粉紅色的指甲在洗刷餐具”
到此為止,筆者從文本實踐的角度分析了《項鏈》中隱含的社會規訓性,但文學作品本身,則是一個實于虛的結合,是一面現世的鏡子。此短篇小說中無疑也可以看得出莫泊桑身處在那個時代所有的隱含的社會規訓性。在馬蒂爾德發現自己借到的項鏈不慎丟失之后,她沒有選擇去買一個假的哄騙福雷斯蒂埃,而是跑遍了整條街所有的珠寶店,以三萬五千法郎買下了一模一樣的項鏈還給了她的朋友。三萬五千法郎,對于小職員家庭不堪重負,他們“開始借起債來……和高利貸者以及各式各樣的放款人打交道,不管將來有沒有能力歸還,他冒著后半輩子生活要受到損害的危險,在借據上簽字畫押”[38],在此之后,馬蒂爾德被莫泊桑塑造成為了一個誠實守信,勤勞在家勞動的婦女,“她早已英勇地下定決心,非還清這筆巨大的債務不可,她相信自己會還清的”[39]。馬蒂爾德“穿著已和平民婦女一模一樣。她手臂上挎著籃子,去肉鋪,去蔬菜水果店和食品雜貨店買東西”[40],她“和店主討價還價,每一個蘇都斤斤計較,有時甚至要遭到辱罵”,但她任勞任怨,“每個月都得償還幾筆債款,同時還要續借幾筆”。就這樣過了十年,他們終于還完了所有的貸款。從此之后莫泊桑筆下的馬蒂爾德已經不是那個“金錢奴隸型女性 人物”[41],而是一位勇敢的承擔起自己犯下的過錯,以勞動來還清貸款,救贖自己的偉大女性,而她也終于能夠“還清了,了結了。如今,我有種說不出來的高興”。長久以來人們對于馬蒂爾德的轉變贊不絕口,對于莫泊桑對于貪得無厭紙醉金迷的上層人士諷刺拍手稱快,但是莫泊桑的筆下,依然滲透著潛移默化的社會規訓的。雖然時隔百年我們已經無法捉摸莫泊桑的寫作意圖,但是早在1791年9月,奧蘭普·德古熱(別名瑪麗·戈茲)就發表了《女權宣言》,詳細論述了17項要求,其中就包括女性的經濟權力,而飛速發展的經濟也出現了相當的勞動力短缺,為女工的大量出現打下了客觀基礎。但是反觀《項鏈》,在馬蒂爾德準備同丈夫一同還清貸款后,莫泊桑對于馬蒂爾德的描寫依然局限于“家里的粗活兒、廚房里的骯臟活兒都由她自己干。她的粉紅色的指甲在洗刷餐具中,不斷和油膩的陶瓷碗盆以及鐵鍋鍋底擦碰,已經磨損得不像樣子了。她清洗臟了的被褥衣衫、餐桌抹布,洗好后再掛在一根繩子上晾干。每天早晨,她把垃圾送到樓下的街邊去,再把所需要的水提到樓上,每上一層樓她都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氣”[42]。莫泊桑沒有描寫任何馬蒂爾德在參與增殖社會經濟勞動的情節,馬蒂爾德從始至終仍然是圍繞家庭勞作的“家庭主婦”式女性。而這個馬蒂爾德的形象,卻被不斷贊譽,這里無疑透露著《項鏈》所有的,對于現實社會映射的潛在的社會規訓性,有待繼續發掘。
注 釋
[1]詳見Maupassant,Guy de. Short Stories of De Maupassant: Including the Necklace, Love, the Piece of String, Babette, and Ball-of-Fat. Book League of America, 1947.
[2]侯曉艷.從瑪蒂爾德的際遇看當時法國女性的處境[J].蘭州學刊,2013(4):217-219.
[3]覃虹.簡論《項鏈》的藝術巧思和本體象征[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8(1):107-108.
[4]雷小青.生存危機與道德拯救——《項鏈》中瑪蒂爾德人格精神分析學解讀[J].社會科學輯刊,2008(4):213-215.
[5]雷小青.生存危機與道德拯救——《項鏈》中瑪蒂爾德人格精神分析學解讀[J].社會科學輯刊,2008(4):213-215.
[6]詳見[1]鄧楠.論莫泊桑短篇小說中的資產階級女性形象[J].外國文學研究,1998(2):110-113;[2]鄭桂華.城市空間與生活表演:《項鏈》的現代解讀一種[J].都市文化研究,2016,0(1):310-322;[3]Nurmalasari, Uning, and Samanik Samanik. "A Stud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France In 19th Century as Portrayed inThe Necklace ‘La ParureShort Story by Guy De Maupassant."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LLiC) Proceedings. Vol. 2. 2018.
[7]章國鋒.后現代主義:回顧與反思[J].外國文學.1996(6):274-297.
[8]盛寧.《關于后現代“表征危機”的思考》.
[9]盛寧.《關于后現代“表征危機”的思考》.
[10]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13.
[11]“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列寧.
[12]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13.
[13]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41.
[14]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21.
[15]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16.
[16]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16.
[17]莫泊桑,《項鏈》.
[18]莫泊桑,《項鏈》.
[19]莫泊桑,《項鏈》.
[20]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16.
[21]落魄貴族將女兒嫁給新興工業資產階級成為保證家族地位的方法,法瑟諾博斯.《法國史(上下)》.1964.
[22]莫泊桑,《項鏈》.
[23]莫泊桑,《項鏈》.
[24]莫泊桑,《項鏈》.
[25]莫泊桑,《項鏈》.
[26]莫泊桑,《項鏈》.
[27]莫泊桑,《項鏈》.
[28]莫泊桑,《項鏈》.
[29]莫泊桑,《項鏈》.
[30]莫泊桑,《項鏈》.
[31]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19.
[32]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19.
[33]莫泊桑,《項鏈》.
[34]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20.
[35]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20.
[36]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75.p.121.
[37]莫泊桑,《項鏈》.
[38]莫泊桑,《項鏈》.
[39]莫泊桑,《項鏈》.
[40]莫泊桑,《項鏈》.
[41]鄧楠.論莫泊桑短篇小說中的資產階級女性形象[J].外國文學研究,1998(2):110-113.
[42]莫泊桑,《項鏈》.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