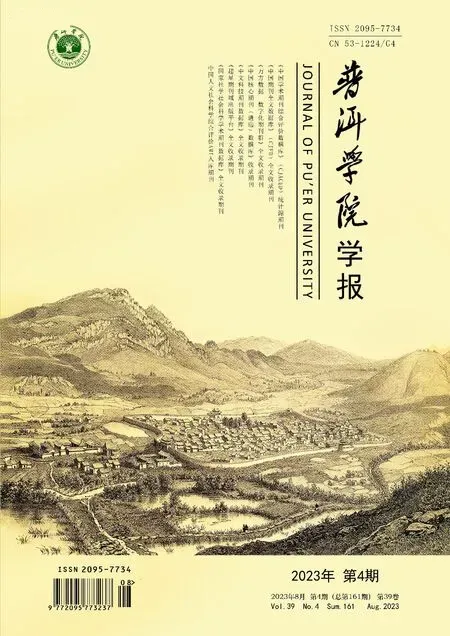存文學《悲愴之城》中區域災難書寫與集體創傷記憶
楊驍勰
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北京 100081
災難母題作為中國歷史悠久的文學傳統之一,從春秋戰國流傳至今,在時間的推移中歷久彌新。現代以來,例如丁玲的《水》、趙樹理的《求雨》、石靈的《捕蝗者》等小說,真實記錄了災難中的社會現實與民生疾苦。進入當代,作家們不僅繼承災難母題敘事的傳統,而且賦予災難寫作社會責任、歷史使命感和文明反思的新內涵。
存文學是當代哈尼族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由于特殊的多民族地區成長背景,其作品的包容性與豐富性是他的最大特色。一方面,他將云南各民族的歷史變遷與社會發展融入到作品中;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打造出原始與現代碰撞、多元文化融合的“第三空間”。1999 年至2008 年間,他對區域歷史題材小說進行了多次嘗試,2003 年的《悲愴之城》正是其中最成功的作品。作為一名少數民族作家,他自覺地參與到區域歷史書寫和集體創傷記憶描述中,這是一種非常可貴的創作思考。
一、 多民族記憶之傷:1918—1949年大瘟疫的創傷記憶
在心理學中,創傷記憶“指對生活中具有嚴重傷害性事件的記憶”[1],是一種主要關乎個人身體、心理與精神的傷害,有個體性、親歷性和情緒性三大基本特征。但創傷記憶也并非是完全個體化的,其已從個體性的創傷記憶升級成為群體性的創傷記憶。
小說《悲愴之城》的歷史背景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1918 至1949 年間,歷史上有“金騰沖,銀思茅”之稱的茶馬古道重鎮思茅,一改過去在人們印象里酒肆茶樓林立,夜夜笙歌不斷的繁榮富饒景象,連年的鼠疫、瘧疾、爛腳桿病泛濫,加之醫療條件的限制及居民思想觀念的落后,使本來繁榮的思茅變成了一座“城池坍塌、百業凋零、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愴之城”[2]。
許多群體性的創傷記憶,在一代一代當地人心中留了不可磨滅的種子。他們將“老虎豹子大白天進城;夕陽西下時魔鬼們上房揭瓦;野馬蜂在瞬息間就把一個小孩的肉叼去只剩一具骷髏;土匪們又如何耀武揚威的洗劫小城”[2]的故事口口相傳下去,成為存文學創作小說《悲愴之城》的靈感來源。于是一本由“事件、事發環境、親歷者及其共同構成的已經過去的‘歷史’”[3]書誕生了。
(一)災難籠罩下的小人物們
“閃光燈記憶”最早由美國心理學家布朗和庫里克提出,指“就像閃光燈的意象所暗指的那樣”的記憶。“閃光燈記憶包含了很多具體的細節,這些細節也許是偶然進入人們記憶中的,但它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事件不的不同方面,反映了個體對時間的不同認識,最終也必然會將分散的、零碎的、印象式的記憶匯聚成一個整體,復原時間的輪廓和面貌”[3]。小說《悲愴之城》就是這樣一個小人物們“閃光燈記憶”的匯總,一場歷經30 年的大災難。
故事從一場劫后余生的婚禮開始。新郎是大生堂熬膠作坊的喬生,新娘是大病痊愈的秀蘭,連年的瘟疫、霍亂、戰爭使人們已經麻木于悲傷之中,這樁喜事給凋敝小城帶來久違的快樂。此時,居民們得知抗日遠征軍要撤回思茅駐軍的消息,往日已經失去生氣的小城,又恢復了活力。可一切期盼在遠征軍到來之際落空,這支潰不成軍的隊伍帶來了更可怕的災難:他們以保護小城之名劫掠財富、強奸婦女,還從緬甸帶回更可怕的瘧疾。剛收獲短暫幸福的新娘秀蘭因被羞辱選擇自殺,新郎喬生則變成游走街道的瘋子,許多居民也因疾病的加速傳播、無法就醫而死亡。遠征軍隊的指揮官朱旅長、縣長徐世清與土匪楊三皮則互相勾結,在災情嚴重的檔口上演了一場又一場監守自盜的鬧劇,最終因他們將國際救濟團的藥品高價倒賣給當地鄉紳和富商,致使疫情無藥可控,反噬自己。
小說沒有籠統的給不同階級人物貼上刻板標簽,而是將親歷者口述的“閃光燈記憶”,以剪切的手法納入到一個個小人物的生活中去,將碎片化的故事片段,拼接起一幅完整的小人物生活長卷,并把史料背后鮮為人知的人物性格和歷史細節,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被小城居民奉為“救星”的醫生鄭濟人因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他在深愛的女孩與瘧疾纏身的病人之間選擇了后者,最終抱憾終身。妓女小芭蕉是縣長許世清的情婦,她的內心雖然厭棄許世清,但為了“錦衣玉食”的生活一直依托于他。可當親眼目睹居民們病魔纏身的慘狀,她決然地離開了許世清,選擇了從良,并加入到抗疫的隊伍中。遠近聞名的惡霸楊三皮,經常到小城中燒殺搶掠,后又勾結許世清盜取軍械庫武裝自己,成為方圓百里的“山大王”。
存文學創作《悲愴之城》的素材,除了史料外,主要來源于幼年時期長輩對思茅大瘟疫的講述與采訪當年幸存親歷者。但筆者認為最后一位親歷者的離開,并不意味著一段創傷記憶的所有細節都會死亡,它可以通過口述、文學創作等介質活躍于后人的記憶中,成為一個族群、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永遠無法抹去的集體記憶。
(二)死亡陰影下的真實人性
在任何年代,災難都是一面放大鏡,環境的高度壓迫、資源的極度失調與物質的過度緊缺,使庸常生活中的所有矛盾集中化、擴大化。重災區則成為人性的修羅場,真善美在這里發揚,罪惡也能在這里釋放。
棺材店老板張四,做的是在死者身上發財的生意,他以免費提供送葬服務為由,把同一口棺材賣給不同的人家,白天送死者落葬,晚上又再悄悄派伙計將棺材板拆回店里組裝后二次銷售。國際救濟團的藥品送到后,他通過兩根金條賄賂許世清,用市場價購買藥品,最后再以十倍價格賣給病重的人家,賺取高額利潤。許世清本來只是個出風頭、貪圖小利的官員,可他在得到土匪楊三皮的大額賄賂后,先與楊三皮勾結“監守自盜”盜取槍藥庫中的武器,后又將救濟團的藥高價賣給賄賂他的鄉紳、富豪,最終導致小城醫院無藥可用,爆發更大規模的疫情,結果他自己在逃亡的路上因身患瘧疾而亡。朱旅長是個徹頭徹尾的反派角色,為了得到金錢與小美人做出許多不可饒恕的惡事,導致自己成為“光桿司令”,只能用虎皮賄賂美國人出逃。
人物二分法理論最早是由E.M.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提出。他認為圓形人物與扁平人物沒有孰高孰低之說,“一部復雜的小說經常既需要圓形人物,也缺不得扁平人物。”兩者相互磨合的結果才“更加接近真實的人生”[4]。存文學的小說《悲愴之城》中正是踐行了福斯特的這種理論,通過“圓形人物”加“扁形人物”的描寫手法,將災難籠罩下世俗人生中的方方面面展現在讀者面前。
除了充滿復雜人性的角色外,小說還塑造出三個完全向善的人物:鄭濟人、劉兆一與楊阿狗。存文學對于向善的扁平人物的塑造,其意在于為黑暗的故事加上光明的曙光。楊阿狗是思茅小城里家喻戶曉的英雄,他本隨著舅舅跑馬幫,在泰國、緬甸與思茅之間做小生意,后來因遇上侵入緬甸的日軍,舅舅慘遭殺害,楊阿狗懷著為舅報仇的心愿加入了緬甸遠征軍,他在戰場上砍掉過無數敵人的頭顱。楊阿狗在遠征軍回歸前一天返回小城探路,卻看到年邁的父母慘死家中。但這并沒有打倒楊阿狗,他表現出了堅韌、樂觀的高貴品質。小學校長劉兆一則是小城里少有的文化人,他大學畢業后,不畏疾病的肆虐,選擇回到家鄉辦學,即使自己染上“爛腳桿”病,也將治療小城的居民放在第一位,甚至甘愿冒著生命危險,成為新治療法的臨床實驗病例。
小說《悲愴之城》是探尋真實世界中人性的一個窗口。作品中,不同的人性在這最密閉的生存空間和最尖銳的物質沖突中展現出來。有的人朝著惡的深淵里越走越遠,最終反噬自己;有的人在善惡之間苦痛掙扎,最終逃不過良心的譴責;有的人受盡命運的不公與折磨,卻仍不放棄尋找希望。
二、區域性反思之痛:思茅地區居民不可磨滅的集體記憶
小說《悲愴之城》并不止于刻畫死亡的慘狀,而是旨在通過小人物們的悲喜生活展示災難下思茅地區的社會全貌。這可以喚起后人對現有生存狀態的反思,與對未來理想追求的重新建構。
(一)共時性: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作為一本描寫災難之下小人物的作品,存文學在創作小說時,通過將親歷者們閃光燈記憶的細節進行匯合,“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事件一份不同方面、反映個體對事件的不同認識”,將“分散的、零碎的、印象式的記憶匯聚成一個整體,復原事件的輪廓和面貌”[3]。這種創作手法暗合了倫理學家瑪格利特在《記憶的倫理》中提出的觀點。他認為閃光燈記憶是個體記憶轉向集體記憶的橋梁,并將集體記憶劃分為共同記憶和分享記憶。
就集體記憶而言,強調記憶主體親歷性的共同記憶,即是不同閃光燈記憶的匯合。它意味著“將所有親歷者的記憶聚合起來,當這些親歷者的數量達到或超過一個限度”[3]時,共同記憶就能成為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集體記憶。思茅地區30 年“大瘟疫”的故事,也正是由當年親歷者們的記憶組合,并轉化成屬于親歷者們及其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作為過去的歷史,后人要完全窺見當年的真實現狀已屬奢望,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共同記憶會變得黯淡與模糊。書中出現的蔡阿婆這個帶有共時性特征的人物,她與《望天樹》中的波西、《牧羊天》中的老紅奶、《碧羅雪山》中的阿鄧多梨拔構成了存文學小說創作中的一種人物類型——記憶老人。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歷史,時間的齒輪始終在向前運動,記憶也永遠在變化和更替之中。
(二)歷時性:世代人的分享記憶
趙靜蓉在《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一書中寫到:“記憶像一條流動的河流生生不息,記憶的主體承載著各自的使命也在永恒的演繹著生命的故事,每個人都有責任實踐和完成自己所擔負的記憶的使命”[3]。1918—1949 年的“大瘟疫”就是這個區域的居民乃至所有聽說過、討論過這段歷史的人們需要共同承擔的記憶使命。就記憶的交流而言的,分享記憶“不單單等同于個體記憶的聚合,因為記憶被聚合并不等于記憶就能被分享”[3],它“意味著在聚合個體記憶之外,還要對那些分散的個體記憶進行‘校準’或‘修正’,使之從一種個體的言說上升為公共空間里可供開放性交流和自由討論的話題”[3]。
小說《悲愴之城》中刻畫了小芭蕉、老大嫂、小美人等形態各色的底層女性角色。小芭蕉的故事是關于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成長史。她本是跟著四川戲班子來到思茅演出,后因整個班子的人馬都染上擺子病死了,只能到涼粉攤前賣唱,結果慘遭土匪楊三皮強奸。小芭蕉為生存先是淪落為妓,后又做了許世清的情婦。但在救下瘧疾纏身的秀蘭、兩次冒風險盜藥、安慰照顧的病人有所好轉之后,她內心的自我蘇醒過來,并勇敢離開依附多年的許世清,成為小城抗疫的中流砥柱。小美人則是亂世中的悲劇女性,她雖為山寨神槍手,卻只能成為楊三皮與朱旅長互相爭搶的玩物而不自知。
除了底層女性外,還有鄭濟人、劉兆一、楊阿狗、張四等知識分子、士兵與小商販的代表。一方面,他們逃不開許世清、朱旅長、楊三皮的“權力大網”;另一方面,在混亂的時局中尋求自我的價值。鄭濟人懷著一顆“醫者仁心”,以“救死扶傷”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劉兆一則把心都撲在教育上,即使自己染上了“爛腳桿”病,也與鄭濟人一起帶著大家抵抗疫情,希望早日迎接復課。他們身上都表現出了知識分子身上濃濃的人文關懷精神。楊阿狗作為士兵,他表現出強烈反抗精神,違背出入令為死去的戰友送葬、為病重的戰友尋藥、幫助戰友們嘗試“刮骨療傷”的新方法,拯救了多位戰友的生命。
作品中,小商販趙四則秉承著“亂世出英雄”的信條,發災難財。許世清、朱旅長與楊三皮分別代表了當時思茅城里的黑暗政治、腐敗軍隊與混亂民間。小說中對災難下各色小人物的描寫,也恰恰暗合了共享記憶對個體記憶的修正與校準功能,使記憶在共享的過程中逐漸完善、代代相傳。
三、人類責任感之思:從“文學創傷”走向“文化創傷”
(一)少數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與公共衛生事件書寫
目前,學者們討論較多的是以下四部作品:劉震云關于河南大旱的《溫故一九四二》,遲子建關于哈爾濱鼠疫的《白雪烏鴉》,阿來關于“汶川地震”的《云中記》與張翎關于“汶川地震”的《余震》。而對于云南少數民族作家的災難題材小說則少有關注。存文學是當代哈尼族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評論家與學者們對其作品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獸靈》《碧羅雪山》《望天樹》等帶有明顯地域特色的作品之上,對《悲愴之城》這部作家隱藏自己的本民族顯性特征,融入大歷史敘事角色的作品一直沒有過多研究。
從文學人類學的角度出發,“少數民族”標簽對于作家而言既是肯定,也是束縛,它既意味著特別,也可能成為遮蔽。按照俆新建的“三重文學敘事”理論[5],自我、群體和國家可以分為“自我敘事”“族群敘事”和“國家敘事”三個層面。其中,“自我敘事”是僅關于個人的淺層。在許世清接受楊三皮賄賂的章節里,大老鼠鬼魅的聲音讓人難以忘懷,第一次與土匪打交道的許世清沉浸在越界的緊張與銀元的快樂中,最后被拖著大尾巴的碩鼠們嚇了一跳。“族群敘事”則是關于某個特定群體的層面。在小說中存文學多次提到沒錢買棺材下葬的平凡老人,睡前會穿上漂亮新鞋的細節描述。由于歷史上的“大瘟疫”,親歷者們有了穿臟鞋的人去世后不能投胎轉世、進入新輪回的習俗,于是為了防止自己在睡夢中離去,沒人幫忙換上干凈的新鞋,老人們一直秉承這個獨特的習俗延續至今。
存文學在小說《悲愴之城》中,對于自我身份的考量已經不限于前兩個層面中,而將“自我”與“人類”的兩端連接起來,是一種文學經驗上的超越。他將自己的本民族身份內置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敘事之中,這種書寫手法是值得關注的。
(二)“文化創傷”的重新建構與再突破
從“文學創傷”走向“文化創傷”,是關于文學與社會學的跨學科交流,它意味著創傷記憶從一個文學主題,演變為哲學、道德甚至倫理主題。美國社會學家杰弗里·亞歷山大在界定“文化創傷”時,認為其是“一種群體性的受傷害體驗,它不只是涉及到個體的認同,而且涉及到群體認同”[6]。
小說《悲愴之城》的故事,與阿來《云中記》和張翎《余震》的區別之處在于,后者作為災難的親歷者,其作品屬于見證文學的范疇,情感激昂且帶有傾訴的性質。而前者是對“大瘟疫”創傷性體驗的事后重建,作家在獲得了反思災難的能力,認識到造成災難逐漸惡化的根源之后,對社會危機的意義有了更加深刻的新思考。屬于對“文化創傷”冷靜而深刻的重新建構,其目的主要在于思考“后災難、后創傷時代的人類應該怎么辦”[6]。
思茅城的瘟疫是由天氣燥熱、環境惡化及衛生欠佳等外在條件引發所致,但惡化的根源還是在于人本身,無序的環境及緊缺的資源,使人性最深處的東西被發掘出來。許世清、朱旅長及楊三皮以救災藥物中飽私囊是災難惡化的直接推手,張四則為了利益倒賣藥品加速悲劇的到來,處于病痛折磨與生活打擊的居民們,本來是這場災難實實在在的受害者,但他們對治療機會及藥物無意識的搶奪造成了更大的混亂。直至故事結尾,在鄭濟人、劉兆一、小芭蕉等人的努力下,災難中幸存的人們開始清醒,并走上自救道路:唯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唯有團結才能戰勝災難。
存文學在后記中談創作《悲愴之城》的初衷:“我國著名作家丁玲生前到過思茅,在座談會上,老人家說,你們為什么不寫思茅?這里發生的大瘟疫是人類史上的大悲劇,一部厚重的大書啊。聽了她的話,我心里萌生了寫一本書的想法。我想,用文學形式展示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2]。可見,他在創作初期就已經意識到要將“文學創傷”深化為“文化創傷”,需要將其放置集體或者世界性的語境中進行考量。
四、結語
小說《悲愴之城》是一部值得重新審視和解讀的小說,其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少數民族作家從本民族身份認同上升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一員身份敘事的典型作品;另一方面,是災難書寫對“繁復的‘單聲部現象’”與“即時性”的突破之作。特別是在當下的特殊時期,為小說中的災難書寫與歷史敘事,提供了一種將個體創傷放到集體性的語境中考量與反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