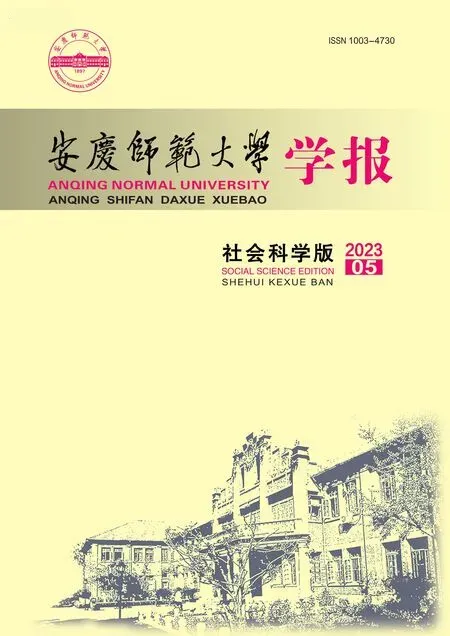方東樹《書林揚觶》論
程 蒙
(安徽大學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方東樹《書林揚觶》的價值久被忽略,清人或褒或貶,皆粗筆帶過。典型如姚瑩和皮錫瑞,前者以為:
植之嘗為《漢學商兌》矣,以近世漢學諸賢妄毀宋儒且誣圣道,故力申考辨,而圣道以明。又嘗為《書林揚觶》矣,以無識之人妄事著書,故詳言古人不肯茍作與夫不得已而有作之旨。是二書者,可謂精于立言矣[1]311-312。
后者則說:
方東樹遂作《漢學商兌》,以反攻漢學,平心而論,江氏不脫門戶之見,未免小疵;方氏純以私意,肆其謾罵,詆及黃震與顧炎武,名為揚宋抑漢,實則歸心禪學,與其所著《書林揚觶》皆陽儒陰釋,不可為訓[2]。
近期有學者專題討論《書林揚觶》之“建白”①參見史哲文《論方東樹〈書林揚觶〉之“建白”》一文,此文從著述體例、行文態(tài)度、時代影響力等角度闡釋《漢學商兌》與《書林揚觶》之關系,又博論方東樹在此書中的“建白”,再以學術史的視野觀照此書的價值,使得人們重新認識和解讀此書。,但也許囿于討論重點和論證體系,還有很多重要問題尚未討論,鑒于此,本文繼續(xù)進行探索。
一、理念尋繹與體例選擇
《書林揚觶》書承《漢學商兌》,《漢學商兌》是方東樹擔當衛(wèi)道、奮力抗爭漢學之作,盡管《書林揚觶》成書時間與其有接續(xù)性,但是兩者著述理念已然有著明顯區(qū)別,《漢學商兌》一書激憤斥責漢學家亂經(jīng)叛道、撻伐漢學空疏無用、貶斥漢學家泥古株守,其目的是不遺余力捍衛(wèi)程朱之道;而《書林揚觶》則門戶之見較為和緩,彼時作者深刻洞察到時人輕事著述的弊端,又進一步從古今著述體例展開深入思考,著眼文事,旁征博引,有獨到的識見。兩書在著述體例的選擇上相似卻有不同,雖然均是先引用他人之言,再加以評論,但是《漢學商兌》中作者大多列舉漢學諸家之言,緊隨以按語形式加以批駁,接著闡明自己的觀點;《書林揚觶》中先節(jié)選宋明理學鴻儒語錄,在此基礎上闡揚自己的主張,駁斥漢學家的言論雖散見其中,行文態(tài)度卻偏于理性。作者選擇語錄加以立說或是對漢學家大力譏諷宋儒語錄類著作的無聲對抗,意圖消解“語錄不文”之病。
方氏在此書上卷主要闡述著書立論的宗旨和原則,針對當時學界存在只重考據(jù)、不重現(xiàn)實學風的狀況提出質(zhì)疑和批評,闡揚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作者在書中深刻表現(xiàn)出對其時學問與現(xiàn)實社會有著巨大斷裂的擔憂,以及對于世人輕易著書不良風氣的勸誡。通過闡明著書之因、追溯著述源流、指摘時人輕事著書的現(xiàn)狀及弊害等,多角度論證這一理念。關于著書緣起,方東樹在卷上開篇有言:
兩粵制府阮大司馬既創(chuàng)建學海堂,落成之明年乙酉初春,首以“學者愿著何書”策堂中學徒。余慨后世著書太易而多,殆于有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3]1。
陳澧亦云:
阮文達公總督兩廣時,桐城方植之客幕府,文達謂桐城人學問空疏(此語余聞之曾勉士先生),當時方必聞之。文達課學海堂士策問堂中人愿著何書,方遂著《書林揚觶》一書[4]。
事實上,方東樹于嘉慶二十四年(1819)赴粵東,道光四年(1824)和五年(1825)授經(jīng)于阮元幕府,在此期間,方東樹兼閱學海堂課文,可見此書一方面是為了學海堂的教學而著,另一方面則是方氏有志挽救乾嘉時期濫于著書學風的弊端,勸誡學者切勿輕事著述。
方東樹追溯著書源流,又將真正經(jīng)典著作分為圣人、賢人、儒人之書,強調(diào)其重要性如布帛菽粟,古今天下不可一日無,提出了“人當著書”的立論:一是著書須有宗旨。首先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放言高論、夸大自矜,在此基礎上再追求言論恰當、可信、有用。由此引發(fā)“君子之言”的概念,即能夠闡明事理、洞察是非。他說:
君子之言,如寒暑晝夜,布帛菽粟,無可疑,無可厭,天下萬世信而用之,有丘山之利,無毫末之損。以此觀古今作者,昭然若白黑矣[3]13。
二是著書要立意高遠,言之有信,而后才能經(jīng)久不衰。因此發(fā)出經(jīng)典的論斷:
學者著書,要當為日星,不可為浮云。浮云雖能障日星,蔽太清,而須臾變滅,倏歸烏有。今日之浮云,非昔日之浮云也,古今相續(xù)不絕,要各自為其須臾耳,而日星雖暫為其所蔽,終古不改[3]13-14。
他慨嘆世間為浮云者居多,深覺世人著書輕率以及隨之產(chǎn)生的流弊,慷慨陳詞地強調(diào)著書必須要有宗旨。
既然人當著書,而現(xiàn)實又存在輕事著書的流弊,其原因何在?方東樹洞若觀火,他分析世人輕易著書的重要原因,即急于求名,導致的結(jié)果是作品支離穿鑿、錯漏百出。方氏大力肯定和推崇古人先賢發(fā)憤著書的傳統(tǒng),堅信心志專一,才能精思深微。又從著書和傳書兩個維度加以觀照,強調(diào)此兩者都不可輕易為之,以免無知者道聽途說、隨意相傳。無知者尚且無害,亂道妄說則會造成流傳疑誤,使得書未通行而先在人心中產(chǎn)生妨害。方氏極力主張要有獨立思考、刻苦求學的過程,方能夠領悟?qū)W問的真諦。他旗幟鮮明地提出辯論學術的傳統(tǒng)和作用不可小覷,但爭辯的立足點應該是明是非、匡正義、救民眾、行大道。其不恥近世學者因為顯名而刻意辯駁以爭勝的行徑,遂引用呂叔簡之語闡明當今學術風氣:
而今講學,非為明道,只是角勝[3]62。
方氏認為著書的重要作用在于闡釋經(jīng)典,他說:
著書說經(jīng),最是大業(yè)[3]67。
梳理古今書籍,討論經(jīng)的著作浩如煙海,義博旨深,古人作傳注來解釋經(jīng)典,今人卻假托經(jīng)典來爭辯傳注,不顧經(jīng)典的義理內(nèi)涵而一味立論著書,對經(jīng)典詮釋越多,往往導致偏離經(jīng)典所蘊含的大道越遠,方氏由此批判漢儒過于重視考據(jù)訓詁,反而錯失其要。
作者在此書下卷重點強調(diào)著書體例的規(guī)范性與重要性。《語錄著書》一章中方東樹對漢學家譏諷宋儒以佛經(jīng)語錄形式發(fā)展宋學極為不滿,他描繪此現(xiàn)狀:
宋儒以來以語錄著書,因于釋氏,俚而不文,世爭譏之[3]77。
方氏義正言辭為之辯白,他指出宋學家論道以語錄傳世,此傳統(tǒng)上可追溯至孔子,以《論語》及圣人之道為標榜。又說:
語錄誠不文,然當審別其所錄之語為何如,不當論其跡也。若剿襲雷同,膚剩淺近,雖文之如子云,亦無取。若是言言心得,質(zhì)之先圣而無疑,俟之后圣而不惑,雖諺何傷[3]78-79?
一方面他認為語言俚俗只是形式上的問題,只要內(nèi)容精當深刻,表達形式其實無傷大雅,但也表明不能過于俚俗。另一方面則明確指出著書目的在于明道、在于是否真有所得,語言上的通達明曉實則有助于道的傳揚。接下來的《說部著書》一章又展現(xiàn)了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他指出:
著書為文,好承用古字句,此最為陋惡[3]84。
承襲古字句并不等同于真實可信,方氏對于漢學家考據(jù)的標準與可信度提出質(zhì)疑:
近世漢學考證家好引雜說以證經(jīng),輒言其時去古未遠,或其人相及,其地相近,執(zhí)此以為確據(jù),而不知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年代之近遠,人地之親疏。世固有子孫言其父祖,弟子言其先師,錯謬失實者多矣,安在時、地、人相近而即可信乎[3]85-86?
其認為說部對于考據(jù)而言不可輕信,從而以此詰問漢學。
方氏對于著作的凡例別有強調(diào),他說:
凡著書欲先定凡例,凡例既定,其書乃有條理可觀,雖商榷長短存乎其人,以視傖俗妄作陋惡不辨體裁者有異矣[3]89。
首先指出后世著書取法經(jīng)典,以其體例為依據(jù),又隨時代的變化做出相應改變。他說:
律生于禮,蓋是事物當然之用,例亦猶是也,可以義起,而后人著書,必云用某家某書例,依于古人,述而不作,取爾雅也[3]89。
其次提出“例生于義”的主張,指出凡例的定立不得與文章大義相違背,否則便是以凡例作為個人任臆詮釋文章的工具。再次歸納出具體細微的的條目與準則,如“著書大例在先,細例在后”“著書不言名稱氏”“著書不避家諱”“著書文字有當跳行另起處”等。最后尤其強調(diào)嚴格規(guī)范引用體例:一是要凡引必注,他引用《日知錄》之語來表明這一觀點:
《日知錄》云:“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則兩引之,不可襲為己說”[3]97。
二是凡引用前人之言,必定要引原文,切忌改竄杜撰、紕繆陋妄,三是規(guī)正注釋體例,應當引用原初文獻,且需注明作者書名、某篇某卷,以便檢校。除此之外,方氏關注到近世偽書泛濫,由此引發(fā)對校讎與版本的闡述:
校讎者,兩本相對,覆校如讎[3]99-100。
編定論次,今則兼須辨別板本繕刻之異同得失,固非淺聞末學所及也[3]100。
綜上可知,方氏高度重視著書旨趣和體例,文本立足點在于著書立論,批駁當時輕事著述的學術風氣,明正學人何以著書、如何著書,他提出的著書必有宗旨、著書不貴多、著書不足重、著書傷物等主張操作性強,對學人的審美認識和文學創(chuàng)作兩個方面都有重要啟發(fā)。
二、價值取向與文學審美
此書不僅彰顯方東樹在著書之法上有獨特識見與深入思考,字里行間又充溢著作者格物致知、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主張,正如管同在題辭中所說:
所論雖專為著書而發(fā),實則窮理格物、行己立身之道悉貫乎其中。學之不講久矣,讀植之書,如在齊聞《韶》也[3]題辭。
姚瑩亦有相似評價:
心平論篤,識精指微,洵衛(wèi)道之干城,救時之藥石。事關千古,豈徒啟蒙發(fā)秘而已[3]題辭?
桐城派文人致力于將理學與經(jīng)世、事功緊密聯(lián)系,展現(xiàn)出鮮明的實學濟世思想與修齊治平的人生主張。姚瑩說:
夫志士立身,有為成名,有為天下,唯孔孟之徒道能一貫[1]233。
劉開用一生實際行動踐行了
負大志,區(qū)畫世務,體明用達[1]107。
一為朝廷重臣,一為布衣,但他們的經(jīng)世主張高度相合。方東樹在此書中也反復表達了對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其有言:
君子之學,崇德修慝辨惑,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之于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達則兼善,明體達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不然,雖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3]113。
可見他講求獨善兼美、重視經(jīng)明行修,認為士人君子肩負道德重建與濟世匡時的雙重重任。更為人稱道的是,他們的經(jīng)世思想不僅只限于口頭和書面上的表達,而且在個人經(jīng)世實踐中取得卓著成效,如姚瑩在經(jīng)濟和邊疆史地、“夷情”防務研究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方東樹強調(diào)文必關乎實政,深刻認識到著書應當有實用價值。他說:
君子先務為急,本末先后,要自有不可倒者。如典章名物固是實學,若施于時用,不切事情,如王制、祿田、考工、車制等,不知何用,則又不如空談義理猶切身心也[3]32。
作者推崇古人將解決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當作著述的首要目的,恰如孔子所重“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在理性省思基礎上創(chuàng)作了《讀禹貢》《治河書》《勸戒食鴉片文》《化民正俗對》等救時濟世之作。
方東樹有意將文章與著書相區(qū)別,強調(diào)文學的獨立性。他說:
文章與著書相等而不同。文士以修詞為美,著書以立意為宗[3]101。
又有
古人有言:“文士如漆,雖無質(zhì)干,而光澤可愛。”吾以為文士如鳳麐,雖不常見,而于世無損,亦唯盛世而始見之。何義門云:“名士如珠玉象犀,初無用而不可少。”此亦如謝玄“芝蘭玉樹”之意耳[3]101。
由此可見,方氏認為以審美為目的的文章與以實用為目的的文章不同,他極力肯定追求審美為目的的文章之美,且引用歐陽修、謝玄、何義門等名家之言來闡明此類文章可貴難求。方氏深具洞見的文學審美認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古文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也為桐城派古文理論的建構(gòu)提供新的活力。
在具體創(chuàng)作過程中,方氏提出著書作文,貴有新意,不可陳陳相因。其言:
凡著書及為文,古人已言之,則我不可再說;人人能言之,則我不屑雷同。必發(fā)一種精意,為前人所未發(fā),時人所未解;必撰一番新辭,為前人所未道,時人所不能。故曰“唯古于詞必己出”,而又實從古人之文神明變化而出,不同杜撰。故曰“領略古法生新奇”。若人云亦云,何賴于我[3]104?
又結(jié)合自身創(chuàng)作體驗說:
維瘠思善,有獲必新。理本大同,心有先得。削其雷同,務絕剿說[3]109-110。
此論極其透辟。在此基礎上方東樹又進一步提出著書為文應追求言簡意深,含蓄蘊藉而余意未盡。綜觀方東樹的詩學觀和古文觀,崇古和求新的立場始終是并行不悖的。方氏大力提倡學古而自成面目,他說:
歷城周編修書昌論文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世人坐先不能真信好古,不知其深妙而思取法,唯以面目相襲,浮淺雷同,何況于變[5]。
又強調(diào):
凡吾所論文,每與時人相反,以為文章之道,必師古人而不可襲乎古人,必識古人之所難,然后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創(chuàng),知正知奇,博學之以別其異,研說之以會其同。方其專思壹慮也,崇之無與為對,信之無與為惑,務之無與為先;掃群議,遺毀譽,強植不可回也,貪欲不可已也。及乎議論既工,比興既得,格律音響即肖,而猶若文未足追配古作者而無愧也。于是委蛇放舍,綿綿不勤,舒遲黯會,時忽冥遇,久之乃益得乎古人之精神,而有以周知其變態(tài)[6]。
可見他提倡創(chuàng)作主體善于學習古人,從經(jīng)典中尋求理論資源,但極力反對因襲前賢,要求言必己出,求變出新。他總結(jié)出文章創(chuàng)作的要義,即風格應似人面而各有不同。行文創(chuàng)作可以摹仿和汲取古人文章的精妙之處,但須得展現(xiàn)自己的獨特感受與寄托。倘若文章一經(jīng)寫成,雷同百家,全然不見作者之真面相,此文章便無足輕重。
方東樹的價值取向與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是緊密結(jié)合、相輔相成的。一方面他從文章的實用價值出發(fā),大力主張文事要適應現(xiàn)實需要,充分發(fā)揮文辭言弊救世的功用。他強調(diào)文無古今,學者文人不僅是以此修身養(yǎng)性,更要通達世務,為文思想是探求實理,尋繹社會及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使學術成為于民生有利的實學。他說:
天下皆言學,而學之本事益亡。本事者何?修己治人之方是已。舍是以為學,非圣賢之學矣。古者修己之學,學處貧賤而已,學處患難而已,學處富貴而已,學處死生而已[7]。
他著力提倡為文寫作需揭示其時之弊,明正治世之道,以救裨當世。另一方面又以審美價值觀照文學,強調(diào)文學作品存在的獨特內(nèi)質(zhì)同樣重要。方東樹在書末清晰地展示了自己的讀書心得,無論處于何時何處,凡有讀書心解、觸事開悟、隨事有獲遂記錄一二,其目的則是:
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以備他日考驗學之進退[3]109。而非著書矜名。其作品蘊含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他推崇前賢孜孜不倦、潛心典籍的精神,以及堅持將文事作為一生唯一信念的品質(zhì),參悟經(jīng)典,他立志歸諸實踐、反諸身心,努力為善,實現(xiàn)價值。
要之,作者注重實用、窮理格物的理念貫穿全書始終,他從多個層面完整清晰地詮釋了這一理念。又發(fā)掘文學作品的審美性與獨立價值,提出求變創(chuàng)新的文學創(chuàng)作原則,并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得到很好落實。因此,方東樹受到后人的推重:
姚門弟子,多聞推方植之,深造推梅伯言。植之之學不純乎文,而其論文去膚存液,有非拘學淺夫所能圈者[8]。
三、思想傾向與理論局限
《書林揚觶》中對《漢學商兌》已提出的“數(shù)十家遞相祖述”的著書泛濫之風以及當時學界整體態(tài)勢提出意見并開展討論[9],兩者在著述上一定程度存在著接續(xù)關系,但不可僅僅將前者視為后者的補充,應認識到《書林揚觶》的獨特價值,也自當正視其中存在的不足。
在此書中漢宋之爭的影響時有顯現(xiàn),方氏也多次毫不含蓄地指摘漢儒一味重視考據(jù)之弊端,但其態(tài)度較《漢學商兌》中的言辭激烈、情感激昂已漸趨緩和。方氏無疑是一位堅定的宋學言說者與護衛(wèi)者,然而在其實際學術發(fā)展過程中對于漢宋兩派實則是兼采和融合的態(tài)度,在此書中存在大量體現(xiàn)這一觀點的言論。如:
凡著書若非不能已于言而徒欲搏名,無一是者。雖擇題而為之,終外強中干,如考訂經(jīng)義最為大題,然非精詣,卓有獨見,則亦陳陳相因,剿說販稗而已。講論義理,亦為大題,然呆衍宋儒語錄,多拾前人緒余,不出里塾拘墟之見,則亦老生學究腐談[3]33。
此處將漢宋統(tǒng)而言之,說明急于搏名、輕事著述并非一家一派之病。盡管他存在大量針砭漢儒考據(jù)之風的文字,卻也認為考據(jù)注疏對宋儒之學的重要作用是無可置辯的,他贊成劉靜修之言:
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中出,特更作正大光明之論耳。傳注疏釋之于經(jīng),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鏟偽得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后疏釋,疏釋而后議論[3]70-71。
后世學者認為方氏一味貶抑漢學、肆意謾罵,如皮錫瑞所言“詆及黃震與顧炎武”,持論或有不公。方氏在此書中多次引錄并肯定顧炎武《日知錄》之語,稱贊其“盱衡今古,意甚高遠”,又引顧氏強調(diào)所成之書必得有所增益之論,發(fā)出“嗚呼。是皆先得我心矣!”的感慨,可見在此書中方氏能夠反躬自省,主張二者應兼蓄并重,不可偏廢。
漢宋兼采、唯務折衷的思想在其作品中其實多有呈現(xiàn)。在《為姬傳先生請祀鄉(xiāng)賢公啟》一文中,方東樹說:
其為學也,考覽六經(jīng),囊括百氏,鉤深探賾,測突研幾。收斯文于在茲,拯微言于未絕。發(fā)明周孔,和調(diào)漢宋[10]。
雖為評價其師姚鼐之言,卻是作者內(nèi)心傾向漢宋兼綜的表征。作者在《漢學商兌》一書中固然激憤批駁漢學、護衛(wèi)宋學,但也存在主張兩者合流之論:
漢儒、宋儒之功,并為先圣所攸賴,有精粗而無軒輊,蓋時代使然也[11]。
不唯如此,方東樹也不期然采用考據(jù)的方法撰述此書,旁征博引,以證己說。
該書運用嚴密的文獻考辭,駁斥考據(jù)學者的主張[12]。
這無疑是方東樹兼采漢學的例證。由此可見作者此時的學術心態(tài)相對客觀,思想傾向趨于兼采并蓄。
嘉道之際,桐城派對漢學進行批評的不乏其人。如梅曾亮、管同、劉開等均以辟漢為己任,尖銳批評漢學末流的弊病,闡明各自的學術主張。但他們和方東樹一樣,盡管對漢學展開批評與表達不滿,卻并非全然否定漢學,而是展現(xiàn)出會通融合的學術取向。如劉開說:
道無不在,漢宋儒者之言,皆各有所宜,不可偏廢也[13]201。
取漢儒之博而去其支離,取宋賢之通而去其疏略[13]203。管同也認為:
大抵漢儒之言,雖或附會而有本者亦多矣,未易卒棄之也[14]。
值得注意的是,在漢學日過中天之時,不僅宋學派在指摘其弊病上眾口一詞,漢學名家如凌廷堪、焦循、王引之等均對當時的漢學之弊有所披露,焦氏痛斥考據(jù)學家“詰鞫狹隘”的不足,他說:
近時數(shù)十年來,江南千余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15]。
由此推重“通核”而貶抑“據(jù)守”,主張融會貫通,兼蓄眾說。而嚴漢宋之壁甚篤的阮元,此時也奉行“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jīng)義實之”的主張,充分展現(xiàn)出折衷漢宋的傾向。實際上此時學者已清晰認識到兩家均存在明顯弊端,也已不再確守己見,在靜觀爭鳴的同時不自覺吸收兩者的優(yōu)點,這一時期學風呈現(xiàn)漸趨融合之勢。正如方濬頤所言:
后之學者當兩宗之,而取其醇,舍其疵,樹其閑,決其障。曉然于訓詁之非義理弗明,義理之非訓詁弗著。合樸學、正學而一以貫之,無穿鑿之害,無空虛之病。斯處則可以為師儒,出則可以為卿相[16]。
盡管文本的思想傾向與作者具體實踐大體上是相互耦合的,不可否認的是此書確有明顯不足。
首先,表現(xiàn)在盡管對漢學家的批評已不似《漢學商兌》般激烈,書寫語言也較之平緩了很多,但書中針鋒相對、出言無狀者不乏其辭。方氏多次稱漢學為诐淫邪遁之說,認為其論輕妄無知,又公開指責楊慎、焦竑兩家言論淺謬輕肆,悉數(shù)他們文章作品中議論程朱之言,全部批駁為忿設诐邪。他將漢學稱為淺學,認為漢儒忌嫉盛名、橫誣丑詆,加之抨擊其說流害人心,將其追隨者稱為流俗庸鄙之夫,未免過激而失真。
其次,在于書中部分論斷矛盾不自恰。其言:
取人貴寬,論義理自有極至不易之則,前賢固當取,究不可指為圣人之道義止于此而已也[3]49。
認識到論義理極至不易,主張應吸取前賢的先見和精華之處,由于人的認識是有限的,也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深化,所以不能說圣人之道止于此,此論可謂公正有識。但他在實際論說中獨尊朱子,將其說置于至圣地位:
三代以后,數(shù)千年以來,止有此一種人品,此一種議論,尊為極至,假使有議之者,則眾共斥為輕妄無知[3]49。
則知朱子非刻于論人,而凡訾朱子者,皆出于妒惑诐邪無知而狂暴也[3]49。
他又提倡著述立論,應當辭氣和平,昭明義理,而不能任臆逞情,呵斥詬詈,但在其實際討論過程中痛詆漢學,從政治層面攻訐漢學為“異端邪說”,甚至對漢學家的批判多有推測與妄加的成分,可見其未能達到自己提出的標準。
最后,是對于程朱之說的絕對尊奉。他指出漢唐以降,儒者論道確有見地,但存在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偏而不全等現(xiàn)象,及至宋代程朱出現(xiàn),才使孔子的述作主張得以光顯:
五經(jīng)《語》《孟》所載宏綱大用奧義微辭,發(fā)揮底蘊,始終有序,進則陳之君子,退則語于公卿,或酬酢朋游,或講之及門,其著述所傳,精深高遠,斯文不墜,后學有宗,所以繼鄒魯而明道統(tǒng)也[3]47。
凡有不利于程朱之言方氏輒為之辯白,凡于朱門有異論者則貶抑之,認為程朱之學無有誤疵,將其作為尋求經(jīng)世之道的理論資源,似乎有失偏頗。
閱方植之(東樹)《書林揚觶》。持論近正,然所舉皆漢學所主而宋儒所未達。于宋儒揚之恐不升,于經(jīng)生則抑之恐不沉,矯檠過中。吾則曰,漢學諸公在山過顙,亦有以召之[17]。
盡管書中主張大多持論相對公正,從修己接物、明德正心、鏡觀古今等方面加以觀照,《書林揚觶》之言至今仍頗具重要價值,但作者所針砭的問題是漢學存在卻也是宋儒沒有完全克服的。無論是宋學還是漢學,發(fā)展至清代中期業(yè)已呈式微之勢,方東樹意圖從程朱理學處尋求經(jīng)世之道也收效甚微,難以解決現(xiàn)實問題。
四、結(jié)語
清代中葉漢宋并立,學人熱衷矜名著書,方東樹則慧眼獨具,論及清人輕事著書造成諸種弊端,又以通觀古今、概要旨歸,在著述體例方面提出規(guī)范標準和嚴格要求,昭明學人何以著書,如何著書,以期糾正時人之風。《書林揚觶》雖為應阮元之命而著,不僅蘊含了作者獨善兼濟、明體達用的人生價值取向,而且著力討論了著書立說的法則、文學創(chuàng)作的原則。不唯如此,此書折射出漢宋之爭的余續(xù),可見桐城派后期優(yōu)秀學者能夠跳出派系之藩籬、去除意氣,從而展開理性思考,從經(jīng)世致用角度兼采漢學,進一步發(fā)揚了桐城派經(jīng)世傳統(tǒng),推動了社會變革時期的學術轉(zhuǎn)型,開拓了晚清理學發(fā)展新路徑。盡管此書存在明顯缺陷與不足,但瑕不掩瑜。深入掘發(fā)此書,不僅能夠彌補方東樹研究之不足,而且從一個側(cè)面加深我們對當時學術生態(tài)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