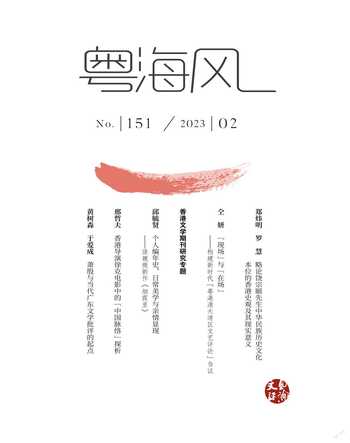概念的選擇:從“龍香”到“大中華詩歌”
許婉霓
摘要:以香港龍香文學社為發端的“龍香文學現象”,始于20世紀八十年代的大灣區詩歌交流,其中,傅天虹的《當代詩壇》幾經變換出刊地址,一直在大灣區參與詩壇建設。《當代詩壇》從創刊之日起便以“溝通兩岸四地,整合海內外漢語新詩”為基本定位,對于“中國詩的現代化”追求的內在動因,與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警惕,使傅天虹及《當代詩壇》同人執著于找出一個概念,以盡可能涵蓋他們的詩學主張。從“大中華詩歌”到“漢語新詩”,不斷地調整正是為了接近準確性,而這樣的愿景實際上并不容易實現。
關鍵詞:龍香 大中華詩歌《當代詩壇》漢語新詩 概念選擇
一、“龍香”與《當代詩壇》:
始于大灣區的詩歌交流
1991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三冊的“龍香文學叢書”。其中,詩集《寫給情人……》由張詩劍主編,收錄了當時龍香文學社傅天虹、張詩劍、盼耕、傅小華、王心果、李剪藕、譚帝森、周蜜蜜、鄒宗彬、非我、夢如、曉帆、紅葉、春華、夏智定、孫重貴等同人的詩作。張詩劍為該詩集作詩《龍香》為序:
不要問我們從哪里來
我們都來自龍的故鄉
不要問我們何時回歸
我們本來就扎根在龍土上
……
我們的詩
就是“龍香”
把愛情播種于龍域
讓希望升上太平山
詩中對“龍香”的解釋,與龍香文學社創始人張詩劍對于龍香群體的定位息息相關。龍香成員多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來港的南來文人,既有像張詩劍一樣生于內地,受過正統高等教育,歷經運動并在青壯年時期來港的詩人,以閩籍為主;也有生在國外,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愛國而回內地,后再南來的詩人。他們因濃厚的愛鄉情結,特別熱愛中華文化,視其為“根”。“從哪里來”與“來自龍的故鄉”,透露出這一群體的“尋根意識”與身份認同,而“九七回歸”這一歷史事件與他們的“尋根意識”恰好相吻合。
龍香文學社緣起,與改革開放后內地尤其是后來屬于大灣區的地區掀起來港的“考察熱”有關。“為促進文學交流,計劃先邀請深圳作家來港”[1],1985年1月,張詩劍、巴桐、夏馬、陳娟、曾聰、田野等在九龍土瓜灣春田街福運大廈二樓商議,成立龍香文學社。最初依托地緣,堅持“請進來”,以邀請深圳作家來港、深港周末文藝營等活動方式組織兩地作家交流。龍香成員與深圳作家協會和《深圳特區報》聯系密切,曾有三十多位成員加入深圳作協,張詩劍更一度是深圳作協副主席,而陳娟的長篇小說也在《深圳特區報》連載了兩年多[2]。由大灣區的深圳、廣州作協延伸,龍香下屬的4個出版社,多次自資或與內地多個出版社聯合出版大型文學叢書。1991年,該社正式更名為“香港文學促進會”并沿用至今,但在論述文學現象時,研究者仍習慣于用“龍香”來指稱該團體。
《當代詩壇》創刊于1987年9月15日,參與創刊的有香港詩人傅天虹、犁青、路羽和臺灣詩人洛夫、張默。該刊發展中,有兩個重要轉折點。一是在尚處早期的第4期,傅天虹加入龍香文學社任常務理事[3],而張詩劍等龍香成員加入《當代詩壇》,以龍香成員為骨干組建了編委:《香港文學報》的主編張詩劍成為《當代詩壇》的副主編,而《當代詩壇》的主編傅天虹成為《香港文學報》的副主編,“兩家編委是重疊的,兩份報刊是一個團隊的兩個犄角”[4],《當代詩壇》由此進入同人刊物時期,并成為龍香文學的一部分。二是2003年第35期始,《當代詩壇》轉移至澳門編輯,并成為雙語詩刊。第36期之后,《當代詩壇》上鮮見香港詩人,從嚴格意義上說,《當代詩壇》作為香港詩歌刊物的研究范圍,應該框定至第35期。
多數時間里,《當代詩壇》“由同人集資出版,利用業余時間、義務編輯”[5],香港藝術發展局也曾自第20期斷斷續續資助至第30期。因資金問題,出版期數并不密集,不定期出版是常態,僅在1992—1993年短暫為季刊,有許多年份只出版一期,另有年份出版兩期,有多期還是兩期合刊出版。
1990年,當代詩學會成立[6],成為龍香成員創辦的四個社團之一[7],《當代詩壇》成為學會機關刊物。學會注冊地是香港,組織機構較完備,但流動性較強,以前三十五期的編委會為例,除傅天虹外,較固定的有張詩劍、路羽、盼耕、春華、譚帝森等。受邀進入編委會的詩人不僅來自香港,還有來自內地、臺灣、澳門及海外。隨著成員越來越多地來自香港外部,本港詩人比例逐漸下降。在傅天虹將《當代詩壇》轉移到香港之外編輯又受聘于北師大珠海分校后,從第45/46期(2006年10月)開始,刊物先后由北師大珠海分校國際華文文學發展研究所、臺灣亞洲大學文理學院、澳門大學中文系協辦,革新刊物開本,將繁體字改為簡體字。不過這是后三十五期時期,原有香港編委早不再參與。可以說,《當代詩壇》盡管多次易地,但一直在大灣區內參與詩壇建設。
二、香港與“大中華詩歌”
《當代詩壇》創刊號的扉頁上,“促進詩藝交流,促進中國詩的現代化”這一宗旨以黑體字展現,在之后多期卷頭語也反復出現。該宗旨與“溝通兩岸四地,整合海內外漢語新詩”的基本定位,即便用上了“交流”“溝通”“整合”的表述,但所指向的顯然是“中國詩”與“現代化”。
主編傅天虹的詩觀很大程度影響了《當代詩壇》的發展方向。他1947年生于南京,內地成長、大灣區旅居以及父母在臺灣的特殊人生經歷,使他志在創造“溝通”可能。他認為,“中國當代詩歌”這個概念偏重“大陸(內地)當代詩歌”,邊緣化了臺灣和香港、澳門詩歌,因此一直在孜孜尋找一個可納入這些部分的概念。從“創刊號”開始,在“為大中華的詩運盡一份力”中,他第一次提到“大中華”的概念,之后在第5期、第10期卷頭語也反復提到“大中華詩藝交流”。他所追求的,是“以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為背景,以天下的漢語詩人為主體,超越國家和區域,超越政治意識形態,構建萬紫千紅的泱泱詩國的‘大中華詩歌”[8]。可見,“大中華詩歌”超越政治意識形態之外,講求的是“新詩完整的中國背景”[9]。他自述20世紀八十年代“懷抱著找一個地方好好寫詩和創辦一份溝通兩岸四地詩刊的夢想來到了香港”,作為一本香港出版的詩刊,《當代詩壇》的定位卻非基于本港,而是從創刊之日起便以“溝通兩岸四地,整合海內外漢語新詩”為基本定位[10]。這也就能解釋為何即便《當代詩壇》作為香港詩刊的前三十五期,香港詩歌也沒有在《當代詩壇》上占據主導地位。
從香港詩人觀之,《當代詩壇》無論是從詩作數量還是詩人陣容來看,顯然較局限。“創刊號”中,相較于當期54位的詩人總數,香港詩人遠少于內地、臺灣等地詩人占比。后續大致保持零星的香港詩人出場,直到第12期新開的“同人詩展”欄目,方有較整齊的龍香成員陣容出現。為“進一步立足香港”與“培養年輕作者”,從第13期開始,新開的“校園詩草”欄目出現了2001年創刊的另一龍香刊物——《當代文學》的辦刊人張海澎,但后續香港年輕詩人也占比不多,與其他地區相比常是最少的(第18期),甚至無人選入(第21期)。第24期表示“明顯加重了香港詩人作品分量和數量,這一方面今后還會加強”(卷頭語),但總體占比并未明顯上升[11]。從第30期始,香港詩人又逐漸零星化,直到第35期的“香港詩輯”才重新有大量的香港詩人出現,不過這一期已是香港詩人最后一期集體出場了。從第36期開始,隨著《當代詩壇》改換出刊地點至澳門,香港詩人基本退出《當代詩壇》[12]。而從陣容上看,其范圍僅限于龍香及與龍香交往密切的南來詩人之作,幾乎對其他香港詩人沒有涉及,顯然無法輻射到整個香港詩壇。從內容而言,像張詩劍、犁青、秦嶺雪、王心果等新詩,或涉及鄉愁,北望歸鄉(張詩劍《鄉愁》);或有關內地漫游與中華文化(犁青《窈窕桂林》、秦嶺雪《潮州韓愈祠》、王心果《武夷山漫游》)。在這些詩作中,香港并未有過多痕跡,相反,香港被隱于詩歌背后,成為詩人北望的一個心理據點。
可見,傅天虹的“中國詩”“大中華詩歌”,因深層的語言文化心理結構相同而有內質上的緊密聯系,涵蓋了《當代詩壇》中的香港詩。雖反復強調要突破內地的獨大,但實際上依然以內地批判現實主義的詩學觀念為中心,而內地之外的詩歌則是向著他理想中的“中華”而來。這也可以推及他更熟悉的臺灣詩壇。在他看來,“大陸(內地)詩歌、臺灣詩歌、香港詩歌和澳門詩歌作為不可分割的詩歌血肉,共同構建成中國當代詩歌”“必須以區域整合與視野重建作為自身詩學建構的一大方向,必須破除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人為藩籬”[13],港臺詩歌皆因與“大中華”的血緣關系而進入“中國詩”之中。不過,結合《當代詩壇》的實踐來看,他提出的“大中華詩歌”概念卻有忽視包括香港詩歌在內的各地區詩歌特色的隱憂,這正是其詩觀的吊詭之處。
三、命名的執著與“中國詩的現代化”
《當代詩壇》以“促進中國詩的現代化”為目標,何為“中國詩的現代化”?傅天虹舉出了若干例子,“如何恢復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如何強調詩歌對人的命運的關懷和人的價值的肯定;如何注重從文化心理傳統上去尋求中國新詩生長之‘根,發掘和重構民族文化精神;如何追求詩歌觀念和審美意識的探索創新等”[14]。排位前二的“現實主義傳統”和“對人的命運的關懷和人的價值的肯定”,可見內地詩觀的深刻影響。在傅天虹看來,“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文學以來內地的文學發展脈絡緊密相關。他在歸納歷次新詩概念命名時,如“現代白話新詩”、20世紀五十年代的“當代文學”“當代詩歌”、八十年代的淡化“現代”“當代”區分的“中國新詩”等,均將基點歸于“對現代化的強烈吁求”。由此,“現代化”成為歷次新詩命名的內在動力,這是包括傅天虹在內的這一代內地知識分子的社會心理。這也就不難理解,以“促進中國詩的現代化”為宗旨的《當代詩壇》以及傅天虹本人為何對新詩命名有著不斷堅持的執著了。而“從文化心理傳統上去尋求中國新詩生長之‘根”則正囊括了上述所言的“大中華詩歌”與“中國詩的現代化”的關系,這種“根”的意識,同樣使“香港詩歌”納入“大中華詩歌”概念擁有了“現代化”這一正當理由。
而命名的另一執著在于,盡管傅天虹認為“如何追求詩歌觀念和審美意識的探索創新等”也是“中國詩的現代化”的一部分,但他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卻始終保持某種警惕。傅天虹并不認可內地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詩人個體意識的“無以復加的強調”,認為“新詩因而走向了明顯的浮泛、后現代式的個人化傾向”。正是這些命名在標準上不統一,不具備“定義式的濃縮性表達、嚴格的規約性言說”,而導致命名的單一化、瞬時性,因此,他不想承認“混雜無端的現實”,想要“正本清源”[15]。所謂“以詩存史”,也是想努力找一個可以涵蓋各種中國百年新詩的概念。
傅天虹認為20世紀六十年代的西方現代主義在整個臺灣詩壇泛濫成災,而后又回歸傳統,詩歌表現形式和手法因此得以豐富。《當代詩壇》早期,洛夫的詩是其中較有實驗色彩的詩歌。洛夫的新實驗詩《隱題四首》(第11/12期),標題本身是一首或一句詩,再將每個字隱藏在詩內,與中國傳統的藏頭詩頗為相似,這或許可歸于對傳統的回歸。洛夫在詩后談到他的詩學思考,“后現代主義后,詩還能玩出什么花樣來?這些詩是我近來做的一系列新形式的實驗……這是一種語言的設計工程,卻仍須要求詩的有機結構”[16]。《當代詩壇》以龍香成員為主的香港詩人中,熱衷探索形式的代表是犁青、譚帝森。犁青從九十年代開始,便在圖像詩和立體詩上進行大量探索。圖像詩是“一種把詞語、詩行按某一圖案或形狀排列而成的詩”[17],如《贈圣諾姆修道女》(第15期)。
不過,這類詩人在《當代詩壇》上畢竟是少數。洛夫在《當代詩壇》發表的詩雖與大部分龍香成員的作品有明顯距離,但不晦澀。在私交上,傅天虹與臺灣“創世紀”詩社及“鐵三角”中的洛夫、張默關系一直較近。洛夫和張默在創刊時就曾資助《當代詩壇》,洛夫曾任名譽社長,張默則歷任編委、副社長。不過,洛夫、張默、痖弦的《創世紀》詩刊當時正處于回歸傳統、親近現實,將現代主義與中國傳統美學相結合的第三次調整詩觀時期,在詩觀上與傅天虹的主張有所交合。犁青的探索則是“抵抗現實主義派的不重視、或反對形式主義的藝術觀;也是抵抗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不重視主題思想、或反對詩的思想性和浪漫激情”[18] 這一觀念的詩學實踐。譚帝森認為“現代詩由晦澀漸趨明朗,由純內心世界返回結合現實世界,由西化向傳統復歸,都是合理的調整”[19]。可見二人均同傅天虹一樣,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多有警惕,注重主題思想,并希望加入現實主義觀照現實,來避免現代主義的晦澀與對內心世界的過度倚重。
四、余論:概念的選擇與愿景
對于“中國詩的現代化”追求的內在動因,與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警惕,使傅天虹及《當代詩壇》同人執著于找出一個概念,來盡可能涵蓋他們的詩學主張。在前三十五期,盡管“大中華詩歌”一直為傅天虹所堅持,但他其實并不十分滿意。“大中華詩歌”為人所詬病的“文化中心主義”的內里,使這一概念在召喚海外漢語詩人方面有著文化沙文主義的隱患,這顯然對傅天虹及《當代詩壇》造成了持續的“概念”選擇焦慮。因此,從第38/39期開始單獨撰寫卷頭語的內地同人屠岸,曾試圖以“中國現代詩”(第40/41期)、“中國現代漢語詩”(第42期)、“中國新詩——或者叫現代漢語詩,包括海外華人的漢語新詩”(第43/44期)等概念加以替代。
在外移出香港,并引進更多的協辦機構后,《當代詩壇》同人的各類學術交流會數量上升,2007年創立的“當代史學論壇”機制,多年來在海峽兩岸輪番舉辦。2008年,在第二屆當代詩學論壇暨張默作品研討會上,以張默的創作為標本,論爭“漢語新文學”與“漢語新詩”概念的有效性[20],“漢語新詩”開始為《當代詩壇》所采納。傅天虹不僅在之后各期《當代詩壇》上大力提倡,還通過主編大量以“漢語新詩”冠名的叢書來推廣——短短一年多時間即以“漢語新詩”為題出版了二十多本書。
從前三十五期的“大中華詩歌”到后續的“漢語新詩”,這一概念的選擇所希望達到的愿景,在他們看來,并不是為了概念的整齊劃一,而是為了接近準確性——這可以從傅天虹、屠岸對另一個概念命名的動機討論入手觀之。2007年,傅天虹、屠岸和脫離了香港色彩的當代詩學會曾試圖從代際入手命名“中生代”以達致關聯詩學問題的厘清。“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們研討‘中生代的命名,是為了探求歷史言說的接近準確性,但無意獲取話語霸權,也不謀求整齊劃一,這原是不可能的。老子說:‘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說,在‘名與‘實之間不可能劃恒等號。我們的目的只是求取這種命名探討的推進。”[21] 這段表白透露出傅天虹等人執著于“概念的選擇”所通往的目的。這里出現了看似吊詭的內核——即便他們明白“名”“實”不可能畫等號,卻仍強調“接近準確性”。這或許與他們對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警惕與疏離相關。因為從后現代歷史觀而言,他們的愿景很可能是一種一廂情愿。
其中的一個問題是,追求接近準確的概念,事實上會導致概念本身的不斷自我瓦解。福柯認為,文本的操作是一種話語實踐。概念或者命名作為一種文本操作,自然也是一種話語實踐。而“詞語僅僅是在世界其他事物之中的事物而已,它們既顯示其力圖表示的對象,又將始終含混不清。所以,當任何思想體系所托付的事物領域的模糊性(obscurity)顯現為對其自身的確認時,這個以求謀劃一個價值中立再現系統的思想體系注定要遭到瓦解”[22]。《當代詩壇》的同人致力尋找到一個概念以“接近準確性”本身,便隱含了否認“詩歌動態發展”的這一前提。反復執著于將新詩這樣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以固定的概念囊括,無疑陷入了本質主義的泥沼,也注定了這樣的愿景無法實現。
而另一個問題是,無論是“龍香”,還是《當代詩壇》從“大中華詩歌”到“漢語新詩”的命名,這諸多概念的選擇顯示了將香港詩歌整合進更大概念中的努力。實際上,這在企圖打破所謂的地區藩籬的同時,又隱含著文學地理與政治、歷史的緊密聯系。以安德森的“想象共同體”這一后現代歷史觀的推演來看,《當代詩壇》的主事人傅天虹和眾多香港同人一樣,他們流動的身份讓他們能夠在海峽兩岸乃至國內外游走,但他們的詩歌創作及詩觀,卻鞏固了內地詩歌“根”的想象,客觀上導致其他地方詩歌創作的獨特之處極易被簡單消解乃至忽視。這種想象,與王德威等人的“華語語系文學”的主張,恰可堪對照。
龍香成員是以“中華”這一具有向心力的文化中心概念來容納香港詩壇,而王德威等人則更希望“從邊緣打入中央”[23],以正視漢語內部眾聲喧嘩的現象,這與葛兆光的“從周邊看中國”亦有同工之處。王德威們關注“異”,以“異”觀察多音復義,以尋求某種對話關系:“華語語系文學……的版圖始自海外,卻理應延至大陸中國文學,并由此形成對話。”[24] 而龍香成員們則注重“同”,希望這些“不同”都能收束到諸如最大公約數的“同”中,香港在這其中被置于“交流”的位置上,其特色被消融掉。這些概念具有的統合意味,以朱壽桐的論述最為直白:“沒有人懷疑海外漢語文學寫作與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之間的血肉聯系,漢語新文學無論在中國本土還是在海外各地其實都是一個分割不開的整體。”[25] 概念的選擇,恰是龍香成員以及這批南來文人心態的最好反映,推而廣之,藍海文主張詩歌創作“珍惜傳統,回歸傳統”,乃至倡導詩歌“新古典主義”,組建“世界華文詩人協會”也是類似。同樣的還有犁青的“《文學世界》作家詩人聯誼會”“國際華文詩人筆會”,犁青也曾在《對“香港文學”幾個問題的看法》中提出“香港文學的回歸問題”[26]。然而,香港詩歌本身具有的不同于內地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恰恰是其特色所在,這是香港詩歌對于漢語詩歌的一種發展與貢獻,也是豐富與繁榮中華詩歌的重要實踐。因此,簡單忽視香港詩歌特色,很有可能走向的恰恰是龍香成員追求概念接近“準確性”的反面。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項目號:19ZDA278)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注釋:
[1] [3] 張詩劍:《六年耕耘 初嘗青果——香港龍香文學社簡介》,《臺港文學選刊》,1991年,第2期,第82頁。
[2] 張詩劍:《龍香,投向詩國的夢——一步一步地去發掘文學典藏》,《臺港文學選刊》,2015年,第10期,第187頁。
[4] 盼耕:《〈創世紀〉詩社詩刊與香港詩社詩刊比較》,蕭蕭:《創世紀60社慶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頁。
[5] 傅天虹:《卷頭語》,《當代詩壇》,1992年,第13期。
[6]《當代詩學會宣告成立》,《香港文學報》,1990年,第8期,第1版。
[7] 張詩劍:《從“龍香文學現象”看香港文壇》,《香江文壇》,2002年,第2期,第85頁。
[8] [14] 南鷗、傅天虹:《傅天虹:以詩存史,正本清源(上)——百年新詩紀念專題〈世紀訪談〉傅天虹篇》,《星星》,2016年,第20期,第59頁。
[9] 傅天虹:《卷頭語》,《當代詩壇》,1988年,第4期。
[10] 同[8],第58—59頁。
[11] 許燕轉(許燕轉:《論〈當代詩壇〉之于“漢語新詩”的視野建構》,《華文文學》,2014年,第3期,第80頁)曾統計第25—60期的各地區詩人占比,第25—30期中,看似香港詩人人數增加,占比上升,但實際上或許其依據的刊物樣本有誤。比如該文提到第25期香港詩人15人,合計詩人24人,但據《當代詩壇》歷期作者名錄(傅天虹:《香港〈當代詩壇〉和她的詩人群——創刊廿四周年同人詩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可知,該期作者有69人,香港詩人15人,占比依然偏低。
[12] 僅有盼耕、秦嶺雪、路羽、犁青等零星出現,如第45/46期合刊、第47/48合刊、第51/52期合刊等,大部分期數已無香港詩人,有的期數也只有零星幾人或一人。
[13] 同[8],第57頁。
[15] 同[8],第55—65頁。
[16] 傅天虹:《香港〈當代詩壇〉和她的詩人群——創刊廿四周年同人詩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頁。
[17] 亞思明、王湘云:《論犁青的“流散寫作”與“立體詩學”》,《南方文壇》,2018年,第6期,第103頁。
[18] 犁青:《犁青論犁青的立體詩》,香港:匯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頁。
[19] 張詩劍:《寫給情人……》,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2頁。
[20] 屠岸、傅天虹:《卷首語》,《當代詩壇》,2008年,第49/50期。
[21] 屠岸、傅天虹:《卷頭語》,《當代詩壇》,2007年,第47/48期。
[22] Hayden White,Foucault Decoded:Notes from Underground,in 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轉引自張京媛:《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
[23] 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年版,第2—21頁。
[24] 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象》,《明報月刊》,2006年,轉引自黃維樑:《學科正名論:“華語語系文學”與“漢語新文學”》,(香港)《文學評論》,2013年,第27期,第34頁。
[25] 黃維樑:《學科正名論:“華語語系文學”與“漢語新文學”》,(香港)《文學評論》,2013年,第27期,第38頁。
[26] 犁青:《對“香港文學”幾個問題的看法》,《香港文學》,1998年,第164期,第4—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