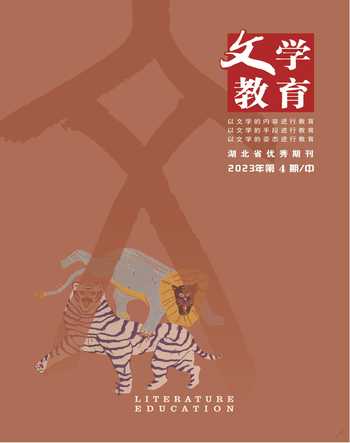后殖民女性主義視域下《使女的故事》解讀
林秋
內容摘要: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于1985年發表長篇小說《使女的故事》。在小說中,她創作了特殊的女性身份——使女,以使女的特殊身份和細膩的口吻描述了在未來信奉極端宗教主義的男權社會中女性所經歷的身份缺失、喪失話語權,繼而被邊緣化、成為屬下階層的遭遇。后殖民理論批評家斯皮瓦克結合了女性主義和種族問題,揭露了殖民主義和男性中心的權力話語對于東方女性以及第三世界婦女的壓迫,話語權力被剝削,她們淪為邊緣化的他者。這與《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國的女性角色遭遇相仿。本文運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探究《使女的故事》中女性是如何淪為邊緣性形象,以及她們與被殖民主體尤其是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婦女的共同之處。
關鍵詞:《使女的故事》 沉默 屬下 后殖民女性主義批評理論 斯皮瓦克
由于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和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都關注屈從于強權下的弱勢群體,都重視語言問題,都試圖解除殖民主義和男性中心主義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加之于被壓迫主體身上的性別、文化、種族等枷鎖。這使得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不可避免地結合到了一起。作為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一種文化批評理論,后殖民女性主義超越了原來的女性主義的局限,進一步擴展了閱讀政治的視野。一批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家涌現。這些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家都批評歐美白人女性主義未能結合具體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語境考察被壓迫女性的生活經驗。因而歐美白人女性主義無法代表并言說其他族裔女性的歷史和利益。(劉巖 2019)
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家斯皮瓦克的貢獻尤為突出,在《屬下能說話嗎?》一文中,她從話語層面闡述了知識和權力的關系。在葛蘭西《獄中札記》中提到的“下層階級”(subaltern)的基礎上,進一步賦予了“屬下”這個詞特殊的涵義。她將屬下概念擴展到了第三世界處于弱勢地位的人群,即無法加入向上社會流動運動的人群(斯皮瓦克 1996:288),因此斯皮瓦克十分關注殖民地女性的生存現實,主張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中審視女性的歷史,尤其是殖民歷史中女性的地位及作用。(劉巖 2019)有學者關注到女性同被殖民者的命運有相似之處:
女性在許多社會里都被歸為“他者”,被邊緣化,且在隱喻意義上“被殖民”。她們深陷于“主權”又從根本上游離于“主權”,被迫用游擊戰來對抗帝國統治。她們與被殖民種族和人民一樣,都有著備受政治壓迫的親身感受,同樣都被迫用壓迫者的語言來表述自己的經驗。(阿希克洛夫特等 2014:164—165)
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虛構了一個男性掌權、信奉極端宗教主義的基列國,基列婦女受到父權制社會下來自男性、宗教、政治的多重壓迫。本文認為,上述的多重壓迫使得基列國的女性成為“屬下”“他者”,她們被剝奪了話語權,身份認同處于長期缺失的狀態。這些都使得她們和被殖民國家和種族的人們尤其是婦女有著相似之處:都被邊緣化,都是屬下階層,都掙扎著抗爭和生存。通過在內心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原有的姓名和身份到最后成功逃脫,將基列罪行公之于眾,女主角奧芙弗雷德的抗爭使得她逐漸獲得自我意識的覺醒,最終找到自己的身份——一個獨立自我的女性主體。
一.沉默的他者
“他者”這個概念頻繁地出現在斯皮瓦克的著作中,在《一個學科之死》中,主要指的是屬下女性。“屬下代表著一種他者性”,在斯皮瓦克那里,屬下女性被構建為一個他者。斯皮瓦克認為屬下也不等同于“有色人種”的概念。“有色人種”的說法基于“色幻學”,即把“白色看作透明的”的,“沒有黑色”的,是對白人自我表征的反映。(斯皮瓦克1999:165)因此《使女的故事》中,盡管大部分描述的是在基列國的白人女性,由于其“無法獲得應給予權力或地位的過程”,成為了無權無勢,生存于主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利結構之外的存在。因此和黑人女性以及第三世界婦女一樣,她們都是被邊緣化的他者。而這種被邊緣化的過程是逐漸實現的。
基列政權和極端宗教分子掌權者一步步將女性邊緣化,方便掌控她們。在基列政府掌權的初期,婦女不允許擁有自己的工作和銀行賬戶,財產由自己的男性親屬接管,這導致了女性首先在經濟層面上要依附于男性。接著服從于新右翼原旨教義者建立起的基列共和國統治的女性要根據社會地位被劃分為不同等級,在嚴格的社會教條規定下,她們被劃分為夫人、使女、馬大(女傭)、經濟太太和嬤嬤。所有的女性將被迫抹去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接受基列政權賦予她們的新的身份。如文中的女主人公奧芙弗雷德(Offred),她的名字由用英文中表示所屬關系的介詞“of”加上她為之服務的大主教的姓“Fred”構成的,意為“弗雷德的”。這表明她已沒有作為獨立個體的身份,她的價值只是依附于有權力的男性,為其誕下子嗣。此外,基列男性掌權的同時,建立了壓迫婦女的文化以控制她們。例如婦女沒有自由挑選衣服的權力,她們衣服的顏色需根據其社會地位不同而定。使女穿象征生育的紅色,還要戴上頭巾不以真面目示人,這從側面反映了她們受監禁的處境;在高官和大主教家做女傭的馬大穿綠色,象征她們地位低下;大主教夫人穿藍色和青綠色,這意味著她們地位高,與其他等級相比擁有一定的自由;經濟太太穿彩色條紋,這代表著她們對于基列政府來說有不同用處,還可以生育孩子;負責教導和控制使女的嬤嬤穿棕色,意味著她們是嚴格遵守教義、沒有獨立思想感情的機器。基列政權用新的身份標簽抹去她們原有的姓名和身份,由于喪失了個體差異性,她們的位置是隨時可被替代的。和黑人女性或者第三世界婦女一樣,基列國的女性處于身份缺失的尷尬境地,成為了被邊緣化的屬下階層。
“屬下忍受著沉默。”(斯皮瓦克 1985:120)在《屬下能說話嗎》一文中,斯皮瓦克討論了女性和沉默之間的關系,通過各種論述,婦女被描述和構建為不存在或沉默的人,她們的聲音不能夠被傾聽。“在斯皮瓦克所檢視的壓制框架中,屬下女性在各種壓制框架中處于最底層,她們構成了種族、階級和性別交叉點上最為引人注目的犧牲品。”(李應志 2008:102)在殖民主義的生產背景下,如果說屬下階層沒有歷史,沒有話語權,那么屬下女性就更是如此了。“我會當作你聽到了我的聲音。可是這無濟于事,因為我知道你無法聽見。”(阿特伍德 2017:44)基列國那些沉默的使女尤其是女主角奧芙雷德,在基列政權的強壓下無法發聲,即使說話也沒有人聽到,正如屬下女性不能被聽到也不能被看到。她們在公共場所不能自由交流,日常對話通常是選取圣經中的語錄。一方面限制她們說話自由,固定她們對話的內容,另一方面是對她們進行潛移默化的洗腦:“祈神保佑生養。”她招呼道,這是我們之間的例行問候語。“愿主開恩賜予。”我也用例行的話回答。(阿特伍德 2017:20)
除了不能為自己發聲,她們也不能閱讀和寫作,“……在我身邊沒有可以書寫的工具,即使有也受到嚴格禁止。”(阿特伍德 2017:44)在斯皮瓦克看來,“知識必然壓抑了差異和延異,一個完全公正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斯皮瓦克 2014:198)基列政府為了從精神層面上控制女性,將她們排除在知識和語言的殿堂外,使得她們更加愚昧地順從政府的統治。
基列政權對女性的管控遠不止于此。由學校和體育館改造的紅色感化中心,向女性灌輸諸如女性低于男性、女性必須服從于男性、生育是女人的首要任務等愚昧思想。在這里,負責管教、監視和壓迫使女的職位叫做嬤嬤,“沒有子女、不育或上年紀的未婚老處女可以通過擔任嬤嬤一職,逃避成為多余人、被裝船送往可怕的隔離營的厄運。”(阿特伍德 2017:351)基列國就像殖民國家那樣,給一些被殖民者洗腦,將其培養為代理人。作為一開始被基列政權洗腦成功的女性,嬤嬤們承擔了一個類似殖民地的代理人的身份,她們享有閱讀寫字、避免被送去隔離營的特權,作為獲得權力的回報,她們為基列政權管理、控制著使女,防止她們有任何反抗的行為。利用女性鎮壓女性,以女性內部的敵對取代女性團結互助,基列政權有效限制、鎮壓了女性的覺醒和反抗。因此,就像被殖民者不僅要受到來自殖民者的壓迫,還要受到那些助長了殖民和帝國主義擴張的本土代理人的壓迫一樣,基列社會的女性不僅受到來自父權制和男性的壓迫,還要受到女性的壓迫。導致基列國中的女性內部因為被劃分為不同等級而產生的敵對情緒更加突出,方便了基列政府對女性的掌控。
二.基列國的女性和被殖民國家的女性
如果將基列國看作一個殖民國家,那么基列國的女性就是被殖民者。她們所處的境地也與被殖民國家和種族的婦女類似。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描述了沉默的、被壓迫的、隨時可被替換的女性形象——使女,《使女的故事》揭露了女性對于男性的統治以及男性對她們各方面的剝削的恐懼:
我們現在正處于這樣一種境況。對我們中間還談得上有什么境況的人而言,其境況確已陷入窘迫。(阿特伍德 2017:8)這不禁令人聯想到第三世界的婦女或黑人女性。殖民者用基督教影響、改變被殖民者的價值觀、信仰、文化和思想等,白人男性和殖民者折磨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她們的精神和身體被統治,一方面面臨著強大的殖民者的剝削,另一方面被剝奪了基本權利。基列國的女性也同樣如此,她們遭受著來自社會、政權以及僵硬死板的宗教教條的壓迫,基列國用新政權控制女性,不投降的女性將受到嚴厲處罰甚至被處死。
在基列,女性不能擔任要職,國家所有重要職位由男性官員大主教擔任,他們掌握著決定權。換言之,女性不能自己單獨做決定,她們被男性掌控,受到大主教的性剝削。而使女作為繁殖生育的機器,只能按部就班地對自己的身體進行保養,直到為大主教生下孩子,再繼續被分配到下一任大主教家里為其生育子嗣。“在她(斯皮瓦克)看來,屬下女性受到了帝國主義和父權制的雙重壓迫,當然,其中也有階級壓迫,她……考察女性在性繁殖中的價值生產問題,重新考察了屬下女性的身體,認為這是一個剝削的場所。”(李平 2008:40)使女遭到大主教的剝削,黑人女性遭到白人男性的剝削,被殖民者遭到殖民者的剝削,在上述的關系中都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
使女被壓迫、剝削,卻不能為自己辯護、反抗。“當女性被主人主體放在哲學之外時,依靠論證,她成為‘不予考慮者。”(斯皮瓦克 2014:116)正如其他不發達國家的女性一樣,基列國中的女性也被邊緣化了。在基列,女性根據原先的社會地位被劃分為不同等級,她們不允許讀書寫字,不可以自由交談。而連自己的姓名都不可擁有的使女,無疑是最悲慘的一個等級。在每月舉行的授精儀式中,使女不可拒絕、反抗。儀式由嚴格的宗教教義規定,目的是防止使女掌控自己的身體和身份,她們必須服從象征著男性力量的大主教。掌握了使女的身體,對使女具有所有權的大主教和強大的殖民者形象類似,默默服從于大主教的性剝削的使女則和被殖民國家婦女一樣忍受著殖民者加諸于她們精神和身體上的迫害。
使女的沉默和順從貫穿了全文,但小說結尾暗示了奧芙弗雷德逃出了基列國,并選擇說出自己的故事,控訴基列政權加諸于女性身上的殘酷暴行。在小說的結尾,可以看出奧芙弗雷德逃出基列國后用錄音帶將她所述的基列國的罪證記錄了下來,由此為世人所知。“……文學與檔案似乎是共謀關系,它們都是濃縮的交叉陰影。”(斯皮瓦克 2014:215)文獻、備忘錄、故事敘述等有創造性的實踐活動可以幫助那些被邊緣化、被壓迫的主體重新獲得并且重建他們失去的身份、挑戰統治者的話語。這些創造性的實踐作為一種“文化反抗”,“既不會消失也不會沉默”。為了利用故事敘述這一強有力的工具揭露基列國的罪行,奧芙弗雷德獲得了繼續生存的力量,重申她不再作為男性大主教的財產和附庸,而是獨立的女性個體。奧芙弗雷德不再沉默,揭開了基列政權對女性的壓迫和殘害,展現了她對父權制和專政體制的不滿和反抗。
綜上所述,《使女的故事》大多篇幅寫的是白人女性所受到的壓迫。她們失去了作為女性和國家公民的身份,導致了她們的身份缺失;她們不可以讀書寫作、自由交談,致使她們失去話語權,成為沉默的他者;部分女性自身也是受害者卻為掌權者效勞,使得基列國的女性群體從內部產生了瓦解,無法自救和抵抗加諸于她們身上的壓迫。針對使女的羞辱也加速了她們對男性掌權者和父權體制的服從。雖然阿特伍德在文中很少提到基列國中黑人女性的命運,通過以上分析,基列國中的女性尤其是使女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和被殖民國家或民族的女性以及黑人女性的遭遇相仿。她們都受到壓迫,遭遇了身份缺失、邊緣化、被迫沉默、成為屬下的經歷。
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中提醒我們要關注在新的世界秩序中逐漸出現的新屬下,阿特伍德這部發生在未來世界的反烏托邦作品創造了新的屬下女性形象。在后殖民時代,對屬下的剝削和壓迫是一個多重決定的問題。屬下女性要為自己正名,需要主動發出自己的聲音。只不過在我們為她們提供幫助時,首先要傾聽她們的聲音。
參考文獻
[1]Gayatri C.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M].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Gayatri C. Spivak. The Spivak Reader: 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rkravorty Spivak[M]. Ed.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Naclea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6.
[3]李平.斯皮瓦克的女性主義研究[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
[4]李應志. 解構的文化政治實踐: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判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08.
[5](印度)佳亞特里·斯皮瓦克著.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當下歷史[M].嚴蓓雯,譯.南京:譯文出版社, 2014.
[6]羅鋼,劉象愚主編.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7]比爾·阿希克洛夫特等. 逆寫帝國:后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M].任一鳴,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8]劉巖. 后殖民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視域:以斯皮瓦克的語境化性別理論為例[J]. 英美文學研究論叢, 2019(01):293-302.
(作者單位:江蘇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