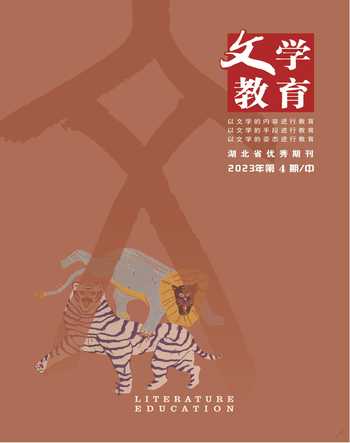迷失與輪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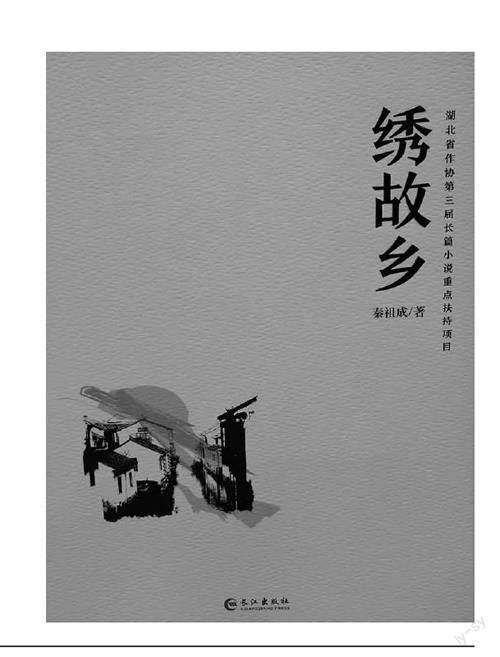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鄉。或在地理上很遙遠,或在精神上很切近。反之亦然。地理的故鄉是我們出發的地方,而精神上的故鄉才是我們內心的棲居地。
每個人的故鄉都有各自的底色。
秦祖成筆下的故鄉呈現的是地理與精神上的離開與回歸,迷失與輪回。他的筆觸對準一處名叫浪溪村的山鄉,一點一滴地進行“工筆加素描”,勾畫出山村人物的失落與喜樂,迷茫與哀愁。郵票一樣大小的山村處處透露出作者試圖表現的他眼中和內心的現實。“繡故鄉”,可以說是本書使用的“筆法”。
表現眼前的現實很難,因為小說的抱負在深入人性的幽暗,看似在講述每個人的故事,實則是要“繡出”人性的花色,太近的現實,往往流于故事的瑣碎。
在現代化突飛猛進高速發展的時代,一切都在被打破,新的東西在取代舊的東西,我們被時代的潮流所裹挾,一個鄉村也不例外。舊的在瓦解,新的還在變幻中,人心在動蕩,人性在凸顯,城鄉在巨變。在這樣的背景下,不管是書寫故鄉,還是書寫城市,都需要沉靜的審視。有一句詩:僅我腐朽的一面,就足夠你度過今生。輝煌中的腐朽,是小說必須抵達的深度。
小說從1980年代第一代農民工遠離鄉村,涌進城市,尋求發財致富的路子寫起,那種背井離鄉的場面,充滿興奮、迷茫和未知。如小說中的丁大壯和黃梅們,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們是城市工業化的生力軍,干的大多是重體力活,等到年老體衰,他們又回到了老家,成為留守老人,回到最本質的農民生活狀態。浪溪村有祖輩們留下的傳統,他們在回歸的時候,也改變很大。如趙之然返回鄉村,基本上已脫胎換骨,他的價值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積累了一些財富,就想以此改變村里的面貌,哪怕從鄉村的臟亂差開始改變。他興建了一處星級的公廁,希望以此教化浪溪村村民。但是除了一個曾離開過浪溪而受過傷害的老光棍黑柱進去外,其他的村民根本不進去使用,并且還遭受到村民的嘲笑。趙之然的“操之過急”,自然起不到良好的效果。貧困限制了他們的想象力,山鄉生活貧窮而簡樸;隨意,本真,也充滿了愚昧與狹隘。
盡管大多數人離開了鄉村,但總有返回鄉村的人。而蘇云兒和馬曉雪是從外地“被哄騙”嫁到浪溪,成為浪溪村村民的。蘇云兒的故事是小說中一根重要的線索,她的“好看”和素養,與浪溪的貧困形成了一種反差。但是她安心于浪溪,成為留守的年輕媳婦,她與趙之然、黑柱微妙關系的刻畫,給小說增添了人性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從浪溪走出去的,有發跡的成功人士,有落魄的,也有做官的。他們在大時代里被淬煉,各自有各自的命運,他們心態復雜,快樂和痛苦,孤獨與失望,都體現在一個個細節里。
小說更多寫了一種堅守,不管是留守的,還是發跡返鄉的,對浪溪的那份眷戀,是一種對故土的骨子里的愛恨。他們恨過去的貧困,恨浪溪的愚昧甚至丑陋,這樣的恨,又出自于愛。愛恨交替的內心沖突,是小說試圖制造的巨大反差。他們如丁小豪、吳大根即便發達了,也依然眷念這片土地。他們一心想改變鄉村,但這談何容易,除了投入大量資金,還需要克服山鄉先天的陋習和世俗的阻礙。比如,一個要拆除老屋,蓋豪華的別墅;一個要保留老屋,拯救修復老屋,給子孫后代留下“鄉愁的味道”。
現實中,我們已經有過改造鄉村的種種范例。許多改造后的鄉村,的確成為城里人休閑和觀光的景點。也有離開本土特色,一味追求奢華,被改造得面貌全非而令人反味的例子也不少。鄉村吸引人們的眼光,在某種意義上,就在于激發一種古老的鄉愁。現代化的進程的確是太快了,人們在快速摒棄一些世俗,換來某種“好處”。信息時代的農村,自然也被新的價值觀念所左右。他們沒有選擇,擺脫貧困天經地義。而這個過程是得到也是失去,是迷失也是輪回。浪溪村走過了一條自我革新的脫胎換骨之路,走上有尊嚴的致富之路,實屬難得。
小說是貼著人物講述的,刻畫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我覺得形象最鮮明的是黑柱這個人物,起初看起來,他是憨傻的,連話也說不清,雇他干體力活,有一種被外人看得起自己的尊嚴感;在后來,他又顯出憨厚、狡黠,身上具有多重而復雜的鄉愿成分。在小說中,他無處不在,好像他是一條主線,串起了各種人物與事件。在小說的最后所寫的紅白喜事,場面極盡渲染。此時的黑柱是個會吹會唱的能手。全面看這個人物十分豐富,有血有肉,但仔細一琢磨,又顯得欠真實。作者對他著墨太多,反而使這個形象顯得用力過度,對整個小說而言,又顯得頭重腳輕。小說里說“黑柱沒有故事,也沒有苦惱”,其實,他的故事是最世俗也最真實。仔細想來,他的確沒有什么苦惱,而他的快樂也不值一提。或許他也沒有能力體驗什么是快樂。
我想問題出在,這個小說的整體框架,是集散似的,有用單個篇章匯集的痕跡,因此長篇的結構顯得松散。
有些情節令人印象深刻,是小說觸動了人性隱秘的痛楚。比如,寫到丁大壯和黃梅老兩口晚年的分家(各自分開,隨著兩個兒子生活),是一種宿命,小說用絲絲縷縷的細節,表現了世俗根深蒂固的陋習,讀者在閱讀中會感受強烈的酸楚。這些章節也是整個小說最結實的地方。
這個小說寫的是鄉村小人物,世俗化的描寫,語言干干凈凈,節奏不緊不慢,以小見大。作者的敘述調性也很符合刻畫普通的小人物。
“每一個往返于城市與故鄉的人,走不出故鄉,也到不了遠方”。浪溪人也大多宿命般回到了家鄉,這是小說的主旨。振興鄉村自然成為浪溪人發家致富最可靠的實踐。小說的正能量自然也體現在這里。矚目整個鄉村現實,也的確走在這條道上。也許小說里的現實,太接近現實的緣故,使得整個小說,還缺乏更深厚的力量。
每個人的鄉村都在淪陷。這是一種有些極端的反思。實際上,淪陷的是傳統價值與世俗倫理,還有人心的散失。地理上的故土,的確發生了大的變化,但人們的內心和堅守的傳統是否在隨之離散,丟失?小說在某些情節里有所涉獵,但對人心的灰暗和價值判斷,還缺乏足夠的真實。
另外有些遺憾的是,一部書寫當代鄉村變遷的長篇小說,對留守兒童沒有半點的涉獵,顯得有些遺憾。老人與兒童,是鄉村的“人氣”,也是鄉村的重要底色。我們眼前的現實也的確如此。現在鄉村改變了,返鄉的人多了,也多少增加了人氣。但是城鎮化的進程,與鄉村的改造進程是同步的,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要求農民進城,一方面要求鄉賢回歸農村。這里就有一個巨大的值得書寫的空間。
小說的開口很小,作為一部長篇,作者“繡出”的我們的浪溪村,是一種希望,一種理想,是作者內心所感所依,也呈現出作者的野心。
作者秦祖成,是十堰市近些年冒出來的少有的具有虛構潛質、并取得一定創作實績的作者。他一手公文,一手小說,在兩者之間切換,心里想必暗藏著無法言說的無奈。用公文混飯,用小說打通精神的通道,只是文體上的切換并不如想象中的自由自在。他是低調到連說話都小聲的人,言談中透著對小說的敬畏和謙卑,我喜歡他這種沉潛的氣質,一聲不響地筑構自己的文學夢想。我相信他的努力會給予他更加深厚的虛構力量。
潘能軍,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曾在《人民文學》《詩刊》《上海文學》《小說選刊》等刊發表作品,出版詩歌、小說、散文作品多部。現為湖北省十堰市文聯《武當風》雜志執行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