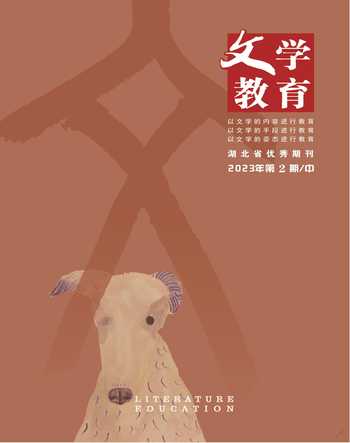檐下阿芳

其實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不知道她叫阿芳,也不知道她姓什么,甚至來自哪里。還是偶爾一次聽對面鋪上的陽春仔在無意之中告訴我,說,阿芳還是我老鄉。當時他給我第一反應就是在開玩笑。后來一問其他的湖北老鄉,阿芳果真是湖北的。好像是麻城的,具體哪里,我已經記不清楚了。
二十年前,在那個“村里有個姑娘叫小芳,長得好看又善良……”歌聲風靡大街小巷的時代里,阿芳既沒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也沒有“辮子粗又長”,但阿芳也絕對算得上是一位美女。一張特別干凈的臉龐上,勻稱地排列著眼睛、鼻子、嘴巴,淺藍色的牛仔喇叭褲緊裹的細腰,如同南國街頭的木棉樹一樣有韻致,楚楚動人。盡管她好像二十四五歲的樣子,也許實際更年輕一些。
那時,我在珠海一個叫白石的棚戶區里上班。破爛不堪的五金廠,在澳門老板的長期經營下,卻制造出出口歐美的精密密碼鎖。工人就六七個人,除下一個保康龍坪的主管隔三差五帶著同鄉女朋友來宿舍外,我們都是單身狗。轟轟隆隆的沖壓機聲音,撲面而來的煉爐熱浪,黑如墨汁的滿地油跡,成了我們單調、枯燥、乏味的日復一日工作常態,好像一個個被裝上了發條的機械鬧鐘。
我們廠里拉柵大門一般都是緊鎖的,只有進貨出貨時才被嘩嘩拉開,上面銹跡斑斑,用手一抹,赫紅色銹粉紛紛落地,手上也沾滿厚厚一層。柵槽下面縫隙里,雜草叢生,一根拇指粗的榕樹,枝葉茂盛,夜晚在燈光下如同一只蹲守在門口的黑狗。我們平時上下班進出都是走廠房左側宿舍小鐵皮門,包括瘦如干柴戴著眼鏡的老板,還有老板那位四十幾歲還沒出嫁的妹妹,我們都叫她“女老板兒”。這個“女老板兒”稱謂,還得益于我那位龍坪老鄉主管,他把鄂西北的兒化音帶到這間廠,就像張騫把石榴從西域帶到中原一樣,連我也覺得“女老板兒”比“女老板”,不管是叫出口,還是聽進耳,都舒服多了。每天都不知道女老板兒挎著皮包啥時候進廠,又啥時候出廠,但她都必須經過我們宿舍那扇鐵皮門,從我們的架子床中間穿過。有幾次剛剛沖涼的工友穿著褲衩從沖涼房里匆匆出來,與女老板兒迎面而遇,尷尬至極。不過,時間長了,好像大家都習以為常了。我是最后一個進這個廠的,我的鋪位離鐵皮門大概就三十公分,每天關門開門成了好像我在這個廠的另外一份工作一樣。推開鐵門,外面就是一條坑坑洼洼的長巷子,一頭是粵海西路,一頭是九洲大道,都是繁華的大道,燈火通明。但這個巷子里,卻只有幾盞昏暗的路燈,忽閃忽滅,勉強可以照清路面。鐵門對面是個叫芳草的電子廠,高高的圍墻,牛皮癬廣告像抗日神劇里日本鬼子的膏藥一樣,招工的、征婚的、交友的、培訓的,像極了一層層魚鱗,常常貼這張廣告的人前腳剛走,后腳另外一家貼廣告的人又來了。再轉身回頭,我宿舍鐵皮門上面是一條一米多寬的鐵皮房檐,也是銹跡斑斑,并且有幾處已經出現破洞,在陽光照射下如同夜空中的燦爛星空。南方炎熱、多雨,多次見路人在檐下奔跑,疾走,遮陰,避雨,也不乏倩影婆娑。
說到這條房檐,不由就會想到阿芳。剛開始,我在鐵門左側十米左右一個小店鋪里,見過她幾次。這個六十多歲的潮汕佬開的小鋪子,都說潮州人精,他也如此。特意從老家請了一個輟學的十三四歲的小孩幫忙看店,門面只有幾平方,貨架煙、礦泉水、檳榔、口香糖及日常用品。而后貨架后面就是麻將桌,時常看見有附近的人進進出出,麻將聲從貨架后此起彼伏傳出來。也有一些打扮花枝招展的女的叼著煙坐在店鋪前的矮凳上閑聊,附近廠里工人不加班了,也和我們一樣,在這里買東西,打麻將,也可以同那些女的坐在一起上看電視,搭訕聊天。我也確實碰到過阿芳幾次坐在那里,她似乎話不多,說話聲音也不快不慢,不高不低。我一直以為阿芳在附近工廠上班。
直到有天夜里回廠,經過宿舍門前的屋檐下,所看到的一幕,讓我深深感到意外。那天夜里,我和幾個工友在馬路對面中國城嗨了很晚才回來。當我們穿過長長的巷子,在巷口的斑駁的榕樹下,幾個女的站在昏暗的巷邊,如同魚一樣游來游去,白色的衣裙格外顯眼。她們好像在漫不經心等人,又好像騾馬市場待人選購的馬匹。隨行的工友告訴我,這些都是站街女。其實不用他告訴,我也知道,因為這場面,許多城中村都有。當我在離工廠宿舍那扇鐵皮門還有二三十米遠的地方,老遠就看見一個身影站在鐵皮門的屋檐下,好像是個女的。剛開始我還以為是龍坪老鄉的女友,因為幾次看見她忘記帶鑰匙而站在鐵皮門外,等我們給她開門進去。直到走到鐵皮門跟前,我才發現是阿芳。雖然只是一眼,借著遠處的昏黃的路燈,我也看得出她特意打扮過。臉上明顯擦過粉,但有的瘆人得慌,上身藍白相間的襯衣,最上面兩顆扣子沒系,領口敞開,前面一片雪白,不用猜,肯定是故意的。下身淺藍色的牛仔短裙,裙邊兩排燙鉆,在昏暗的路燈下閃耀著溫和的光。
見我們開門,阿芳臉上一陣不自然,身子微微向旁邊挪了挪。有個工友還笑著跟她說:“進去坐,一會兒吧”,那里個“坐”字音拖的特別長,語氣也特別重,她沒有回應,好像不認識我們一樣。
工友們都若無其事地說說笑笑進去了。我最后一個進門,側身正準備關門,我和她的目光迎面而遇,宿舍燈光潑在她的臉上,像乳白色濃霧,而我看不出她任何表情,在我低頭轉身那一瞬,我看見她雙手手指不停地纏繞著她腰間的粉紅色裙帶。
“哐當”一聲,我把宿舍鐵皮門關上,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會那么大力,以至于自己被關門聲嚇得一驚。我隨手插上門栓,工友們在宿舍里天南海北地大聲閑侃,而我的心好像還停留在外面,莫非她也是……
后來,一位海南叫阿枝的工程師告訴我,阿芳是站街女,并且還帶著一個三歲多的女兒。我當時一懵,原來那天晚上她在鐵皮檐下是招攬客人。
后來,我也經常在潮汕小店里看到阿芳,但她好像再也沒有站在我們宿舍外的鐵皮檐下了。幾次見到她拉著一個小女孩從菜市場,或者服裝超市采購大包小包的東西,從小店樓梯間上樓。她的女兒似乎還不太會說話,只能偶爾發出呀呀呀呀的聲音,連走路也是東搖西歪的極不穩妥,但小丫頭特別漂亮、乖巧。她八分像阿芳,黑油油的小辮子,上面綁著好看的蝴蝶結,碎花連衣裙,配一雙粉紅色小涼鞋,甚是可愛。
據說阿芳轉到離這里大概五十米遠的一處垃圾分揀站的檐下,那檐短了許多,根本不能擋風遮雨,夜晚光線更暗,那里蚊蟲鼠蟻特別多,還有撲鼻難聞的氣味。
有次聽見一個陽春的沖壓工告訴我,阿芳與海南的工程師阿枝關系有點不一般。大概他們是在潮汕老頭的麻將店里混熟了,有次阿枝把阿芳帶進我們宿舍,他們坐在架子床前的矮凳上磕瓜子,聊天。幾個工友一嘀咕,一起出門把門鎖上了,結果阿芳與阿枝孤男寡女在宿舍一夜,結果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每次提到這事兒,阿枝都一直笑著滿口否認,說什么事都沒有發生過。
春季年后開工時,工廠的幾個爺們兒都從各自老家帶來特產,湖南株洲的醬鴨,湖北襄陽的臘肉,廣東高州的桂圓,海南文昌的椰子……準備湊到一桌吃飯喝酒。沒想到阿芳也帶著她母親寄過來的麻城魚面和我們一起,并親自掌勺,為我們做了一桌豐盛美味的開工飯。那天我第一次離她那么近,無意中瞧見她手背上有幾個煙頭大的傷疤,后來才知道是他老公的杰作。我特別拘束地與她干杯,甚至不知道說什么好,只顧悶聲一口把一杯酒倒進胃里。她反而落落大方地跟我們干杯,夾菜,調侃。
幾杯酒之后,阿芳的臉一片酡紅,就像夕照晚霞隱褪后的夜色一般。幾個爺們兒也都喝得頭暈眼花,在凳子上坐也坐不穩,手里筷子好像不聽使喚一樣。不知道是誰心直口快地問道,阿芳,你咋做這個呢?大家一下子愣住了,誰也沒有想到會有人直截了當地提出這個問題,阿芳也是。不過她很自然放下筷子和酒杯,不快不慢地講述她的遭遇。
阿芳三個月大就被親生母親遺棄在河邊,一戶好心人將她收養,最后又轉賣給現在的養父養母,養父母原本無子嗣,買下阿芳只為給自己養老送終,一開始對阿芳視若親生。誰知,自兩年后生下一男孩,阿芳在他們眼里成了累贅,待她雖不如以前,但也算過得去。阿芳勉強初中畢業,十八歲那年,她經人介紹到鎮上食品廠上班,憑借努力很快得到廠長賞識,提升為組長。這時,追求她的更是不在少數,包括廠長的侄子和鎮干部的兒子,但她都不為所動,因為她早已有心儀之人,就是她一個初中姓楊的同學。她們在一次校慶的文藝匯演上認識的,同學雖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他高大帥氣,成績更是一直名列前茅。阿芳芳心早許,姓楊的同學也是信誓旦旦說以后要娶她,只等姓楊同學大學畢業,他們就完婚。誰知,阿芳五年的等待,結果換來是一封撕心裂肺的絕交信。姓楊的同學在讀大學時,認識一高干女兒,他經不起前途一片光明的誘惑,最終拋棄了阿芳。阿芳正絕望至極,又恰逢養父腦癱臥床不起,養母身患絕癥,高額的治療費用,成了這個家庭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這時村里一個煤老板主動答應借錢給她,條件就是讓阿芳嫁給他。雖然煤老板渾身黑得跟他挖出的煤炭一樣,又離婚兩次,年紀也大阿芳二十幾歲,但一想到養父、養母治病,弟弟讀書,都需要錢,她一咬牙答應了煤老板的要求,先向煤老板借錢給父母治病。最終養父母病都沒有治好,弟弟又要上大學,這時已向煤老板借錢二十幾萬,阿芳沒辦法還錢,只好妥協嫁給了煤老板。結婚后,阿芳才知道煤老板是個變態,喝酒后,直接拿煙頭在她身上燙,常使她遍體鱗傷,同房時,更是變著法子折磨她,連例假期間都不放過。更不幸的是,煤老板的礦上出事,一下子死了十幾個人,煤老板連夜跑路了,追債的人把她圍得水泄不通,一查財務才知道,煤老板早把公司掏空了,剩下一亂堆債務,最終所有資產被法院拍賣抵債,連房子也未幸免,她連一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了。即便如此,依然資不抵債,每天追債的人一撥接一撥,雪上加霜的是,她竟然懷孕了,母親的天性讓她最終選擇生下女兒。女兒剛滿月,她就抱著女兒來到南方這座陌生的都市,原本以為這里充滿希望,可以改變自己的困境,可是因為帶著女兒不能上班。當花光身上僅有的一張錢后,她只能露宿天橋底下,結果女兒發燒急需住院,已經三天兩夜沒有吃東西的阿芳,把自己身子給了一個開玩具廠的六十幾歲澳門老板,澳門老板見她可憐,也沒有食言,不僅給了她女兒住院的費用,還給她母女倆租了套房子,每個月給她三千塊錢,算是包養了她。半年之后,澳門老板的老婆知曉此事,來大鬧一場,把她趕出出租房,她抱著女兒又流落街頭,最終做了一名站街女,用麻木的身子換來母女倆的日常開支。
阿芳講完自己的故事,已經淚流滿面,一種痛不欲生樣子。使我們幾個大爺們都低著頭喘不出氣來,連捏筷子的力都沒有。
后來,某天深夜,宿舍里就我一個人。我在睡夢中,感覺宿舍的鐵皮門被拉開,看見我們廠的老板,領著一女子,從宿舍穿過,直接上了二樓老板的臥室。朦朧中,我感覺那女子背影特別像阿芳,我一下子驚醒了。當我起身朝二樓望去,二樓一片漆黑,黑夜吞沒了一切。第二天我留意二樓老板臥室的門一直緊閉,究竟老板和那女子還在不在上面,什么時候離開的,我都不得知了。
再后來,我們很少見到阿芳了,有人說她被大老板包養了;也有人說她帶女兒回老家了。但每次路過那個鐵皮檐下時,我都會心里一陣悸動,默默地在心里問道:阿芳,你還好嗎?
半年后,我離開了那間五金廠,再也沒有回去了。三年后,那里棚戶區全部拆遷,一棟棟嶄新洋氣樓房如三月雨后的筍尖兒拔地而起,一條條凸凹不平的巷子變成寬敞明亮的街道。環境優美,綠樹成蔭,行人絡繹不絕,這個樓盤并且有一個特別時尚的名字:芳草雅苑。據說開發商是個礦老板,樓盤依他愛妻命名。
張道虎,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現居湖北保康,在《文學教育》《西南文學》發表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