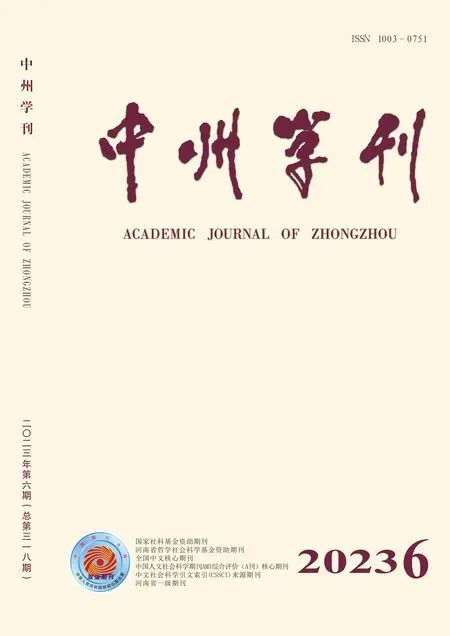從康熙朝南陽綠營兵亂看清代地方文武關系
吳志遠
綠營自建立之日起所形成的標、協、營、汛四級制度在鞏固綠營制度的同時也幫助清廷實現了從省到縣的有效軍事控制。除鎮守地方的軍事職責外,綠營還承擔著緝捕罪犯、押解犯人、平息械斗、轉運錢糧、傳遞文書等體現社會管理作用的職責,因此清代綠營的營、汛起到了現代警察的作用①。目前學術界針對綠營兵的研究成果大多側重于宏觀層面,主要是探討清代綠營制度對于維護邊疆安全、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②。可見目前清代綠營制度的研究具有很強的宏觀性和區域性。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南陽府爆發的綠營兵亂不僅反映了清代河南南陽地區的綠營駐防情況,也反映了清代綠營武官對地方社會的參與及其與文官的關系。因此筆者決定從這一事件出發探討清代地方文武關系,以期進一步完善清代綠營制度及地方治理研究。
一、建威銷萌:清代南陽鎮綠營的駐防
南陽府為清代豫南重鎮,與陜西、湖北兩省接壤,是兵家必爭之地,正如嘉慶《南陽府志》所說:“南陽用武之地,四達之區也。”[1]13故清廷于順治三年(1646年)設立南汝鎮,統轄南陽府、汝寧府、光州等地的綠營兵。
1.南陽鎮綠營的駐防情形
南陽鎮長官為總兵官,駐扎南陽府,統領本標官兵及分防、城守各營官兵。南陽鎮總兵標下分左、右二營,以鎮標左營為中軍,掌號令之事。鎮標下屬武官、兵丁情形可見表1[2]294。南陽鎮除統轄本標外,還統轄一定數量的城守營、分防營,所轄各營情形可見表2[2]294。南陽鎮綠營兵丁駐防范圍較廣,基本覆蓋豫南全境,也足見南陽鎮總兵大權在握,半省的軍事力量盡在其手中。通過對比鎮標及各營可見南陽鎮標存在兵丁數量多且集中的特點,原因在于各營需分汛防守,而鎮標一般不必分汛,故總兵本標兵丁數量要多于下屬各分防、城守營,以治理下級營、汛。總兵標兵雖多,但標兵僅為全鎮綠營的一部分③,總兵不能掌控全鎮之兵。此便是清代綠營的大小相制原則,可見清代綠營制度之嚴密。

表1 南陽鎮標武官及兵丁數量情形表

表2 南陽鎮所轄各營武官及兵丁數量情形表
2.淅川縣綠營的駐防情形
南陽兵亂的起源地是南陽府淅川縣,那么淅川縣綠營駐防情況如何,其與南陽鎮關系如何?下文做詳細分析。淅川縣曾屬內鄉縣,明成化八年(1472年)自內鄉縣分置淅川縣,歸屬鄧州管轄,清代因之。淅川地勢險要,下轄荊紫關這一要隘,故有“淅鄧扼荊紫之險”[1]13一說。咸豐《淅川廳志》記載稱:“自順治初年停止藩封,特設南汝總兵,其所屬鎮標右營舊有駐防淅川汛把總一員。其鎮標右營守備,乾隆十八年奉文移駐荊紫關。”[3]可見,淅川因轄荊紫關這一要隘,故清廷先是派撥鎮標右營把總分防,隨后又將鎮標右營守備移駐荊紫關,嘉慶七年(1802年)又設副將一員協防荊紫關。從南陽鎮標分汛防守淅川一事足以證明南陽鎮與淅川汛的密切關系。
總的來說,清廷雖在豫省布置的綠營兵數量不多,但出于注重對戰略要地的控制,在軍事要地仍集結了一定的綠營兵力,以南陽鎮尤為顯著,故后人將咸同兵燹、寇警日至之際而南陽無虞的原因歸于“備之者有素也”[4]。因淅川縣有荊紫關這一連接豫楚陜的重要關隘,故淅川一直是清廷軍事控制的重點。正是清廷所重視的南陽鎮及淅川汛,卻在康熙五十七年爆發了兵亂,而起源地正是南陽府淅川縣,這何嘗不是綠營武將兵丁跋扈的結果,也是地方文武不和所導致的結果。
二、文武殊途:南陽綠營兵亂中的文武官員
1.兵亂中的文官
南陽綠營兵亂這一事件涉及了多位朝廷官員,涉及的文官主要為淅川縣知縣崔錫、南陽府知府沈淵,二者與兵亂的起因有著密切關系。淅川縣知縣崔錫為直隸人,舉人出身,于康熙五十七年任淅川知縣,兵亂恰于此年發生。康熙五十七年四月,淅川綠營兵違例聚眾賭博⑤,被知縣崔錫發覺。出于對失察之責的恐懼,崔錫決定介入這群綠營兵賭博的事件,將參與賭博的綠營兵當場抓獲。為懲戒這些不守“規矩”的綠營兵丁,崔錫決定將參與賭博的兵丁楊四枷責以示懲罰。楊四是南陽鎮標右營分防淅川把總羅士英手下兵丁,把總羅士英及兵丁得知楊四受枷責后,十分同情楊四的遭遇,并深感不平。于是羅士英親赴淅川縣衙向崔錫聲稱楊四為己兵,意圖施壓放人,在此期間,羅士英兵丁閆觀行甚至將楊四連枷一同強行抬去。此案隨即鬧至南陽府,南陽府知府命令行提楊四等人同淅川縣知縣會審此事。此時南陽府知府為沈淵,沈淵為浙江紹興府山陰人,歲貢出身,于康熙五十三年首次擔任南陽府知府,康熙五十六年再次出任南陽知府。沈淵治理南陽期間頗有政績,他曾召集泌陽縣農民進入馬仁坡開荒修堰,荒蕪坡地逐漸成為村落,百姓頗為感恩[5]。若沈淵任內無重大的變故,最終可以以“父母官”的美譽升遷,可謂前途光明,孰知在其任內發生了兵亂。五月初一日,兵丁王爵突將楊四連枷抬至南陽府堂,冀圖知府沈淵能夠為楊四做主。沈淵見王爵等人已將楊四連枷抬至府堂,便諭令給楊四開枷將就此事進行審理。兵丁卻以為淅川縣知縣未到南陽府衙,又將楊四連枷一同抬去。把總羅士英見此情形也認為崔錫故意不至。武官和兵丁本就對知縣崔錫頗為惱怒,而崔錫所謂遲遲不至的傲慢進一步惹怒了這群武人。在盛怒之下,把總羅士英將怒火發泄在沈淵身上,唆使兵丁趁沈淵因公外出之時將其圍困并抬至教場。最終憤怒的兵丁依羅士英意聚眾將知府沈淵抬至教場,百般羞辱,至三日后在南陽鎮總兵高成的勸諭下方才放還。此事涉及的兩位文官在行為上似無不妥,反而忠于職責,卻因此引發了綠營武官的不滿,招致報復。從兩位文官的遭遇可見地方武官的跋扈,跋扈的背后是水火不容的文武關系,也展現了面臨兵亂時,當事文官喪失話語權與主動權的一貫特點⑥。
2.兵亂中的武官
文官是南陽兵亂的起因,武官則是南陽兵亂的推動者,正是南陽鎮武官在處理這一事件時夾雜私心、無所作為,才使得兵亂最終發生并持續惡化。本事件所涉及的武官主要為淅川把總羅士英、南陽鎮標游擊王洪道、南陽鎮總兵高成。上文已提到羅士英是南陽兵亂的煽動者,高成是南陽兵亂的平息者,王洪道在這一事件中雖未多次出現,但對事件需負有一定的責任。據載王洪道為陜西人,行伍出身,康熙五十二年任南陽鎮右營游擊[1]160。關于王洪道在此事中的角色,大部分史料未曾提起,如《清實錄》對于此事的記載是高成標下兵丁以王爵為首將沈淵抬至教場,內容較為簡略⑦。在時任河南巡撫楊宗義給康熙皇帝的奏折中可發現,在右營把總羅士英率領兵丁汪朝宗將沈淵抬至教場時,時任南陽鎮標右營游擊王洪道隨同眾兵丁至教場,百般恐嚇沈淵,直至總兵高成聞訊趕至,兵丁才最終散去⑧。楊宗義的奏折充分體現了游擊王洪道在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為。王洪道參與、縱令兵丁羞辱沈淵的原因在于與沈淵不和,以至總兵高成趕至后,仍違背高成命令,拒不解散兵丁⑨。后朝廷在審理南陽鎮掛名兵弊病時,王洪道居然“倚恃職員,尚無切供”[6],可見,王洪道跋扈至極。與同案的其他武官不同,王洪道在南陽兵亂中的所作所為純屬個人恩怨,但又與同案的武官有著一定的共性,其共性表現為武官對文官的輕覷、欺凌。此現象產生的原因除以王洪道為代表的綠營武官行伍出身,文化素質不高外,也與清代的政治環境及地方文武職責有一定的關系。王洪道等綠營武官在這一事件的形象及所作所為充分反映了清代地方文武不和的現象。
3.地方與中央的應對
南陽兵亂爆發后,河南巡撫張圣佐因未將情況奏聞及失察屬員遭到彈劾,已于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去職,而新任巡撫楊宗義要到五月十七日才到任,此時河南按察使張孟球便擔負起處理此事的重任。張孟球認為:“‘南陽地連襄、鄖,急則鋌而走險,事未可知’。密令附近諸縣嚴守御,諭:‘止誅首惡,自首免罪。’”[7]后誅殺為首者七八人,南陽綠營得以穩定。兵亂結束后,四川道監察御史楊汝谷聞其事,上書彈劾總兵高成縱兵毆官。康熙皇帝命刑部尚書張廷樞,內閣學士高其倬處理此案,隨后于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出具審判結果:帶頭起事兵丁王爵等照光棍為首例,擬處以斬立決;從犯劉長子擬處以絞監候,待到秋后處決;游擊王洪道因煽動兵丁,且違背總兵高成命令,被處以斬監候,待到秋后處決;羅士英身為淅川縣把總,未能管束手下兵丁,因此被處以杖責,發配邊衛充軍;南陽鎮總兵官高成因平日未能約束兵丁,且事件發生后未能及時題參,照溺職例革職⑩。案件的審判結果也進一步證明了游擊王洪道在兵亂中的惡劣影響。王洪道所任游擊一職于綠營中是中級武官,身負要職卻縱容、推動暴亂,目的僅是為報復沈淵,行為可謂惡劣,故被處以斬監候。此番文武較量中被處理的官員主要是南陽鎮各級武官,上至總兵下至把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而文官雖受辱,但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三、文武不和:清代地方治理機制的弊端
南陽綠營兵亂反映了清代承平之際地方文武官員不和的現象。清代地方文武不和在順治朝就初現端倪。順治十年冬,“總兵劉某養馬汝寧,時大雪,兵馬寒甚,必欲入城”,汝陽縣士紳百姓擔憂兵士騷擾,泣于知縣,并請求知縣出面勸阻。時任汝陽知縣的許應鹍深受紳民感染,決心出城面見總兵官,并試圖勸阻,不料卻被官兵凌辱詈罵。知縣許應鹍不堪羞辱,憤而自縊。總兵劉某見知縣自縊,擔心事情難以控制,激起事端,便率兵繞汝陽而走[8]。康熙十八年,因山東裁撤提標,導致兵丁嘩變,新任山東巡撫施維翰查明事情經過后,指出兵亂的原因在于“巡撫提督文武不和,遂致兵丁生變”[9]1062。康熙十九年伊僻即將出任云南巡撫時,康熙帝告誡其“文武調和,則諸事易于就理。文武不和,則諸事掣制,難以徑行”[9]1137。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告諭在平定三藩之亂時立有軍功的溫州總兵官陳世凱、南贛總兵官許盛,稱“朕每見功大者,易生驕傲,以致文武不和,地方多事”[9]1169。康熙帝頻繁的告諭正是地方文武官員不和,以致事端多發的反映。面對地方頻發的文武矛盾,康熙帝曾有“至地方文武共事,每多不和”[9]383之嘆。可見清代文武不和現象較為嚴重。清代名宦黃六鴻對這一現象有著深刻的看法:
凡州邑俱有營弁駐防,大約非守備則千把總也,從科目出身者,未免輕覷營官,而營官亦恃管兵,未免銜憤。州邑每遇兵民相共,各自護持,而民往往為兵所欺凌,或值地方偶警弁先混報,而地方往往為弁所騷擾,此皆文武不和之故也。[10]
黃六鴻認為清代文官與武官因出身不同而互相輕視,文官以科舉正途出身,認為武官粗鄙,武官因手握重兵,內心銜恨,伺機報復。部分綠營兵騷擾百姓的惡習更是加劇了兩者的矛盾。
矛盾的產生除了與康熙帝所說的武將驕橫、黃六鴻所提及的文化素養差異有關外,也與清代奉行的“文武相制原則”存在一定關系,此種原則的產生與明末清初文武合一論逐漸深化的現實有關[11],也是清王朝對明末武將驕橫局面的反思。清朝以武功得天下,尚武之風濃厚,但部分漢族官員秉承重文輕武的思想,主張壓抑武人。清朝統治者鑒于前明之事,不愿過于壓抑武人,他們甚至會賦予武人更大的影響力,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犧牲文官,因為他們仍要把軍事置于嚴格治理之下[12]。如康熙朝官員趙申喬多次參劾武官的行為引發了康熙帝的不滿,康熙帝痛斥趙申喬說“抑武人乃明代陋習”,但康熙帝也不得不承認趙申喬的觀點存有可取之處,隨后委婉說出了“武人粗魯,不宜抑之太甚”[9]385之語。此事凸顯了康熙帝重武但又抑武的矛盾心理,使清廷雖給予武官一定的權力卻又重重制約,為文武矛盾的產生埋下了伏筆。從清代督撫與提督之關系上便可見文武相制因素的存在,提督是清代一省綠營的最高專職武官,卻又設置督撫文官統率標兵,節制武職,文武相制用意明顯。此舉雖使得文武相互制衡,不至權傾地方,卻加劇了綠營武官與文官的矛盾,削弱了戰時綠營與地方文官的配合能力。從雍正帝上諭可見文武挾制之風氣及惡果:
至于文武雖屬兩途,然同為朝廷之官,同辦國家之事,實為一體,所當和衷共濟,據實秉公,以盡勿欺之道。聞得外省有文官已申文書,而武員恐其干礙,或于中途掣回者,或勉強令其更改者。武既可以施之于文,則文亦可以施之于武。似此挾制成風,茍且遷就,何以得事之實情,除事之弊實,況目前雖草率結局,而嫌隙自此而生,文武不和,實始于此,著該督撫提鎮通行曉諭,嚴加禁約,倘所屬有犯此等情弊者,即據實參奏,毋得姑容。[13]
因部分武官存在脅迫文官的行為,雍正帝據此認為“武既可以施之于文,則文亦可以施之于武”,若不制止,將導致文武不和,因此雍正帝下令若再發生文武相爭之事,牽涉之人要被嚴懲。雍正帝在康熙帝“文武和衷”思想的基礎上試圖調和文武矛盾,但日后仍有類似事件發生,可見清朝地方管理中文武矛盾之深。
清廷的“文武相制”之舉正如一把雙刃劍,“文武相制原則”一方面使地方權力不至于集中至某人之手,利于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在導致政令不暢的同時,也加劇了文武官員的矛盾。而清朝統治者對此心知肚明,他們也深知“抑武人乃明代陋習”,但在具體的制度設計方面,他們仍試圖實現文武間的權力制衡,乃至出現與“文武和衷”唱反調的情況。如乾隆年間,云南布政使徐嘉賓奏稱:“各省文武員弁不能和諧,請分別情罪議處。”乾隆帝卻認為:“文武不和全在上司化導,定以處分,殊非至當,且定以何等處分耶,此見甚小。”[14]171徐嘉賓提議應對文武不和的現象加以懲治,而乾隆帝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文武不和出現的原因在于上級官員教化不周,換句話而言,解決文武矛盾的關鍵即在于上級的教化、勸導,而不在以重典懲治。
但是一些特殊區域,如邊疆之地,因其“民夷雜處,撫綏化導,職任尤重”[14]305,若當地文武矛盾頻發,勢必影響清王朝對邊疆地區的控制,因此,清廷對邊疆地區文武不和的現象,呈現出嚴肅整頓的姿態。乾隆帝也稱:“至于文武不和,乃地方之大患,其在苗疆更宜嚴禁而重懲之,嗣后若有懷挾私意,彼此齟齬,致誤公事者,該督撫提臣即行題參,從重議處,毋得姑容。”[14]305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雖提及對涉事文武官員的懲處,但所謂的懲處僅是在“誤公事”的情況下,即在引發較大的事故后,方給予懲處。因此,從相關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眾多清朝統治者訓誡文官亦或是武官要其和衷的描述,但從具體的制度運行層面來看,清廷關于調節文武矛盾的措施可謂是少之又少,原因即在于,清廷認為文武矛盾解決的關鍵在于上司的教化,而不在于懲治,因此清廷并未拿出強有力的舉措來解決這一問題。此外,因清廷所奉行的“文武相制原則”的存在,導致文武矛盾這一問題無法徹底解決。
清代“文武相制原則”加劇了文武間的矛盾,其在地方實行的“文武協防制度”更是進一步加劇了兩者的矛盾。清廷在動用以文為代表的文官、鄉紳來加強對地方社會的治理之外,還動用了武官,即清廷在地方不斷調整、增加駐防營、汛以強化對地方社會的管控。地方駐防武官主要負責彈壓群體性暴亂事件以及履行地方巡查治安,起到彌補文官力量不足的作用,正如江西巡撫輔德所說:“州縣額設捕役多者不過十名,少者數名,偵緝勢難周到,是以責令營兵協緝。”[15]1841
關于地方“文武協防制度”的提議可追溯至順治朝。順治十六年戶部左侍郎林起龍曾向朝廷提議,應將捕盜等地方事務交由綠營官兵負責,是年十月,簡親王濟度與眾大臣對這一提議展開討論,最終商定,“地方大伙賊盜,著營兵捕拏;其竄匿城市鄉村盜賊,仍設番快緝拏”[16]。在文武官員配合的基礎上所建立的文武協防治安體系,就此形成。但順治年間的討論僅是構建了文武協防體系的大致框架,而就其如何具體實施,各地督撫大員則有著自己的理解。如雍正五年(1727年),河南巡撫田文鏡向雍正帝上《請停分緝協緝疏》,提出了自己對“文武協防制度”的看法,他在文中說道:“嗣后城內失事,緝拿之事專責之文職,同城武職令其協助;道路、墩鋪失事,緝拿之事專責之武職,該管州縣文職令其協助。”[15]1842奏疏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文武協防這一地方治理模式,即文官負責城內事件,武官協助;武官負責城外事件,文官協助。此舉充分考慮到了文武官員能力的區別,因文官處理民眾暴亂事件主要依靠民壯、差役,故城內突發事件主要由文官處理,武官協助。武官處理民眾暴亂事件主要依靠防汛兵丁,其兵丁分布各交通要道,部署范圍較廣,因此城外事件主要交由綠營武官處理,文官協助。田文鏡此舉意在使文武官員相互配合以達到共同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目的。但部分地區由于匪患較重,州縣衙門差役力不能及,緝捕之責全由綠營承擔,以至出現“遇有大伙梟販,武職弁兵自應首先擒捕,方不至于免托”[14]701的情形。以清代檔案的相關記載為例,可以更為清晰地觀察到清代“文武協防制度”的具體運轉情況。
雍正八年十二月,河南南陽府葉縣的一伙賊人“越墻進院,撞門入室,明火執械”[17]28113,將戶主沈睦捆綁,向其索要銀錢,沈睦之子沈峰存趁賊人不備,試圖反抗,卻反被賊人砍傷,最終賊人盜走二千多銀錢及部分財產。在賊人走遠后,沈睦急忙將此事報于保正,遂上報于縣。葉縣知縣便帶領差役前去沈睦家查驗,并移會營弁,“責差慣捕,勒緝贓賊務獲,并關會臨境州縣營汛,遍加協緝”[17]28135。后葉縣差役前往襄城等地打探消息,無意中得知當地人趙來子平時多行不法之事,便以趙來子為突破口,破獲了此案。此案雖已告破,但據清制規定,若地方發生盜劫等案件,需對文武官員展開追責。經查,“汛弁平日懈于巡查,臨時又不追捕,疏防殊甚”[17]28135,因此葉縣汛武官應承擔相應的責任,而葉縣負責治安的文官也難逃其咎。因涉及本案而被題參的官員主要為:“葉縣典史葉芝殿,前任知縣楊永升,兼攝南陽府糧捕通判事南陽府知府程秉禮,分巡南汝二府、汝光二州道副使董自超;專汛葉縣千總事,今署河南營中軍守備李大威,協防外委千總今署陳州營把總王世林,兼轄南陽鎮標標右營游擊翁世熊,屬邑失事例應并參[17]28143。”僅部分官員因公外出而躲過了被題參的風險,葉縣甚至南陽府的多位涉及捕盜賊事項的文武官員均被題參。
此外,發生在城外的劫案也凸顯了“文武協防”這一制度的特點。山西太原人師傳儒以往來直隸河南販賣糧食為業,嘉慶元年(1796年)三月,師傳儒前往內黃縣楚旺集購買糧食。二十二日申刻,在途經宋村東北曠野時,兩個賊人突然攔住了師傳儒的去路,并將其拽落下馬,搶其銀兩而去。師傳儒遂將此事告知附近的村民,村民與其一同前往追趕至泊口集,發現賊已不見蹤跡。地保周寧將此事告知知縣許長浩,許長浩便“選差勒緝,并移臨封營縣一體協拿”[17]154599。此案是三月發生,但至七月間,劫犯仍未歸案,因此“疏防限滿”,當地文武官員俱被題參:“捕官系內黃縣典史張湜,印官系內黃縣知縣許長浩,兼轄官系彰德府糧捕通判福祿,不同城知府系彰德府知府讬金,統轄官系彰德衛懷道蔡共武;武職專汛官系駐防內黃縣把總馮杰,兼轄官系彰德營都司陳國瑚。”[17]154604
清制規定:“凡道路村莊被劫以失事之日起,扣限四個月盜犯未獲,題參疏防。”[18]而楚旺鎮劫案已過去四個月,案犯仍未能歸案,因此內黃縣負責捕盜的文武官員俱被題參。由上述“文武協防制度”的具體運作情形來看,武官深入參與到了維護地方的社會秩序、穩定及日常政務運轉中去,但地方武官部分職責與文官重疊,在實際執行時往往因為雙方的認知不同而產生矛盾。
在地方社會的治理中,武官所起到的只是輔助作用,其治理主體仍應是文官,武官的過多參與也易引發文官的忌憚和不滿。湖廣道監察御史李時謙曾向康熙帝條奏弭盜事宜,稱應“令文官舉報,緝拿則責之武官”,則盜案自可消弭,康熙帝看后稱:“凡巡查鄉村嚴緝奸宄,是其專責。今若置之不論,獨責之武官,則州縣兵少,不但不足以緝盜,即使業已緝獲,文官審訊時又謂其誣良為盜,此豈可行者耶。”[9]548康熙帝認為緝盜一事是文官專責,若按李時謙建議,即由文官舉報,武官緝拿,如無法在期限內緝捕到案最終被題參的必然是武官,即使緝捕歸案,文官也會以“誣良為盜”的借口彈劾武官,若以此行之,只會進一步加劇文武官員的矛盾。李時謙與康熙帝的言論無意中透露了清代地方文武官員在緝盜問題上的矛盾,矛盾可大致概括為文官忌憚武官拿獲盜賊,即“文官最忌營汛獲賊,通報上司即形其短,慮生嫌疑”[15]1841。原因在于清廷官員對地方社會治理存有一種認知,即州縣文官是百姓的父母官,也即是州縣事宜的第一責任人,正如瞿同祖所言:“在治理實踐中,州縣官被賦予地方行政的各項職責,被視為集‘法官、稅官和一般行政官’為一體的全能型官員。”[19]而綠營只是州縣文官的補充力量,尤其在緝盜等事宜上,其雖時常參與,但只負責緝拿,而后續的審理等則緊緊地攥在文官手中。
文官雖對“外來”的武官心存不滿,但“低成本”運行模式下的州縣行政能力不足的現實困境卻又在提醒文官不可不與武官合作。《杜鳳治日記》中記載了大量杜鳳治等官員與武官協同配合剿匪之事,如杜鳳治向參將林福祥、守備銜千總龍玉齡送禮以尋求今后支持[20]。類似之例還可見遂溪知縣徐庚陛在縣內發生宗族械斗之事后,向府、省及提督通稟,并請求“就近撥派兵勇三四百名”[21]。但因武官的驕橫及其對文官的不滿,在應“協防”之時,不僅不予以協助,反而處處刁難文官,最終出現“愚悍之將無事則侵官溺職,而有司不能治,一旦有事則又相抗相諉,而有司不能發一策,為州縣者,惟有瞠目束手而已”[15]1840的局面。
結 語
清前期以來,綠營逐漸成為清王朝“文武協防”基層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主要體現在對社會治安的維護,參與具體基層事務等方面。但“文武協防”基層治理體系也面臨著風險和挑戰。如康熙朝南陽鎮綠營兵亂事件,其歷時雖短,未釀大禍,但暴露了清代地方治理中存在的文武不和問題。該事變的發生正是武官借機泄憤于文官的結果。南陽鎮游擊王洪道等綠營武官面臨兵丁作亂時,不是設法安撫,而是縱令兵丁羞辱知府沈淵,其原因竟是王洪道與沈淵有隙。因此,此類現象雖是個案,但體現出地方文武官員的不和,一方面易使州縣基本的政務難以施行。另一方面也加劇了兩者的矛盾,使“文武協防”體系遭到挑戰。
此種現象在清代不是孤案,時人已經有所注意,清廷也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但因秉承的“文武相制”原則及理想化的文武協防地方治理機制,未能對此類現象根治。此事件對清廷觸動較大,并波及后世。如嘉慶朝平定白蓮教起義時,部分清軍將領將已降賊匪遣散,但嘉慶帝對此不滿,就援引南陽鎮一事指出鎮兵凌辱長官已屬罪不可赦,今部分白蓮教徒曾是營伍之人,而今行謀逆之事,其罪甚重,并發布上諭要求“各督撫提鎮等督飭營員,隨時查察,嚴行管束”[22],以防兵丁參與教亂。可見,南陽綠營兵亂影響深遠。嘉慶帝只看到了兵丁的暴亂,卻未關注過兵丁暴亂背后的武官在這一事件中的角色及行為,更未意識到地方文官與武官之間的矛盾。清朝地方制度設計存在理想化傾向,將綠營這一軍事組織視為清王朝平衡地方基層治理的“第三方”,但綠營與地方文官、民間力量的協同程度,一定意義上決定了“文武協防”的成效。而清王朝雖然意識到該制度存在弊病,但其不愿、也不能根本地解決這一問題,只是不斷地試圖協調兩者的關系,因此產生的文武矛盾反而削弱了地方治理、控制的效果。
注釋
①“直至清末,綠營的地方單位‘汛’始終都承擔了極為重要的警察功能。”參見太田出:《清代綠營的管轄區域與區域社會——以江南三角洲為中心》,《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②現有針對清代綠營兵的主要研究成果為:秦樹才:《清代云南綠營兵——以汛塘為中心》,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秦樹才:《綠營兵與清代的西南邊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李永忠:《甘肅綠營兵與清代西北邊疆》,云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王愛英:《清代廣東綠營標兵與地方社會治安防范研究》,《清史論叢》2020年第2期;王剛:《漠北漢兵:清代烏里雅蘇臺將軍轄區的綠營換防》,《清史研究》2021年第3期。③據表中數據可知南陽鎮標兵共有1710名,南陽鎮以下各營共有兵力3045名,南陽鎮標兵占總鎮兵力36%。可見標兵數量在總鎮兵丁總數量中不占優勢。④商城營為汝寧營兼轄。參見《大清會典則例》卷一一〇《兵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94頁。⑤清代一向是嚴禁八旗、綠營兵丁賭博,官員失察還要被處罰。清制規定:“一兵丁聚賭,本官自行查出,申報者免議,失于查察者,每次罰俸三個月。明知賭博不行查,別經發覺者,將本官罰俸一年。參見《兵部處分則例》卷三十二《雜犯》,《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9頁。⑥在兵亂發生時,明清兩代官員很少能夠及時發揮主動權,扭轉局面,有學者針對明代兵變特點進行分析,指出:“兵變對巡撫群體的影響較大,他們或是在變亂中被殺,或是由于應對兵變不得力而被免職。”參見郭海東、陳武強:《奏報與應對:明嘉靖朝九邊兵變中御史的作用》,《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⑦“河南南陽總兵官高成標下兵丁因查拿賭博人等,至知府署內爭鬧,將知府沈淵抬至教場,看之三日。”參見《清圣祖實錄》卷二八〇,康熙五十七年七月甲戌,《清實錄》第6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40頁。⑧“該營游擊王洪道隨同眾兵,百般恐嚇,直至該鎮高成親至校場,乃散。”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8冊《河南巡撫楊宗義奏報南陽鎮標營弁辱嚇知府等員折》,檔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頁。⑨“游擊王洪道素與知府不和,縱使兵丁將知府圍繞教場凌辱。又違總兵令箭,不諭兵丁解散。”參見《清圣祖實錄》卷二八四,《清實錄》第6冊,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壬辰,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75頁。⑩南陽總兵高成曾于康熙五十七年五月與河南學臣查嗣庭上疏請求留任河南巡撫張圣佐,但因奏疏存在捏稱內容被湖廣道御史彈劾。筆者認為南陽鎮兵亂這一事件的發生進一步加深了朝廷對高成的不滿,使其最終去職獲罪。兵亂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五十八年九月鹿祐即將升任河南巡撫,或是對上年發生的兵亂仍心有余悸,康熙皇帝告知其“蒞任后,須文武和衷,兵民一體為要”。上文提及康熙帝曾多次與文武官員提及文武調和之事,可見和衷、調和觀念成為康熙帝處理文武矛盾的主要思想。參見《清圣祖實錄》卷二三九,康熙五十八年十月丙午,《清實錄》第6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3頁。如“嘉慶二十年廣東綠營武官馮日升因典史戴振掌責好友吳武升,便懷恨在心趁機將典史在衙署門外扭跌落馬,并撕破其衣領”。參見祝慶祺:《刑案匯覽》卷三十八,《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頁。本文在資料搜集上得到了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宋允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
注釋
[1]嘉慶南陽府志:卷1[M]//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南府縣志輯:第56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
[2]大清會典則例:卷110[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3]咸豐淅川廳志:卷3[M]//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南府縣志輯:第59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162.
[4]光緒南陽縣志:卷8[M]//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南府縣志輯:第57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210.
[5]陳廣,張曉剛,劉紹明.南陽歷代郡守知府[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68.
[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M].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256.
[7]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10206.
[8]嘉慶汝寧府志:卷15[M]//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南府縣志輯:第48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152.
[9]清圣祖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0]黃六鴻.福惠全書[M].無錫:廣陵書社,2018:73.
[11]陳寶良.明代的文武關系及其演變:基于制度、社會及思想史層面的考察[J].安徽史學,2014(2):16.
[12]衛周安.清代戰爭文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132.
[13]清世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6:275-276.
[14]清高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5]賀長齡.清經世文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2.
[16]清世祖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6:1002-1003.
[17]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18]六部處分則例[M]//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32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820.
[19]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
[20]張研.清代縣級政權治理鄉村的具體考察:以同治年間廣寧知縣杜鳳治日記為中心[M].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130.
[21]徐庚陛.不慊齋漫存[M]//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5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69.
[2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83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