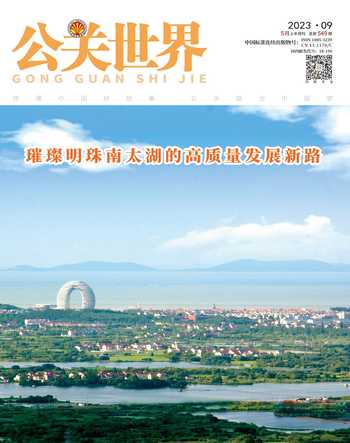滄海桑田,公共關系何以濟世
在《公關世界》創刊30周年之際,雜志社編輯邀我分享個人感悟,我欣然從命。《公關世界》是傳布公關思想、聚集公關同仁的重要平臺,我愿借此機會以微薄之力鼓與呼。
常言道,“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而如今身處滄海桑田的歷史劇變中,我國公共關系該如何立世?筆者以為,公關的價值只能體現在對人類實踐的專業指導上,唯有入世,直面現實,披荊斬棘,充分釋放公共關系引領人類進步的能量,才能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與必要。唯有濟世,方能立世。具言之,我以為主要路徑有二:一是及時迭代公關概念及其核心理念,滿足人類對理論分析工具的強烈需求,二是藝術性地踐行公關思想,以行動展示公關人非凡的專業水平和修為境界。
一般而言,理論的創建、發展、傳播與消亡都會符合特定的利益與框架,盡管世人或一時難以準確識別其邏輯。在近40年的專業研習中,筆者深刻體會到,很多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在引入中國時,都經過了有意或無意的篩選,遭受了一定的誤解或曲解。因此,盡可能多地引進不同維度的觀點是全面理解相關概念和理論的重要前提。公共關系的引入與迭代亦不例外。
何謂公共關系?在此筆者介紹美國公共關系協會(PRSA)的兩個定義。該協會1982年的定義是:“公共關系旨在幫助組織及特定群體相互適應。”該定義中的英文publics是復數形式,如將其簡單譯為“公眾”則有失準確,而且在漢語中具有歧義。我個人認為,將publics理解為“利益相關者”更為準確。從投資與回報(ROI)視角,健康的組織都會盡力界定目標受眾的優先等級。
2011年至2012年間,PRSA向社會征集公共關系的定義,并請公眾對三個入圍的定義進行投票。最終勝出的定義是:“公共關系是一個戰略溝通過程,旨在組織及特定群體間建立互利關系”。與1982年的定義相同,這個定義中的publics也是復數。PRSA官網解釋道:“公共關系的核心是在眾多平臺上接觸關鍵利益相關者,與之建立關系并影響他(她)們”。這兩個定義都表明,公關的使命是優化組織所處的生態。正因為如此,我們公關人在處理沖突時,一般都會選擇相對溫和的方案,因為我們更看重長遠的生態平衡。
戰略溝通,也譯作“戰略(性)傳播”,在英語中已存在上百年了,2001年9月前主要用于廣告、公關、營銷等領域。美國《國防部軍事術語詞典》對戰略傳播定義如下:“美國政府集中努力接觸和理解關鍵受眾,使用與所有國家行動協調同步的項目、計劃、主題、信息和產品,來創造、加強或保持有助于促進美國政府利益、政策和目標的環境”。結合此定義,我們或能更深刻地理解公共關系的本質。
常言道,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英語也有諺語說,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行動勝于言論)。要揭示公共關系的價值,唯一的途徑就是能人所不能,以可觀察、可測量的行動宣示公共關系的能量。換言之,我以為就是展現卓爾不群的信息與傳播素養。近十年來,我抓住一切機會向社會大眾普及傳播學核心概念,為此我曾自謔為“傳播學布道者”“播火人”。
一般而言,個人價值的實現程度和社會地位,與其信息能力息息相關,而所謂信息能力,是指對信息的采集、分析、儲存、應用與傳輸能力。為深刻理解真相坍塌時代的認知過程,筆者建議借助“認知安全”概念。2020年8月我在“亞太公共安全論壇”上做大會發言時,將“認知安全”定義為“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免受蓄意干擾和操縱的運行狀態”。之后我在《國家形象藍皮書:中國國家形象傳播報告(2020-2021)》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概念。
我們必須提醒公眾“認知不公正”(epistemic injustice)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它妨害了我們的充分發展。專家們區分了三大類認知不公正:歧視性、分配性、發展性。歧視性認知不公正是指因對認知主體的身份持有偏見而造成認知不公正,分配性不公正是指侵犯認知主體的知情權,而發展性不公正是指通過不恰當地限制某人的自我發展能力從而妨害了其追求個人利益的可能性。在這些概念的啟發下,世人會逐漸意識到認知領域存在的認知問題,進而意識到捍衛個人“認知自主”是何等重要又何等艱難。
認知安全及認知不公正等概念,不僅適于個人層面,同樣適用于組織、民族、國家,乃至文明之間。掌握了相關概念,世人不僅能夠大幅提高信息免疫力,而且信息的生產與傳布也會更具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就能自覺地實現政治正確和技術正確的有機融合。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呈現的分析工具及專業水準能夠改善社會對公共關系的觀感。戰略傳播強調行為作為介質的重要性,而上述公關實踐本質上就是公關人的戰略傳播作業。
保護“跨界溝通者”

無論是管理視角還是傳播視角,公關實踐都涉及雙方的維度關系。想當年,人類學的內外視角交織法曾讓我耳目一新,至今深受其益。在理解目標群體時,我們得“進入”對方的經驗世界和意義世界,否則就難以真正理解“他者”。與此同時,我們還得掌握適時抽離的技術,退回到一定距離重新審視目標群體,從而實現“內部視角”與“外部視角”的交織融合。
再后來我接觸了跨文明對話理論,明白了在對話中如果雙方處于同一緯度,就更容易遭遇“不可溝通性”難題。如能從彼此共享的世界中跳脫出去,從更高的維度俯視彼此關系,可能會看得更清楚。這就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基本含義。系統論也說,只有跳出一個層次,才能看清這個層次。我們公關人能具足這個抽離和跳脫的意識與能量嗎?
在一定意義上,公關作業是跨文化溝通乃至是跨文明對話,所以如何準確、深刻、全面理解對方是關鍵。我們需要理解的作業環境包含靜態和動態兩個層次,前者包含制度、文化、歷史、習俗、意義系統、決策體系與決策風格等,后者中最重要的是對方的愿望、恐懼及其表達方式。這些都是制約文本解讀的重要語境成分。中國文化倡導求同存異,但在跨文化交往中,異質性因素才是引發誤解和沖突的主因,所以異質性研究是預防沖突的關鍵步驟。
不同文化群體中都存在一批“跨界溝通者”(boundary spanners),他們能夠自由穿越社會群體邊界,推動知識的跨界分享和價值觀對話。這類人大多曾在異質文化中生活過一段時間。跨界溝通者是一個健康群體特別需要的橋梁,但在現實中這些人時常生活在夾縫中,承受著雙方的懷疑和誤解,甚至會面臨一些重大風險。事實上,越是沖突激烈的群體間,越是沖突激烈的歷史時期,越需要“跨界溝通者”。即便在和平時期,世人同樣需要他們的“哨聲”。所以我一向認為,促進社會包容性、保護“跨界溝通者”,是我們應有的覺悟和擔當。
助推中外價值觀溝通
瑞典和平學者彼得?瓦倫斯滕將塑造大國關系的因素分為四大類:地緣政治、現實政治、理念政治和資本政治,但很多學者并沒有這么復雜。在一般性研究中,利益與價值觀被視為影響外交政策的兩大因素,但二者的權重并非一成不變。理論上,價值觀差異會作為制約文本解讀的語境要素,放大其它方面的沖突。反之亦然。正如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所言:“國家間對于特定價值觀和規則的認同有助于相互信任的培育。”
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曾建議,“中美關系的發展必須找到價值觀上的共同點。如何找出共同的價值觀,并利用它來鞏固兩國關系因而顯得非常重要。” 筆者曾數次呼吁,要改善中美關系,就不能無視雙方價值觀的差異。在公共話語空間,如今我們公關人的聲音微乎其微。在關乎國家乃至人類命運的重大議題上,公關人不應缺席,而應解放思想,主動擔當,積極提供公關視角的見解與方案。
祈愿更多公關人能在《公關世界》平臺上砥礪才智,凝結共識、匯集能量,為社會和解、世界和平、人類進步做出更大貢獻!
(作者簡介:畢研韜,海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深圳報業集團深新傳播智庫專家、海南省新聞道德委員會委員)
(責任編輯:李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