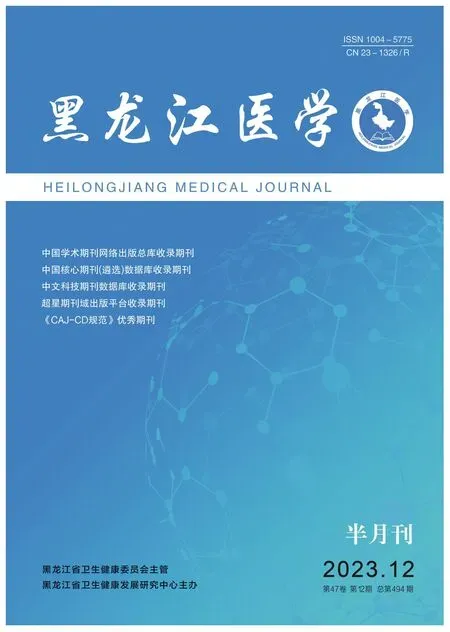BMI及BMI-z對青少年血壓的影響*
趙燕飛,丁 贊
深圳市寶安區中心醫院,廣東 深圳 518102
基于已經確定的健康風險評估及患病率的大幅提高,超重與肥胖已成為全球主要的健康挑戰之一,顯著地增加人群死亡的風險,同時也是高血壓患病的重要危險因素之一[1-3]。目前,發展中國家的兒童和青少年中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有所增加,其中男生從1980 年的8.1%增加到2013年的12.9%,女生從8.4%增加到13.4%[4]。
鑒于未成年肥胖癥的遞增趨勢,國內外一些橫斷面研究發現體重、腰圍、體重指數(BMI)或腰臀比等指標升高的兒童和青少年患高血壓的風險可能增加,表明肥胖癥是高血壓的良好預測指標,也強調了預防超重和肥胖對防控未成年人高血壓的重要性[5-10]。《2018 年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還指出高血壓與內臟型肥胖關系較密切,高血壓患病風險隨著內臟脂肪指數增加而增加[1,11]。但在國內,尤其是在深圳市這些經濟發達的新起城市,針對青少年肥胖各指數對血壓的影響研究還是有所欠缺。因此,本研究擬基于深圳市在校新生的一項橫斷面調查來進一步探討青少年青春期BMI 及BMI-z 對血壓的影響,為制定青少年早期肥胖和高血壓的綜合干預措施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12]。
1 材料和方法
1.1 數據收集
調查于2018 年2 月至2019 年6 月開展,共納入了深圳市寶安區9 所初高中的新生。靜息血壓,收縮壓(SBP)和舒張壓(DBP)采用歐姆龍電子血壓計自動測量。被檢查學生光腳穿著輕便衣服進行身高和體重測量,加以收集每個學生的個人特征數據(如年級、班級、出生日期和性別)。剔除數據缺失以及年齡<9 歲或≥18 歲等樣本后,共7 805名10~17歲青少年納入統計分析。
1.2 統計學方法
BMI=體重/身高2,kg/m2;BMI-z 根據WHO 網站提供的R 軟件代碼計算(https://www.who.int/growthref/en/)。根據BMI的z得分,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將BMI-z>2SD定義為肥胖,1 SD <BMI-z≤2 SD 為超重,-2 SD≤BMI-z≤1 SD 為正常體重,BMI -z <-2 SD 為低體重;其中SD 是BMI-z 得分的標準偏差[13-14]。本研究的肥胖程度第二個分類依據是根據亞太地區BMI 的分類法[15],將所有青春期學生分為4 個BMI 子組(<18.5 kg/m2為低體重、18.5~22.9 kg/m2為正常體重、23.0~24.9 kg/m2為超重和≥25.0 kg/m2為肥胖)。數據按照年齡(10~13 歲或14~17 歲)和性別(男或女)展開統計分析。采用SPSS 22.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在R 語言和易侕統計中擬合平滑曲線圖。采用Spearman’s等級相關分析血壓與BMI及BMI-z的關系。
2 結果
2.1 基本特征分析
共納入7 805例10~17歲青少年學生,其中55.3%新生為男生(4 313 例),54.2%為14~17 歲(4 229 例),年齡平均為(14.15±1.71)歲。在全部青少年中,平均BMI 為(19.98±3.54)kg/m2;男生BMI值高于女生,14~17歲組高于10~13歲組。對于BMI-z,男生BMI-z大于女生,但14~17歲組小于10~13歲組,見表1。

表1 2018~2019年深圳青少年樣本的基本描述
2.2 BMI及BMI-z對血壓影響的效應分析
根據青少年血壓與BMI 及BMI-z 劑量反應關系的平滑曲線擬合圖,SBP 和DBP 均隨BMI 及BMI-z 增長而近似直線增長;當BMI>40 kg/m2時,樣本量極少(只有2 例),所以出現預測血壓值下降且95%置信區間范圍很廣的情況,但不影響整體結論。不管是按BMI 還是按BMI-z 劃分的青少年肥胖標準,低體重、正常體重、超重和肥胖組的平均SBP 及DBP 均呈遞增趨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2和表3。

表2 按BMI分層的血壓水平 mmHg

表3 按BMI-z分層的血壓水平 mmHg
2.3 BMI及BMI-z與血壓的直線相關分析
10~17 歲青少年的SBP 水平與BMI 呈正相關關系(r=0.238~0.328;P<0.001),DBP 與BMI 的相關性相對弱一些(r=0.147~0.266;P<0.001);血壓水平與BMI-z也呈弱正相關關系。在血壓與肥胖指數的相關性中,男生和14~17歲組表現比女生和10~13歲組略強,見表4。

表4 血壓與BMI及BMI-z的Spearman秩相關系數
3 討論
按亞太地區BMI 的分類法,商丘市一所醫學院校的214 例護士生的研究發現,低體重、正常體重、超重和肥胖組的平均SBP/DBP 分別為92/62 mmHg(1 mmHg=0.133 KPa)98/69 mmHg、101/73 mmHg和110/85 mmHg[16];而本文按照相同的BMI分層法,發現四組學生的平均SBP/DBP 分別為(109.3/69.9、113.3/71.8、117.7/74.2、122.4/76.8)mmHg,整體血壓水平高于護理學生組,但血壓隨BMI 級別升高而升高的趨勢不變。如韓國[8]、巴西[9]、沙特阿拉伯[10]、印度[5]、中國香港[17]、馬來西亞[18]等流行病學研究也發現越胖人群血壓越高的類似結論。同樣是基于12~17 歲學校學生,馬來西亞一項比較體重指數、腰圍、腰高比和體型指數(ABSI)在預測青少年高血壓效果的橫斷面研究指出:BMI 均值及高血壓患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男生比女生擁有更高的腰圍均值和高血壓患病率[18]。
針對年齡和性別標準化的BMI-z 分類指標,江蘇省昆山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納入超過58 萬非超重的6~17 歲的未成年人的研究發現BMI-z 評分與高血壓前期及高血壓之間均存在非線性關系:與BMI-z=0 相比,BMI-z 為-1.2, -1.0, -0.5, 0.5, 0.7 和0.8 時,發生高血壓的風險比值比OR值(95% 置 信 區 間)分 別 為0.56 (0.54~0.58)、0.62(0.61~0.64)、0.81(0.80~0.82)、1.17(1.16~1.18)、1.23(1.22~1.5)和1.27 (1.24~1.29);BMI-z 評分越高(即超重程度越嚴重),發生高血壓及高血壓前期的風險越大[19]。體重或肥胖相關指數越大則患高血壓的風險越大。
其他相關研究也指出:不同的民族及人種,肥胖指標對血壓的影響效果不同。基于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健康中心賴利兒童醫院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接受肥胖治療的873 名兒童中,與年齡及BMI 相仿(即BMI-z 近似)的白人兒童(107/50 mmHg)相比,黑人兒童(112/59 mmHg)和西班牙裔兒童(112/59 mmHg)血壓升高的風險更大[20]。此外,在國內一項基于連續三次全國性橫斷面調查(2005年、2010 年和2014 年)共納入22 萬名少數民族及66 萬漢族兒童和青少年(7 至18 歲)的一項研究展現:肥胖對少數民族高血壓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呈持續上升趨勢,但對于漢族人來說是穩定的[7]。來自于突尼斯共和國、印度、韓國、波蘭、伊朗、中國和美國的七項全國性橫斷面調查的58 899 名6~17 歲兒童和青少年的數據分析指出,與第5~24百分位數的參考亞組相比,第25~49百分位數亞組高血壓的優勢比OR=1.27(95%置信區間1.14~1.41),第50~74 百分位亞組OR=1.55(1.39~1.73),第75~84百分位亞組OR=2.17(1.92~2.46)[21]。在可接受的正常體重范圍內,BMI 與兒童青少年血壓升高和高血壓的風險增加有關;對于兒童青少年來說,保持較低的BMI對于預防和控制高血壓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