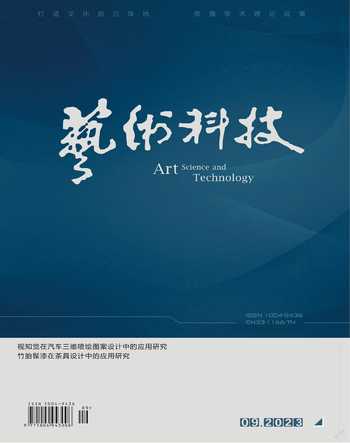審丑到歸真:土味文化背后的地域認同研究
摘要:新媒介的賦權推動以廣大小鎮青年為代表的鄉村短視頻內容創作者走進大眾視野,鄉村空間的地域形象在土味視頻的傳播中被塑造。土味短視頻成為推動鄉村網民參與大眾文化傳播的重要手段,不斷拆解人們對鄉土社會的刻板印象和場域想象,喚醒了人們對鄉土文化的關注,增強了城鄉文化領域的互動與對話,成為風靡社會的土味文化現象。隨著短視頻在移動互聯網文化生產中的普及和流行,土味文化從邊緣走向主流,受到廣泛關注。如今,人們逐漸開始關注短視頻背后鄉村青年群體所展現出的積極生活態度,以及對于生活本真的追求和熱愛,而不只是單純地陷入感性體驗和非理性視覺消費審美。因此,文章基于“我是云南的”系列短視頻走紅原因的探討,試圖探究土味文化的傳播價值,研究發現碎片化表達下的迷因傳播、娛樂化傾向的全民狂歡、身體與容貌成為消費景觀、地域認同下構建想象共同體構成“我是云南的”系列短視頻走紅的原因。土味短視頻引導觀眾對土味文化由居高審視走向共通理解,彌合了主體間的差異;鄉村青年們在此基礎上實現了自我呈現與意義建構,獲得了相對穩定的映像空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土味,為鄉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媒介話語權由“公共”轉向“個體”,以個人視角重構城市形象傳播路徑。
關鍵詞:土味文化;地域認同;傳播價值;城市傳播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09-0-03
0 引言
2022年5月,來自云南怒江傈僳族的小伙“蔡總”憑借一則對口型視頻在快手平臺走紅,視頻中魔性的背景音樂以及自報家門式的歌詞引發了各平臺用戶集體模仿,類似視頻迅速蔓延至全網。截至2023年4月4日,熱門衍生話題#全國各地來上分了#播放量突破111.9億次,再次喚醒了網友們塵封已久的土味記憶。
在城鎮化不斷加快的背景下,鄉村文化一直被冠以“土味”的帽子被城市流行文化所遮蔽,長期面臨被城市主流文化解構與收編的風險[1]。短視頻的普及讓土味文化從昔日的邊緣位置重回網絡文化生產場域[2],土味短視頻的興起使鄉村生活的空間可見度得以提高,其原生態內容也被納入城鄉話語體系的構建中,進而促進了城鄉文化之間的交互與對話[3],同時也成了鄉村青年形塑地域認同與身份界定的空間,隱喻出他們獨特的價值旨趣與別具一格的生存態度[4]。
“蔡總”的爆火引發人們的熱議及思考,土味短視頻的火熱是不是對土味文化的重構?在這場賽博狂歡中又是什么調動著用戶的參與?又能從“審丑”文化盛行的背后窺見什么?本文基于對“我是云南的”系列土味短視頻走紅原因的探討,試圖探析土味文化的生產傳播形式與價值。
1 “我是云南的”系列短視頻的走紅原因
1.1 意義瓦解:迷因傳播下的全民狂歡
道金斯提出迷因理論,認為迷因主要依靠內容和形式的自我復制與傳播繁衍,并在傳播過程中發生不可預知的文化變異[5]。社媒時代的虛擬交互性與去中心化催生出網絡迷因,作為一種數字化文化片段,網絡迷因的內容與形式更易于記憶與模仿,引發病毒式傳播[6]。《我是云南的》作為網絡迷因的“神曲”,其自身歌詞加旋律具有可復制性,觀眾無須投入成本便可以模仿和生產。同時,視頻充斥著碎片化的歌舞曲目和場景,加劇了用戶碎片化的內容消費,形成了彌散于互聯網場域的碎片式奇觀體驗[7]。
互聯網時代,狂歡的形式不再桎梏于固有空間,逐漸引申為網絡中某一事件或現象的“圍觀”與“加入”行為,表達對現狀的抗議以及群體對自由平等的向往。“蔡總”通過奇觀化的視覺符號敘事引起圈層內用戶的獵奇快感,從最開始的“看熱鬧”到“親自加入”,用戶不僅受獵奇心的驅使參與到土味文化的娛樂消遣中,還暗含著用戶對“土味”背后意蘊的認同。在土味文化的狂歡中,以土味為引子進行的雙向溝通與交流促使更多聲音被外界聽到,他們在狂歡中瓦解著世俗的意義,宣泄著對包括“蔡總”在內的“土味小伙”境遇的同情以及對階層固化的不滿,在瘋癲的表象下共享著默契的價值認同。
1.2 視覺傳播:身體與容貌成為消費景觀
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中提出了“景觀”這一概念,認為當今社會已發展成為一個“景觀社會”,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的龐大堆積,任何生活細節都將被異化為景觀的形式[8]。短視頻的出現促使視覺景觀的產生,身體逐漸成為傳播的中心節點,身體景觀的建立將傳統的身體轉化為外觀,切斷人們與真實身體的連接。
短視頻時代的身體景觀體現為“以影像作為中介”的社會關系,人們認識身體方式轉變為由圖像、視頻等技術手段的呈現,從“觀看真理”轉向“觀看身體”,其中,容貌是身體傳播的重點部分[9],對容貌的重視被視為視覺媒體的特性,這種特性在短視頻媒介流行后,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極致,并不斷影響受眾[10]。兩年前《我是云南的》的原創茶雄軍沒有火,今年對口型的“蔡總”卻火爆全網,和此前走紅的丁真相似,他的個體形象完全符合視覺景觀邏輯主導下的短視頻平臺,特色的少數民族容貌和標志性的狼尾長發在人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在短視頻建構的視覺景觀中迅速“殺”出重圍。
1.3 地域認同:鄉土本質構建想象共同體
智媒時代的人際交往得到了技術賦能,但“地域”“地址”所代表的身份象征,依舊深刻影響著社交媒體平臺上的認知交往模式,人們會不自覺地在互聯網上尋找某種身份認同,而建立在地緣關系上的家鄉、地域最為簡單、直接,無疑充當了一種建立身份認同的方式。“我是云南的”系列土味短視頻以地域為載體,在無形中引發集體共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出“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概念,他認為“想象的共同體”是一種想象中內部“平等的社群”,共同體是共同的情感、文化和意義的建構。蔡總這則對口型視頻營造了具有通感意義的地域文化傳播情境,以至于只要魔性的背景音樂響起,相同地域的人會不約而同地投身于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中。在土味文化熱度逐漸消退的當下,以地域位置與民族方言作為傳播內容,不似以往浮夸雷同的土味語錄,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觀眾對土味的反感,喚醒了用戶對故鄉家園的依戀。
2 土味文化的傳播價值
2.1 主體間性:居高審視走向共通理解
胡塞爾提出了“主體間性”理論,認為交互主體通過互動共同建構世界。在網絡交往中,主體間性也可稱為“互網絡性”,這種研究范式超越了傳統的主客對立思維,減少了自我優越感,并承認他人主體在自我的意義和價值建構上的重要性。同時,它強調了交往、對話和理解是協調主體間差異的基本方式,重視多元主體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作用[11]。從最初網友對視頻土氣的評價,到外圍觀眾逐漸了解到包括“蔡總”在內許多社會底層人物的生存壓力,甚至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存在不被主流社會理解與接納的問題,網絡用戶在潛移默化的交流中增強了認同感,實現了對“自己”以外的“他者”的理解,促進了不同主體之間交流,彌合了主體間的差異,增進了情感的雙向流動。
2.2 出圈背后:鄉村青年的自我呈現與意義本真
類似“蔡總”這樣的鄉村青年短視頻作者,通過作品表達了對純真質樸鄉村文化的熱愛與敬仰,同時也體現了其對都市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但當他們試圖融入都市生活時,卻由于無法獲得身份認同而產生孤獨與邊緣感,這使其常常陷入對自我身份懷疑的循環往復之中。鄉村青年們借助短視頻創作,得以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影像空間中消解自身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搖擺與不安。通過土味文化的生產與交互,他們成功建立了先前被主流文化拋棄與排斥的土味敘事結構,從而形成地域認同、尋求群體參與和歸屬感。
雖然互聯網存在眾多對土味文化的批判與解構,但人們在新奇造型與夸張對話的審丑文化背后,對鄉村青年群體努力而獨特的生活態度有了一定的認知,體會到他們對生活本真的追求與純粹,而這恰巧是城市生活所缺乏的。
2.3 重審土味:為鄉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寫道,“土味只是鄉土社會和現代社會的習俗在不兼容的情況下產生的誤解”[12]。社會的發展使傳統文化面臨著轉型的挑戰,其中鄉土文化也經歷著被遺棄和重新發掘的過程。然而,中國人民擁有的源遠流長的鄉土傳統以及無法割舍的鄉土情感,使土味文化在近年來成為流行文化之一。人們重新審視土味文化,通過新穎的表達方式為鄉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土嗨”文化則是其中一種具體的表現形式。
曼紐爾·卡斯特曾指出,具有歷史根源和共同經驗的“地方空間”會隨著人口流動和全球化的發展被拆散與分離,但不同地區和民族仍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征。“蔡總”的視頻作品融入了民族特色,并通過網絡媒介在“流動的空間”內得以傳播和分享,實現了跨越地域和時間的社會交互。這種流動性的社會實踐為鄉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重新組織了帶有“民族土嗨”意味的網絡社會關系。
2.4 城市傳播:個人本位下重構城市形象
短視頻平臺以個體視角切入,媒介話語權由“公共”轉向“個體”,用戶對城市形象的描繪逐漸浸入日常生活空間中。對城市場景全方位的復刻、記錄與再現,最終都將作用于城市整體形象的記憶建構與加強[13]。“蔡總”意外走紅后,直接帶動了云南當地的旅游業發展,區域網紅的巨大流量嫁接城市宣傳,成了借助外部力量的城市宣傳范本。此種回歸“人”本位的個體創作方式,使創作者得以利用傳播技巧控制自我表演,在傳遞扁平化、個性化媒介符號形象的同時,助推觀眾產生傳播者希望其產生的印象。在此過程中,用戶出于對傳播主體、生產內容或形式的認可,以點贊、評論、轉發等行為完成媒介符號的認知、識別、解釋[14],從而加深對城市形象的認知構建與確認效果。
盡管短視頻受限于信息容量、用戶視野等因素,可能會導致短視頻中的城市傳播呈現出微觀化、碎片化的特點,但從用戶信息接收的角度看,正是這種不模式化、不刻板化、不流于集體的內容輸出成為當下城市形象傳播的發展之勢[15]。
3 結語
從鄉村歷史的角度出發,土味文化代表了互聯網對于個體價值彰顯和意義建構效應從城市向鄉村擴散的意義。透過土味文化的流行與變遷,也得以瞥見中國近年來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縮影,土味文化不僅僅是專屬于底層人民的一種文化展演形式,它同樣是各階層間的文化交流媒介。從網絡文化的視角看,不同的土味文化僅僅是網絡文化大潮中轉瞬即逝的浪花,類似“我是云南的”系列視頻此類現象級土味文化的傳播也如同拍岸那一朵,無論其聲勢多么浩大,待新鮮感褪去之后,都終將難逃沒入網絡文化深海的命運。但如果將視角轉向土味文化創造者,轉向底層人民的網絡話語實踐,不難發現,盡管土味文化創造者囿于自身動機與能力的差異,其創造出的土味文化呈現出或惡俗,或本真的外在特征,但不論其形式如何,土味文化背后沉淀的仍是人們共有的鄉土情結,是大眾對純粹、真摯、自由的精神追求。
作為互聯網空間中一種獨有的文化現象,相關部門與平臺方應對土味文化進行適當的規范與引導,謹防逾越社會規范、傳播負能量的內容在網絡空間泛濫成災。而對于網民而言,更多的是需要在眾多現象級土味文化面前保留一份冷靜與思考,謹防自身投入一場場虛幻盲目的文化狂歡之中。
參考文獻:
[1] 劉娜.重塑與角力:網絡短視頻中的鄉村文化研究:以快手APP為例[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5(6):161-168.
[2] 劉懿璇,何建平.土味視頻生產消費中的情感結構與趣味區隔[J].新聞與傳播評論,2022,75(3):53-63.
[3] 楊萍.賦權、審丑與后現代:互聯網土味文化之解讀與反思[J].中國青年研究,2019(3):24-28.
[4] 劉娜.重塑與角力:網絡短視頻中的鄉村文化研究:以快手APP為例[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5(6):161-168.
[5] 常江,田浩.迷因理論視域下的短視頻文化:基于抖音的個案研究[J].新聞與寫作,2018(12):32-39.
[6] 張亮,楊閃,張頔.互聯網迷因傳播的實證分析:以57個網絡流行語為例[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6,39(12):81-85.
[7] 陸新蕾.短視頻中的網絡民族主義初探[J].當代傳播,2019(6):98-100.
[8] 居伊·德波.景觀社會[M].王昭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11-15.
[9] 許高勇,鄭淑月.“容貌焦慮”:議題、身份與文化征候[J].傳媒觀察,2022(9):59-64.
[10] 呂鵬.線上情感勞動與情動勞動的相遇:短視頻/直播、網絡主播與數字勞動[J].國際新聞界,2021,43(12):53-76.
[11] 孫慶斌.從自我到他者的主體間性轉換:現代西方哲學的主體性理論走向[J].理論探索,2009(3):35.
[12]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36-37.
[13] 譚宇菲,劉紅梅.個人視角下短視頻拼圖式傳播對城市形象的構建[J].當代傳播,2019(1):96-99.
[14] 黃欣榮.論芒福德的技術哲學[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2):54-57,62.
[15] 周敏.“快手”:新生代農民工亞文化資本的生產場域[J].中國青年研究,2019(3):18-23,28.
作者簡介:樊雨露(2000—),女,山東菏澤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網絡文藝、新媒介文論、媒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