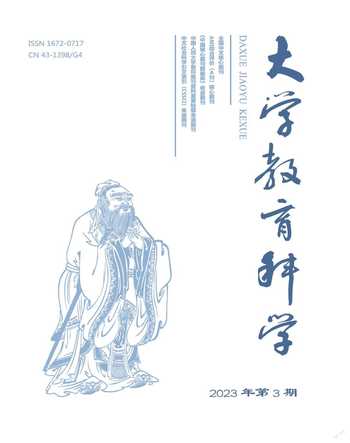解讀大學隱喻:一個本體論的哲學視角
于正陽
摘要: 大學在持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多樣的隱喻,不同的隱喻基于相應文化語境在一定程度上承載著不同的大學理念,成為對大學認知方式和價值判斷的重要表征。基于本體論的哲學視角,對有關大學性質、結構、功能的隱喻進行舉隅與分析發現,從“象牙塔”隱喻到“復合體”隱喻的演化中,大學性質理念漸趨整合化,大學本體系統進一步制度化;從“學人共同體”隱喻到“開放社區”隱喻的流變中,大學本體結構經歷了從建構到解構的過程,漸趨多元化和開放化;從“鏡子”隱喻到“燈塔”隱喻的紛爭中,大學功能理念始終面臨“適應論”和“超越論”的博弈。大學隱喻呈現出明顯的客觀流變性、理念遺存性和對立統一性特征,其背后蘊藏了多維度的大學理念紛爭和大學本體演化規律。新時代高等教育轉型既需要重構大學想象力,也對通過隱喻創新賦能大學本體轉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關鍵詞:大學隱喻;大學本體;理念紛爭;大學想象力
中圖分類號:G640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717(2023)03-0022-10
自大學誕生之日起,許多學者就以“取象比類”的隱喻作為表征大學本體的重要手段。從中世紀時期的“獨立王國”“國家的神殿”,到啟蒙運動后的“學院回廊”“學術修道院”“帝國的心智”,再到現代以降的“多元化大都市”“社會軸心機構”“才智之都”,每個“喻體”背后往往對應著解讀大學“本體”的重要條件。盡管大學隱喻變動不居、繁復多樣,不同隱喻指向大學“本體”的不同方面,但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隱喻作為用替代性話語指明與表達對象同一意義的語言手段[1],可以對所描述的事物或現象本質進行高度概括[2]。加雷斯·摩根在論述組織本體論時指出,我們關于組織的認知是概念性而非物質性的,這些概念經由想象連結整合,建構于我們已知的事物之上[3]。羅珉基于該理論,從哲學視角探討了組織隱喻問題。他認為,隱喻作為“人類思維表象的集中體現”和“概念思維演化的關鍵階段”,是對從特定經驗領域提升出來的東西進行話語化,可以形象地表現相關經驗領域,通過本體論的哲學視角對組織進行認知的范式已經實現“從啟蒙到成熟”的跨越,“組織及其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從本質上是由隱喻所支配、控制的,隱喻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對組織及其管理的看法和組織理論研究的方式、方法和路徑選擇”[4]。基于本體論哲學對大學隱喻進行邏輯梳理和整合,能夠得出大學組織的概念性認知。
本體論的研究視角聚焦于事物內部根本屬性和質的規定性。在自然科學領域,對事物本體性質、結構、功能以及彼此之間關系的探索一直是基礎研究的前沿課題;同樣,社會科學也要基于此揭示“社會現象的本質特點、事物之間的本質聯系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5]。對大學性質、結構、功能三個維度的隱喻進行舉隅與分析,極具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大學性質的隱喻:從“象牙塔”到 “復合體”
對于大學本體屬性的探索貫穿了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始終,大學性質作為一個復雜概念不僅難以言說,而且極具流變性。布魯貝克指出,高等教育的概念模糊不清,大學存在不同的性質,其界限埋嵌于歷史的發展中,并通過滿足各自所屬歷史階段的不同程度的需求而獲得合法性,相關哲學理念隨之分化發展,形成爭鳴的態勢[6](P2-9)。諸多有關大學性質的隱喻蘊藏于浩若煙海的哲學和高等教育學著作中,反映了學者們對大學性質多元化的認知。
(一)“象牙塔”:認識論哲學與隱喻的肇始
“象牙塔”一詞由何人創造已不可考。該詞最早出現于《圣經》,用以描述女子頸項的美好。根據布魯貝克的分析,在大學發展初期“象牙塔”隱喻的實質是大學通過讓渡一部分暫時利益而“成為保護人們進行探索的自律的場所”[7](P15)。這種理念極富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色彩,自治性、獨立性、學理性、內部邏輯的發展主導性是其主要特征。“象牙塔”隱喻本身也埋嵌于歷史發展之中,其內涵和外延不斷發生變化,先后建構起兩種不同的“象牙塔”模式。
“象牙塔”的最初形態是歐洲中世紀大學通過長期斗爭或參與教權和王權的博弈而建立起來的。由于缺乏主權國家的強力約束,歐洲中世紀大學經常憑借其國際性和流動性的特征,通過罷課、示威和遷徙等手段為自身爭取權益。12世紀70~80年代,巴黎大學成立之初,內部師生團體便向教會爭取3項基本權利:錄用新教師的權利、制定規范大學內部活動規則的權利、推舉大學參與外部事務代表的權利。在多方博弈和大學的爭取下,教皇最終于1231年頒發“特許狀”,巴黎大學成為特許的自治機構[8]。與“教師型”巴黎大學相對應的“學生型”博洛尼亞大學同樣在建立初期便主張自身獨立發展的權利,其章程分別于1252年和1253年得到市鎮當局和教皇的承認,獲得獨立法人資格[9]。在原生型大學的影響下,同時期歐洲的其他大學也陸續獲得教皇或政府的承認,成為獨立的自治體。無論是獲頒特許狀還是大學章程得到外部承認,都意味著大學自治權正式獲得法理認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會和政府干預大學事務的權力。這是大學成為“象牙塔”的基礎保障。
在大學內部,同樣呈現“象牙塔”的獨立狀態,主要表現為界限分明的團體組織和學者們基于“閑逸的好奇”而自由探索的學術活動。中世紀時期,民族團(Nations)、學系(Faculty)和學院(College)是至關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學術組織,這些組織根據民族或學科而聯結起來,開展行政事務管理和學術活動。譬如民族團作為大學產生初期“最基礎和最重要”的組織,不僅按照大地區和國家進行劃分,還在大民族團之下繼續細分小的民族團,形成“塔式”結構;各民族團有自己的徽章、規則和經費來源,各自推舉首領管理本民族團內部事務,并代表民族團參與大學管理[10](P46)。從學者個體的學術活動來看,中世紀大學學者也可以享有相當大的學術自由,他們通過課程講授獲得經濟來源,能夠基于“閑逸的好奇”不斷開拓知識邊界,成為“象牙塔”中的主要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中世紀大學在生成之初便建構了“象牙塔”的初始形態,但這種形態是相對低程度和不完備的,與后世對“象牙塔”的特征描述還有相當的差距,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世紀大學的法人身份并非完全獨立,其本質是特許法人;與之相應,中世紀大學特權的本質也是外部“恩賜的特許權”。不同于“法人權力”“法人獨立”等現代法人概念,中世紀“法人”極具妥協意味,中世紀大學的特許法人身份建立在承認教會或國王統攝實質的基礎上[11]。中世紀大學中神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優勢地位,以及大學對宗教“異端”的懲戒正是其外在表現。同時,法人的確立更加強調大學的整體屬性,導致大學越來越脫離其成員而抽象化,這一法人團體被視為單獨存在、虛構性的個人[12],而這一“個人”角色又往往被大學實質的行政管理者據有,并借此形成集權滿足于個人利益。從這一角度來看,大學在“象牙塔”模式下享有的特權并非由大學成員分有,“大學自治”頂層設計之下“學術自由”的缺失值得注意。其次,中世紀大學缺少標準入學選拔制度,社會準入門檻較低,與脫離社會基層且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隱喻存在較大差距。中世紀大學對于入學沒有明確標準和選拔程序,“理論上,只要達到基本的入學年齡和入學水平,任何人都可以進入大學學習”。例如,13世紀巴黎大學的文學院就規定,年滿14歲且掌握基本拉丁語的學生皆可入學[10](P48)。當時,大學的許多學生來自農民和普通市民階層。譬如,出身于破落貴族家庭的學生皮科羅米尼就通過自己在大學的進修,而成為教皇[13](P51)。可見,中世紀大學“象牙塔”之門尚未完全關閉,成為底層民眾實現階級躍遷的重要階梯。最后,中世紀大學學術活動的學理性較弱,實用性更強。“中世紀大學大多是職業性的機構,期望從社會各領域獲得資源和回報”,“即使是邏輯學和辯論術的概念也帶有濃厚的功利和實用色彩”[13](P50)。中世紀大學在非功利性學術探索之外的教學活動中,一直起著為職業生活做準備的作用。
大學真正具備現代話語體系中“象牙塔”的意義,還應追溯到19世紀初期由洪堡引領的新的大學理念和大學改革實踐。首先,洪堡重申“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理念,并通過學院制、教師等級制、教授會制、講座制、利益協商制等頂層制度設計使之確立下來[14]。特別是利益協商制度,給予大學教授直接與政府交涉和確定財政撥款的權限,極大地提高了大學學者的地位,從而保障大學抵御外部誘惑,成為研究純粹學問的場所。其次,洪堡以“研討班”作為人才培養方式,一方面促使人才培養水平有了質的改善,另一方面也導致隨著大學教育成本和入學門檻的提升,大學“象牙塔”之門向社會底層關閉。最后,洪堡強調大學活動的學理性,反對功利性。洪堡將大學定義為帶有研究性質的高等研究機構或學術機構的巔峰,大學的要務在于發展純粹科學——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標,只進行純知識、純學理的探究[15]。
根據這種哲學觀點,大學本質是“高等研究機構或學術機構的巔峰”,圍繞純粹知識中心進行各項探索活動。這個過程應當表現為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即通過“價值自由”的原則,求得“不受價值影響”的客觀學術成果[6](P13-15)。由此,一個充滿高等教育認識論哲學意味的大學“象牙塔”隱喻被相對完備地建構起來。
(二)“服務站”:政治論哲學與隱喻的紛爭
與大學“象牙塔”形態的建構進程相伴隨,“走出”和“回歸”象牙塔的紛爭從未息止。特別是貫穿于19世紀的工業革命,將大學流溢的知識迅速轉化為現實資源。由此,一種強調大學學術研究對現實予以觀照的政治論哲學開始興起。“服務站”或“動力站”的大學隱喻正是這種哲學觀的重要話語表現形式。1862年,美國頒布《莫雷爾法案》,興起贈地運動的同時,也開啟了大學服務社會的職能。大學成為“僅次于政府的主要社會服務機構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工具”,“大學越來越經常地被喻為服務站”[7](P16-20)。但大學在發揮社會服務職能時出現的種種問題,導致“服務站”或“動力站”的大學隱喻出現了較大紛爭。
一方面,新興的政治論哲學擁護者認為,認識論哲學那種為了探索高深學問致力于擺脫價值影響的大學發展范式本身存在悖論,其一是無論從事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學者個體不可能完全擺脫價值判斷,其二是基于價值交換而建構的社會系統中,大學如繼續自我封閉且不能回應社會需要,必然將面臨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因而,他們呼吁大學走出“象牙塔”,成為社會發展的“服務站”。德里克·博克不僅呼吁,走出“象牙塔”已成為現代大學責無旁貸的義務,還在論著《走出象牙塔——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中充分論證了現代大學作為“服務站”的特征及其應然性[16]。哈羅德·珀金則從歷史的視域提出,若想通過一個形象的喻體來表現大學從中世紀到后工業社會在知識和科學方面的關鍵作用,那必然為“大學是社會服務的動力站”[17]。
另一方面,許多大學走出“象牙塔”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以純粹學問為中心的傳統原則和學術規訓,“如奴隸般逆來順受地充當了國家發展目標的主要工具”[18](P63)。“服務站”隱喻的工具主義傾向不僅為大學科研帶來“唯科學主義”和“唯計量主義”的迷思,導致人才培養過程中“人文主義”的缺失,還助長了大學“野性”。奧爾特加·加塞特指出,“服務站”隱喻狀態下喪失文化傳統的現代大學只會受到功利主義驅使,培養專精一業而對其他任何事業全然不知的人,造就大學野性——他將歐洲局勢的分裂動蕩歸咎于缺乏人文精神的野性大學造就了野性的歐洲人[19]。因而,許多持認識論的學者主張堅守、回歸甚至重建“象牙塔”。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認為大學淪為“大眾服務站”是“極其糟糕的事情”,必然導致大學異化,大學異化的產物盡管有其用途,但已喪失大學的寶貴品質[20]。日本學者永井道雄同樣強調,學術過于實用化將妨害大學創造性,形成“現代大學的危機”,因而大學應該“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21],回歸“象牙塔”。“象牙塔”和“服務站”及其背后高等教育認識論和政治論的紛爭,其本質在于對大學知識創造、知識傳遞和知識轉化活動進行價值判斷、價值選擇,并在彼此之間加以平衡。
(三)“有機體”:存在主義哲學隱喻及其整合化
自然科學強勢崛起及其對其他領域的滲透,不僅改變了客觀世界,也改變了社會科學的認知方式。在“象牙塔”和“服務站”兩種隱喻理念紛爭之際,源自生態學的“有機體”概念逐漸成為大學新的喻體,并試圖通過其內涵的整合品性,調和兩者矛盾。埃里克·阿什比系統論述了大學的“有機體”隱喻:“大學像一個有機體,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就遺傳的角度看,它表現為大學教師對‘大學意義共同的、一致的理解。例如,大學應代表人類的精華、客觀無私、發展理性、尊重知識的固有價值等。就環境的角度看,那就是資助和支持大學的社會體系和政治體系。”[22]“有機體”隱喻既不像“象牙塔”只關注大學價值無涉的學術活動和古典傳統,也不像“服務站”過度強調大學的社會和政治功能,而是將兩者整合,形成一種強調主體理性的高等教育哲學。除此之外,弗萊克斯納還通過“有機體”的隱喻為高等教育認識論和政治論的整合提供方法論。他指出,大學“作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要以理性分析和價值判斷為基礎[23](P3),實現“精神與目的的統一”[23](P156-158)。
可以看出,“有機體”的隱喻不僅預示著現實主義的“憂郁心情”[18](P2)和大學主體意識的覺醒,還表現出存在主義哲學的顯著特征。首先,存在主義哲學提出“存在先于本質”[24](P6-7)的世界觀原則。“有機體”的隱喻主張大學本體及其屬性并非天賦或者給定的,沒有關于大學的正確模板和標準范式,而是先存在、出席、登場,之后才能為自己下定義,回答自己“是什么”。也正因如此,大學才能在遺傳和環境中重新定義自己。
其次,存在主義哲學強調“自由選擇”的方法論原則。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指出,“存在的本質懸置在人的自由之中”[25],人能夠作為一種真正實現主體性的客觀存在,通過理性意志而自由選擇成為某種存在,并在這一未竟的過程中創造自身的活動進而規定為他的本質[24](P20)。因而,在“有機體”隱喻中,大學中的主體可以通過自由的理性選擇和“有目的的自由活動”建構大學本體。這正契合了弗萊克斯納“大學是一個有機體,其特征是有高尚而明確的目標”[23](P156-158),“以理性分析和價值判斷為基礎”[23](P3)進行自我建構的觀點。
最后,存在主義哲學認為自為存在不斷生成的可能性和不確定性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賦予意義和價值。這體現了雙重的價值取向:其一,主體可以通過自由選擇而造就多樣的自身本質和價值,這賦予了主體按自身內部邏輯活動的合法性;其二,主體必須為自由選擇所造成的外部影響負責,薩特認為,“自為存在的特質是將價值凝結為具體的行動”,主體在社會互動中“模鑄了自己的同時也模鑄了他人”[24](P9),應當為自由選擇的后果負責,負責任的行動與價值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24](P21-31)。這種重視大學內部邏輯和外部責任的理念,正體現了“有機體”隱喻對“象牙塔”和“服務站”的整合品性。作為“有機體”的大學既保有按照“象牙塔”內部邏輯自由發展的權利,同時也不能忽視自身對外部社會的責任。尤其步入現代社會,大學在“遺傳”和“環境”之間保持合理張力是其“有機體”隱喻的重要追求。
(四)“行政復合體”:實用主義哲學隱喻及其制度化
馬克斯·韋伯指出,強調理性精神、專業秩序和效率邏輯的科層制度成為現代組織形態主流發展趨勢[26]。伴隨大學走向社會舞臺的中心,不僅其知識生產范式實現了由小科學時代向大科學時代的轉型,大學規模日益擴張,而且,隨著創新性知識的產出速度越來越快,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知識的密集性、廣博性和自主性程度也越來越高[27](P16-17)。為協調和管理日益復雜化的知識生產、傳遞和轉化活動,現代大學普遍建立了完備的行政科層系統并使之制度化。
弗萊克斯納指出,美國最好的大學并非“有機體”,而實際成為“行政復合體”[23](P158)。無序擴張的大學建制規模和學術工程項目對管理和協調效率的需求,迫使大學內部行政科層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縱向和水平結構“行政體”的聯結與協作方式復雜多變,造就了一個龐大的“行政復合體”。盡管是“行政復合體”隱喻的提出者,弗萊克斯納最初對大學這一隱喻狀態持批判態度,他認為這種盲目順從社會要求而竭力擴展的“復合體”多樣、多變且復雜,已經喪失大學理想,另外,過度行政化的“復合體”導致大學作為“有機體”被解構[23](P158)。伯頓·克拉克則認為,大學“行政復合體”形態是在高等教育任務激增,信念繁多,官僚、政治、學術等權力向各方牽拉的情況下,維持大學整體秩序的有效形式。在“行政復合體”隱喻下,大學行政官僚制的整合表現為以下5個特征:其一是“分層”,即“一個行政梯隊堆上一個行政梯隊,不停地探索協調、對稱、邏輯和全面的秩序”,分層導致行政金字塔加高,為龐大復雜的系統提供了有效的縱向協調機制,溝通了系統外部的利益相關者;其二是“擴大的管轄權”,賦予各級行政單位更為寬泛的管轄權,導致行政金字塔更加寬廣,結構更為鞏固;其三是“擴大的編制”,大學行政人員數量擴張,但其職位獲得制度性保障;其四是“行政專門化”,掌握專門知識和技能的專業學術管理人員在大學運行中發揮了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其五是“條例泛濫”,行政體數量的增長導致行政條例和規程迅速泛濫,造成嚴重的實踐問題[27](P153-167)。可以看出,大學系統行政科層化發展追求專業化和高效率的運作模式,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哲學色彩。這種“行政復合體”模式的大學形態具有相對完備的制度保障,并成為現代社會制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有機體”與“行政復合體”兩種大學隱喻,正如理想和現實的關系。雖然“行政復合體”的建構有導致大學作為“有機體”解構的風險,也招致諸多批評,然而作為一種制度化了的大學形態,“行政復合體”自有其優勢特點,在實踐中也尚未遭逢能夠超越科層制度的新的大學發展模式。
二、大學結構的隱喻:從“學人共同體”到“開放社區”
大學結構是形成其本體屬性的基礎要素。大學系統的內外部結構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內部邏輯和外部環境變化不斷調整,經歷了從建構、變革再到解構的過程。
(一)“學人共同體”:大學系統的初步建構
在形成初期,歐洲中世紀大學很大程度保留了師生行會的組織結構形式,特別在未獲得官方特許狀和未占有大量固定土地資產之前,流動性一直是歐洲中世紀大學的顯著特征。12世紀之后,大學邊界逐漸確定下來,但帶有明顯商業和手工業行會色彩的“學人共同體”(universitas magistrorumet scholarium/universitas studii N.)作為形容歐洲中世紀大學的組織隱喻不僅沒有喪失,反而得到官方認可和強調。譬如,1205年,教皇英諾森三世在書面上稱巴黎城的教師和學生為“universis magistris et scholaribus Parisiensibus”[28]。此后,教廷一直以“共同體”對大學進行稱呼:1208~1209年稱巴黎大學為“教師共同體”(universitas vestra and magistrorum),1210~1213年稱其為“你們的共同體”(vestra universitas),1228年稱其為“教師和學生共同體”(magistri et universitas scolarium),1231年稱其為“學生共同體和教師共同體”(universitas scolarium and universitas magistrorum vel scolarium)[29]。
在“學人共同體”隱喻狀態下,大學本體具有明顯的邊界性和非標準化的部落式結構特征。從內部結構來看,大學行政管理結構和學術結構的中心分散于不同的民族團和學系,形成松散的“學術部落”,不同部落之間界限分明。盡管后期伴隨學科知識的分化與整合,歐洲中世紀大學形成了文、法、神、醫等不同的系科;13世紀之后,大學課程逐漸由大學規程或教皇敕令固定下來,但不同大學的內部管理結構和學術結構很長一段時間都未達成統一化和標準化的目標。譬如在巴黎大學,教師和教皇任命的校長在決策和管理上占據主導地位,內設文學、法學、神學、醫學四個完整的系科,文學系帶有明顯的基礎和預科性質;而在博洛尼亞大學,學生在大學事務管理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且學術結構中只有法律系和醫學-文學系,文學和法學、醫學沒有上下的銜接關系[10](P51-55)。除此之外,不同大學民族團的組織結構以及學生培養計劃、修業年限等都有很大差異。從大學的外部結構來看,“學人共同體”隱喻的概念本身就含有“團體一致”的意味,中世紀時期教皇對大學以“共同體”相稱,實際上也承認了其“獨立王國”的地位。盡管歐洲中世紀大學常常被裹挾于宗教神權和世俗王權之間的斗爭,學術實踐和日常生活也無法脫離世俗社會,但這些外部聯系相對簡單,很少對大學本體發展產生持續性的根本影響,大學的重心依然聚焦于內部邏輯。總之,盡管大學組織尚不完善,但“學人共同體”的隱喻昭示著,大學作為一個由松散學術部落組成的統一體被建構起來并取得外部承認。這是大學系統結構建設的肇始。
(二)“軸心機構”:大學系統的結構化變革
19世紀之后,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在意識形態維度的長期影響,以及科學知識分化、社會專業分工的客觀環境變化,大學的內部和外部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化,理性邏輯和結構主義哲學成為大學結構變革的重要思想來源。大學為了擺脫前期新興科技與社會發展“局外人”的隱喻,引入科學教育,在內部基于知識邏輯建構大學專業結構,同時改變了大學同外部的互動結構。丹尼爾·貝爾稱現代大學為“軸心機構”,在他看來,人類社會即將步入以知識生產(替代物質生產)為軸心組織起來的“后工業社會”,大學作為理論知識的創造者將成為新的社會軸心機構[30]。“軸心機構”的隱喻顯示出崇尚科學和理性的指向。
一方面,在大學內部結構層面,大學學科知識體系、管理組織的結構化變革往往經過嚴謹的理性考量和科學改造,更加注重知識生產的需要,這不僅是大學“以標準化科學知識為軸心的結構特征”,也是使大學成為社會“軸心機構”的基本條件。在19世紀,無論是早期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密爾和愛奇沃斯,還是科學主義思想家斯賓塞、赫胥黎,無不強調科學化和系統化的知識結構對大學軸心地位的重要意義。貝爾也指出,以理性精神塑造知識基礎,抵御非理性主義文化的侵蝕和加強“科學的精神氣質”的涵養,是大學在后工業時代成為“軸心機構”的兩條重要路徑[31]。
另一方面,大學作為“軸心機構”的隱喻重點在于指出大學本體在外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地位。近代以來,大學創造的科技成果中蘊藏的巨大效益通過結構化的知識轉化體系得以顯現,甚至成為變革社會的重要力量。同時,大科學時代以巨額資金投入、較長研發周期和大規模協作為特征的學術模式,也導致大學注定無法維持傳統自足的孤立發展結構。“軸心機構”的隱喻本質正是基于理性探索大學融入現代社會結構的實踐路徑,并使大學內外部結構相互調適,符合理性原則。美國學者亨利·埃茲科維茨提出了“大學—產業—政府”的三螺旋概念,將大學作為實現“三螺旋”協同發展中的一軸[32]。伯頓·克拉克也提出政府權力、學術權威和市場三因子作用的“三角協調模式”作為高等教育結構的分析模型[27](P154-159)。這正說明大學作為“軸心機構”與社會系統結構緊密嵌合的狀態。總體來說,“軸心機構”的隱喻下,大學擺脫了中世紀時期松散的“學術部落”式結構和社會“局外人”的狀態,在大學內外都建立了穩固的理性主義結構體系。
(三)“開放社區”:大學系統的解構
與結構主義通過頂層設計和結構改組以建構理性的大學發展秩序相對,解構主義哲學的視角聚焦于在“科學理性”和“最優化大學標準”遮蔽下的大學發展的更多可能性。這種理念伴隨世界多元化發展態勢受到重視。1963年4月,克拉克·科爾在哈佛的講座上提出“開放社區”[18](P26-29)、“智力城”[18](P62)、“思想城”[18](P65)等隱喻,建構了一個以多元化和不確定性為特征的大學形態。2009年,彼得·布拉德韋爾提出與“開放社區”相似的“無邊界大學”隱喻,從技術視角宣告大學內部和外部的傳統結構走向解體——不僅其內部知識體系、學科專業、人員互動的邊界被解構,大學與社會的界限也逐漸模糊[33]。“開放社區”或“無邊界”的隱喻不僅消解了高等教育與更廣泛社會之間的界限,更詮釋一種“前沿”的概念。這個隱喻暗示了以解構主義為原則的大學走在進步的前沿,顛覆著大學過去的傳統結構和慣性[34](P100)。
在實踐層面,大學作為“開放社區”的屬性日益明顯。有學者從復雜系統科學的視角研究發現,現代大學不僅僅是一種存在有序結構的“自組織”,還具有開放性的“他組織”特征[35]。一方面,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和終身學習型社會深刻變革了大學人才培養結構。大學不僅在授課形式上實現了如微課、慕課、翻轉課堂等以信息化、多樣化、人機互動為特征的變革,其學位結構也突破以往的單一機制。比如,英國在短短數十年時間便建構起包含哲學博士、專業博士、“1+3”博士、課程博士、實踐博士、新制博士在內的多元化博士培養和學位授予體系[36]。馬丁·特羅指出,在實踐中高等教育的許多概念已經發生解構,需要重新定義,為此他也不得不對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理論進行檢視與反思[37]。另一方面,大學中以問題為導向的科研活動與合作項目也進一步突破學科、方法、范式和地域國界的限制。以歐洲“博洛尼亞進程”為代表的諸多新型合作項目與協作形式,也以開放多元的特性不斷解構傳統的大學發展結構。
在理念層面,大學結構走向“開放社區”的隱喻狀態下,涌現了多樣的大學結構范式。如:“流體大學”(形容大學被裹挾進外部社會結構形成的漩渦力量的狀態)、“網絡大學”(描述大學結構的流動性、空間性、不同樞紐或節點之間的互動性)[34](P19)以及“大學是‘一組噴泉,在公共空間里迸發出思想的火花”。大學是“一組噴泉”的隱喻不僅具備半透明大學向公眾開放的特征,其內部結構也無限復雜——“它的水滴以不可預知的方式聯結在一起”[34](P44)。可以看出,在解構主義的哲學理念中,大學本體結構也解構成多樣、復雜甚至充滿矛盾的喻體,這些喻體同具體的大學實踐導致現代大學結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同時,也賦予其多樣的發展可能性。
巴尼特認為,現代社會進入“超復雜性”時代,傳統大學發展結構面臨解構的風險,實用主義、相對主義乃至元批判主義等思潮不斷沖擊高等教育的認識論基礎[38]。那些充滿想象力和極具顛覆性的解構主義大學隱喻的涌現證明了這一點。現代化進程中,高等教育不斷解構自身,“使活潑潑的課程、教師、學生從‘舊結構中被解放出來”成為邏輯必然[39]。大學的未來是多樣化的未來,而非單一的未來,不可能為所有大學找到一個普遍適用的改革之道或萬全之策;關于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思考也絕不是只有“現實可行性”這一條進路[40]。盡管“開放社區”“無邊界大學”等隱喻或許尚未完成系統化建構,理念體系表現出分散、凌亂抑或充滿悖論的特征,以“解構主義”為內核的隱喻對大學在系統結構和傳統秩序“被解構”的前提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尚不能給出絕對完善的答案,但這些隱喻為大學“未來的可能性”提供了創新性思路。大學隱喻的多元建構要求我們以更加包容的心態對待在風險和不確定中進行探索的各類思維和實踐。
三、大學功能的隱喻:從“鏡子”到“燈塔”
(一)“鏡子”隱喻與高等教育適應論
卡瓦納提出,舉起“鏡子”是大學的本分[41](P108-110)。“鏡子”的隱喻既強調大學對于客觀世界本體的認知工具屬性和解釋功能,同時也要求社會以大學為鏡鑒,尊重大學的科學知識,建構實踐理性。大學“鏡子”隱喻受到普遍關注源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贈地學院”運動的興起與發展。1904年,威斯康星大學校長范海斯提出“大學為州服務”的理念:一方面,威斯康星大學適應了社會生產和發展的需要,發揮“鏡子”作用,“領導和映射了全州的進步主義思想”,“為全州人民拓寬了文化的范疇”;另一方面,州政府也積極接納威斯康星大學參與州的公共事務,“把整個州交給大學”,使得“整個州成為大學校園”[42],才造就了大學作為社會“鏡子”的成功案例。
在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國家的“鏡子”隱喻往往是基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將大學視為“上層建筑”的存在,認為大學受到社會發展程度、個體認知水平以及科學知識發展邏輯等多方制約,大學功能主要體現在通過學術實踐實現知識增殖,并服務于社會進步和人類個性全面發展的需要。潘懋元先生的“兩個規律論”正是這種理念的代表。潘懋元先生指出,教育外部關系規律是“教育必須受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科學文化所制約,并為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科學文化服務”,而教育的內部規律則是“教育應當培養全面發展的人”[43]。
大學“鏡子”的隱喻表現出諸多明顯特征。首先,“鏡子”隱喻重點強調大學對客觀世界的認知、解釋和服務功能。大學對于客觀世界的認知和解釋必須客觀、堅守真理性標準,“如同傻子一般基于勇氣和理性向權威舉起鏡子”,以達到服務社會的目的[41](P108-110)。其次,“鏡子”隱喻強調客觀因素對大學功能的限制性。潘懋元先生曾舉出1958年教育大躍進的案例證明教育脫離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最終只能導致大起大落[44];同樣,高等教育脫離人的成長規律和知識發展邏輯也將帶來消極影響。最后,“鏡子”隱喻反映出大學發揮社會和個體功能的歷史常態,即盡管大學為社會發展變革做出了突出貢獻,但在歷史發展的大部分階段大學都作為社會前進的適應者和服務者而非直接引領者。我們希望大學成為社會的“燈塔”、改革的先鋒,但回溯歷史,我們卻得到另一個截然相反的答案,那就是大學往往是保守的。面對外部世界的需求和社會變革甚至知識變革,大學的回應經常不及時,有時甚至是抵觸的。比如在科學革命中,大學被認為幾乎是置身事外的[45]。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大學轉型更多是適應內外部環境變化,而非引領社會變遷。
(二)“燈塔”隱喻與高等教育超越論
與大學的“鏡子”隱喻相對立,許多學者認為,大學作為科學知識的主要策源地和創新的前沿,具備引領社會發展的功能。一方面,正如布魯貝克指出的,現代大學成為“新思想的源泉、倡導者、推動者和交流中心”,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工具”[6](P21)。另一方面,即使基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立場,同樣要重視“高等教育對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作用”[46]。永恒主義哲學代表人物赫欽斯提出,大學“應是燈塔而非鏡子,應引導社會而非迎合大眾淺近需求”[47]。大學“燈塔”隱喻同樣存在于中國,竺可楨先生曾指出,“大學猶海上之燈塔,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陳佳洱校長也強調,“引導社會向前發展”是大學應完成的使命[48]。這充分說明,大學發揮“燈塔”引領作用是大學實現其社會功能的一種至關重要的形式。
在實踐中,大學發揮“燈塔”作用的現象在后工業時代的知識經濟模式中十分普遍。20世紀中期美國“現代科技大廈締造者”萬納瓦爾·布什提出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工程開發—市場經營”線性技術程式就強調大學基礎研究對于社會整體創新系統的起點和引領作用[49]。在該理念的指導下,布什和康普頓造就了麻省理工學院通過知識創新、傳承和轉化,引領科技產業升級的發展模式,打造了美國128號公路科技產業走廊;布什的學生、有“硅谷之父”和“電子革命之父”之稱的弗雷德·特曼也秉承其師理念,他擔任斯坦福大學校長期間通過大學改革發揮了斯坦福大學的科研引領作用,塑造了硅谷科技產業園區。這兩所著名創業型大學成為引領美國社會信息化轉型的“燈塔”。
大學“燈塔”隱喻具有明顯的永恒主義和理想主義特征。首先,“燈塔”隱喻強調大學對社會的引領作用,反對大學被動滿足社會發展淺近需要,即大學要領航而非逐波。其次,大學的超越性是建立在大學自身對“認知理性”發揚的基礎之上,反對工具理性、政治理性和傳統“實踐理性”取代大學“認知理性”在教學和科研活動中的核心地位[50]。最后,“燈塔”隱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大學的偉大理想和卓越追求,是大學被動恪守現代社會改制規程情況下,對強調大學自身發展邏輯的理念傳統的一次回歸。
四、啟示:創新大學隱喻賦能本體變革
通過歷時性分析可以看出,大學隱喻的發展具有客觀流變性、理念遺存性和對立統一性的特征。一方面,大學本體經歷了一系列秩序建構,在保留古老理念和文化傳統的同時,逐步順應現代文明發展大勢,走向標準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大學建立的理性秩序在變動不居的時代中充滿了不確定性,面臨格特·比斯塔所說的“美麗風險”[51]。但伴隨現代制度的普遍確立,大學的隱喻逐漸封閉。大學被納入國家統一的政策框架和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受到制度規訓的大學“似乎并不想以一種更廣闊的形式想象自己”,多元的大學想象和大學理念逐漸讓位于對“研究型大學”或“創業型大學”等標準大學模板的承認[34](P1-17)。這種封閉體現在意識形態功利化、空間互動的限制和倫理自利等多個維度[34](P1-2)。根據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52]。大學隱喻同樣如此。在高等教育系統,社會對高等教育轉型的迫切要求,對高等教育現有理論解釋力、建構力和實踐力的質疑,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研究不得不面對的合法性危機。危機的解決不僅需要通過大學隱喻解釋大學本體發展規律,更要創造新的大學隱喻重構大學想象力,通過隱喻賦能大學本體變革。
首先,通過創造新的隱喻來認知和變革大學,需要激發大學理念創造的“想象力”。巴尼特認為,隱喻作為一種裝置,把我們從對世界的既定表象中帶離,以一種充滿想象力的方式,去重新認知眼前的世界現象。他指出了激發大學想象力和建構創造性隱喻的四個標準:其一,要“想象不可能的夢”[34](P25-26)。想象力首先要克服的挑戰不在于它太不切實際,而是它太植根于經驗。隱喻要具有創新性和理論高度。客觀來說,高等教育的世界充滿隱喻,戰略方針、目標、要點都是軍事隱喻,消費者、消費者滿意度和選擇都是市場隱喻,但隱喻的能量表現在其本身對傳統邊界的超越[34](P18)。其二,隱喻要成為一個“可行的烏托邦”,隱喻的“烏托邦”為大學變革造就了理想的范本,但這個范本必須具備現實可行性[34](P26-28)。其三,大學隱喻要探索大學本體在多重維度的可能性,羅伊·巴斯卡將“本體論”世界分為經驗的、現實的、本質的三個維度,大學隱喻和想象不僅要著眼于經驗世界,更要深入其本質,具備一定抽象能力。只有這樣,其“重塑大學的潛能才不會被削弱”[34](P28-29)。其四,大學的隱喻或想象應該有不同的類型和多重結構,實現與“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有機結合,在對現有大學范式批判的基礎上提供新方案[34](P29-34)。我們應當創造出具有變革價值的隱喻,為變革大學本體實踐提供理論先導。
其次,創造新的隱喻賦能大學本體變革,需要生成利于創新性大學隱喻發展的制度和文化空間。富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學隱喻往往是顛覆性的和“逆意識形態”的,因而為大學隱喻提供包容性的制度和文化空間至關重要。營造思想自由的空間,有利于生成充滿想象力的創新性隱喻,將大學從目前的結構、話語和觀念中解放出來[34](P45)。在現代社會,保障學者以真理性為標準開展自由研究的權力仍舊至關重要。通過大學隱喻的流變我們可以看出,大學隱喻往往基于不同的價值和立場,反映出不同學者對大學實然狀態的認知和應然狀態的思考,這些隱喻不僅復雜、多變,而且往往形成激烈的理念紛爭和現實爭鳴。大學本體正是在這些看似雜亂無序并且充滿爭議的隱喻引領和驅動下,不斷得以發展。相反,如果缺乏生成創新性大學隱喻的制度和文化空間,學術自由得不到保證,那么學者往往只能屈從于一種權威聲音,淪為主流理論的注腳。
最后,創造新的隱喻賦能大學本體變革,需要高等教育理論和實踐共同體的持續努力。通過對大學喻體的梳理和探索可以發現,許多經典大學喻體的提出者往往并非單純的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者,而是兼具豐富高等教育實踐經驗和高深理論素養的“實踐型”學者,如弗萊克斯納、伯頓·克拉克、克拉克·科爾、赫欽斯、竺可楨等人本身就是擔任大學校長或研究院院長等行政職務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建構創新性大學隱喻并用以賦能大學本體變革,本質上正是一個理念創新并引領實踐革新的過程。“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高等教育理想研究范式,要求高等教育研究者轉變觀念,用“實踐共同體”的理念凝聚共識,在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共同協作下,實現大學本體的變革和發展。
參考文獻
[1]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苗力田,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673-674.
[2] 孫芳.不同隱喻下大學治理模式的選擇[J].現代教育管理,2014(07):17-20.
[3] Gareth Morgan.Images of Organization[M].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2006:3-6.
[4] 羅珉.基于哲學視角的組織隱喻研究前沿探析[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9(04):1-9.
[5] 胡建華,等.高等教育學新論[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30-32,307.
[6] [美]約翰·S·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M].王承緒,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7] Brubacher J S.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M].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1982.
[8] 胡建華.大學內部治理與外部治理關系分析[J].江蘇高教,2016(04):1-5.
[9] [英]艾倫·B·科班.中世紀大學:發展與組織[M].周常明,王曉宇,譯.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68-74.
[10] 黃福濤.外國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11] 覃紅霞.中世紀大學自治的誤讀與重釋[J].高等教育研究,2017(06):86-92.
[12] [美]泰格·利維.法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M].紀琨,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109.
[13] 賀國慶,等.外國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14] 別敦榮,李連梅.柏林大學的發展歷程、教育理念及其啟示[J].復旦教育論壇,2010(06):8-15.
[15] [德]威廉·馮·洪堡.論柏林高等學術機構的內部和外部組織[A].陳洪捷,等.國外高等教育學基本文獻講讀[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31-134.
[16]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M].
徐小洲,陳軍,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5-59.
[17] [美]伯頓·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M].
王承緒,徐輝,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
[18] [美]克拉克·科爾.大學的功用[M].陳學飛,等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19] [西班牙]奧爾特加·加塞特.大學的使命[M].徐小洲,陳軍,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6.
[20] Abraham Flexner.University:American,English,Germa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44.
[21] 沈國經.中外著名教育家事典[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700.
[22] [英]埃里克·阿什比.科技發達時代的大學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14.
[23] [美]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論——美英德大學研究[M].徐輝,陳曉菲,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4] [法]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M].周煦良,湯永寬,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25] [法]薩特.存在與虛無[M].陳宣良,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56.
[26]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218-219.
[27] [美]伯頓·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王承緒,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28] Olaf Pedersen.The First Universities: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33-151.
[29] 高露,王云龍.行會視角下西歐中世紀大學起源——以巴黎大學為例[J].外國問題研究,2021(02):80-86,119.
[30] 展立新.后工業時代高等教育面臨的雙重困境——解讀丹尼爾·貝爾的世紀性預言[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6(02):166-176.
[31] [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M].高铦,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212-378.
[32] [美]亨利·埃茲科維茨.三螺旋——大學·產業·政府三元一體的創新戰略[M].周春彥,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3.
[33] Peter Bradwell.The Edgeless University[M].London:Demos,2009:53.
[34] Ronald Barnett.Imagining the University[M].New York:Routledge,2013.
[35] 李福華,來文靜,陳晨.為“他組織”辯護:對大學組織特性的質疑與反思[J].大學教育科學,2022(02):37-44.
[36] 胡欽曉.英國新制博士學位的特色與啟示[J].教育研究,2013(08):125-132.
[37] 黃福濤.馬丁·特羅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理論的檢視與反思——基于歷史與國際比較的視角[J].高等教育研究,2022(03):33-42.
[38] [英]巴尼特.高等教育理念[M].藍勁松,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4-17.
[39] 盧曉東.在世界之中應合:高等教育現代化與創新驅動戰略之間[J].大學教育科學,2023(01):19-21,24-25.
[40] 王建華.知識社會視野下高等教育的隱憂與超越[J].高校教育管理,2022(04):1-10.
[41] Donncha Kavanagh.The University as Fool[A].Ronald Barnett.The Future University[C].New York:Routledge,2012.
[42] 陳學飛.美國高等教育發展史[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64-65.
[43] 楊德廣.高等教育“適應論”是歷史的誤區嗎——與展立新、陳學飛商榷[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3(03):135-148.
[44] 潘懋元.潘懋元文集(卷一)[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9-50.
[45] 賀隨波.大學與科學革命的發生:爭議與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22(01):86-98.
[46] 展立新,陳學飛.哲學的視角:高等教育“適應論”的四重誤讀和誤構——兼答楊德廣“商榷”文[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3(04):150-172.
[47] Robert Maynard Hutchins.The Learning Society[M].
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68:131-132.
[48] 袁廣林.從象牙塔、服務站到燈塔——隱喻視野下的大學理念[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9(05):54-58.
[49] Vannevar Bush.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M].
Washington: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20:15-21.
[50] 展立新,陳學飛.理性的視角:走出高等教育“適應論”的歷史誤區[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3(01):95-125,192.
[51] [荷]格特·比斯塔.教育的美麗風險[M].趙康,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序言1.
[52]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9.
Abstract: Universities have formed a variety of metaphor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cultural context, different metaphors carry different university concept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university cognitive methods and value judgments. Through the example and analysis of metaphors related to the natur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universities, the analysis of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ontology found that in the evolution from the “ivory tower” metaphor to the “complex” metaphor,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na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grated, and the ontology system is further institutionalized. The evolution from the metaphor of “academic community” to the “open community” shows that the ontology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construction to deconstruction that gradually becomes diversified and open.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metaphors of “mirror” and “lighthouse” shows that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function always faces the game of adaptation and transcendence. The university metaphor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arent objective rheology, the persistence of ideas, an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There are multi-dimensional disputes over university ideas and the evolution law of university ontology behind it. The need for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reconstructing university imagination and empowering university ontology transformation through metaphor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metaphor; university ontology; conceptual dispute; university imagination
(責任編輯? 黃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