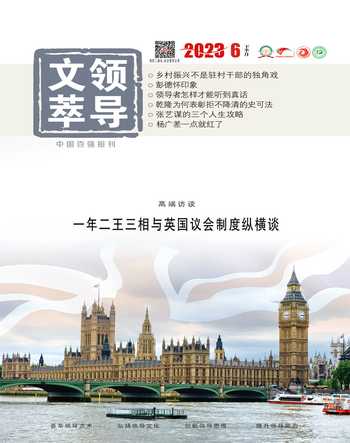平均負債上百萬元,求解“小村大債”
吳超

2023年兩會期間,民盟中央向全國政協提交了《關于開展“小村大債”綜合治理,助推鄉村振興的提案》。提案從鮮有關注的村級債務出發,直擊鄉村治理中的薄弱環節。
“‘小村大債是我國實施鄉村振興的‘攔路虎。”民盟中央在提案中直言,據農業農村部抽樣調查,截至2019年上半年,全國70萬個行政村中,村級債務總額已達到9000億元,村級組織平均負債已達130萬元。
村級債務存量較大,增量的成因復雜,集體“包袱”有越來越重的風險。如湖南省2020年統計,負債村占全省總村數的72.49%,村均負債108萬元。
“越是新建的村,通常債務就越重”
一般來說,村級債務指的是村委會(含村民小組)、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單位或個人之間形成的負債。
在全國范圍來說,并非所有行政村都形成了負債。部分經濟發達地區,行政村經濟收入夠多,就沒有債務負擔。
民盟寧夏區委會參政議政處在調研中發現,村級負債主要來自兩個方面:村委會形成的建設性債務以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性負債。前者的形成主要與村莊建設或者基礎設施配套相關。“越是新建的村,通常債務就越重。”提案的素材提供者馬學梅解釋。
民盟中央的提案顯示,近年來,在新農村建設中,很多村由于自身財力不足,普遍舉新債實施項目,導致村級債務額難以鎖定,呈現出總額繼續上升的趨勢。
通過金融機構和其他單位及個人的借款形成的債務,都需要支付利息,即使不增加新的債務,利息也使債務總額不斷增長。
“現在村里還欠五十多萬塊,每個月都有人上門要錢。”張健是南方某省的一位村主任,他向記者介紹,這主要是修路等支出無力承擔后,欠了施工隊的錢。
“有可能是村集體經濟虧損,或者項目不適合本地,經營不達預期等原因。”馬學梅介紹,經營性負債比較復雜,她調研過一個鄉村,前幾年建倉庫,村里出了錢,鄉里也補貼了一部分,“結果建好了,三年沒租出去”。
民盟中央的提案描述,鄉村從銀行、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貸款的難度不斷增加,貸款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為償還銀行債務和利息而“拆東墻補西墻”,鄉村開始不斷向私人借款,相當一部分村民成為鄉村債務的債權人。
村集體承擔部分政府職能
在兩種債務來源中,經營性負債主要是商業行為,建設性債務背后,村集體正承擔著部分政府的職能。
民盟中央的提案寫道,基層村鎮推行美麗鄉村、養老院、移民新村建設等,由縣區財政承諾補助,但數額少且難兌現,很多村集體不得不舉債維持運營。此外,村莊綠化、人飲工程改造等公益事業缺口部分的資金最終也都轉化成為新的村級債務。
在出現負債問題的村集體收入中,除了租金、投資性收益等,有一部分來自政府補貼,但難以滿足運轉的資金需求。
記者獲得的一份云南大理州某鎮村級收支情況顯示,2022年該鎮12個村委會共收入549萬元,其中村集體經濟收入331萬元,補助收入165萬元。同年上述村委會共支出659萬元,屬于收不抵支的情況,其中,其他支出占比最大,為326萬元,人員補助216萬元。“其他”是什么內容并未解釋。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團隊也曾舉例說明,公共設施配套為村莊帶來的負債問題。中部H省的J村,1990年代初到2000年初是縣里的明星村。隨著村辦企業的衰落,村集體收入大幅下滑,如今每年收入20萬元,主要來自生態補貼。
J村積極爭取了道路建設和拓寬、自來水管道鋪設等項目。其中,村級道路建設花費了200萬元,缺口180萬元;自來水項目耗資210萬元,三峽總公司資助80萬元,村集體自籌130萬元。截至2020年,J村的村級債務為911萬元,主要是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提檔升級過程中產生的。
對于有持續性經營收入的村集體來說,負債只是暫時困難,可以通過拉長還款周期,降低貸款利率等方式調節。如果沒有“造血”能力,村集體形成的負債,將變得十分棘手。作為群眾自治組織,村級債務無法由政府兜底。
長期以來,村級財務都是由鄉鎮一級代管,簡稱為“村財鄉管”。
“村里面只有出納,會計在鎮政府,負責做賬。村里的財務情況,每個月會進行公示。”浙江一位副鎮長向記者介紹,村里的負債主要用于壯大集體經濟,“每一筆投資貸款都要經過鎮政府同意,我們會仔細考慮投資收益率”。
然而,民盟中央的提案中提醒,“村財鄉管”的模式存在漏洞,無力處置各村較為復雜的財務問題。上述一位村主任介紹,鎮里知道村集體的負債情況,但依然缺乏還款來源,村里財務狀況也未公示。
建章立制防止村級債務反彈
村級債務問題并非這幾年才出現。早在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就曾印發文件,要求徹底清理鄉(鎮)、村兩級不良債務。
文件中寫道,一些地方的鄉村兩級(鄉鎮政府、村委會和鄉村集體經濟組織)不顧農村經濟實際狀況,超過自身承受能力,盲目向單位、個人舉債,主要用于非生產性支出,甚至揮霍浪費,使鄉村兩級不良債務大量增加,債務包袱沉重。
此后,國務院等部門發布多份涉及村級債務的文件。2020年,農業農村部再次印發《關于開展全國村級債務摸底調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實摸清村級債務情況。
隨后,湖北、甘肅、湖南等省份陸續發布通知,要求化解村級債務,并制定細則。記者查閱了多個省份的化債方案,首先都是要求核實村級債務,鎖定村級債務總額,并對不同負債額度的村子進行分類。
鎖定債務的過程中,一般會先剝離經營性債務。在全面清查的基礎上,對有明確償還來源和化解途徑的經營性債務,制定還款計劃。對未履行程序擅自舉債、形成不良經營性債務的,通常按照“誰批準,誰負責;誰借錢,誰償還”的原則,落實化債責任。
對于建設性債務,許多地方政府制定了政策減免措施,或由政府單位幫扶化債。2021年10月,湖北省農業農村廳公布了宜都市化解村級債務的途徑,1.26億村級債務中,兜底減免清債1564.3萬元。其明細中解釋,對村欠農業銀行257.35萬元債務、農村商業銀行414.08萬元債務,市屬國有企業分別與2家銀行簽訂債權轉讓合同,支持鄉村振興做核銷處理。對村欠財政周轉金、世行貸款、基金會債務,市財政局按呆賬做核銷處理。此外,市直單位幫扶化債254萬元。
除此之外,核銷虛空賬、清收原有債權還債、發展集體經濟化債、自籌資金化債等,都是常見舉措。針對村集體與往來單位、個人、農戶形成的三角債,則在協商自愿的前提下,采取債權債務人自愿結對、協商互抵、相互置換銷債等辦法。
加強村級債務管理,更重要是防止出現化解-新增-再化解的惡性循環。
宜都市在新的管理辦法中規定,凡是村級的基礎設施和農業生產開發等項目,各部門都不得要求村級負債配套資金。村級新上項目,從立項審核就嚴格把關,必須有足額資金不增加村級債務,凡有村級債務或無資金來源的,一律不予審批。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