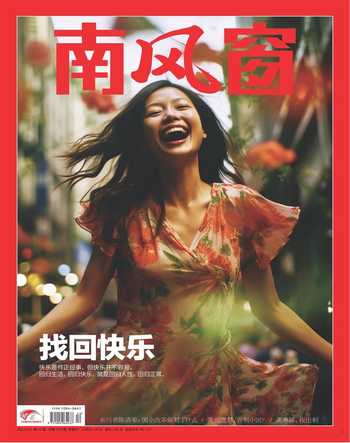網紅街,還能紅多久?
胡萬程

有人說,世界上本沒有網紅街,街上的人多了,也就變成了網紅街。
這句話放在以前是對的。上海的武康路、廣州的東山口、重慶的李子壩站,這些本無意吸引人流的街道因為某些元素獲得了游客的青睞,成為社交媒體上“不可不去”的打卡點。
但時至今日,網紅街卻并非都這么隨緣。相反,其中的相當一部分都是刻意而為。
幾乎每個中型體量以上的城市,都會有那么一條特色街道。拍照墻、涂鴉房,建筑刷得粉粉綠綠,別問,問就是“Ins風”。
年輕人手拿鐵板魷魚、竹筒奶茶、臭豆腐這類千篇一律的小吃,穿行在各個網紅街的義烏小商品店,努力凹著造型,最后在“千修百改”的照片上打上“what a lovely day”的賽博水印。
年輕人在網紅街的圣地巡禮,與中年人在景區大門前的“到此一游”合影,本質上并無二差。只是網紅街的存在,給了新一代們前行的目的地與消費動力罷了。
“流水線”式造街
首先要明確的是,“網紅”一詞本身并非貶義,是相對中性的。
借助網絡傳播的放大效應,迅速提升知名度,一些曾經被埋沒的、很難被注意的事物因此獲得了巨大的流量。像長沙、重慶、西安、淄博等城市,都是網絡流量的受益者,網紅城市的標簽給它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商業活力。
在“人人都能成為15分鐘名人”的網絡時代,打造網紅街,無疑是一種相對公平的、高性價比的,甚至可以以小博大的投資。
但人們不滿的,是網紅街的嚴重同質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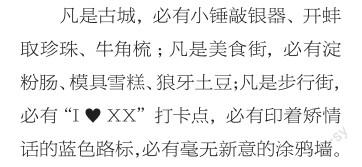
位于嶺南的東莞網紅街,與遠在中原的大同網紅街,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內容高度雷同,究竟為什么會這樣子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樣的網紅街都是批量制造出來的,出自市面上大同小異的設計服務公司手筆。他們承包從設計到施工,再到布景的一攬子服務,價格越低的團隊,其內容越區域雷同。
那些網紅街的“配件”就更加簡單。“我在XX很想你”的指示牌,網紅快餐攤位,Ins風墻飾,這些帶有濃郁網紅味道的東西直接在網購平臺下單即可。它們大多數也是出自同一個地區的同類企業,產品的差異很小。
比起正正規規地做一條商業街區,這種流水線式的網紅街區打造,成本要小得多。
據業內人士透露,如果僅僅是一段半公里的以美食為主打的網紅街的話,節約著去弄,預算可以控制在200萬以內。對比那些花上數億才能完成的方案,這類方案可謂是投資少、回報周期短的好東西。
但好東西必然效仿的也多,眾多財力捉襟見肘的中小城市,特別是旅游城市的景區就偏愛此類方案。這使得高性價比的網紅街應用地越來越多,同質化現象也愈發嚴重。游客們逛久了,看不到屬于當地的特色,看到的只有一鍵復制粘貼,自然也會失望。
不是沒有人想過搞差異化,但差異化就意味著要特殊化定制,其設計和施工的費用與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通用方案”不可同日而語。
而網紅街的打造是典型的重資產項目,風險較高,投資者更愛選擇能穩穩賺到錢,有足夠利潤空間,最好是被反復驗證過的模式。那些非標準化的,單價比較高的,利潤不夠厚的,不適合走量的,追求復購率的東西,對于投資者是一個更加危險的選擇。
網紅街的打造是典型的重資產項目,風險較高,投資者更愛選擇能穩穩賺到錢,有足夠利潤空間,最好是被反復驗證過的模式。
可以說,“千篇一律”是城市治理者從經濟角度看到的最優解。
商業化和生存
但城市特色商業街區的打造,經濟性并非唯一著眼點。而且,隨著網紅街的嚴重同質化,它的吸引力也在快速消退,游客來得少了,消費少了,經濟上也變得不再劃算。
尤其是那些地理位置一般,本就是人為打造的網紅街區,一旦背上“同質化”的名聲,基本上就難逃沒落的命運。
比如2021年10月,號稱投資1.5個億的杭州蕭山聞堰老街開街,但不到一年,這條街就漸漸沒落:從去年的20家商家入駐到現在只剩幾家,從一開始的游客人山人海到現在的門可羅雀。
翻看小紅書,你還能找到這樣的“避坑貼”—“去年老街開業的時候去過一次,宣傳號稱的江鮮一條街,其實就幾個七拼八湊的小吃攤。原來是破舊不堪,現在是不三不四、不洋不土,沒有一點老街的韻味,這樣的改造太令人失望。”
當“網紅街”的大風刮過后,人們發現那些活得好的商業街區,只剩下那些真正花了心思的,在設計、商業、運營上都下功夫的特色街區。
長沙的太平老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條老街,長380米,寬不過7米,火了兩千多年。在長沙,太平老街是一張厚重的歷史名片,也是一個時尚的城市地標。
魚骨狀的街巷位于湘江一側,北臨五一大道,南連解放西路,是長沙古城保留原有街巷格局最完整的一條老街。所謂“千年太平街,一部長沙史”。
2006年6月,長沙市政府斥資1.5億元啟動太平歷史文化街區一期保護整治工程,即380米主街、155米金線街的地下管網、地面設施和立面改造。
2007年,恢復后的太平歷史文化街區正式開街,街區不僅保留了賈誼故居、長懷井、金線街麻石路、辛亥革命共進會舊址、四正社舊址等文物古跡和近代歷史遺跡,也給乾益昇糧棧、利生鹽號、楊隆泰釘子鋪等歷史悠久的名老字號注入了生機。
之后,老街在2018年、2019年又先后啟動了支巷“有機更新+微循環”改造。改造涉及太平街東、西兩廂8個節點,在保留老街文化底蘊的基礎上,疏通街區的“毛細血管”,將主街業態與人流引入支巷,使整個太平老街片區都“活”了起來。

在呈魚骨狀的太平老街街區,游客們可以玩上很久。在太平街散步,你不時會看到一對對情侶牽手走過,手捧茶顏悅色,拿著虎頭局的糕點,合影留念。
在這里,有古樸的麻石路、封火墻、小青瓦、木門窗,還有鱗次櫛比的商鋪、現代文創的景觀、眼花繚亂的美食、望不到頭的人潮,歷史的厚重與市井的煙火相互碰撞。
不應是“平行宇宙”
除了長沙的太平老街、成都的寬窄巷子、廣州的永慶坊這種對于老街區的改造外,憑空而建的網紅街更考驗設計者的規劃能力。
無錫的拈花灣景區,可以算作新造網紅街的翹楚。
當人們在拈花灣·禪意小鎮看著熙熙攘攘的游客、人聲鼎沸的小鎮繁華時,很難想象這里繁華景象之前的樣子。
1994年,國家級旅游度假區政策落地不過兩年,無錫市西南端的馬山(靈山小鎮所在地)還是一片荒草叢生之地。
1990年代,造佛像、造廟宇是許多地方發展旅游業的慣常做法。無錫也是如此,造出了由小靈山、祥符禪寺、靈山大佛及分布于其間的其他景點所組成的靈山勝境,一時間游人如織。
現狀是大多數投資者和運營者水平不夠,他們能做的,就是保留一個歷史文化的空殼,按照刻板印象來打造,在內里填充同質化的小商品和餐飲店。
然而,靈山勝境有著許多觀光型旅游景區的通病,游客停留時間短,門票之外人均消費極低,而作為重資產的景區,投資體量大,如何變現盈利成為一個問題。基于市場經濟的考量,著眼于沉浸體驗的拈花灣應運而生。
作為一個宗教文化類主題街區,主打禪境觀光、禪意休閑、禪心度假、禪修康復、禪學培訓等項目,目標群體是略懂佛教文化、急欲洗滌心靈的中產富裕人群,相比其他景區,有著極高標準的酒店、民宿以及各類景觀。
自誕生以來,拈花灣小鎮就因其“禪文化”和沉浸式體驗,多次被評價為“文旅小鎮典范”、無錫“城市客廳”“文化名片”。
但諸多溢美之詞,只代表了拈花灣的繁極一時。
IPG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柏文喜曾說:“拈花灣所謂的成功其實都是表象,最多是設計與建造上的成功。在財務和投資回報上,拈花灣從來都是失敗的。”他認為,拈花灣面臨的最大困境是資產太重和負債過重,導致其運營壓力極大。
據了解,拈花灣的打造曾耗資48.74億元。開業后的兩年,拈花灣曾靠房產銷售回款約5個億,略微緩解了一下當時的現金流壓力。
重資產模式對于投資者來說,終究是風險過高。即便綜合實力如萬達這樣的企業,在現金流吃緊時,也不得不選擇割愛文旅城。
選擇高性價比的“千篇一律”,還是大力砸錢的“標新立異”,這件事沒有正確答案,在不同的時間點上,答案并不相同。
可惜的是,現狀是大多數投資者和運營者水平不夠,他們能做的,就是保留一個歷史文化的空殼,按照刻板印象來打造,在內里填充同質化的小商品和餐飲店。
如果游客只去這個城市的網紅街,某種程度上就是進入了這個城市的平行宇宙,它們與正常市民的生活是割裂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打造一個網紅街區,絕不單單是跟風潮流、刺激游客就行,想讓網紅街長久不衰地活下去,需要培養一種投資者、管理者、商家、游客以及本地市民都能互惠共利的環境。
網紅街從來不應該只存在于懸浮的精修濾鏡中,它應該真正沉淀生活,帶給人們真的美好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