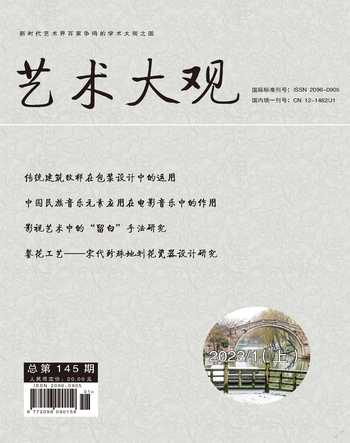任伯年繪畫線條的藝術魅力
溫林霞


摘 要:任伯年是前期海派畫家重要成員之一,在風云變化的清末時期,任伯年的繪畫呈現出不同以往的藝術特色,他用線“緊勁連綿、風趨電疾”,這種“寫”意性不同于傳統文人繪畫的“寫意性”,是在前期海派畫家橐筆為涯的生存之道下,逐漸形成的共有特征。任伯年作為海派巨擘,其繪畫中線條的表現力則更具代表性,是敏銳于時代審美風尚變化的一次主動選擇,是面對悠久傳統和新穎西畫的一次獨特創新,為后世的人物畫家提供了可觀的范本,其繪畫技法方面的革新將中國繪畫的命題——“技與道”的討論推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限于篇幅,本文只淺談任伯年繪畫中線條的藝術魅力,對于任伯年人物畫中技法的研究,將為我們提供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
關鍵詞:任伯年;線條;人物畫
中圖分類號:J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01-00-03
一、任伯年簡介
任伯年(1840-1896),名頤,字小樓,后字伯年,浙江山陰航塢山人,善畫花鳥,尤善寫真。父親任聲鶴是民間畫像師,善畫人物。任伯年在來滬之前主要停留的地方為靠近紹興的蕭山區域,那里是他的出生地,成年后分別在寧波、鎮海、杭州和蘇州待過數年,文人畫和浙派繪畫在這些地域影響較大,這無疑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任伯年的繪畫創作[1]。
二、中國傳統和西方技法的融合
(一)對傳統繪畫中“線”的學習與傳承
在中國繪畫藝術萌芽之初,線條已經作為繪畫的表現形式出現在古代藝術中,到魏晉時期便有了關于“線”的繪畫理論,如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中的“骨法用筆”,強調以筆畫“骨”,勾取物象的輪廓。
明末陳老蓮獨具匠心的線條設計和編排,對海派畫家及任伯年開創自己的風格奠定了基礎。與任伯年交游的畫家是極多的,其中有學識淵博的鄉紳,也有世面開闊的商人,更有同為生存賣畫的畫家。他們或相互學習砥礪,或合作賣畫,線條相比古人沒有了優雅的弧度,追求一種“雅俗共賞”的審美情趣,在繪畫風格上難免有相似的地方。
任伯年的線條早期有著任熊的影子,任熊作為前期海派的領導者,不僅思想獨到而且有過人的技法,從其《自畫像》可以看出,相比之前畫家大多反映文人生活,他用頂天立地的構圖、方折剛勁的線條表達出了畫家自我品格的堅韌,追求俠士風范的灑脫和氣概。任伯年有與之相似的用線作品,如《大士圖》,線條剛勁、頓挫有力,雖不似任熊自畫像那般以濃黑重墨將人物身上的衣紋畫得剛勁無比,此幅人物畫中的筆意卻是相似的,大士懷抱一嬰兒,神情若有所思,將人物的高大和嬰兒的弱小形成了對比[2]。
任薰雖在年齡上長任伯年五歲,但對任的賞識和提點卻是毫不吝嗇的。任薰治學嚴謹,功力深厚,相比于其兄多了一分含蓄和內斂,線條遒勁圓韌,構圖也別出新意,任伯年跟隨仁薰學畫時,多與其合作。仁薰傳世人物作品有《群仙祝壽圖》《瑤池霓裳圖》《麻姑獻壽圖》等。圖1《群仙祝壽圖》與仁氏二兄弟相比,整個畫面的布置是符合視覺舒適感要求的:構圖使用以虛襯實的手法,以流暢的游絲描和釘頭鼠尾描營造出仙界的虛無縹緲,人物的安排高低錯落、組合有主有次,回環曲折的衣紋形成了仙界人物瀟灑活躍的熱鬧氛圍,人物的身體動態相互顧盼,情節更為自然生動,在透視上兼用散點透視和“隔斷”,使得畫面之間的過渡更為自然,觀者的視覺想象延伸至畫外,比仁薰及任熊的圖2《群仙祝壽圖》有過之而無不及[3]。
(二)對西方技法的學習與借鑒
任伯年生活的年代,同上海從小漁村成長為商業繁華的大都市是同步進行的,1840年后,西方的繪畫作品和技法廣泛地傳入中國,如果說從郎士寧開始,中西繪畫有了初步接觸,此時,西方的繪畫技法更為廣泛地傳入中國,開始全面借用西式技法描繪中國的景物和圖像。
沈之瑜在《關于任伯年的新史料》里,指出了任伯年直接受到西洋畫特別是素描的影響。張充仁在《文匯報》著文補充說:“擁據我了解,任伯年的寫生能力很強,是和他曾用3B鉛筆學過素描有關系的,他的鉛筆是從劉德齋處拿來的。當時中國一般人還不知道用鉛筆。他還曾畫過裸體模特兒的寫生。”[4]因此,任伯年線條更加奔放,并且熟練地將西方技法的寫實、明暗運用到繪畫中。
任伯年對西方技法的學習使得他的人物畫相較于之前的人物畫家,在五官和造型上得到突破,他用中國的毛筆借鑒速寫和素描之法,構圖安排上更加輕松,將曾鯨圖3《王時敏像》和圖4《俠名肖像》對比,人物在面部用淡彩皴染,注重虛實變化,增強了體積感,衣紋則用速寫的方式,用大量工細的線條表現人體的轉折結構,并出現并置的雙線,染出凹凸質感,這和速寫有異曲同工之妙。從這幅畫中可以反映出任伯年在前人基礎上的創新和高超的造型能力。
三、任伯年用線的藝術特點
任伯年繪畫藝術中最突出的特征,便是他的意筆用線,即線條的自由寫意性,寫意性是一種作畫的狀態或者方式,要求畫家以一種放松的“虛靜”狀態和簡括對象的方式進行作畫,這相對于西方的科學求真,兩種繪畫從根源上便顯現出“基因性”的不同。任伯年能夠熟練地應用“工寫”技法,以“寫意性”為指導作畫的理念,在面對不同物象時,線條使用方式也不同。
(一)用筆工致的人物畫
任伯年早年跟隨過費丹旭學習工筆仕女畫,因此有許多仕女作品,這批畫幅較小的作品中,侍女形象溫婉,線條凝練,可以看出任伯年對傳統工筆有著多年的學習與研究,又有陳洪綬、華嵒、閔貞之衣缽,因此在用筆工致的人物畫中,用線如行云流水,緊勁連綿、循環超乎,如作品《沈蘆汀讀書圖軸》《葛仲華二十七歲小像》《外祖趙德昌夫婦像》。
明代鄒德中《繪事指蒙》有“描法古今一十八等”之說,清代王瀛將其付諸圖畫,并注明每種描法的要點,又將這十八種描法歸為三類,即游絲描類、柳葉描類、簡筆描類。任伯年的繪畫中多用釘頭鼠尾描,落筆處如鐵釘之頭,線條呈釘頭狀,行筆收筆,一氣拖長,如鼠之尾,頭重尾輕,因此用線輕快,意在筆先。如《蕉蔭納涼圖》,描繪的是吳昌碩的寫真像,五官及身體的塊面轉折處用淡墨染出體積感,配景和衣紋起筆頓筆勾出,即用釘頭鼠尾描,凝練放達,身體輪廓部分則用線平穩流暢,用線清、淡,與衣紋、書、芭蕉形成節奏關系,韻味十足,在畫面安排上將上下兩組繁密的線條區分開來,這種巧思巧用在系列蕉蔭納涼的人物畫中皆有體現,如《大腹納涼圖》畫中線條的應用松弛有度,用線有主有輔,有虛有實,外輪廓結構用線為實,再輔以幾根虛線畫出視覺空間感,再用顏色概括統染,人物左手拿扇屈肘放在書摞上,右手搭在翹起的腿上,線條墨色濃淡相宜,將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現得恰到好處[5]。
(二)用筆放達的人物畫
風俗畫和文人畫是兩種不同市民階層的繪畫,任伯年游走于這兩者之間時,最大限度地用世俗的審美去打破文人畫的局限性,也用文人的情懷去描繪民間世俗之態。
1.民間風俗畫
民間風俗畫主要承襲了陳洪綬的衣缽,風俗畫題材豐富,創作空間自由,如《鐘馗》《麻姑獻壽》《風塵三俠》《群仙祝壽圖》等。《鐘馗》人物形象奇偉,用線方折有力,筆法蒼老潤潔,頗有古人之遺意;《風塵三俠》用筆迅捷,線條自如流暢,將三位歷史人物的俠客風范以極為率意的筆法繪出,抒發了對家國前途命運擔憂的情懷。在以民間為根基的人物畫家中,任伯年無疑是最能代表民間傳統和為民間大眾塑像的畫師之一,徐悲鴻說他用筆進入了“揮寫自如,游行自在”的境界,這樣的“自由”正是由于他深深地扎根于民間傳統,以民間傳統為養分,這才以“十八般”武藝式的線條塑造出喜聞樂見、生動活潑的藝術形象[6]。
2.文人畫
蘇軾“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明確提出自己對繪畫的見解,認為欣賞者在品評畫作時如果只以形似論畫,那真是兒童的見識了,因此可以看出線與所描繪的形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依附關系,線在中國畫中獲得了極大的自由。
任伯年的文人畫中,一方面,傳統用墨及文人畫家題字來表現作品的文質性,另一方面,用民間繪畫空間的廣闊性彌補文人畫的羸弱,線墨結合,激情四溢,使得文人畫增加了視覺圖像的層次。如作品《賈島驢背敲詩圖》系列,寥寥數筆勾勒出人物形態,背景則深淺墨色營造氛圍,以及在設色明凈、構圖新巧的侍女小品畫中,線條收斂含蓄,少了放縱。他多用簡逸放縱的線條,表現出人物的品格之美,如《周閑像》,線條瀟灑利落,猶如高古游絲,人物的性格和身份特征通過用線,一位周游名山大川的文士形象便生動地落于紙面。
四、結束語
著名美術史論家王伯敏認為:“對于任頤個人來說,花鳥畫的成就比較高,但以當時畫壇的情況而言,他的人物畫影響比較大。因為人物畫在清末已經衰微,畫人物的畫家并不多,所以像任伯年在人物畫方面能有那樣的造詣,作為在畫史上的評價,當然首推他的人物畫。” [7]徐悲鴻評價他是“仇十洲后中國畫家第一人”,對他的贊賞不吝溢美之詞。從兩位大師的評價中,一些人僅肯定其在人物方面的創造,一些人則將其視為畫史上開宗立派的重要人物。任伯年是近現代的畫家,對其離世也僅近兩百年,對他在畫史上的貢獻有待我們歷代的后人去評判。
任伯年一生創作了大量的作品,花鳥、人物、山水都能信手拈來,尤其在人物畫史上,主要在繪畫技法和繪畫形式方面做出變革,對現代意筆人物畫有極大的影響。此外,他作為名垂青史的畫家,對自我職業畫家的身份是認同的,將對技法的追求作為其一生的使命。但中國傳統歷來輕技重道,《莊子·天地》:“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認為“道”重于“技”,“技”服從于“道”。明董其昌后如是,他總結性地提出“文人畫”概念,將歷代有名畫家是否歸于文人畫系統做了甄別,對后世中國畫的創作產生了極大影響。因此,任伯年以民間畫師為職業身份的態度和其對技法的不懈追求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道以技顯,技因道進”。任伯年的繪畫線條表現出技法的高超,如果沒有其對“道”的追求,即對傳統的理解和世間百態的觀察,就無法創作出垂范后世的作品,相反如果沒有對“技”也即“線”的錘煉、西方寫實技法的學習借鑒,那他也不可能開創人物畫史上的新篇章!《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故事中,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技”可進“道”,正是庖丁在解牛的過程中,做到了對牛身體構造的了如指掌,從而實現了手起刀落式的精準切割。由此可見,任伯年人物繪畫中“線”的藝術魅力,也體現了“技”與“道”的關系,實現了創作中審美的藝術精神與創作技巧的相統一。
參考文獻:
[1]薛云祥.任伯年繪畫藝術初探[J].藝術教育,2018(13):112-114.
[2]徐發敏.任伯年“寫真”題材創作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19.
[3]王國棟.任伯年肖像畫研究文獻紀年訛誤考辨[J].美術觀察,2021(09):41-47.
[4]張充仁.任伯年繪畫藝術讀畫會[N].文匯報,1961-11-24(04).
[5]滕靜.徐悲鴻為何如此推崇任伯年[J].收藏,2021(02):42-49.
[6]李宗奎.任伯年繪畫的公眾指向性[J].美術大觀,2014(01):40.
[7]李仲芳.任伯年評傳[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