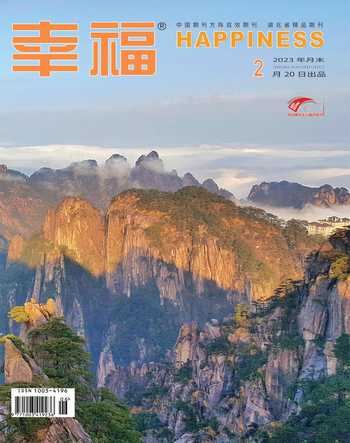捆滿鐵絲的矮松
趙興國

六月的校園,和外面的田野一起,陷入一種難以名狀的安靜。這安靜,在天地間彌散開,似乎在等待著什么,好像燒制瓷器的窯口即將打開,又像是水面上的魚漂,在輕輕地抖動。
校園里,課間的喧鬧,好像被教學樓廳倒計時器上的數字,壓縮到窒息的狀態。偶爾有老師走過,也是急匆匆的腳步,鞋底敲擊地板,發出欻欻的聲響,在空蕩蕩的走廊里回響。田野上,昨天還綠油油的麥子,在暖醺醺的南風面前,只過了一晌午,便黃了麥梢,開關獻城。往日抽水機艱澀的吭哧吭哧,換成一兩聲布谷鳥輕快的叫聲。田間小路上,匆忙的農人,也只有早上過來,小心翼翼地用粗手指剝開麥穗,把麥粒放進嘴里嚼一嚼,然后若有所思地倒背起手,緩步走遠。只剩下風,如海潮般從遙遠的天際,一波一波浩蕩而來,又浩蕩而去。
女人坐在籃球場門口的大理石石球上,好像有一段時間了。我記得我和同事三對三打球的中間,到門口撿出界球的時候,她朝我微笑了一下。我心里雖然有些詫異,可還是禮貌地還以微笑。無意間,我看見風正扯動著她鬢邊的細發,輕輕地抖動。
我帶著淋淋漓漓一身汗水,正要離開球場的時候,那女人起身攔住我。
“你是趙老師吧?我是浩軒的媽媽。”聽女人說出“浩軒”這個名字,我腦際迅疾閃現出一幅畫面來,一個五年級的男學生,翻著白眼,站在一株矮松前。
我一邊慌忙停下來,一邊答應著,大腦也閃電般快速地思索著,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情。同時,我也感覺有一點尷尬。一來是自己一身汗水穿著球服,和教師扣脖嚴領的著裝形象嚴重不符。二來,如果早知道她是有事找我的學生家長,我完全可以暫時不打球,過來處理完她的事,再打不遲。依著我多年的經驗,一丁點兒小事,如果處理不好,學生家長便會糾纏不休,需要耗費很多口舌,更不要說她的孩子在學校打架受委屈受傷了。
“你咋不叫我一聲呢?讓你等我這么長時間,多不好意思啊。”我說。浩軒媽媽說她也沒啥事。浩軒媽媽三十多歲的年紀,鬢角已經有幾根白發,右手食指上纏著白色的醫用膠帶。
當我聽浩軒媽媽說,是因為彭浩軒同學成績下滑,才來學校找我之后,我懸著的一顆心,這才安穩放下。她帶著一臉不自然的笑,和我說了她家的一些情況。她和丈夫在村里經營著不大不小的一家篩網廠,丈夫常年在外跑業務,她在家帶著四五個人守著幾臺機子制作篩網。因為忙,她大部分時間把孩子交給婆婆看管,連吃帶住,上學接送。
“都讓他奶奶慣壞了。上一年級那時候,是我看著他,語文數學還都能考90多分。家里干了篩網,我這一忙,就顧不上他了。前幾天群里發測試成績,我這才知道浩軒的成績這么差。并且,我每次問他有沒有作業,他總說在學校就做完了,還經常連書包也不往回拿。尤其是過年的時候,俺們鄰居家那個上七年級的小偉,總騎著電車過來找他。那個小偉,爹媽離婚了,法院判的小偉跟著他爹,他爹又給他找了一個后媽。這孩子,也抽煙也喝酒,逃學上網……”
我聽浩軒媽媽這樣說著,也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她口中所說的孩子,我平日里見的太多了。我所在的學校,生源大部分來自周圍的農村,能像浩軒媽媽這樣,來學校當面找老師談一下自家孩子的家長,已經是很不錯了。更多的,是家長把孩子往校園一送,萬事大吉。更有甚者,一部分家長認為:孩子學習好了,是自家孩子聰明;孩子成績差了,是老師教得不好。
“趙老師,你多費心,該打就打,該訓就訓,我回家讓他爸爸狠狠地治治他。”
我囑咐她放心,我會在學校盡心管理她的孩子。看著浩軒媽媽遠去的背影,我也回教學樓門廳去簽退,一路走,浩軒媽媽的那句“該打就打”,一直回旋在我耳邊。
“能打嗎?啥時候該打,啥時候不該打呢?”我問我自己。
“該”這個字,大概是所有漢字中,最矛盾的一個字,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界定標準。
浩軒這個學生,我從三年級一直帶過來,相比之下,是很熟悉的。他活潑好動,腦子靈活,成績在班里能排到中游偏上一些。他喜歡讀書,趁我上課不注意,偷偷摸摸地就讀課外書,可是,讀書不細致,囫圇吞棗過眼即忘。這也是他們這個年齡段的孩子的通病。去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在家上了三個月的網課,回來后,我就發現這個孩子有些變化,具體也說不出,直到今年過了年,到了五年級下學期,我才注意到,他幾乎每次都說家庭作業忘了帶。我有心懲治一下,可總想不出好的辦法。
我知道:打,是肯定不行的。
教育局領導、校領導開會,三令五申不允許體罰。各種大小新聞,只要是有學生和老師發生沖突的,無一例外一邊倒地斥責學校老師,口口聲聲地高喊“保護未成年人”。有的老師因此被降職,有的被調離,有的,丟了“飯碗”。就我,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年逾知天命的老老師而言,能保住自己的“飯碗”,也就“阿彌陀佛”了。
我也知道:不管,肯定也是不行的。因為我的身份是教師,職責就是教書育人。
我曾把我的困惑告訴朋友,朋友用輕快的口吻告訴我說:“冷處理唄,又不是你家孩子。你能安全退休就是好事,多大年紀了,還沒活明白嗎?”
我知道朋友的“冷處理”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真的是沒有“活明白”,在我看來,“冷處理”,也是不行的。我總要找一個辦法,“敲打敲打”這個“家伙”。另外還有個原因,那就是這個浩軒,在前些日子,把我氣得夠嗆,好長時間,我心中總有一股怨氣,散不開,咽不下。為此,我還失眠了兩個晚上。
那是一個上午的大課間,我不記得是因為什么事情,正在教學樓的連廊經過,突然,我看到浩軒和另外一個學生,躲在連廊水泥柱子后面,偷偷地往操場上看。在操場上,其他學生都在做課間操。這個浩軒,可也真是淘氣,手把著柱子,也不老實,他左手手指把柱子上的展板框撬起來,撥動著,發出“吧嗒吧嗒”的聲響。
我見他不做課間操,還破壞公物,心里當時也不知道哪兒就來了一股火氣,幾步走過去,大聲呵斥道:“你有病嗎?弄這展板干嗎?你弄壞了咋辦?”
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用牙咬著嘴唇,反問我說:“老師,你咋罵人呢?”
這話一下子把我問愣了,要知道,教師說臟話亂罵人,這頂“帽子”,可是會把人壓趴下的。我說我哪有罵你。浩軒梗著脖頸說:“那我說你有病,你愿意嗎?”他那冰冷且尖銳的口氣,讓我好像受了極大的屈辱一樣無法接受,我突然有上去踹他兩腳的沖動。可是,這個沖動只是在我身體里跳動著胡亂沖撞了幾下,就被我硬生生地壓了下去。我說:“你破壞公物還有理了嗎?到那邊站著去。”
浩軒翻著眼睛看著我,嘴里嘟嘟囔囔地說:“當老師還罵人,還為人師表呢?”然后慢吞吞地邁著腳步,走到樓廳門口的矮松下,扭著身子,極不情愿地站在那兒。而我的胸口,也仿佛被無形的拳頭重重擊打了一下,透不過氣來。
矮松在教學樓門廳前面,大約有兩米高的樣子。起初,我并沒有留意到它,直到那天,我和浩軒同學來到矮松近旁的時候,我突然看到,在矮松身上,捆綁著許多細細的鐵絲,形狀很像一把傘,傘柄是主干,鐵絲是支撐,下端拴住樹干,上端斜斜地捆在矮松散開的枝杈上。我想,這鐵絲肯定是用來修整矮松枝杈的,迫使那些原本朝上生長的,服從鐵絲的拖拽,服從人們的審美意向,而平平地延伸開來,以便于“虬枝婆娑”。我又走近些,用手扶著矮松的枝杈。我看見鐵絲有的已經嵌進樹皮里面,很多地方,已經生了銹。我用手按了按,枝杈硬挺挺的,很是有力,似乎要把鐵絲拽斷。鐵絲呢,盡管銹跡斑斑,也是繃得緊緊的,堅守著自己的職責所在。我漸漸開始平息的心里,忽然想起龔自珍的《病梅館記》來,再看看身邊的浩軒,我竟然一時間有些茫然。
那時候,盡管我有很多話、很多道理要和浩軒講清楚,可因為下一節有課,我只能忍住,讓他回教室上課。上課的時候,我利用學生做練習的間隙,眼睛總是自覺不自覺地瞥向他那里。而他,似乎已經忘了剛才發生的事情,正利用我轉身的空檔,偷偷看抽屜里的課外書。雖然我想借此發一頓脾氣,可是,我還是平心靜氣地把他的課外書拿出來,放在講臺上,并囑咐他,認真完成我布置的練習。
摘自《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