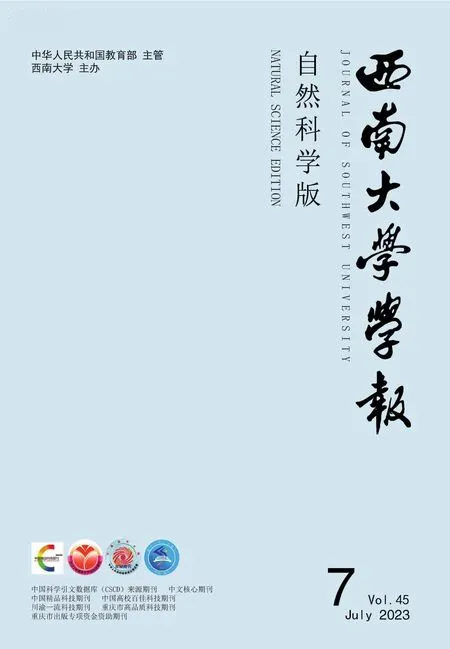城鎮化進程中耕地時空格局演化及其驅動機制研究
——以揚州市為例
禹文東, 吳濤, 羅云建, 李曉明
揚州大學 園藝園林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9
耕地是人類生存的基礎資源, 事關全球的糧食安全, 世界范圍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使得耕地面積發生很大改變[1-4]. 據統計, 1961-2015年, 全球人均耕地減少了37.5%[5]. 同時, 耕地也隨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質量下降, 其面臨的荒漠化、 破碎化、 鹽漬化及邊際化等威脅在不斷加劇, 特別是2000年后, 耕地面積總量、 人均耕地面積減少的國家數逐年增多, 尤其是人口總量較大的諸如印度、 中國、 孟加拉國等發展中國家.
中國的經濟高增長率所帶來的城鎮化進程導致耕地總量不斷減少, 特別是東部地區還受到農業結構調整與生態退耕等因素影響, 多數地方的耕地數量減少的趨勢更加明顯, 而耕地質量也隨之有明顯的下降. 根據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結果顯示, 以2019年底為標準時點, 中國耕地總面積約1.3億hm2, 近10年來耕地迅速減少, 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的糧食安全[6]. 為此, 堅守18億畝的耕地紅線成為國家的既定政策, 耕地保護政策也在逐步轉型, 更加注重耕地在數量、 質量和生態等方面的綜合保護[7].
近年來耕地保護方面的研究較多地聚焦于其數量與質量的時空演化規律與機制, 如不少學者在流域、 區域或省域等宏觀尺度上, 對耕地時空演化特征及其驅動因素進行分析與探討, 這類研究部分是從統計數據的角度來解析耕地變化規律, 或者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對區域內部耕地變化的空間動態性與分異性做進一步梳理和研究, 進而識別耕地變化的驅動因素[8-11]. 如張永生等[12]獲取華北6省(市)的土地數據, 在省域尺度上對2000-2010年耕地的景觀格局進行分析與探討, 梁小麗等[13]揭示廣西區域范圍內一定時段耕地利用形態分異規律并識別其主要的驅動因素, 王雨楓[14]對1990-2020年遼寧省耕地空間分布演化與影響機制做了分析與研究. 此外, 部分學者還以不同地域特有形態的耕地為研究對象, 對其時空演化做了分析與研究. 如選取了云南坡耕地[15]、 原陽縣黃河背河洼地耕地[16]、 江蘇里下河平原耕地[17]、 陜西渭北旱塬區耕地[18]等. 上述研究多數關注于宏觀尺度或者特定類型的耕地資源, 而對我國新時代經濟發展背景下的中小城市的耕地時空演化規律較少涉及.
筆者認為要實現新時代我國經濟的高質量、 可持續發展目標, 中小城市的高質量協同發展是核心, 聚焦長三角地區, 中小城市的高質量、 特色與個性化發展, 是一體化協同發展的關鍵環節和戰略支撐. 江蘇省揚州市作為長三角地區的中等城市(次中心城市)正處于蘇北與蘇南經濟發展的過渡地帶, 在承接大城市產業轉移、 疏解大城市生活壓力、 高效利用耕地、 協調鄉村振興等方面發揮的作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為此, 筆者選取揚州市耕地為研究對象, 運用ArcGIS空間分析與經濟計量分析方法, 通過分析2000-2020年的時空演化規律, 揭示其演化特征, 找出其演化的驅動因素與機制, 以期為同類型的城市耕地高質量使用與管理、 自然資源優化配置、 生態保護和協調發展等提供參考與借鑒.
1 研究區概況
揚州市(32°15′-33°25′N, 119°01′-119°54′E)地處江蘇省中部, 位于長江北岸、 江淮平原南端, 下轄邗江、 廣陵、 江都、 寶應、 高郵和儀征等6個區(縣). 全市總面積6 591.21 km2, 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 揚州市常住人口為455.979 7萬人. 2020年揚州市地區生產總值達到6 048.33億元.
2 數據與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研究以2020年行政區劃為依據, 以揚州市域范圍的6個區(縣)的83個鎮、 鄉和街道為基本單元開展相關研究. 本研究用到的土地數據來自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http: //www.resdc.cn)開發的中國土地利用/土地覆蓋遙感監測數據集(1970年至今), 其空間分辨率為30 m. DEM數據來自地理空間數據云(http: //www.gscloud.cn), 空間分辨率為30 m×30 m. 利用ArcGIS 10.4, 從DEM數據中提取研究區的海拔數據, 并計算得出研究區的坡度數據.
地區生產總值、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第一產業增加值、 第一產業構成、 固定資產投資城鎮人口、 城鎮化率等數據來源于《揚州市統計年鑒》(2000,2005,2010,2015,2020年), 在ArcGIS 10.4中運用表鏈接功能與揚州市鄉鎮邊界矢量文件結合.
2.2 研究方法
2.2.1 耕地的時空變化
1) 耕地凈變化率. 這一指標是用來衡量在某時期內耕地的變化程度, 一般是用一定時期內耕地的凈變化量與初期總量之間的比值來反映. 公式表述如下:
(1)
式中:R為耕地凈變化率;Ua為末期耕地總量, km2,Ub為初期耕地總量, km2.
2) 耕地變化動態度. 本指標主要用來反映耕地在某個時期內的變化情況, 能夠衡量耕地的穩定性, 其值越高則耕地越趨向于不穩定. 公式[19]如下:
(2)
式中:m為耕地變化動態度;T為研究時長, a.
3) 核密度分析. 這個非參數的方法是用來估計概率密度函數, 能夠表征耕地的空間集聚狀態. 一般是將起始耕地信息處理為像元大小300 m的柵格數據, 并將其轉化為點數據, 再進行核密度的分析, 計算公式[20-21]如下:
(3)
式中:fn為耕地地塊分布核密度測算值;k為核密度函數;h為帶寬;n為耕地點數據的數量;x-xi為耕地點x到樣本點xi的間距.
2.2.2 景觀格局指數計算
景觀格局指數是采用定量指標來表征景觀格局的基本信息, 并能反映其結構組成以及空間基本格局特征[22]. 通過對耕地圖斑信息的統計可以獲得耕地數量變化的基本情況, 但其空間變化的特征不能僅通過數量變化來反映, 耕地變化過程會導致景觀形狀復雜、 破碎等一系列威脅耕地質量的問題, 進而影響耕地的功能, 而景觀格局指數則可以測度這些基本特征. 景觀格局指數是景觀格局信息的高度概括, 并通過景觀指標量化表達, 進而呈現出景觀格局及其空間分布狀態, 在耕地時空演化研究中被廣泛使用[23].
借鑒近年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24], 綜合考慮揚州的自然條件與社會經濟發展現狀, 本研究選取了8個主要的景觀指數, 即斑塊數量(NP)、 斑塊密度指數(PD)、 景觀形狀指數(LSI)、 聚類指數(CLUMPY)、 斑塊凝聚度指數(COHESION)、 景觀分割指數(DIVISION)、 聚集指數(AI)以及分離度指數(SPLIT), 通過Fragstats軟件對上述指標數值進行計算分析, 進而研究區域內耕地格局變化與破碎化的情況.
2.2.3 驅動力分析
1) 驅動力影響因子的選取. 耕地的變化是各種驅動力綜合影響、 相互作用的結果, 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發展情況[25-27]. 本研究選取了13個影響耕地變化的因子, 包括地理空間中的6個因子, 即海拔、 坡度、 距水體距離、 距建成區距離、 距市中心距離以及距區縣核心區距離; 經濟因素中的2個因子, 即人口與人口密度; 社會因素中的5個因子, 即人均GDP、 財政收入、 第一產業占比、 第二產業占比以及第三產業占比, 選用增強回歸樹(Boosted Regression Trees, BRT)算法來定量揭示上述13個因子的潛在驅動力對耕地變化的影響.
2) 樣本點的提取. 將各時間段(2000,2005,2010,2015,2020年)的土地利用圖層進行疊加, 把經耕地轉出為其他用地的像元賦值為1, 仍是耕地的地類賦值為0. 采用ArcGIS中創建隨機點的工具模塊, 隨機在耕地轉出及不變的像元中, 分別抽取500個樣本點. 利用ArcGIS的空間統計工具箱中的近鄰分析工具, 計算每個樣本點到水體、 建成區、 市中心、 區縣核心區的歐幾里得距離, 利用空間分析工具箱中的值提取至點工具, 提取每個樣本點的海拔和坡度, 運用標識工具將鄉鎮的經濟社會數據賦予樣本點.
3) 驅動力分析. 本研究選用BRT算法來定量揭示上述影響因子的潛在驅動力對耕地變化的影響. 為獲得可信的分析結果, 需要合理設置5個參數, 即交叉驗證折數、 損失函數形式、 學習速率、 交互深度(又稱樹復雜性)以及重抽樣比例. 在判斷耕地能否轉出的應用實踐中, 采用較為實用的Bernoulli分布方法, 并結合本研究特點將重抽樣品的比例設定為0.5、 交叉驗證的折數設定為10. 其中, 學習速率和交互深度需要根據數據的實際情況進行多次比較來確定, 并需滿足至少1 000個分類樹的要求. 為此, 本研究分別設置學習速率的梯度為0.1,0.05,0.01,0.005, 樹復雜性的梯度為1,2,3,4,5,6,7, 而后通過選取不同的學習速率和交互深度來對模型進行調優. 經過多次調試, 最終確定BRT算法的最優參數組合是學習速率為0.005和交互深度為5.
3 結果與分析
3.1 不同時期耕地整體數量變化與空間特征
3.1.1 耕地總體數量變化特征分析
揚州的耕地面積在2000-2020年期間有持續下降的趨勢, 總面積減少了約4.45萬hm2(表1), 全市人口在這一時期變化幅度較小, 相對2000年, 2020年的戶籍人口有小幅度下降, 耕地的減少速度大于戶籍人口減少速度, 這也使得全市人均耕地面積21年間下降了約8%.這種變化對農業生產穩定性造成一定威脅. 由于林地、 草地、 水體、 未利用地等變化幅度較小, 可以推斷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城鎮發展、 農村居民點及區域性設施等建設用地的增加與擴張. 此外, 2010年以來, 因江蘇省城鄉“增減掛鉤”、 集約用地等政策的實施, 對全市耕地面積的快速縮減有較好的抑制作用.

表1 2000-2020年5個時期揚州市各地類面積及占比情況
從5個時期土地利用變化的空間分布(圖1)來看, 揚州的6個區縣(市)的耕地面積均出現不同程度減少, 其中高郵市和江都區的耕地面積減少值得關注, 高郵市2000-2020年耕地減少面積高達9 030 hm2, 占揚州市耕地減少面積的20.23%, 這同高郵的快速城鎮化有關, 而江都區的耕地也減少了8 972 hm2, 經過調查這些減少的耕地多是城區周邊及近郊較為優質的耕地, 而村莊布局優化、 莊臺合并、 農用地內部調整等往往是耕地增加的主要原因, 這也真實反映了揚州減少的耕地多為高質量農田, 而增加的往往是莊臺復墾地或者養殖場整治地等, 其質量優劣不一.

審圖號為: GS(2016)2893號, 底圖無修改.
3.1.2 耕地凈變化率特征
由圖2可以看出, 揚州在2000-2005年及2015-2020年2個時段耕地變化具有中部減少而東西部增加的特點; 在2005-2010年時段耕地則呈現凈流失現象, 很多區域耕地的凈流失率超過1%, 僅有寶應縣的2個鄉鎮及廣陵區的1個鄉有較大幅度的增加, 其他的基本都處于流失狀態, 2010-2015年時段揚州的耕地凈流失區域有較大幅度縮小, 甚至有些區域耕地面積還略有增加, 但整體來看, 耕地仍然呈現凈流失之勢. 總之, 近21年來揚州耕地整體呈現凈流失狀態, 流失面積持續擴大, 以揚州市區及3個區縣周邊鄉鎮的耕地流失較為嚴重, 可以看出快速城鎮化帶來的城市擴張是揚州市耕地流失的主要原因.

審圖號為: GS(2016)2893號, 底圖無修改.
3.1.3 耕地變化動態度分析
從圖3可以看出, 2000-2020年時段耕地變化動態度超過6%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揚州主城區, 其他多數區域的耕地變化動態度多停留在2%以內, 揚州市的耕地變化在2005-2010年時段最為突出, 主要體現在儀征市區南部區域到邗江區、 廣陵區及江都區的南部區域, 其耕地變化動態度都超過6%, 局部甚至大于8%, 另外在高郵市區和寶應縣城周邊的耕地也有較大幅度的變化. 2010-2015年整個揚州市的耕地變化動態度絕大多數都保持在2%以內, 2015-2020年耕地變化動態度變化較大的區域一處集中在高郵市區周邊, 另一處則是江都區和廣陵區融合發展的區域, 這一時段恰好是江廣融合發展的時期, 耕地變化十分明顯. 總體來說, 揚州耕地變化動態度在2000-2020年時段基本處于中等變化幅度, 全市耕地資源的穩定性有一定幅度下降, 位于南部的揚州主城區及儀征市的耕地動態變化度相對較大, 而相應時期的耕地凈變化率波動特征與之基本對應.

審圖號為: GS(2016)2893號, 底圖無修改.
3.2 耕地空間集聚分析
應用核密度分析對揚州耕地的空間集聚狀況進行分析研究, 對其核密度值(帶寬h=5 325 m)進行計算分析. 該值可以反映耕地的空間聚集或離散的狀況, 值越小則耕地越離散, 反之則越聚集. 結果表明, 揚州市耕地核密度值范圍為0~1 111 點/km2(圖4), 依據自然斷點法可將核密度值劃分為7個等級: 極低密度區(0~135 點/km2)、 低密度區(136~362 點/km2) 、 中低密度區(363~566 點/km2)、 中密度區(567~736 點/km2)、 中高密度區(737~867 點/km2)、 高密度區(868~980 點/km2)、 極高密度區(981~1 111 點/km2). 從圖4可以看出, 揚州市耕地的空間分布在不同區域的差異較為顯著, 中西部湖泊較多, 邵伯湖、 高郵湖、 寶應湖分布在揚州的中西部邊界位置, 東北角(即寶應縣東北區域)河流湖泊分布也較多, 因此, 耕地核密度極低的區域主要分布在這些位置. 另外通過5個時期的耕地核密度圖分析, 可以發現揚州主城區的耕地核密度極低的區域在持續擴大, 西部(儀征和邗江區域)的高密度區和極高密度區在逐步變小, 出現了破碎化的趨勢. 中東部地區(高郵和江都的北部區域)耕地在初期以極高密度區域為主, 連片整體度較好, 但在2010,2015,2020年時間節點, 耕地極高密度區的范圍在持續變小, 在空間上也出現擴散的態勢, 而中高、 中密度區范圍也在持續擴張. 這進一步顯示揚州耕地的空間核密度首先是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和限制, 其次城市擴張、 工業發展及農業產業結構優化等因素對其影響也較為顯著.

審圖號為: GS(2016)2893號, 底圖無修改, 單位: 點/km2.
3.3 耕地景觀格局變化分析
如表2所示, 揚州耕地在2000-2020年時段破碎化程度在持續加劇, 斑塊數量(NP)在2000-2020年共增加了42個, 斑塊密度指數(PD)在2005-2010年從0.02水平上升至0.03水平后趨于穩定. 景觀形狀指數(LSI)則表現出持續增大的態勢, 揭示出耕地斑塊的形狀復雜化與不規則化. 占用耕地并使得原有圖斑割裂化, 進而連通性降低, 使得耕地斑塊的平均面積進一步減少, 這些成為揚州耕地破碎化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 景觀形狀指數(LSI)在2010年后的變化逐步趨緩, 可能原因是此后的各項保護耕地的舉措發揮效力, 2010年后的時段內揚州耕地保護意識持續加強, 無序占用耕地的情況變少, 注重耕地的整體連片性, 一定程度上優化了耕地的景觀格局. 景觀分割指數(DIVISION)從0.81增加至0.84, 聚類指數(CLUMPY)、 聚集指數(AI)與斑塊凝聚度指數(COHESION)的值均在持續減少, 而分離度指數(SPLIT)值則從5.32%增至6.31%, 這些變化都表明耕地斑塊出現了離散的態勢, 耕地的破碎化程度在加大. 總體來說, 揚州耕地的空間分布呈現集聚的狀態, 斑塊的凝聚度也較好, 但隨著城市的加速發展, 耕地數量持續減少, 其空間集聚程度也在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受到削弱.

表2 揚州市2000-2020年耕地景觀格變化指數表
3.4 驅動力分析
自然、 經濟和社會等因素對耕地變化有一定的影響, 而各因素之間既相互關聯又相互限制, 其綜合的作用和影響改變了土地使用狀況, 進而對耕地數量與質量也產生了影響[28]. 選取揚州耕地的4個時段(2000-2020年的每5年), 采用BRT方法分別對其時空演化的驅動力進行分析與研究. 結果表明, 選擇的13個因子可以較好地闡明揚州耕地時空演化的主要原因, 其闡述力分別達到73%,78%,79%和76%, 訓練數據和檢驗數據的AUC值常用作模型的評價標準, 取值范圍為0.5~1, 值越大則檢測方法真實性越高, 本研究均在0.85以上, 對揚州耕地的轉出能作出較好的闡述.
地理空間的6個因子對耕地時空變化的影響最大, 其在4個時段的相對影響分別為84%,77%,75% 和72%, 呈現出減小的趨勢(圖5).

圖5 2000-2020年揚州市耕地轉出驅動力的相對影響
在這些地理空間因子中, 影響最小的是海拔(2%~4%). 2005-2010年, 海拔增加時有部分土地轉化為耕地, 但海拔10 m以上的土地沒有顯著的改變, 其他的時段海拔對耕地轉化的影響不顯著(圖6); 距水體距離這一因子對耕地轉化的影響范圍為8%~39%, 其對2000-2005年時段的耕地轉化影響較為明顯, 距離水體越近的土地轉化成耕地的可能性越大, 而在其他時段這種影響較小; 距市中心距離和距建成區距離這兩個因子的相對影響表現出先增后減的趨勢, 前者從2000-2005年時段的13%增大到2005-2010年時段的21%, 然后又減至2010-2015年時段的10%, 后者從2000-2005年時段的11%增大到2005-2010年時段的14%, 然后又減至2010-2015年時段的11%. 這些變化表明兩個因子對耕地轉化有明顯的影響, 即越靠近市中心和建設用地的耕地轉變成建設用地的可能性越大(圖6); 距區縣核心區距離的相對影響隨著4個時段的推移逐步變大, 分別為16%,26%,32%,31%, 其中2010-2015年時段影響最大, 這一因子對耕地變化的影響結果與距市中心距離和距建成區距離兩個因子的影響作用類似.
關于經濟的影響, 2015-2020年時段比2000-2005年時段顯著增加了9%, 相較于地理空間而言, 其影響的幅度相對較小. 第一產業占比和第二產業占比這兩個因子在整個經濟因子中的影響幅度最大(2%~6%), 其他因子的影響幅度相對較低(2%~5%). 在2000-2005年時段, 財政收入增加使得其他地類向耕地轉化, 但在2005-2010年的時段耕地卻在減少, 其他兩個時段的影響則相對較小; 人均GDP對耕地變化也有一定的影響, 2000-2005年時段人均GDP增加促進耕地增多, 2000-2005年時段反之. 2005-2010年時段第一產業占比增加對耕地增加有較為明顯的促進作用, 但其他時段這一影響卻很小; 2005-2010年時段的第二產業占比增加對耕地減少的影響作用較大; 第三產業占比小于20%時, 對耕地變化影響不明顯. 占比在20%~40%之間時, 即在2000-2015年間對耕地增加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而在2015-2020年卻加速了耕地的流失. 當第三產業占比超過40%時, 對耕地增加總體呈現出顯著的抑制作用.
相對于地理空間和經濟因素而言, 社會因子的影響最小, 對耕地影響表現出先增后減的趨勢, 由4%(2000-2005年時段)增加到8%(2010-2015年時段), 隨后又降低到7%(2015-2020年時段). 在整個時段內人口數量及人口密度兩個因子對耕地變化的影響起到先促進后抑制的效果.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論
本研究對不同時期的揚州耕地變化情況進行分析與研究, 在宏觀層面揭示了耕地時空演化的基本特征, 并采用BRT算法對耕地變化的驅動機制做了定量研究. 結果顯示, 2000-2020年時段, 揚州耕地數量呈現逐步減少的態勢, 21年間共減少44 523.81 hm2, 而減少的耕地多數是轉成建設用地, 其次是林地和水體[29]. 一般而言, 耕地空間格局多數情況下取決于地理空間因子, 而控制著耕地轉化的數量、 時空演變的方向與速度的因子往往是社會和經濟因子.
揚州耕地面積自2000年以來大幅減少, 其主要受地理空間因子的影響. 這些因子包括距水體距離、 距建成區距離、 距市中心距離以及距區縣核心區距離等. 而社會經濟因子, 諸如人均GDP、 人口及財政收入等對耕地面積也有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影響. 耕地與人類的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 其受不同地理空間的作用和影響較大, 故而各類區域耕地變化的驅動力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差異. 如潘佩佩等[30]認為1985-2015年期間太湖流域的經濟發展區建設用地擴張與耕地的減少具有空間對應的關系, 經濟發展導致的建設占用則是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 而周翔等[31]認為江蘇蘇錫常區域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地理空間因子, 如距中心城區距離、 鄰域效應以及交通可達性等.
目前對耕地景觀格局特征識別是耕地質量評價的主要依據. 空間動態性及時空轉移等是耕地資源多樣演化的基本特征. 隨著人類社會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耕地與其他地類的轉化越發變得頻繁而復雜[32], 僅僅依賴簡單的數量統計或者單一的質量監測, 難以與實際耕地變化情況相吻合[33]. 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耕地破碎化的問題, 不僅影響規模化農業發展, 也難以有效發揮耕地的生態及生產功能. 蔡漢等[34]以江蘇揚州的耕地景觀為例, 通過對景觀安全指數的構建與研究, 分析出快速城鎮化地區耕地景觀生態安全格局時空演變特征及其驅動機制和空間差異. 本研究選取了8個景觀指數來分析與研究揚州耕地的破碎化程度及特征, 為更好開展揚州的耕地保護提供借鑒.
隨著經濟及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 揚州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在增加, 同時還要面臨生態環境保護的壓力, 這對相關的主管部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要能夠應用經濟、 社會或者法律、 技術等手段與方法, 提升耕地質量, 優化耕地空間布局, 有效落實耕地保護政策, 對“三條紅線”, 即永久基本農田線、 生態保護線、 城鎮開發邊界線做好科學劃定, 進而建立長效的耕地保護機制, 強化資源集約利用, 促進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協同發展[13]. 此外, 采用產權流轉、 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等方式與方法對土地利用加以調控, 對當前鄉村振興實踐具有現實意義. 本研究從耕地時空演化的視角分析研究了揚州耕地變化過程及其影響因素, 對其具體的驅動力進行分析與探討, 未來將進一步對耕地質量、 連片集中度、 規模效益、 生態投入與收益等方面做分析與研究[35-37], 為此類中小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下形勢如何進行耕地資源的有效利用與路徑調控提供理論依據.
4.2 結論
2000-2020年間, 揚州地區的耕地凈流失面積逐漸增加, 主要發生在揚州市區和3個區縣的周邊鄉鎮. 建設活動是導致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在揚州市主城區和其縣(市)城區周邊. 這種占用行為導致耕地連片性和整體性不斷受損, 使耕地的破碎化程度不斷加劇. 分析數據表明, 揚州市的土地整治、 耕地保護初見成效, 主要表現在耕地斑塊的破碎化趨勢進一步趨向緩慢, 聚類指數、 聚集指數與斑塊凝聚度指數等3個指數的數值變化幅度也在不斷變小. 經BRT算法分析表明, 地理空間和社會經濟因素共同作用呈現出揚州耕地時空演化特征結果. 在自然因子, 如海拔、 水體等條件的限定與影響下, 道路交通、 距建成區距離、 人口以及人均GDP等地理空間和經濟社會因子也驅動著耕地的時空演化. 在新時代高質量經濟發展形勢下, 揚州要轉變城鎮發展理念, 工業及城市擴展需要由外延擴張式轉變為內涵挖潛式, 減少或避免對高質量耕地的占用, 并進一步探索基于區域差異化的耕地質量提升與保護的相關策略, 建立起切實可行的耕地生態補償機制[38], 為促進同類型城市的自然資源優化配置、 生態保護以及耕地高質量使用與管理等方面提供參考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