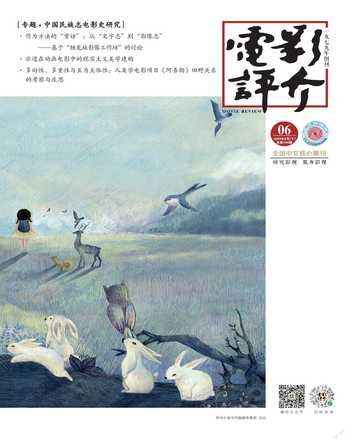《都市風光》:走向三十年代高峰的探索之作
王海洲 丁明

袁牧之編導的處女作《都市風光》(1935)被時人以“大膽嘗試”[1]“噱頭頗多”[2]稱奇,但該片始終“沒有得到普通觀眾的理解”[3],以致上映后“營業上不能賣錢”[4]。此后,復雜的政治語境導致《都市風光》又被影史一再擱置,致使該片成為浩瀚影視的浮光掠影。近年來,該片由于其樂劇的開拓形式以及西洋鏡的敘事機制被部分研究者影史淘金,認為其是“三十年代中國電影現代性的杰出代表”[5],甚至“包含諸多虛擬現實的特質”[6]。事實上,該片確實在表層形式上多有創新與開拓:在該片中,不僅能夠感受到跨時代的全聲實驗,也能體會到創作者寫實與寫意兼具的創作主張以及延續古典并實現現代表達的敘事策略。在形式之外,袁牧之亦借助這些開拓性的語言闡述生命的感悟與時代的感言,使人“如警鐘頻敲,發人深省”[7]。總而言之,《都市風光》“和以前所聽見所看見的中國影片里的大不同了,甚而和外國片子里的也大不相同”[8],可謂中國電影走向三十年代高峰時期的嘗試之作。
一、寫實與寫意的交織互補
經歷了“五四”的思想啟蒙與文化革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審美觀念趨于多元:部分文人試圖以西式的知識架構與話語體系建立理性認知與文化秩序;部分文人保留著民族文化的自信,在復雜的價值危機中謀求文化復振的可能和出路。盡管兩者顯得分裂且抵牾,但同為“五四”啟蒙后寶貴的精神遺產,兩者皆是民族危機時刻文人的理性激蕩與精神重建,集中體現出他們對國族衰弱的傷痛以及對復興中國路徑的探尋。在此種文化風氣之下,有識之士思考文化革新的道路與方向,更是積極探索文明戲、電影等新興藝術形式的審美追求。其中,作為西學東漸后產生的近代詞——“寫實”便在這一階段被廣泛運用,甚至成為“文藝理論中的一個關鍵詞”[9]。
寫實強調精準表現客觀物象,重視“物質現實復原”。與之相對的寫意則是一種“善能借對象抒發熱烈的情感和幻想”[10]的創作思路,偏重于想象性與精神性。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不乏有創作者/理論家將其介入戲劇與電影創作中。其中,“國劇運動”旗手余上沅認為:“我們建設國劇要在‘寫意的和‘寫實的兩峰間,架起一座橋梁。”[11]這種跳脫二元對立的羈絆,試圖重建中國新型藝術創作局面的美學認識較具時代意味。不僅是戲劇,一部分電影人在這一階段同樣有“寫實”“寫意”的補足傾向,譬如費穆便認為“不是說電影可以任意地,或直接地表現一切。在相當的限度內,它也應該用含蓄的迂回的手法”[12],這也被梅蘭芳看作是“在寫實與寫意之間別創一種風格”[13]。事實上,這些創作觀點與藝術認知具有探索意義,它們同樣與20世紀30年代的影/戲創作高峰相互關聯。
創作于三十年代的《都市風光》便是以寫實與寫意交織、互補的藝術實踐,展現出袁牧之的藝術探索與創新之路。整體而言,《都市風光》多以實景實拍的方式描摹火車站的迎來送往以及上海的都市風光,更展現出三十年代中國社會的風情面貌以及現實弊病,可謂社會現實的面面觀。但在寫實之余,整部影片借助寫意的手段豐富影片的表達,使之在兩者之間來回穿梭、游動自如,而這種運用方式在該片的第一個鏡頭中便初露崢嶸。在電影開端,導演以一個搖鏡頭,自下而上地展現了一場“鏡花水月”——起幅中,波光粼粼的水面倒影著“都市風光”的燈牌;落幅中,真實環境中的“都市風光”燈牌漸顯,導演又將鏡頭向前一推,聚焦于這四字之上。這種寫實與寫意融合的方式巧妙地表達了水面/鏡像不僅是現實世界的一抹倒影,更是現實存在的一種復現。這一方式不僅關乎影片的敘事目的,也是袁牧之本人影像創作觀的寫照。
在進入幻境之初,袁牧之拼貼式地展現出大上海形形色色的廣告牌,緊接著是都市的典型建筑、燈紅酒綠的場所以及人群與煙花等絢麗畫面,這些畫面跟著賀綠汀制作的音樂節奏而疊化、變幻、流轉,形成一段巧妙的都市交響樂。可以說,真實的場景與蒙太奇方法的拼貼使畫面在寫實與寫意中自如游走,猶如萬花筒一般,給予觀眾奇幻的心理暗示與想象空間。有趣的是,這一段落也在其后編導的《馬路天使》中被復用,可見袁牧之十分得意于這種拼貼式的藝術效果。此后,整部影片可以說在寫實與寫意間切換自如。整部影片的空間趨于寫實,尤其是火車站人來人往、上海都市風光等場面,整體上更是以寫實的手法加以描摹,展現出三十年代大上海的浮華。
但在寫實之外,袁牧之也尋求一種詩意化的表達,譬如李夢華看到銀行招貼廣告時對于汽車的幻想、寫作時抱著存錢罐對于愛情的幻想以及小云對于身穿華服的幻想、對父親小店廣告的幻想等。此外,祿神與裸女、垃圾與李夢華、狗與秘書、洋娃娃與小云等內容的組接同樣頗具寫意色彩,它們都反射出陷入消費主義泥潭的個體/社會以及異化、吊詭的時代亂象,體現出袁牧之豐富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可以說,袁牧之借助寫實與寫意的融合與互補,將高度個人化、主觀化的表達以及濃郁的隱喻性語言,與現實的場景與時代的癥候和諧地交織于一體,共同打造出審美現代化的追求,而這也在影片《馬路天使》中得到承襲與發展。
二、造境與破境的全聲實驗
在電影的聲音創作尚不完善的三十年代中期,袁牧之將《都市風光》作為全聲實驗加以創作完成,這亦是該作不可忽視的價值所在。袁牧之在文章中談道:“在蠟盤替代聲帶發聲的中國有聲電影草創時代要談聲音藝術是不可能的,就連最近的過去的,僅把無聲片中的字幕改收了聲帶的幼稚時期,對于聲影藝術的運用是還沒有達到一個成熟的階段”[14]。誠然,“收音機械的不完備,專門的音樂人才的缺乏,經濟的限制”[15]等因素都導致這一時期的中國有聲電影發展緩慢,而袁牧之的大膽探索與嘗試,使中國電影走向漸入佳境的全聲時代。有趣的是,這些實驗性的聽覺元素完成造境/破境的審美想象,供觀眾自然融入/超脫于外。
所謂造境,便是借助藝術形式打造“‘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天人合一的意境”[16],讓觀眾如臨其境。值得言說的是,創作者追求的影像之境未必是自然的、現實的,抑或是超越的、想象的,《都市風光》便更傾向于后者:袁牧之以多元的視聽元素織構想象空間,供觀眾進入其中。其中,聲音創作更是可圈可點。由趙元任作曲、孫師毅作詞的主題曲《西洋鏡歌》,在該片中由袁牧之扮演的西洋鏡師唱出,該曲由三組首尾相連的句式構成,一詠三嘆地表現出都市繁華表象后的荒涼與衰敗。此外,回環往復的曲調以及鬼魅的表演方式能夠讓人產生“請君入甕”的聯想,使觀眾與片中人物一同進入創作者構造的幻境之中。不僅是主題曲,由賀綠汀傾力打造的音樂元素同樣有著造境的效果,尤其是片頭的“都市交響曲”,更是讓觀眾不自覺地陷入想象的天地。
在造境之余,賀綠汀打造的音樂元素也有著較強的形式感與表現力,具有破境的藝術效果。所謂破境,便是以反常規、反理性的創作形式讓觀眾意識到影像世界與現實之間的邊界,從而超脫于外進行審美想象。在影片伊始,一段以鼓聲為主的、富有節奏感的音樂先入為主,四位主人公配合著音樂的節奏與旋律互相攙扶、左右張望,等待著前往上海的列車。賀綠汀在文章中談道:“中國過去的影片,從來沒有用音樂來描寫劇中人的動作,心理變化以及劇的場面的移換。”[17]這一設置巧妙地外化了人物的心理狀態,服務于角色的塑造與完善。更重要的是,伴隨著音樂的節奏,人物的表演和走位極具舞臺表現力,具有“非現實”“內心化”的整體感觀,而這也使觀眾意識到影像與現實的間離。值得言說的是,這種形式也恰與影片滑稽的內容與幻境的敘事相自洽。
不僅于此,該片的聲音元素具有反常規、反敘事的特征,不斷深化破境的藝術氛圍。其中,賣貨郎叫賣的橋段尤其值得言說,在上海街頭,兩位賣貨的青年雙手翻動著手里的貨物,有節奏的以“哇啦哇啦哇,哇啦哇啦哇”聲代替叫賣。這一富有節奏的叫賣聲與樂隊演奏的音樂配合在一起,極具戲劇效果。但隨著鏡頭的上搖,樂隊演奏也如同戲曲場面一般被展現出來,這種反常規的電影敘事加深了破境的氛圍,使觀眾具有“臺上—臺下”的觀影感受。不同于戲劇的是,當切到父女兩人離開的畫面,“哇啦哇啦哇”等擬聲元素以及樂隊的演繹依舊回蕩,這種聲畫錯位的運用不僅富有喜劇性色彩,更是無限放大了異化的社會現實。值得言說的是,“哇啦哇啦哇”“略略略略略”等擬聲詞在影片中多次代替對白出現,這些音調起伏、高低不同的啞劇式演繹,讓影片區別于現實空間的同時更富表現性底色。可見,《都市空間》確實不負“中國第一樂劇”[18]的美譽。
三、延續與創變的幻境敘事
不僅是視聽的塑造,影片的敘事策略也具有創新意味——它既是幻鏡敘事的延續,又具有后現代意識的影子。在影片中,四位主人公從起初醉心于繁華上海的迷夢,到后來陷入徘徊與掙扎,與該片的主體部分——“西洋鏡”中的幻境敘事有著直接的聯系,這一幻境“很技巧的像照妖鏡一樣的,將現社會都市的形相徹底的和盤托出,籍可喚醒醉心都市人士的迷夢。”[19]《都市風光》中的四位主人公在等候前往上海列車的間隙,通過西洋鏡進入幻境之中。在幻境里,他們從流民搖身一變,轉而成為繁華上海中窘迫的市民階層:窮書生李夢華盡管外表光鮮,但卻囊中羞澀;小當鋪股東與妻子也為生計操碎了心;他們的女兒張小云愛慕虛榮,周旋于男友李夢華與茶葉販王俊三之間。隨著故事的進展,李夢華因失去愛情而欲要自盡,小云父子也在發現王俊三逃跑后追至花車站,他們于上海發財的美夢終成泡影。有的研究者順著這一敘事策略的脈絡,挖掘出其延續了傳奇小說《枕中記》的敘事傳統[20];有的研究者深度探索了這一敘事策略的“形而上‘夾層”[21],認為其是裹挾著都市異化的寓言。誠然如此,這種幻鏡敘事的策略與中國古典敘事的文脈休戚相關,更是被覆上洞見人生的深沉寓意。
事實上,這一幻境敘事暗合了中國古代“人生如夢”的觀念與認識,這一觀念能夠追溯到莊子的《齊物論》,可謂源遠流長。在《齊物論》中有“夢之中有占其夢焉,覺而后知其夢也”[22]的認識。而后,該篇中又以莊周夢蝶的寓言結尾,在這則寓言中,莊周醒來后分辨不清是自己做夢化為蝴蝶,還是蝴蝶做夢成為莊周,人生與夢境之間的界限被其徹底消解。換言之,莊子將人生看作是虛幻迷離的一場大夢。在古代的《列子》一書中,同樣記載著大量關于人生與夢境的討論;在《周穆王》一篇中有周穆王夢游化人之宮的經歷;《黃帝》一篇中有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的歷程,類似夢中神游的故事不斷復現。傳入中國的佛教更是隨處可見“人生如夢”的論斷——鳩摩羅什所譯的《維摩詰所說經》中有“是身如夢,為虛妄見”的認識;禪宗素來重視的《金剛經》更是直接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為要義,闡釋著有色世界的夢幻與虛空。
在道禪哲學的雙重影響下,“人生如夢”的觀念深入人心,更催生出無數與之相關的幻境敘事文本。早在南北朝時期,劉義慶編纂的志怪小說集《幽明錄》中便有《焦湖廟祝》的故事。故事講述了一個縣民在焦湖廟巫師的引導之下,借助枕仙于夢中發跡,醒來方知是大夢一場的故事。到了唐朝,幻境敘事在傳奇中司空見慣,比較典型的當屬《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櫻桃青衣》等。其中,沈既濟創作的《枕中記》講述了盧生在道士呂翁的幫助下進入夢境,經歷了榮華富貴的一生。醒來后,他們所在店鋪的店主蒸上的黃粱飯還未熟透。這一場夢境以黃粱為比照,從黃粱開蒸伊始,以黃粱未熟而終,展現出人生一夢的短暫與虛浮。《都市風光》與之極其相似,該片以列車未進站伊始,以列車開出站告終,借用了幻鏡敘事的框架。此外,元雜劇中的《邯鄲道省悟黃粱夢》、明清時期湯顯祖的《邯鄲記》、蘇無俊的《呂真人黃粱夢境記》、蒲松齡的《續黃粱》都是幻鏡敘事的延續和再造。值得言說的是,《續黃粱》的故事并非借幻境展現創作者嗟嘆如夢人生的虛無,而是帶有幾分諷刺現實世界的味道。
盡管《都市風光》接續了這一古典敘事的策略,但又在這一基礎上加以創變,顯得頗為有趣。袁牧之一改前人常用的“枕頭”這一幻境媒介,轉而以更具視聽張力的“西洋鏡”為介質,從而實現了以視聽為主體的致幻方式。為了讓觀眾更加明確影片即將進入幻境敘事之內,袁牧之切入了一個由手繪的漫畫形象與人物照片拼貼而成的二維畫面,這個二維畫面作為人物進入角色的異質空間,成為通往幻境的通道,這一構思亦十分具有想象力與創造性。值得言說的是,將二維圖像運用到電影中的情形在幻境中頗為常見,這些畫面讓觀眾產生了游離于現實的觀感,并反復揭示著這本是一場幻覺的實質,頗具游戲感與后現代意味。
除此之外,袁牧之還將卡通畫面有機地融入幻境敘事之中。這個在萬氏兄弟看來猶如“當頭刀劈”[23]的新型嘗試,涵蓋了“戲中戲”影像的雙層寓言。在幻境中,李夢華與小云到影院看電影,動畫電影的內容完美地扣合了幻境中發生的一切:形似米老鼠的主人公帶著禮物到女友家拜訪,狼先生(女友的父親)在家門口上下打量著主人公,并十分輕蔑地用手杖敲了他的頭。收到主人公禮物的貓小姐與其擁吻在一起,看到這一切的豬母親氣得滿頭大汗、肚子猛脹。這一段擬人化的動畫在形象設計上盡管顯得夸張與變形,但卻與李夢華與小云及其父母的處境相吻合——不僅以動畫的形式夸張地演繹出拜訪的經過,更以動畫的形象暗合了人物的特征。正因如此,盡管后景中的觀眾捧腹大笑,但李夢華和小云卻是尷尬對視,兩相對比同樣饒有趣味。必須說明的是,這一場“戲中戲”不僅增添了本片的趣味性價值,也玩味地揭示出幻境與現實之間存在觀照的關系。
四、循環與復沓的時空意識
時間與空間不僅作為電影敘事的坐標,更顯現著導演的風格與觀念、作品的價值與訴求,而《都市風光》正是借此實現了探索與創新。事實上,《都市風光》的時空建構整體呈現出無往不復的流動傾向,這也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古典敘事觀念休戚相關。《周易·泰卦第十一》有“象曰:‘無往不復”的認識,也就是說,事物的運動是循環反復的;《周易·彖傳》亦有“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的觀念,也就是說周而復始的生命循環便是天地的心;老子認為“天地周行而不殆”,生命更是一個周行不止的存在;莊子亦有“始卒若環”的時空認識;中國的佛學亦對生命的輪回有著豐富的闡釋與深刻的理解。總而言之,隨著多元的思考與豐富的想象,無往不復的觀念沉淀“成為一個普遍的文化認知”[24],影響著中國傳統藝術以及古典敘事創作,更成為“一種理想的作品結構方式”[25]。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便流露出無往不復的時空意識,尤其是《镕裁》《章句》《附會》等篇章中提出的“首尾圓合”“首尾議題”“首尾相援”“首尾周密”等觀念便顯現出其對這一意識的認同。《西游記》便是“開頭以天地之數起,結尾以經藏之數終,左右回環,前伏后應”[26]的典型。除此之外,《紅樓夢》中第一回便提及空空道人路經青埂峰偶遇大石的經歷,而小說又以其再過青埂峰又見大石為結尾,可謂時空往復、互為呼應。在一些學者看來:“中國歷代敘事文本都以千姿百態的審美創造力,畫著一個歷久常新的輝煌的‘圓。”[27]
《都市風光》正是承襲了古典敘事中無往不復的時空意識,該片開頭結尾以視聽互補的方式達成鮮明的呼應之感。在電影開端的演員表字幕結束后,鏡頭起幅對準新村通往上海的標牌,而借助移鏡頭畫面也落在四個主人公身上——他們用滑稽的行徑展現出急于離開破產的鄉村、迫切前往繁華上海的愿望。隨著袁牧之扮演的西洋鏡師鬼魅一笑,一場“請君入戲”的戲碼即將拉開,而電影的主題曲《西洋鏡歌》也被叫賣式地演繹出來。影片結尾則對這場精心營造的開場以完美“回應”:隨著鈴聲響起,這首《西洋鏡歌》再次唱響,那塊由新村通往上海的標牌亦隨鏡頭移動展現出來。盡管前后時空相互連接,但四人經歷“黃粱一夢”之后,一改對上海的盼望而陷入面對來往車輛的徘徊與擺蕩之中。總而言之,該片的開頭結尾時空相連、互為呼應,繼而構成了一個無往不復的循環。
不僅如此,創作者反復使用同樣的元素,加強了影片周而復始的時空感觀,譬如開端與結尾分別出現了眼部開合的特寫。這一內容成為進出幻境的敘事機制:它于“西洋鏡”播放前后出現,直接觸動觀眾“入夢—出夢”的聯想,極具后現代之感。有趣的是,袁牧之還重復組接了石獅子的鏡頭,大有向《戰艦波將金號》“三頭石獅子”的經典片段致敬之意。除此之外,影片還多次出現問號(?)的畫面,袁牧之更是以此作結,為沒有出路的底層百姓發出了深沉一問,這一收場在時人看來盡顯“‘歧路亡羊之苦”[28]。除基本的表意功能之外,這些反復出現、復沓回環的內容有形且富有張力地為觀眾建立了一種周而復始的觀感,推動了這一時空觀念的建立。
袁牧之更是將這種無往不復的時空意識幻化為無數個圓,并以構圖與調度等方式直觀地呈現出來。在上海交易所中,袁牧之以頂拍的方式拍攝參與“博弈”的人群,他們在畫面中激動地揮舞著手臂,共同圍成一個大圓圈,交易所的場地亦幻化為一個類似于賭場的大圓盤。這一場景在電影中多次出現,極具后現代意味,闡釋著陷入循環的博弈人生以及繁華上海的投機本質。電影結尾的“圓”同樣可圈可點,創作者用一個遠景俯拍四個主人公繁華夢斷后,越過列車,在一來一去的列車中間圍著圓柱不停地轉,而這最終也通過動畫的形式被轉化為一個無限循環的圓。這個被看作是“中國電影歷史當中非常有經典性的視覺藝術表達的例子”[29],有力地揭示出個體在動蕩社會的猶豫與彷徨,以及其在特殊年代中往復循環的苦難人生。
“在中國古人看來,宇宙萬物都循圓而動,體現了字宙的終極本原——‘道的變化循環、無往不復的圓之運動軌跡。那么,體現了天地萬物流轉過程中的時間結構,必定也是一個循環往復,周而復始,如環無端之圓。”[30]袁牧之通過一個又一個“無端之圓”,將時下社會的尷尬局面以及周而復始的人生亂象直觀地傳達而出,頗顯荒誕與玩味。總而言之,《都市風光》在傳統的思路上加以改良,并借助略顯后現代意味的視聽表達,傳遞出無往不復的時空觀念。
五、怪誕與戲謔的左翼鏡鑒
有趣的是,不同于這一時期略顯嚴肅、周正的問題劇,《都市風光》在整體上呈現出怪誕、戲謔的敘事傾向。因此,批判的命題也被披上了喜劇的外衣,并借助“插科打諢”的方式演繹出來。袁牧之在文章中指出:“喜劇,我想不該是跌跌打打的噱頭或是苦苦鬧鬧的低級趣味所范圍的。所以,我試想著能在這里貢獻些能在笑里顯現出丑惡的笑料。”[31]正是由于他的這一“貢獻”,有的觀眾認為該片“別具一種風光,使人感到一些輕松,一些不知不覺的舒適”[32];有的觀眾也領略出“片中隨處帶著‘冷嘲熱諷的態度,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33]。這種機智喜劇的創作早在袁牧之從影以前便已然建立。此前,一直參與戲劇創作的袁牧之作為辛酉劇社和戲劇協社的中堅,不僅能從“‘少女演到‘老頭兒”[34],更是繼丁西林之后成為創作機智喜劇的一代翹楚[35]。
事實上,中國的古典敘事之形態并非只有橫眉冷對、口誅筆伐的揭露,亦可以是嬉笑怒罵、幽默怪誕的嘲諷。在學者羅藝軍看來:“中華民族是個富有幽默感的民族,有豐富的喜劇傳統。”[36]他在文章中提到,正如八大山人“哭之”“笑之”的自況一般,其作品多通過戲謔的畫法,展現鳥雀魚鳶白眼向天的狀態,以表達對清王朝的孤憤之情。沿著八大山人的脈絡,羅藝軍闡述了中國傳統藝術在觀照社會生活中的丑惡一面時,也有白眼以對的姿態。[37]不難發現,中國古典敘事同樣有借嬉笑怒罵諷刺現實存在的一條創作脈絡。其中,晚明書畫家徐渭認為“無所不可,道在戲謔”[38],他以詼諧筆墨創作的《掏耳圖》調侃了仙人對于人間事事不耐聽的狀態;在牡丹畫上題“茅屋半間無得住,牡丹尤自起樓臺”,以嘲諷貧富不均、兩極分化的現實處境。馮夢龍作為通俗文學的集大成者,其收攏/編纂的三部笑話集——《笑府》《古今譚概》《廣笑府》雅俗共賞,深受讀者喜愛,他在自序中闡述道:“吾愿人人得笑矣乎而食之,大家笑過日子,豈不太平無事億萬呼。”[39]然而,在“笑”的背后,卻隱藏著馮夢龍對現實的諷刺與鞭撻。中國戲曲中的“丑角”并非只為以滑稽博人眼球,個中更摻雜著創作者對社會現實的觀察與揭露,這在《借妻》《打金枝》等諸多戲碼中皆有顯現。
《都市風光》是承襲了傳統藝術的怪誕一派,袁牧之以表面光亮的皮鞋上漏有大洞的橋段戲謔李夢華表里不一的現狀,更是影射了繁華上海的衰敗實質。當李夢華的硬幣掉落在地板上時,房東便開門討要租金,李夢華急中生智地將口香糖黏在腳底,并順帶黏走這枚掉落的硬幣。為了使這一橋段更具詼諧感,袁牧之又切入其路過修路的路面并將奇特的鞋印印在馬路上的特寫畫面。另外,小云要拿走父親當鋪的狐貍披肩,店員恰逢其時地說:“狐貍怎么可以拿去呢?”這樣的設置可謂一語雙關:一面是阻攔小云之意,一面將小云與狐貍作比,不禁讓人捧腹。小云離開當鋪之時,面對包車夫富有表現形式的拉客,她狼狽至極,名貴的狐貍披肩與囊中羞澀的現狀同樣富有諷刺意味。最終,小云亦陷在物質與金錢的迷霧之中難以自拔。另外,當捉襟見肘的李夢華前往當鋪典當,正巧撞見典當出來的小云父親時,兩個人尷尬地打著招呼,彼此隱瞞著前來的目的,但后景中偌大的“當”字卻成為創作者的調侃。凡此種種,都證明袁牧之企圖用詼諧的筆調諷喻繁華上海的尷尬處境——跌入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陷阱的現狀。
不僅如此,當李夢華走投無路、只得流浪街頭之時,袁牧之以大段落的跳接展現其從最初的西裝革履,逐漸衣衫襤褸,最終衣不蔽體的人生走向。這樣一組蒙太奇句子不僅再次印證了編導的趣味性旨趣與風格化追求,也借李夢華的境遇映照著繁華都市中底層群體的生存局面,成為頗為玩味且荒誕的現實寓言。另外,鄉民急于奔往城市,又困惑在城市中無法安身立命,最終陷入徘徊境地的狀態同樣是現實社會的寫照。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農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經濟破產、政治紛亂、社會失序、鄉村教育衰敗,中國農村開始走向衰敗之路。與此同時,農民也陷入了群體性生存危機中,但集體的遷移仍舊不能滿足底層的生存。或者說,充滿欲望的都市也并非是他們的生存之所,反而成為剝削他們的場域,這也是影片內容所指的關鍵。
可以說,袁牧之借著一場詼諧的情感鬧劇直接書寫了三十年代的社會現實,批判了“無路可逃”的社會困境,具有鮮明的“鏡鑒”的意味。所謂鏡鑒,也就是“電影的空間和現實的空間有一種‘鏡照的關系”[40]。換言之,影片的影像觀照著現實,并讓觀眾有所鑒別、判斷得失。事實上,三十年代的左翼電影正是借助鏡鑒重新探討了社會現實的困境,完成了意識形態的傳達。盡管《都市風光》不同于嚴肅、周正的左翼電影,但卻嬉笑怒罵式地揭示出繁華背后的腐朽與破敗、投機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瘋狂與可笑,這也與當時盛行的左翼風潮不謀而合。因此,《都市風光》也可以說是左翼電影的一聲號角。
結語
袁牧之的《都市風光》在形式、內容與題旨上皆具開拓的意義,它以頗具風格化、藝術化的影像締造了一場關乎現實的幻境寓言,言說著三十年代的時代癥候。另外,從它身上也看到袁牧之導演“一面采擷外來的菁華,一面接受古代文化的濡染涵育”[41],并不斷鉆研、探索出一套屬于自己的創作理論。這次創作可謂意義深遠,為袁牧之其后創作出《馬路天使》這樣的現實主義力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也為三十年代中國電影的時代高峰吹響了號角。總而言之,《都市風光》值得被全面審視與重新評估。
參考文獻:
[1]“都市風光”中導演有大膽嘗試[N]社會日報,1935-08-04(3).
[2]袁牧之導演的“都市風光”噱頭頗多[N].世界晨報,1935-10-02.
[3]袁牧之.興趣·志愿·生活[ J ].中學生,1936:98.
[4]笳.袁牧之:脫離電通的因果[N].時代日報,1935-11-12.
[5]李立,彭靜宜.感官文化視野下的中國電影史研究——以《都市風光》為例[ J ].當代電影,2018(05):96-99.
[6]張語洋.多重媒介與虛擬現實視野下的〈都市風光〉[ 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1(12):90-99.
[7]志新.都市風光觀感[N].申報本埠增刊,1935-10-10.
[8]濟公.我也來談談“都市風光”[N].申報本埠增刊,1935-10-10.
[9]王云亮.宗白華中國畫理論的“寫實”一詞[ J ].美術研究,2009(01):100-103.
[10]張茂材.民族藝術的寫實與寫意[ J ].榮寶齋,2021(03):92-121.
[11]余上沅.國劇[N].晨報,1935-04.
[12]費穆.雜寫[ J ].聯華畫報,1935(05).
[13]梅蘭芳.我的電影生活[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2:69.
[14][15]袁牧之.漫談音樂喜劇[ J ].電通半月畫報,1935(9\10).
[16]胡銘穎.《林泉高致》造境之法探析[ J ].美術文獻,2020(10):9-11.
[17]賀綠汀.都市風光中的描寫音樂[ J ].電通半月畫報,1935(10\11).
[18]推薦中國第一部樂劇:《都市風光》[ J ].電影新聞,1935(09):5.
[19]董耀卿.“都市風光”談[N].大公報.1936-01-20(11).
[20]謝雅琴.傳承與現代化轉型:《都市風光》里的“黃粱夢”[ J ].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9(06):78-83.
[21]陳墨.換一只眼看《都市風光》[ J ].當代電影,2005(03):51-55.
[22]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02.
[23]都市風光中卡通樂劇的嘗試人言[ J ].電通半月畫報,1935(9\10).
[24]王海洲,丁明:“逝者如斯夫”:中國電影的時間敘事觀[ J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22(03):15-23.
[25]傅修延.中國敘事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28.
[26]趙奎英.從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看傳統敘事結構的空間化傾向[ J ].文藝研究,2005(10):58-66.
[27]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699.
[28]一談“都市風光”[N].大公報,1936-01-28(11).
[29]鐘大豐.紀實與創造:吳印咸的電影世界[M].惑學思影錄:鐘大豐中國電影史論集.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344.
[30]危磊.中國藝術的尚圓精神[ J ].文藝理論研究,2003(05):75-81.
[31]袁牧之:漫談音樂喜劇[ J ].電通半月畫報,1935(9\10).
[32]都市風光[ J ].電聲電影周刊,1935(42):907.
[33]一談“都市風光”[N].大公報,1936-01-28(11).
[34]袁牧之.民報[N].1934-0701(2).
[35]田禽.中國戲劇運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4:44.
[36][37]羅藝軍.中國電影與中國文化[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5:234,224.
[38]徐渭.徐文長三集[C]//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3:582.
[39]馮夢龍.古今譚概[M].北京:中華書局,2007:2.
[40][41]林年同.中國電影美學[M].允晨文化,1991:94,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