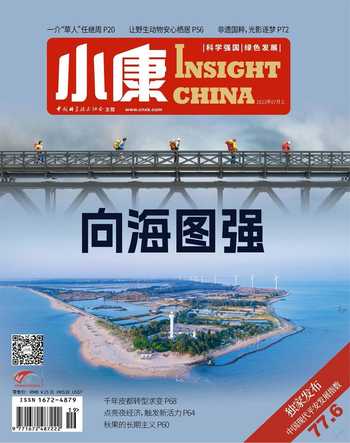逐夢深藍,科技向未來
降蘊彰

我國是名副其實的海洋大國,但目前還不是海洋強國,部分海洋產業的關鍵核心技術仍受制于人,必須進一步加快海洋科技創新步伐。
海洋科技創新是建設海洋強國的根本動力,是貫穿全局、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因素,加快海洋開發進程,振興海洋經濟,關鍵在海洋科技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海洋科技創新取得一系列重大標志性成果:以“蛟龍”號、“深海勇士”號、“奮斗者”號、“海斗”號、“潛龍”號、“海龍”號等潛水器為代表的海洋探測運載作業技術實現質的飛躍,核心部件國產化率大幅提升;自主建造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雪龍2”號破冰船,填補我國在極地科考重大裝備領域的空白;海洋油氣勘探開發實現從水深300米到3000米的跨越,“海洋石油981”在南海首鉆成功,超深水雙鉆塔半潛式平臺“藍鯨1號”在南海成功試采可燃冰……
壯大海洋經濟,關鍵在科技創新。在接受《小康》雜志、中國小康網采訪時,北京大學海洋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繁榮工程”特聘教授金永明等多位海洋專家一致表示:我國是名副其實的海洋大國,但目前還不是海洋強國,部分海洋產業的關鍵核心技術仍受制于人,必須進一步加快海洋科技創新步伐。
“大國重器”顯實力
在談到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海洋科技所取得的成就時,自然資源部副部長、國家海洋局局長王宏表示:“十年來,深水、綠色、安全等海洋高技術領域自主創新不斷取得新突破,多個領域躋身世界前列。”他列舉出一長串“潛水器”名稱:“蛟龍”號、“深海勇士”號、“奮斗者”號、“海斗”號、“潛龍”號、“海龍”號……他強調,以這些潛水器為代表的海洋探測運載作業技術,均實現了質的飛躍,核心部件國產化率大幅提升。
潛水器又稱深潛器、可潛器。為了趕超發達國家的深海援潛救生水平,2002年科技部將深海載人潛水器研制列為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重大專項,正式啟動了“蛟龍號”載人深潛器的自行設計、自主集成研制工作。
2010年5月至7月,“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在中國南海進行了多次下潛任務,下潛深度達到了3759米(全球海洋平均深度3682米),并創造水下和海底作業超過9小時的記錄。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蛟龍”號載人潛水器集成技術的成熟,標志著我國成為繼美、法、俄、日之后,世界上第五個掌握3500米深海載人深潛技術的國家。
2011年7月21日,“蛟龍”號5000米載人深潛首試成功;次年7月16日,“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完成7000米級海試任務。時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科學技術部部長萬鋼表示,這是我國海洋科技發展的又一個里程碑,是各有關部門、參試單位通力合作的典范。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明確指出要“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由此開始,我國進一步加快了“蛟龍”號、“深海勇士”號、“奮斗者”號等一系列潛水器的科研步伐。
從2013年起,“蛟龍”號正式進入試驗性應用階段。歷時十多年,我國為“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專設的863專項經費累計投入3.5億元。該科研任務是由中國大洋礦產資源勘探開發協會辦公室牽頭,會同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中國科學院等系統共100余家科研院所和企業完成;驗收專家組是由來自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等單位的15位專家組成,中科院院士徐冠華擔任專家組組長。
中船重工702所研究員胡震是“蛟龍”號副總設計師,據他介紹,早在2009年,我國就開始了第二臺大深度載人深潛器“深海勇士”號關鍵技術的深入研究。按照計劃,“深海勇士”號的下潛深度回撤到4500米,但關鍵技術國產化率超過85%。這也意味著,“深海勇士”號的研發難度并不小于“蛟龍”號。
2017年10月3日,“深海勇士”號載人深潛試驗隊在中國南海完成全部海上試驗任務,12月1日,在北京完成全部驗收,“深海勇士”號的關鍵部件國產化率達91.3%,主要部件國產化率達86.4%。這是繼“蛟龍”號后中國深海裝備的又一里程碑,實現了中國深海裝備由集成創新向自主創新的歷史性跨越。
隨著對深海了解的深入,深潛試驗不能只有“蛟龍”號、“深海勇士”號,必須打造一系列譜系化的潛水器來全面掌握核心技術。在此基礎上,我國在大深度載人深潛領域又研制出“奮斗者”號、“海斗”號、“潛龍”號、“海龍”號等潛水器,核心部件國產化率大幅提升,實現了我國海洋探測運載作業技術質的飛躍。
王宏在肯定海洋科技取得重大標志性成果的同時直言,與發達海洋國家相比,我國戰略性、基礎性、顛覆性的海洋科技創新能力仍然不足,原創性和高附加值創新成果也較少,核心技術與關鍵共性技術“卡脖子”問題還比較突出。
對于海洋科技發展的現狀,胡波、金永明等多位海洋經濟專家同樣深有感觸,均表示,整體上,我國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粗放、海洋產業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等問題依然存在,建議聚焦深海領域進行科學勘探和資源開發,圍繞海洋核心關鍵技術加強自主創新,加快發展海洋信息技術,培養海洋科技發展急需人才。
著眼短板?重點發力
在胡波、金永明等海洋經濟專家看來,我國在從海洋大國邁向海洋強國的進程中,目前還存在諸如海洋科技基礎整體較弱、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技術開發人才缺乏等諸多短板,需要盡快補齊不足、補上短板。
據遼寧師范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韓增林介紹,在美、日等發達國家,海洋科技對海洋經濟的貢獻率已達到60%以上,海洋科技已經實質性地表現為海洋開發的主導力量,而我國海洋科技對海洋經濟的貢獻率多年來卻一直徘徊在30%左右,海洋科技創新引領和支撐能力明顯不足。
金永明認為,我國以企業作為主體的海洋技術創新體系尚未形成,基地、園區和創新平臺的服務帶動能力都較為薄弱,創新生態環境需要盡快完善。
他建議,我國應搞好海洋科技創新總體規劃,重點在深水、綠色、安全的海洋高技術領域取得突破,尤其要推進海洋經濟轉型過程中急需的核心技術和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究開發,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努力用自主研發的裝備開發海洋資源,提高能源自給率,保障國家能源供應安全。
國家“十四五”規劃中的第三十三章“積極拓展海洋經濟發展空間”為涉海內容,其中明確提出,將“圍繞海洋工程、海洋資源、海洋環境等領域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國家海洋局方面也明確將實施《“十四五”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堅持把實現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作為戰略目標,優化國家海洋科研力量布局,全面塑造海洋未來發展的新優勢。
對于下一步我國海洋科研力量如何布局?如何加快實現海洋科技高水平的自立自強?王宏也有所透露。他表示,將重點在“強化海洋領域國家科技力量”“著力突破海洋核心裝備和關鍵技術瓶頸”“加強海洋基礎性、前沿性和戰略性技術儲備”“提高海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等四方面進行攻關,力爭取得新突破。
具體來說,“強化海洋領域國家科技力量”,按照自然資源部有關部署,將大力推進山東威海、浙江舟山、廣東珠海和海南三亞建設國家海洋綜合試驗場;加強建設海洋領域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和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等;加快建設國家深海基因庫、國家深海標本樣品館和國家深海大數據中心。
在“著力突破海洋核心裝備和關鍵技術瓶頸”方面,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出,“開展蛟龍探海二期、雪龍探極二期建設,開展深海運維保障船和裝備試驗船、重型破冰船等科技前沿領域攻關”。下一步,自然資源部、國家海洋局等方面將推進實施“蛟龍探海”二期、“雪龍探極”二期、“深海礦產開發”重大科技專項、海域動態感知系統工程、海洋生態衛星工程等一批海洋科技重大項目,重點突破海洋觀測監測新型傳感器、無人智能平臺和目標探測識別等技術。
對于如何“加強海洋基礎性、前沿性和戰略性技術儲備”,我國將持續開展海洋科學、極地科學的基礎研究,爭取在海洋動力過程、陸海相互作用、海洋生態系統變化規律等方向實現原創性突破。
在“提高海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發面,將大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強化海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市場化服務,著力打造一批創新能力強的龍頭企業和“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推動建立海洋產業創新聯盟,其目的主要是加快海洋科技成果產業化。
從近海走向深海
自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海洋強國以來,我國各界都增強了對海洋戰略、海洋意識和海洋治理的探索。我國政府多次強調“不走西方老路、超越地緣政治競爭、永不稱霸及和平解決爭端”的立場,和平、合作、包容和互利的新時代中國海洋觀躍然紙上。
國家“十四五”規劃的第三十三章,在部署“圍繞海洋工程、海洋資源、海洋環境等領域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的同時,還提出要“深度參與全球海洋治理”,進一步的闡述是:“深度參與國際海洋治理機制和相關規則制定與實施,推動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海洋秩序,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深化與沿海國家在海洋環境監測和保護、科學研究和海上搜救等領域務實合作,加強深海戰略性資源和生物多樣性調查評價”;“參與北極務實合作,建設‘冰上絲綢之路”;“提高參與南極保護和利用能力。加強形勢研判、風險防范和法理斗爭,加強海事司法建設,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有序推進海洋基本法立法”。
胡波表示,建設海洋強國應有全球視野,我國在“深度參與全球海洋治理”的同時,要重視“在深海的利益及訴求”。他認為,“深海”是未來我國最可能出現重大技術創新與突破的領域。
長期以來,由于美國超強的海上力量,國際海上軍事行動和海洋安全秩序基本上由美國主導。5月下旬,美日印澳四國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提出將全力支持東盟的發展,并且提出要支持太平洋小島國家以完善防務體系。胡波認為,表面上,這份聲明中只字未提中國,但卻從各種角度都提出了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
海南師范大學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研究員劉鋒表示,“印太”地區所涵蓋的印度洋、孟加拉灣、南海及南太平洋等關鍵海域,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運行的重要通道,這無疑將對我國正在開展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產生一些影響。
胡波表示,隨著許多國家的海上活動重點從近海轉向深海遠洋,從管轄海域轉向公海、海底“區域”等公共海洋空間,從水面、空中、海底轉向全海深、全方位,深海技術創新將是一國在海上進行空間及權力拓展的最重要前提。他建議,我國應加快在深海進行經濟開發和戰略布局,并進一步加強在深海科技開發領域的創新與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