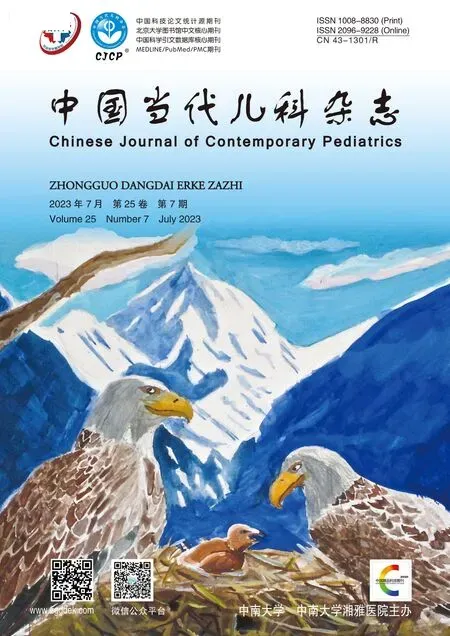兒童原發性擴張型心肌病的臨床特征及遺傳學分析
鄭奎 武菲 婁美娜 王瑩雪 李博 郝京霞 王永麗 張英謙 齊煥軍
(1.河北醫科大學研究生學院,河北石家莊 050017;2.河北省兒童醫院心內科/河北省小兒心血管重點實驗室,河北石家莊 050031)
擴張型心肌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是兒童心肌病中最常見的類型,也是導致兒童心源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和心力衰竭的常見原因之一[1-2]。DCM病因復雜,不同病因與患兒的預后顯著相關[2]。當前兒童DCM 的診療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早期精準化病因診斷困難、病死率高等問題仍沒得到顯著改善,且缺乏有效的危險分層方案。隨著基因檢測技術的發展及應用,30%~40%的DCM患兒具有遺傳學病因基礎[3],并且多項研究顯示存在致病基因突變的DCM患兒病死率更高[1,4]。不同突變基因型、同一基因不同突變位點及環境因素等均與患兒預后密切相關[5]。進一步深入研究兒童DCM基因型-表型的關系有利于患兒的精準預后評估及治療。當前國內關于兒童DCM 遺傳學病因研究報道較少,且缺乏根據遺傳學背景來精準評估患兒預后的臨床資料[6]。本研究通過對比基因突變陽性和基因突變陰性DCM 患兒之間的臨床特征及預后,并分析基因突變陽性患兒的遺傳學特征,以期為DCM 患兒的精準預后評估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選取2018年7月—2023年2月河北省兒童醫院收治的44 例原發性DCM 患兒為研究對象,且所有患兒均已行基因檢測。DCM 診斷標準參考2019 年《AHA 兒童心肌病的分類和診斷科學聲明解讀》[1],排除炎癥性、高血壓、心臟瓣膜病、缺血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心動過速、化療藥物或維生素D 缺乏等導致的繼發性DCM。所有患兒均接受常規抗心力衰竭藥物治療(米力農、地高辛、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利尿劑等),定期于我院心內科門診規律復診。
根據基因檢測結果將44 例患兒分為基因突變陽性組(17例)和基因突變陰性組(27例)。本研究獲得患兒監護人知情同意,通過河北省兒童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202136號)。
1.2 基因檢測
基因檢測均選用全外顯子組測序技術(不含線粒體基因),委托第三方公司(北京邁基諾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醫學檢驗所或福州福瑞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完成檢測,所有患兒家屬行Sanger 測序進行驗證。根據2015 年美國醫學遺傳學與基因組學學會指南[7]對變異的致病性進行分類。實驗室報告的致病變異或疑似致病變異定義為基因突變陽性;未檢出明確與臨床表型相關的致病/疑似致病變異,或檢出臨床意義未明變異但與患兒臨床表型無關或家族其他成員無心肌病表型(不符合家系遺傳模式)的定義為基因突變陰性。
1.3 資料采集
臨床資料主要通過查閱電子病歷系統收集,包括首診時年齡、性別、臨床表現(主訴及體征)、既往史、家族史(心肌病或SCD)、實驗室檢查、心電圖、動態心電圖及超聲心動圖等。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5.0 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卡方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兩樣本t檢驗;偏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首診時臨床資料比較
44 例患兒中,男性21 例(48%),女性23 例(52%),中位首診年齡為12(7,96)個月;首診臨床表現以咳嗽、氣促等呼吸道癥狀最常見(34%,15/44),其次以食欲差、腹痛、嘔吐等胃腸道癥狀多見(27%,12/44)。兩組患兒性別、家族史、首診年齡、首診時臨床表現、心功能分級Ⅲ~Ⅳ級比例,以及首診時腦鈉肽、肌鈣蛋白Ⅰ、肌酸激酶同工酶等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兩組首診時心電圖、超聲心動圖檢查結果比較
患兒首診時心電圖以ST-T 段改變最常見,占73%(32/44),其次分別以竇性心動過速(34%,15/44)、室性期前收縮(27%,12/44)、左室高電壓(27%,12/44)較為常見。基因突變陽性組患兒首診時心電圖表現為PR 間期延長、左室高電壓、竇性心動過速比例高于基因突變陰性組(P<0.05)。兩組患兒首診時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和左心室短軸縮短率(left ventricular fraction shortening,LVFS)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首診時心電圖、超聲心動圖檢查結果比較
2.3 基因檢測結果
基因突變檢出率為39%(17/44),新生突變占24%(4/17)。17例基因突變陽性患兒為TTN基因3例(18%),LMNA、TAZ、MYH7基因各2 例(12%),DMD、PCCB、CTNNA3、TNNI3、FLNC、FBN1、ATAD3A、SGCD基因各1 例(6%)。17 例基因突變陽性DCM患兒首診時基本資料見表3。中位隨訪時間為23(8,35)個月,死亡9例(20%)。基因突變陽性組患兒病死率高于基因突變陰性組[47%(8/17)vs 4%(1/27),χ2=12.05,P=0.001]。基因突變陽性組8 例死亡患兒包括3 例TTN、2 例LMNA、2例TAZ和1例ATAD3A基因突變患兒。

表3 17例基因突變陽性DCM患兒的臨床資料
3 討論
本研究中兒童DCM 基因突變檢出率為39%(17/44),與Wang 等[3]報道的約35% DCM 患兒存在致病基因突變相近。基因突變陽性組和陰性組患兒首診時臨床表現、心功能分級Ⅲ~Ⅳ級比例、惡性心律失常、LVEF 和LVFS 等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提示DCM 患兒首診時的嚴重程度與是否存在致病基因突變無關。本研究中17 例基因突變陽性DCM患兒以TTN基因突變最常見,占18%;其次為MYH7、LMNA和TAZ基因,各占12%。基因突變陽性組患兒病死率高于基因突變陰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基因突變導致的DCM 患兒預后相對更差。TTN、LMNA、TAZ和ATAD3A基因突變的患兒均在隨訪期間死亡。
TTN基因突變是DCM 遺傳學病因中常見的致病變異,多為TTN截斷突變(TTN-truncating variant,TTNtv)。有研究報道在成人DCM 患者中TTNtv占18%~25%,2%~3% 的健康人群攜帶TTNtv[5]。本研究中TTN基因突變占所有基因突變的18%,在DCM 患兒中的發生率為7%(3/44),與Khan 等[8]研究報道的TTN基因突變發生率為9%相近。TTN基因突變可導致多種骨骼肌病和心肌病,心肌病中以DCM 最常見,其次為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骨骼肌病包括兒童中央核肌病、Salih 肌病等[5]。同時TTN基因突變可使部分患兒臨床表型重疊,而且女性TTNtv攜帶者有患圍生期心肌病的風險[5]。本研究中的3例TTN基因突變患兒均死亡,且3例患兒首診時LVEF 較低(均≤30%)。Khan 等[8]報道的10 例TTN基因突變DCM 患兒,其中6 例也在首次住院或隨診期間死亡。提示TTN基因突變導致的兒童DCM 往往預后不良,且容易發生惡性心律失常或SCD[3,5]。此外,發病年齡越早或男性的兒童預后相對更差[5]。
MYH7基因突變是HCM 常見的遺傳學病因,占30%~50%[9]。1%~5.3%的MYH7基因突變與DCM 表型相關[9]。但本研究中MYH7基因突變占所有基因突變的12%,在DCM 患兒中的發生率為5%(2/44)。MYH7基因突變的不同位置、不同突變類型及遺傳模式等均與HCM 患兒的嚴重程度及臨床表型密切相關[9-11]。發生于球狀頭部及頸部的MYH7基因突變多見于HCM,遠端尾部區的突變多與骨骼肌病及DCM表型相關[9-11]。據報道MYH7基因突變相關DCM 表型具有高外顯率,多在兒童早期即出現相關表型。van der Meulen等[12]報道過8 例MYH7基因突變DCM 患兒中有6 例為嬰兒(<1歲)。本研究中2例MYH7基因突變患兒發病年齡也較早(均<1 歲)。de Frutos 等[10]對106 例MYH7基因突變DCM 患者分析發現,男性發病明顯早于女性[(33.3±18.0) 歲vs (41.7±18.6)歲],隨訪5年約12%的患者預后不良。本研究中2例患兒隨訪期間均存活,但2例均為女性患兒,其中1 例c.3956T>C(p.L1319P)突變患兒LVEF 值恢復相對較差(近期LVEF 34%);1 例c.602T>C(p.I201T)突變患兒對常規治療有較好的反應(近期LVEF 58%),但其哥哥因心肌病死亡。提示性別差異可能會影響MYH7基因突變DCM 患兒的預后[9]。
LMNA基因負責編碼核纖層蛋白A/C,核纖層蛋白A/C是細胞核膜的主要組成成分。LMNA基因突變可導致DCM,有研究報道LMNA基因突變是DCM 遺傳學病因中第2 常見的突變類型,僅次于TTN基因突變,占5%~10%[13]。本研究中LMNA基因突變占所有基因突變的12%,與Ferradini 等[14]報道結果相近。多項研究顯示LMNA基因突變是DCM患兒預后不良的標志[1,3,14]。LMNA基因突變相關DCM 是一種高致病性和年齡依賴性的惡性疾病,心臟不良事件發生率高(4 歲時病死率為12%,12 歲時病死率高達30%),同時也是目前指南中唯一獲得植入式心律復轉除顫器一級預防適應證的基因[15]。LMNA基因突變患者具有較高的房室傳導阻滯、室性心動過速、SCD等發生率,且病情進展迅速[16]。本研究中2例LMNA基因突變患兒分別于2歲與9歲發病,且均在首次住院或隨訪期間死亡。一項包含8 000例成人DCM患者基因檢測結果的Meta 分析也顯示LMNA基因突變的患者發生心臟不良結局(包括心臟移植、死亡等)的風險顯著高于其他突變基因[16]。提示LMNA基因突變相關DCM 患兒多預后不良,其惡性程度相對更高。
TAZ基因突變較為罕見,據報道其突變頻率為1/300 000~400 000[17]。TAZ基因突變在本研究中占所有基因突變的12%。TAZ基因突變常導致一種X-連鎖隱性遺傳的線粒體肌病(Barth 綜合征),Barth 綜合征患兒多在1 歲內發病,同時約70%的患兒可表現為DCM[18]。本研究中2 例男性患兒均在1歲內發展為DCM,且均在隨診期間死亡。但有部分女性患兒因X染色體傾斜失活而表現出早期發病且嚴重的DCM表型[17-18]。
DMD基因突變常導致X-連鎖隱性遺傳的神經肌肉疾病,患兒多在12歲左右發展為DCM[19]。據報道男性新生兒中DMD發病率約為1/3 500[20],但在本研究中較為少見,占所有基因突變的6%。可能與DMD 患兒多在病程早期明確診斷后未能及時到專科門診隨診或治療有關。大樣本隊列研究報道,超過50%的DMD患兒在確診之后未進行DCM相關治療或預防治療[21]。DMD 患兒失訪可能低估了DMD基因突變在兒童DCM 遺傳學病因中的占比。本研究中還分別發現了ATAD3A、PCCB、FLNC、CTNNA3、FBN1、TNNI3、SGCD基因突變導致兒童DCM各1例。其中1例ATAD3A基因突變的DCM患兒在隨診期間死亡。
綜上所述,兒童DCM具有顯著的遺傳異質性,同一基因突變可導致多種臨床表型。本研究顯示DCM 患兒首診時的嚴重程度與是否存在致病基因突變無關,但致病基因突變導致的DCM 患兒預后相對更差,特別是與TTN、LMNA、ATAD3A和TAZ基因突變相關患兒均在隨訪期間死亡。不足之處是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小樣本研究;個體化治療可能會影響患兒的預后;隨訪時間相對較短,遠期預后有待進一步追蹤;先證者家庭的其他成員未進行基因級聯篩查,因此本研究中家族其他成員攜帶的基因突變可能被低估。今后可開展多中心、大樣本研究,以對本研究結果進行驗證。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