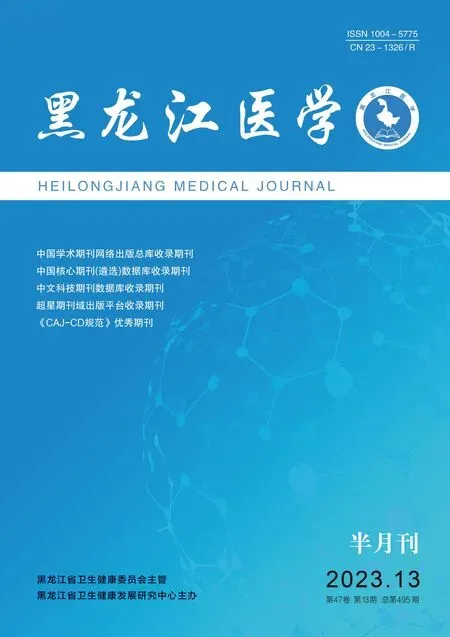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療晚期原發性肝癌患者的效果及對血清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和缺氧誘導因子-1α水平的影響研究
蘆明月
佳木斯市腫瘤結核醫院腫瘤一科,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2018 年我國原發性肝癌(PHC)發病率為9.20%、死亡率為12.90%,分別居世界癌癥發病和死亡的第4位、第3位[1]。當前,手術治療是PHC患者的首選方案,但多數患者確診時已為中晚期,錯失手術時機,手術切除率僅為20%~30%[2]。經導管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為中晚期PHC 的一線治療方案,而載藥微球經動脈化療栓塞術(DEB-TACE)中使用的載藥微球為新型血管栓塞類材料,能夠使腫瘤血管的栓塞更徹底,且可緩慢持續地釋放抗腫瘤藥物,提高腫瘤局部濃度,促使腫瘤完全壞死[3]。甲磺酸阿帕替尼為腫瘤靶向治療藥物,可抑制新生血管生成,從而抑制腫瘤生長[4]。本研究選取佳木斯市腫瘤結核醫院2017年2月—2019年2月收治的84例晚期PHC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療晚期PHC患者的效果及對血清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和缺氧誘導因子-1α(HIF-1α)水平的影響,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佳木斯市腫瘤結核醫院2017年2月—2019年2月收治的84 例晚期PHC 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表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各42 例。觀察組:男28例,女14 例;年齡43~74 歲,平均年齡(63.27±5.75)歲;BCLC 分期為B 期24 例,C 期18 例;Child-Pugh 分級為A級22例,B級20例;病灶直徑3~7 cm,平均病灶直徑(4.26±0.39)cm。對照組:男27 例,女15 例;年齡43~72歲,平均年齡(63.34±5.76)歲;BCLC分期為B期23 例,C 期19 例;Child-Pugh 分級為A 級23 例,B 級19例;病灶直徑3~7 cm,平均病灶直徑(4.24±0.37)cm。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具有可比性(P>0.05)。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納入標準:(1)經CT、MRI及病理學檢查確診,且符合《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9年版)》[5]診斷標準。(2)巴塞羅那肝癌臨床分期系統(BCLC)為B 或C 期。(3)肝功能Child-Pugh A 級或B級。(4)預計生存期≥3 個月。排除標準:(1)嚴重肝功能障礙、凝血功能障礙、心肺功能不全。(2)合并活動性肝炎、嚴重感染。(3)遠處廣泛轉移。(4)合并其他惡性腫瘤。(5)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
1.2 方法
對照組給予DEB-TACE治療。局麻,采用Seldinger法行股動脈穿刺,行腹腔干、腸系膜上動脈造影,確定腫瘤病灶部位、大小、數量、血供等情況,采用微導管超選擇插管至腫瘤供血動脈內,透視下將1 瓶100~300 μm 聚乙烯醇載藥微球與40~50 mg表柔比星(北京協和藥廠,國藥準字H20143165,規格10 mg)充分混合后進行栓塞治療,復查造影腫瘤未見染色,則栓塞成功,術畢。觀察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于術后第3 d 給予甲磺酸阿帕替尼(江蘇恒瑞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40103,規格0.25 g)治療,500 mg/d,口服。如治療期間監測到嚴重不良反應發生,應立即停藥,并經對癥治療好轉后,從半數劑量開始逐步至足量。
1.3 觀察指標
(1)兩組患者近期療效。治療4周后,參照實體瘤療效評價標準(RECIST)1.1[6]進行評價。完全緩解(CR):腫瘤消失,維持≥4 周;部分緩解(PR):腫瘤體積縮小≥50%,維持≥4 周;疾病穩定(SD):介于SD 與PD 之間;疾病進展(PD):腫瘤增大≥25%或出現新病灶。(2)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情況。評價治療后3個月內的不良反應,包括發熱、腹痛、惡心嘔吐、骨髓抑制、乏力、高血壓、蛋白尿、手足綜合征、皮疹等[7]。(3)兩組患者血清VEGF和HIF-1α水平檢測。治療前及治療3個月后,抽取患者空腹靜脈血3 mL,離心,取血清,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進行檢測。(4)出院后隨訪:每2周電話隨訪1次,每3個月門診復查CT 1次,隨訪截至2021年2月。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生存情況采用Kaplan-Meier 生存曲線描述。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短期療效情況
觀察組客觀緩解率(ORR)為45.24%、疾病控制率(DCR)為76.19%,分別高于對照組的23.81%、52.3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短期療效情況
2.2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情況
兩組患者發熱、腹痛、惡心嘔吐、骨髓抑制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乏力、高血壓、蛋白尿、手足綜合征、皮疹發生率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情況例(%)
2.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VEGF、HIF-1α水平情況
治療前,兩組患者血清VEGF、HIF-1α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患者血清VEGF、HIF-1α水平均低于治療前,且觀察組血清VEGF水平、HIF-1α水平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VEGF、HIF-1α水平情況(±s)pg/mL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VEGF、HIF-1α水平情況(±s)pg/mL
組別觀察組(n=42)對照組(n=42)t值P值VEGF HIF-1α治療前198.64±18.63 197.42±18.57 0.301 0.765治療后108.73±9.84 139.52±12.94 12.275<0.001治療前418.31±39.45 416.89±39.38 0.165 0.869治療后298.63±28.67 331.42±33.05 4.857<0.001
2.4 兩組患者生存時間情況
觀察組中位生存期為(11.84±1.05)個月,對照組為(7.69±0.74)個月,觀察組長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0.937,P<0.05)。
3 討論
PHC為常見的消化系統惡性腫瘤,惡性程度較高,預后較差,5 年生存率僅約15%,其發生原因主要與過度飲酒、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肝硬化等有關[8-9]。TACE為當前治療晚期PHC 的主要手段,常規TACE 栓塞劑為碘化油+化療藥物混合栓塞,不僅會隨血流進入全身循環系統,增加毒副作用,而且瘤周側枝循環沖刷碘化油,造成栓塞不徹底[10]。聚乙烯醇載藥微球為新型栓塞劑,能夠彌補上述不足,以可控的方式向腫瘤局部釋放化療藥物,使其長期維持有效的藥物濃度,且栓塞更為徹底,能夠更明顯地促進腫瘤組織缺氧、缺血壞死[11]。但單純給予DEB-TACE的抗腫瘤效應有限,根本原因在于DEB-TACE術后腫瘤微環境處于缺血、缺氧狀態,在HIF-1α、VEGF介導下促使腫瘤新生血管生長,誘發腫瘤復發、進展。
甲磺酸阿帕替尼是選擇性最高的新型生長因子受體-2(VEGFR-2)抑制劑,可抑制VEGFR-2磷酸化,并可通過與VEGFR-2 高度選擇性結合,競爭性抑制VEGFR-2 與VEGF 結合,抑制新生血管生成,以此發揮抗腫瘤效應[12-14]。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ORR、DCR 高于對照組,與曾云建等[15]的研究相似。分析其原因在于,DEB-TACE的化療效果持久性更佳,且術后早期聯合使用甲磺酸阿帕替尼能夠更快地控制體內VEGF水平,并可逆轉化療耐藥,增強化療藥物的抗腫瘤效應,故而短期效果更佳。腫瘤及其轉移瘤的生長離不開血管的形成,VEGF、HIF-1α為血管生成因子,具有較強的誘導血管生成能力,參與腫瘤的復發、轉移過程[16]。楊錦鋒等[17]的研究證實,PHC患者血清中VEGF、HIF-1α水平均呈高表達,其表達情況與臨床分期、腫瘤轉移存在相關性,且二者表達越高,生存期越短,預后越差。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后,觀察組血清VEGF、HIF-1α水平均低于對照組,觀察組中位生存期長于對照組。分析其原因在于,DEB-TACE術后給予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療協同抗腫瘤效應更強,能夠抑制腫瘤血管生成、進展,減少復發轉移風險,延長患者生存期。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乏力、高血壓、蛋白尿、手足綜合征、皮疹等不良反應發生率均高于對照組,提示上述不良反應經對癥處理、藥物減量后均得以緩解,表明患者用藥耐受性較好。
綜上所述,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療晚期PHC患者能夠提升患者的治療效果,降低其血清VEGF、HIF-1α水平,延長其生存期,但相關不良反應有所增加,需加強監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