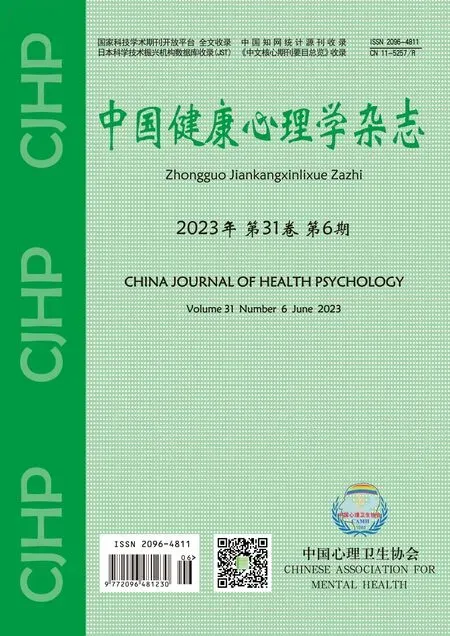早年應激與重性抑郁障礙機制研究進展(綜述)*
郭文韜 張麗麗 栗克清 李 冰 張云淑△
①河北大學附屬醫院/河北大學臨床醫學院(保定) 071000 ②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河北省重大精神與行為障礙疾病研究重點實驗室/河北大學第六臨床醫學院
重性抑郁障礙(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MDD)是一種復雜的疾病,病因目前尚不明確,有學者認為其與多基因效應和復雜的心理社會環境因素有關。社會心理壓力源,尤其是早期創傷事件在MDD的病因學中起重要作用。研究顯示,早年應激(early life stress,ELS)占MDD風險歸因的54%,且童年創傷增加自傷、自殺等行為的風險[1]。最近一項Meta分析發現,有ELS經歷者患MDD的患病風險比沒有ELS經歷者高3倍[2]。伴ELS的MDD可能是抑郁癥的一個重要亞型,具有其獨特的發病機制,是抑郁癥研究中值得關注的類型。本文將綜述ELS與MDD發病機制研究方面的新進展。
1 ELS與MDD的腦結構異常
童年期是大腦生長發育的關鍵時期[3],在這一時期,大腦可塑性發揮重要作用,包括新突觸形成、新神經連接和新血管的生成,是大腦發育、大腦修復和人類行為適應性的基礎[4]。童年期的大腦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5]。
在ELS和MDD發病機制的關系中,研究最多的大腦結構是海馬體、杏仁核和額葉皮層。
1.1 ELS與MDD的海馬結構異常
海馬是大腦結構之一,很多證據表明ELS和MDD之間存在相關性,ELS通常會導致MDD患者海馬體積減小。有學者研究發現在患有MDD的參與者中,ELS與海馬體積呈顯著負相關[6]。此外一項Meta分析觀察發現,在MDD患者中觀察到海馬體積減小,可能是高風險基因多態性和ELS暴露共同作用的結果[7]。同時有學者對海馬的亞區進行了研究,有證據表明ELS影響特定海馬亞區的發育,例如角狀回(cornu ammonis,CA)和齒狀回(dentate gyrus,DG)。在左側CA2-CA3和CA4-DG亞區觀察到ELS和海馬體積減少之間關聯性最強[8]。綜上,ELS可能通過影響大腦可塑性導致海馬體積減小,從而導致MDD的發生,但目前仍缺乏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假設,而且其導致海馬體積減小的原因尚未明確,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
1.2 ELS與MDD的杏仁核結構異常
杏仁核位于海馬的末端,呈杏仁狀,是產生情緒,識別情緒和調節情緒的腦結構,屬于邊緣系統的一部分。動物模型研究顯示,慢性不可預知溫和應激(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CUMS)會增加患MDD雄性大鼠杏仁核神經元的樹突棘密度和數量、樹突狀分支以及樹突長度[6,9-10],從而導致杏仁核體積增大。然而有學者研究發現相反的結果,CUMS減少易感小鼠杏仁核中興奮性突觸的數量并且增加突觸間隙的寬度,從而導致杏仁核體積減小[11]。臨床研究中也類似的發現,針對有ELS經歷的MDD患者的影像學研究報告顯示杏仁核體積減少[12-14]。然而,一項針對健康被試的研究報告表明,經歷ELS的個體杏仁核體積增大[15]。綜上所述,動物實驗和臨床研究均證明ELS會導致MDD患者杏仁核結構發生改變,然而目前相關研究不充分,在導致BLA體積增大還是減小這一問題上,專家學者們持不同意見。
1.3 ELS與MDD的前額皮層結構異常
前額皮層指的是初級運動皮層和次級運動皮層以外的全部額葉皮層,是另一種經常研究的大腦結構。文獻中有證據證實前額葉皮層參與ELS暴露的MDD發展,但很少有研究將兩者聯系起來。有學者認為,ELS可能會導致攜帶該基因高風險個體的易感個體的FKBP5基因去甲基化,這反過來又與大腦結構的變化有關[16]。ELS可能會導致前額皮層體積減小,前額皮層減小與MDD的臨床癥狀相關,但相關研究較少,且機制尚不清楚,需要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ELS是大腦結構改變和MDD的危險因素。ELS可以誘導與壓力相關的大腦結構發生生物學變化,從而可能在成年期變得適應不良,使人們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不過,三者之間的關系尚未得到充分證實。
2 ELS與MDD的腦功能異常
隨著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ELS與MDD患者大腦區域的異常活動和功能連接模式有關[17]。在一項61名MDD患者和80名健康受試者的研究中,發現ELS對MDD的腦功能有負面影響[18]。
前額葉皮層似乎通過連接神經網絡參與了ELS和抑郁癥狀之間的聯系。有學者研究發現,暴露于CUMS的大鼠中,內側前額葉的網絡連接減少,從而減少了在大鼠探索行為信息從內側前額葉到杏仁核的傳遞[9,19-20]。最近一項動物研究中發現,早期創傷性應激誘導了青春期大鼠杏仁核的神經元發育功能障礙。更重要的是,這些異常大部分會持續到成年期,表明ELS對神經元發育的長期影響會導致成年后個體容易患抑郁障礙[21]。
綜上,童年時期發生的創傷事件對大腦功能產生影響,且這種影響長期存在,可能是導致成年期MDD發生的重要發病機制之一。人們對不同腦區的功能和連通性的研究,使得精神疾病潛在的神經變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
3 ELS與MDD的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異常
BDNF是在全腦中均有表達的腦神經營養因子,能夠增加突觸完整性和可塑性并促進神經元發育[21]。在發育的早期階段,它的作用尤其重要,此時大腦的可塑性增強,而且對環境刺激高度敏感。ELS可以降低大腦中BDNF的表達,減少神經元數量并誘導神經元萎縮[22],這與MDD的發病機制密切相關[23-24]。在小鼠及大鼠模型的實驗中,均發現ELS會減少大腦中BDNF的表達并導致抑郁樣行為[22-25]。此外,BDNF敲除小鼠表現出腦BDNF表達降低和抑郁樣行為[26]。近期有學者發現,抗抑郁治療能夠改善抑郁癥狀并增加大腦中的BDNF水平,抗抑郁藥物可通過促進BDNF的合成而產生抗抑郁效果[26]。以上結果說明,BDNF產生的降低是導致伴ELS的MDD發生的重要因素。然而,尚未有足夠的證據表明,ELS是否通過改變大腦可塑性來導致MDD的發生,未來需要結合腦影像學、分子生物學來進行深入研究。
4 ELS與MDD的HPA軸功能異常
HPA軸在應對外部和內部刺激(包括心理壓力源)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HPA軸活動已被確定為抑郁癥風險的關鍵生物學標志物。大量文獻記錄了MDD與HPA軸活動異常之間的聯系[27-28]。
HPA軸的激活本質上是人體為應對環境改變的適應性機制,它使人體能夠調節壓力而保持生理穩定性[29]。HPA軸的動力學需要嚴格控制激發和抑制的平衡,以充分響應壓力和適應環境需求[30]。在應激情況下,人體會在HPA軸上啟動一系列反應:下丘腦釋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觸發垂體釋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最終刺激腎上腺釋放皮質醇進入血液。此時人體會形成反饋,皮質醇與相應受體結合后會抑制興奮性的增加,使人體從應激誘導的激活中恢復。HPA軸的慢性激活會引起損傷和病理反應。因此,皮質醇通常被用作心理壓力和相關精神或身體疾病的生物標志物[31]。
有研究發現無論是否患有MDD,在有ELS病史的人中發現皮質醇水平較高。在伴ELS的MDD患者中發現給予地塞米松后對HPA軸的抑制減少。然而,在不伴ELS的MDD的患者中沒有發現HPA軸異常[32],這表明在MDD患者中發現的HPA軸異常不是由MDD本身引起的,而是由ELS的共存引起的。上述壓力會觸發HPA軸的過度活躍,這反過來又會使個體容易患上MDD和其他疾病[33]。HPA軸異常可能先于MDD,因此ELS可能是MDD的原因或風險因素,而不是后果或癥狀。同時MDD的發展會加重HPA軸功能障礙。
綜上所述,ELS使皮質醇水平的慢性升高和HPA軸反饋系統的功能障礙,在MDD的發病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
5 ELS與MDD的炎性細胞因子異常
目前廣泛認可的炎性細胞因子包括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Meta分析發現ELS與炎癥生物標志物之間存在顯著關聯。觀察到對TNF-α和IL-6的影響最大,其次是CRP。與情感虐待相比,兒童期性虐待和身體虐待患者表現出更大的促炎作用[34]。
炎癥已被證明會降低四氫生物蝶呤的可用性,而四氫生物蝶呤是調節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的重要輔酶因子。由ELS引起的DNA 甲基化改變可能反過來改變基因表達,影響促炎活動的風險,進而影響抑郁癥的發展[35]。此外,有研究表明,僅在遭受中度至重度童年創傷的女性中,左腹側紋狀體和腹內側前額葉皮層之間的功能連接性與炎癥標志物呈負相關,而這種連接性與炎癥評分高的參與者的抑郁癥狀相關。結果表明,兒童虐待會導致全身性炎癥增加,從而影響獎勵回路,從而導致成年期出現抑郁癥狀[36]。
炎癥生物標志物和治療調節劑的發現對于幫助改善治療反應和患者報告的結果具有重要意義。根據Meta分析的結果,一項調查抑郁癥患者細胞因子減少的綜述發現抗TNF-α藥物可減輕炎癥患者的情緒癥狀[37]。表明抗炎藥可以通過神經保護功能改善伴ELS的MDD患者預后。但目前相關研究較少,未來需要深入研究,這或許為伴ELS的MDD患者的治療提供新的思路。
6 ELS與MDD遺傳的相互作用
ELS會增加重性抑郁障礙的發病率,但并非每個暴露于早期生活壓力的人都一定會患上精神疾病,也不是每個患有精神疾病的成年人都會遭受一些童年時期的虐待或忽視。這證明了遺傳特征和個體易感性在抑郁癥發展中的重要性。
發育中的大腦對早期壓力源非常敏感,尤其是由于一系列壓力敏感基因通路的重新編程[38]。因此,早期壓力是精神疾病(如抑郁癥)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可能導致疾病病程延長和對治療的敏感性降低。抑郁癥、基因多態性和應激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已得到證實[39]。近年來,研究越來越集中于闡明抑郁癥的遺傳機制。完整的基因組關聯研究促進了對某些精神疾病遺傳機制的理解,但還不足以完全闡明抑郁癥的遺傳基礎[40]。
有研究表明,童年時期的虐待與海馬中糖皮質激素受體的表觀遺傳減少之間的關聯。研究發現一組有ELS經歷的自殺者在海馬中表達的糖皮質激素受體數量較少,這與編碼這些受體的基因啟動子的甲基化有關。隨著基因轉錄率的降低以及受體水平的降低,這種甲基化可能使個體對壓力的耐受性降低,從而出現自殺傾向[41]。
有學者提出了基因與環境之間的兩種干擾模型。一種是素質-壓力模型,其中個體繼承了表達某些特征或行為的傾向,這些特征或行為在暴露于壓力經歷時會被激活;另一種是基因-環境相關模型,由心理學家提出,他們通過幾項研究已經發現基因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十分復雜[42]。根據這個模型,遺傳負荷會增加個體在生活中經歷壓力事件的可能性,從而導致基因激活。例如,具有遺傳易感性發展某種疾病的人,也可能具有相應的人格特征,即沖動性,這使他們易暴露于環境風險因素中,從而引發與疾病相關的遺傳易感性。表觀遺傳學可以部分解釋環境因素調節抑郁癥風險的機制。DNA甲基化模式是可遺傳的,這可能解釋了抑郁癥的部分遺傳性。當然,它們也受到環境暴露的調節,通過一組稱為DNA甲基轉移酶的特定酶和一些蛋白質易位家族的活性,分別負責DNA甲基化和去甲基化[43]。
在一項研究中,對88名企圖自殺的人進行了HPA軸耦合基因位點的調查,研究人員發現甲基化轉變與自殺企圖的嚴重程度有關。在高風險組中,兩個CRH相關的基因位點顯著低甲基化,并且與自殺企圖的嚴重程度有關[44]。
精神障礙不再只有一個原因,而是多種原因,這些原因結合在一起,最容易患上抑郁癥。這種易感性與環境和遺傳因素有關,是抑郁發作的基礎。對精神疾病的易感性源于在大腦發育的關鍵時期暴露于環境因素。這些表觀遺傳調控過程發生在環境和基因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持續時間很長,可以連同與其相關的基因一起傳給后代[45]。
7 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大量證據支持ELS與MDD的發病有關。早年應激可能通過HPA軸功能異常、炎性細胞因子異常等機制引起MDD。早期應激或創傷可能通過特定的表觀遺傳作用,如不同基因DNA甲基化改變(如BDNF基因),而引起與重型抑郁障礙有關的神經生化改變。這些假說都有待進一步的驗證。在以后的研究中結合環境因素、腦影像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學等綜合因素,進一步闡明經歷童年期創傷MDD可能的發病機制,促進疾病的早期診斷,為此類患者的治療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