漿染尚蕪湖
易瑾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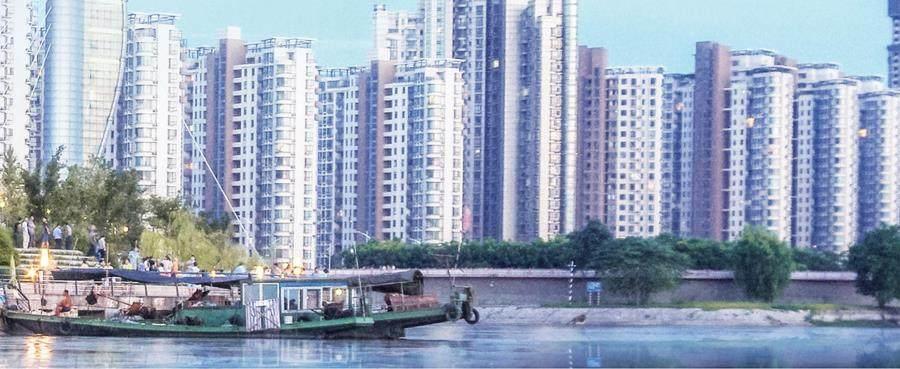
長江是我國水量最豐富的河流。古往今來,中華人民的民族智慧在長江流域的開發活動中展現得淋漓盡致,長江沿岸的工商業活動吸引了無數學者對其進行深入探究。明代中后期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借助長江的天然水道,我國的工商業在這一時期發展迅速,這一點在我國江南地區及其鄰近區域表現得尤為突出。徽州商人在這一時期遍布全國各地。安徽境內的蕪湖是經濟活力較高的一個地區,一方面,其瀕臨長江,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迅速;另一方面,也與徽商等客籍商人關系密切。蕪湖在這一時期擁有聞名全國的漿染業,這與名叫阮弼的徽州商人有很大的關聯。阮弼其人對于蕪湖漿染業的發展,甚至對于整個蕪湖的市鎮經濟發展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目前,關于我國古代長江流域經濟活動的研究,從空間上來看,主要是從長江上游、長江中游和江南地區展開。從研究方法來看,歷史地理學、移民史、社會史、經濟史等專門史學方法的運用層出不窮。首先,在對長江上游經濟活動的研究中,郭聲波闡明了四川地區歷史時期農牧業生產區域的分布與變化,各生產區域的農業生產結構,主要農作物的由來與分布,各生產區域農業生產水平的演變與差異以及農業生態環境的變化等;山田賢試圖從“地域統合”“地域變異”等概念入手來解析四川移民社會自起步到終結的社會變化過程,并時刻關注構筑于“地域”的秩序與籠罩傳統中國社會的“國家”秩序之間的關系;王笛研究了“清代長江上游區域由傳統向近代的發展,力圖展示一個內陸社會演化的動態,描繪社會近代化的過程及特征”。其次,在對江南地區的研究中,張海英認為,“明中葉以降,隨著全國性市場的不斷發展,江南商品的流通范圍已大大超出了地方消費的范疇,并逐漸納入了全國性的、遠距離貿易的市場體系之中。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其商品的全國性市場及至海外市場的形成,是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劉石吉認為,“就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的發展而言,宋代以來,直到十五世紀末年(明成化、弘治年間),可以說是市鎮的萌芽和形成時期。在此期間,農村地區的草市及定期市逐漸演化為商業性的聚落,居民貿易,日以增盛。而傳統的城鎮,隨著商業化的影響,軍事及行政機能漸趨退化,商業機能則日漸浮現”。傅衣凌認為明代社會“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逐漸出現,盡管他們仍受到封建勢力的壓迫,然而這種新力量已在江南及沿海城市里稀疏地看到,則是事實”。李伯重總結了江南早期工業化的特點,分析了這種工業化的主要成因,論述了其可能的發展前景,并對以往明清經濟史研究中流行的西方中心主義史觀進行了檢討和批判。范金民認為,“自明代起,江南成為全國最大的棉布和絲綢商品生產基地,兩大支柱性商品棉布和絲綢商品生產基地,兩大支柱性商品棉布和絲綢都在國內外擁有廣闊的市場,改變了人們的衣著生活”。
總之,現有研究大多集中于長江流域的工業、農業、商業等產業開發方面,或是集中于長江流域的移民活動,這些都屬于宏觀層面上的長江流域開發活動,對研究長江流域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有著重要的影響。但是現有研究在微觀層面上的長江流域經濟活動,包括某些重要人物在長江沿岸市鎮經濟發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方面仍然有著較大的創新空間。為此,本文從這一方面進行創新,對明代商人阮弼與江城蕪湖漿染業發展的關系進行探討。
明代蕪湖的區位條件、徽商概述和漿染業地位
蕪湖坐落于安徽東南部,位于長江下游,水運交通發達。孫中山先生在蕪湖考察期間,曾贊嘆蕪湖為“長江巨埠,皖中之堅”。然而,與江南地區經濟活動豐碩的研究成果相比,對明代蕪湖的研究卻略顯不足,對于明代中后期蕪湖漿染業發展的研究和與之有重要關聯的徽商阮弼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事實上,蕪湖的地域樞紐地位非同小可,“蕪湖扼中江之沖,南通宣歙,北達安廬,估客往來,帆檣櫛比,皖江巨鎮,莫大此乎”。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水文條件為明代蕪湖的工商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故在明代中后期,江南商品經濟的繁榮也為蕪湖帶來了進一步發展的契機,蕪湖在這一時期成為全國聞名的商業市鎮。“蕪湖附河距麓,舟車之多,貨殖之富,殆與州郡埒。今城中外,市廛鱗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魚鹽襁至而輻輳,市聲若潮,至夕不得休。”這一時期蕪湖的重要商業地位,從中央政府在此設立榷關可見一斑。蕪湖榷關始設立于成化七年(1471),“成化七年三月,工書王復請于太平之蕪湖……遣司屬親往其處抽分竹木,變價解京,以供營繕之用。”萬歷年間蕪湖又增設戶部榷關,“萬歷時,稅使四出,蕪湖始設關,歲征稅六七萬,泰昌時已停”。《明實錄》中也對蕪湖榷關有所記載:“……若湖口之抽分,每歲于九江、蕪湖鈔關量加數千金……務足稅額。”當然,蕪湖的商業取得長足發展,多是憑借外地商販在此苦心經營,明初人黃禮曾說:“其(指蕪湖)居厚實,操緩急,以權利成富者,多旁郡縣人。土著者僅小小興販,無西賈秦翟,北賈燕代之俗。”這里提到的“旁郡縣人”大多來自徽州,即聞名天下的徽商。
徽州地處群山之中,土壤貧瘠,人口眾多,這在徽州地方志中有記載:“本府萬山中,不可舟車,田地少,戶口多,土產微,貢賦薄。”眾所周知,交通便利程度是一個地區發達程度的重要寫照,徽州“不可舟車”,交通運輸條件惡劣,資源流轉極為不便。在古代農業社會,徽州“田地少”,則更反映出當地缺乏生產生活資料的必要條件。“戶口多,土產微”則生動反映出當地的資源十分有限,無法滿足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民以食為天,家境優渥的人家更重視食物的質量,但即使是徽州當地的富人,也只能“食惟饘粥,客至不為黍”。徽州當地的生產條件之惡劣可見一斑。所以為了生計,許多徽州人選擇離開徽州,客旅他鄉,從事商業活動,由此徽商群體逐漸形成。明清時期的徽商更是遍布全國各大中小市鎮,這一時期全國聞名的徽州商人遍布江南及其鄰近區域,葉顯恩說道:“明代晚期至清代乾隆末年,是徽商的黃金時代。營商人數之多,活動范圍之廣,資本之雄厚,皆居當時各商人集團之前列。營商已作為徽州人的重要職業。”明人王世貞也曾說:“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則十一在內,十九在外。”顧炎武對徽人經商的評價是:“出賈既多,田土不重。操貲交揵,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徽州商人的強大實力在謝肇淛的記載中也有所體現:“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
徽商經營范圍極其廣泛,其大宗有鹽業,自明朝的鹽業管理制度由開中法向折色法轉變以后,商人不再需要將糧食運往邊疆以換取鹽引,而是直接可以在鹽運司用銀兩換取鹽引,這樣一來,本來在地理位置上遠離邊疆地區的徽州商人逐漸踏足鹽業,且“自古煮海之利,重于東南,而兩淮為最”,徽州商人憑借與兩淮鹽場距離較近的優勢,逐漸成為最具實力的鹽商。
除了鹽業外,徽商經營的茶業規模也很大。徽州自古以來就是茶業產地,早在唐朝,“歙州、婺州、祁門、婺源方茶,置制精好,不雜木葉。自梁、宋、幽、并間,人皆尚之。賦稅所入,商賈所賚,數千里不絕于道路”。到了明清時期,徽州的松蘿茶行銷全國,茶業逐漸成為徽州商業經營的主業之一。
因徽州地處群山之間,所以盛產木材,因而徽州商人也經營木業。在宋代,“女子始生則為植杉,比嫁斫賣,以供百用”。由此可以看出,徽州盛產的木材是用來維持當地居民生計的。到了明清時期,徽商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進行營利,并通過長江進行運輸,木業得到進一步發展。
在明清時期有俗語“無徽不典”,這反映出徽商經營的另一重要行業——典當業。大明律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并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違者笞四十。以余利計贓,重者坐贓論罪,杖一百。”雖然明廷規定不允許取利超過三分,但在實際經營中,大多典商仍舊超過規定限額。所以取利較低的徽州典商逐漸獲得了更多典當者的青睞,并在與其他典商的角逐中占據了優勢。徽州典商的實力,從當時的記載中可見一斑:“新安大賈與有力之家,又以田農為拙業,每以質庫居積自潤。”
除經營鹽、茶、木、典業外,其他諸多行業徽商也大多都有涉及,譬如糧食貿易和棉布業等。徽商不僅經營行業多,營商活動所涉地域也十分廣泛,沿江市鎮幾乎都充斥著徽州商人的蹤跡。
明清時期蕪湖的漿染業在全國有著很高的知名度,“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織造尚松江,漿染尚蕪湖”。明清時期松江府的織造在全國聞名遐邇,而此時蕪湖的漿染業可與松江織造齊名,蕪湖的漿染在全國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翦伯贊說道:“在這里(指江南),已經形成為五大手工業的區域,即松江的棉紡織業、蘇杭二州的絲織業、蕪湖的漿染業、鉛山的造紙業和景德鎮的制瓷業,他們之間已保持了極緊密的商業聯系。”
阮弼在蕪湖的經營
這一時期在蕪湖的徽州商人中,阮弼十分具有代表性,阮弼也與蕪湖興盛的漿染業發展緊密相關。可以說,徽商阮弼對蕪湖的漿染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阮弼,字良臣,號長公,歙縣(屬徽州)巖鎮人。阮弼少時家道中落,他曾嘗試過用多種方法謀求未來的發展,卻不得不感嘆道:“吾欲為良士,無脩糈則無師,良士安可為也;吾欲為良醫,醫必歷試,一不驗將殺人,良醫安可為也。”阮弼認為“則之蕪湖,蓋襟帶一都會也,舟車輻輳,是可以得萬貨之情”。“就諸梱載者悉居之留都轉運,而分給其曹,利且數倍。”后來阮弼發現設立染局有利可圖,“乃自蕪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灌輸,弗省而利滋倍”。阮弼在蕪湖設立染局,發展漿染業,“五方購者益集,其所轉轂遍于吳、越、荊、梁、燕、豫、齊、魯之間”。此處可以看出阮弼在蕪湖設立的染局已經頗具規模,而后阮弼“則又分局而賈要津”“升降贏縮莫不受成”,設立分局擴大產業規模。經過阮弼多年的慘淡經營,開創了“蕪湖巨店”的佳話。
當然,阮弼的成功與其所處時代背景不無關聯。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發展迅速,與此同時,社會風尚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人由明初的崇尚勤儉節約、只求吃飽穿暖的觀點逐漸轉變為追求艷麗裝束的觀念,這種追求物質享受的奢靡風氣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及鄰近地區尤其盛行。張顯清在《明代后期社會轉型研究》中說道:“從成化后期開始,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活躍,社會上拜金主義之風的盛行和人們價值觀、倫理道德觀念的趨變,人們開始不斷地違反服飾禁令,有關禁令形同虛設。各個階層的人們均追求物質上的豐腴,追求美成為一種時尚,‘美開始進入普通人家。”漿染業的發展得益于此時人們對艷麗服飾需求的推動。
在立業之初,阮弼本錢匱乏,難以獨立開設染局作坊,且根據明律規定:“諸物行人,謂諸色貨物本行之牙人也……凡諸物之價,評在行人,必平等估計,而后買賣兩便。”明代的牙人在商業交易中的地位極其重要,“市中貿易,必經牙行,非是,市不得鬻,人不得售”。所以當時蕪湖的漿染業大多為牙行所控制,客籍商販不允許與漿染店鋪進行直接交易,阮弼便托請當時同在蕪湖的徽州同鄉疏通關系,最終獲得了官府印發的牙帖。由此可見,阮弼成功的背后,還有眾多徽州商人。在明朝時代背景下,作為經商者,倘若沒有官府的許可,要想在蕪湖開展漿染商業活動是十分困難的。
棉布染業在蕪湖漿染業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蕪湖棉布染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在明代中期以后,如前文所述,與諸多徽商在此投入人力物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明代手工生產出的棉布,其質量的優劣是由其制作流程決定的。棉布的產出共經過紡織和漿染兩大流程,而漿染的質量取決于“碾石”的質量。蕪湖附近的荊山所產的石頭是制作漿染碾石的絕佳材料,用這種碾石漿染時不容易發熱,可以使產出的布帛、絲織品緊而不松、顏色鮮艷、不易褪色。阮弼在兼并了一批染布作坊后,在蕪湖設立總局,號稱“蕪湖巨店”“首尚佳石”。阮弼的染布作坊產出的布帛質量上乘、色澤艷麗,其所采用的碾石便是荊山碾石。質量較好的碾石價格昂貴,“每塊佳石,值十余金”。此時的阮弼已然成為蕪湖漿染業中的巨擘,且“長公為祭酒”。此處的“祭酒”,并非國子監的學官,而是指同行業商人所推舉的、得到官府認可的調解人和管理者,其性質類似于今天的商會主席。
阮弼對蕪湖工商業的守護
明朝嘉靖年間,倭寇肆虐,“島夷自越突新都,且薄蕪湖”“守土者束手無策”。值得一提的是,這里的“守土者”之所以“束手無策”,可能與明清時期地方財政匱乏有關。陳支平認為,明代嘉靖、萬歷年間全國各地的存留數約占田賦總收入的40%。這就意味著諸如構筑城防、抗擊倭寇這樣重要的事情,地方政府因財政拮據而很難有所作為,從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當地的富商提供財力、物力、人力支持。此外,明中葉以后,政治腐敗,軍隊戰斗力下降,譚綸曾說:“比來法令廢弛,行伍空虛。各該衛所官兵大都桀驁不馴,頑鈍無恥。驅之戎行,則恍然自失;責之城守,則恬若罔聞。”在此境況下,阮弼“倡賈少年強有力者,合土著丁壯數千人”“刑牲而誓之”,最終“寇偵有備,而宵遁”。其所部將抵御倭寇的首功歸于阮弼,“且下章服”,阮弼力辭曰:“賈豎子何敢以此釣奇?有如異日者寇至,亦將倚辦諸賈人,則吾為之俑也。”
由此可見,阮弼在倭寇來犯時能夠組織城防,保護了蕪湖的安全,守護了蕪湖的工商業。當然,在“守土者束手無策”的情況下,阮弼能夠成功組織蕪湖的防務,可以看出阮弼有著非同一般的組織能力和財力物力,以及當地政府對阮弼的倚重。后來蕪湖的西門名為“弼賦門”,可能就是為了紀念阮弼為蕪湖所做出的貢獻而命名的。
明代蕪湖的漿染業能夠獲得迅速發展,這與當時的很多條件和因素密不可分,包括蕪湖的地理位置,蕪湖良好的工農業基礎,徽商等客籍商人的投資,社會風俗的變化,商品貨幣的流通等。
在阮弼之前,蕪湖的漿染業已經頗具規模,在技術上更是別具一格。“布青初尚蕪湖千百年矣。以其漿碾成青光,邊方外國皆貴重之。人情久則生厭。毛青乃出近代。其法取松江布染成深青,不復漿碾,吹干,用膠水摻豆漿水一過,先畜好靛,名曰標缸。入內薄染即起,紅焰之色隱然。此布一時重用。”這種毛青布的漿染方法一直沿用至近代,對全國各地的漿染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外,江南地區的織造業從一開始就帶動了蕪湖漿染業的發展。蕪湖位于青弋江和長江的交匯處,松江府的棉布行銷全國,蕪湖這一重要交通樞紐自然會承接大量的漿染業務。明朝中期全國共有22個織染雜造局,安徽境內已經有三處有織染雜造局——徽州、寧國府、廣德州。蕪湖與安徽境內三個織染雜造局所在地的距離較近,為漿染業的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
市鎮經濟是商品交換的產物,隨著明代中后期商品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商販離開故土赴外地經商,推動了商業市鎮的形成和發展。從總體來看,在明代蕪湖市鎮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徽州商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阮弼代表了無數不畏艱險、跋山涉水的勤勞的徽州商人形象。
蕪湖漿染業的發展,早于阮弼,也盛于阮弼。在今天重新回顧這段歷史、談起蕪湖漿染業時,阮弼必定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阮弼之于蕪湖,相當于佳石之于漿染,阮弼就是蕪湖漿染業最上乘的“碾石”。若沒有阮弼這塊“佳石”,蕪湖漿染興許會褪去幾分本該艷麗的顏色。
當然,研究阮弼與蕪湖漿染業發展的關系也只是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本文力求從微觀層面剖析古代長江下游的經濟活動,對阮弼與蕪湖漿染業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事實上,一座市鎮的發展,或是一段流域的開發,其背后飽含著無數勞動人民的辛勤付出。阮弼是時代的縮影,是勤勞聰慧的徽商在蕪湖的縮影。本文從微觀的人物出發,探討其背后更深層次的意義,以期對古代長江流域商業經濟的研究有所創新。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