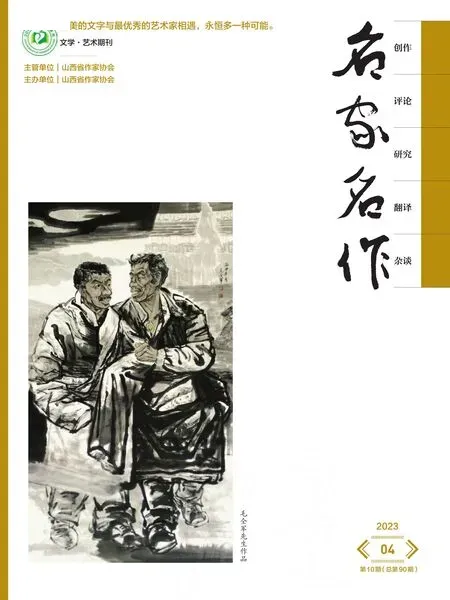淺議古長安書法文化對當代書法發展的啟示
金旭光
一部中國書法史,一半在長安,一半在江南。如果從兩周時期的鐘鼎文算起,到秦代的小篆,到漢代的隸書,再到隋唐的書法盛世,處處都烙有長安的印跡。從這一意義上講,“長安書法文化”不是單指出生于長安,或祖籍在長安的書法家,更是指以古長安文化為引領的“書法文化圈”。歷史上的長安城是西周、秦、西漢、新莽、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十三朝的首都,有十三朝古都之稱,其中西周、秦、兩漢、隋、唐幾朝又是中國政治中心東移之前,中國書法史上成就最鼎盛的幾個歷史時期。因此,古長安文化孕育了長安書法,長安書法又影響著一代又一代書家。
從西周時期的《毛公鼎》《大禹鼎》《墻盤》,到秦代的《石鼓文》,到兩漢時期的《曹全碑》《華山碑》《石門頌》,再到隋唐時期的李世民、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薛稷、徐浩、李邕、顏真卿、柳公權、楊凝式等,都是中國古代特定歷史時期優秀書法文化的杰出代表,他們在書法藝術領域或開疆擴土,或獨樹一幟,無不影響著古代書法藝術的發展,堪稱中國書法的典范。一直到近現代的于右任、劉自櫝、衛俊秀、曹伯庸等都是長安書法文化的杰出代表。
一、古長安書法文化概念的界定
對于古長安書法文化的界定包括三個方面:其一為文人書法流派興起之前,在這一地域的政權所主導的書風都是屬于“長安地域性質的通行文字”,從周開始到秦漢大一統,這段時間所有的通行文字都與“長安”這一地域有著莫大的關聯①從周王朝定都鎬京(現今位置為西安市長安區西北),到秦王朝的統一文字,不管文字在東周時期是呈現什么樣的散布發展狀態,總之秦王朝之所以能夠順利的統一文字,是在這種散布的地域性書風中存在著統一的趨勢(六國之文字都是由周文字發展而來,其中必然就會帶有周文字之因素,故此秦王朝之文字才能順利地統一),也就是說商周以來古文字是經秦王朝統一文字的一脈相承的發展。所以可以說在文人書法流派興起之前的文字演變階段的“古代通行文字”與“長安”這一地域有著莫大的關聯,故此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一部中國書法史,一半在長安”。;其二為文人書法流派興起之后的“盛唐書風”,此時的“長安”為唐王朝的都城,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故此盛唐之風可以稱之為“古長安書法文化”;其三為從書法藝術發展的邏輯出發,“古代通行文字”本來不可以稱之為書法藝術,但是由明末清初所興起的“篆隸學習風氣”使當時書家臨學“古代通行文字”。對于周、秦、漢一系文字的學習也能看成是“長安地域性書風”的一種延續。
周、秦一系之通行文字有《毛公鼎》《大盂鼎》《墻盤》《石鼓文》《曹全碑》《華山碑》《石門頌》等這類書法都成為清代碑學的經典。
唐代書家有李世民、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薛稷、徐浩美、李邕、顏真卿、柳公權、楊凝式,但是其中能夠真正代表盛唐之風的只有顏、柳這一種典型的風格,與宋以后以江南為中心的書法文化圈重書卷氣、強調秀雅放逸一路的書法有著明顯的、本質的區別。
書法自清中葉以來出現了帖學與碑學之別,而早在唐中葉開始,清人眼中所謂的帖學體系內部出現了流美與渾厚兩大派系,其中流美指以二王一路為代表的江南尺牘風流,渾厚指以顏真卿為代表的渾厚質重一路的書法體系。其中帖學中渾厚一路的書法與碑學一路的書法,都與“長安書法文化”有著密切且深厚的歷史關聯,故此我們可以說半部中國書法史在長安。
(一)顏真卿書法中的篆隸義理與法度
顏真卿是唐時著名書法家,陜西西安人,善寫楷書,其楷書雄秀端莊,大氣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的氣象。其書法用筆渾厚強勁,善用中鋒,饒有筋骨,字內元氣鼔蕩,呈外拓之勢,與當時流行的二王流美、內厭一路的書法形成鮮明對比,在王派之后形成新的風尚,因其字點畫厚重,用筆藏頭護尾,常以藏鋒示人,點畫有篆隸書法的特點,論者常言其有“篆隸筆意”。
自秦代使用篆書,漢代使用隸書以來,字就有了義理,書法就以嚴瑾為頭等重要的標尺來看待。魏晉以后,書法家開始以書法中的筆勢為依據對字的筆畫作了簡省,從此以后以篆隸為中心的時代就終結了。人們對于篆籀的義理和隸書的嚴謹也就慢慢不太了解了,但是顏真卿《大唐中興頌》以后的書法都體現出了篆籀八分中的義理和法度。
所謂“篆籀八分中的義理和法度”,宋代朱長文在《續書段》中有論:
魯公《中興》以后,筆跡迥與前異者,豈非年彌高學愈精耶?以此質之,則公于柔媚圓熟,非不能也,恥而不為也。自秦行篆籀,漢用分隸,字有義理,法貴謹嚴。魏、晉而下,始減損筆畫以就字勢。惟公合篆籀之義理,得分隸之謹嚴,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①朱長文:《續書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第324頁。
顏真卿書法中既有篆書的義理又有隸書的法度,而這其中的含義又不同于清代碑學中的“篆隸筆意”。顏書中“篆書的義理”是指,顏體正書中如同周秦之鐘鼎銘文的一種氣息,就其本質而言是為了體現一種更具古老、高貴的廟堂氣;而“隸書的法度”是指顏體正書的裝飾和漢代官方正體隸書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都是將當時通行的文字加以修飾形成如同漢代八分的美術字,這當是顏體楷書中所謂的“篆籀之義理與分隸之嚴謹”。而清代書法中的“篆隸筆意”指的是書法家模仿鐘鼎、石刻文字中的筆道尋求筆法與運筆的感覺,運用到書法創作中以求體現出一種金石的韻味。這是清代碑學興起所賦予篆隸筆意的新內涵。故此,我們在研究盛唐書風中顏書的“篆隸筆意、篆籀氣”時應該要先明確這一點。
而周秦時代的篆書和兩漢時期的隸書正是“長安書法文化”中的重要內容,因此可以講顏真卿的書法既是“長安書法文化”的代表,同時也是“長安書法文化”的集大成者。對于顏真卿的楷書,尤其是晚年以后的楷書,后世學習者頗多,以至于出現了“學書當學顏”的說法。
“學書當學顏”這句話可以看作是顏真卿這一脈所代表的“長安書法文化”對后世的影響。后世學顏真卿書法或受顏真卿書法影響的書法家非常多,如宋代蘇東坡、黃庭堅的書法受顏真卿影響很大,清代劉墉、錢灃、翁同龢、華世奎也等都學顏真卿書法。在明白顏書的“篆籀之義理與分隸之嚴謹”之后,我們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這些書家門為什么都會提倡學顏,除了顏真卿之氣節之外,更大程度上是因為顏書具有一種美術字的傾向。
(二)長安書法文化碑學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
這里的“長安書法文化”指的是在漢代文人書法流派興起之前所謂的具有長安地域性風格的通行文字,這里具體指的是當時這片區域中政治集團所通用的文字,包括周秦一系的古文與漢代通行隸書。這類文字在明清之前都是實用文字,不能稱之為書法藝術,但是明清之際所興起的帶有金石韻味的書法,使這樣一種通用文字變成了書法藝術中的經典。
這一審美體現如何構建,清人阮元在《南北書派論》中有精彩的論述:
正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由鐘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鐘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尚沿北派余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啟犢,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是則中原古法,至隋末唐初,猶有存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為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為北派。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②阮元:《南北書派論》,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第630頁。
由此可見,所謂北派書法與南派書法有著本質的區別,用阮元的話講是“判若江河”,南派重行草,善寫尺牘,北派重正書,傳承中原古法,善寫榜書,這一點無論是在柳公權、歐陽詢,還是當今長安書法都是這樣,傳承性極強。而阮元所論“南北書派”的區別,正是構建清代碑學理論體系的依據。
碑學是晚明以來在學術圈中逐步醞釀開來的新的書法創作理念,在乾隆年間正式確立。以碑學命名主要是因為在這一書法創作理念下,書法學習和臨寫的范本大多是周、秦、漢、唐時期的金石拓片,清代以來的碑學書法理論體系以及碑學書家雖然在地理和心理上都是以東部沿海文化圈為中心,但是他們所取法的對象卻大多出土于以長安城為中心的關中地區。譬如鄭簠隸書學《曹全碑》,吳昌碩篆書學《石鼓文》,楊沂孫、吳大澂以及黃牧甫書學秦地出土的青銅銘文等。
從這一角度來看,清代的碑學雖然萌發、生長、活躍于東部沿海一帶,但其所取法追摹的對象大多來源于長安書法文化中心的關中地區,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清代的“碑學書法”受“長安書法文化”影響頗深。
二、長安書法文化對當代書法發展的啟示
綜上所述,長安書法文化雖是以古長安城為中心,但其影響并不止于一時一地,而是全方位的,與長安城在歷史上的地位密不可分。在唐代以前,歷史上的王朝大多選擇在長安建都,由此留下了大量的書法歷史遺產,這些遺產基本反映了中國書法前期的發展軌跡,是后世書法發展的根與本,也是當代書法發展的重要依托。
(一)顏真卿“篆隸筆意”與清代“篆隸筆意”之區別對書法學習的啟示
上文有論,顏真卿篆隸筆意的含義與清人所謂篆隸筆意的含義不同。顏書中的“篆書的義理”是指,顏體正書中如同周秦之鐘鼎銘文的一種氣息,就其本質而言是為了體現一種更具古老、高貴的廟堂氣。而清代書法中的“篆隸筆意”指的是,書法家模仿鐘鼎、石刻文字中的筆道,體會其中筆法與運筆的感覺,運用到書法創作中以求在作品中體現出一種金石的韻味,這是清代碑學興起所賦予篆隸筆意新的內涵。
這一點對于我們現在的書法學習有重要啟示。在過去的書法界一直流傳著學書當從篆隸書開始的言論,認為篆隸書是寫好其他書體的基本保證,但從顏真卿“篆隸筆意”與清人篆隸筆意之差別中我們看到,兩者在用筆上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清人在篆隸筆意中更強調“常使筆在畫中行”的中鋒用筆,而顏真卿的篆隸筆意是指作品呈現出來的篆隸書中的義理,本質上和用筆無關。
由此啟示我們在日常書法學習中要將帖和碑分開,這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書寫技巧與審美追求也存在天壤之別,不可混為一談。
(二)清代碑學體系的構建對書法史學習的啟示
清代碑學是在明代晚期碑學衰敗的情況下以金石學為依托創造的一種新的藝術觀念,這一觀念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反對帖學經典地位的意圖,將書法家的眼光拉到了帖學生發以前的時代,并在這一非經典體系的滋養之下創造出新的經典。
這就啟示我們學習書法史要從這兩個體系出發,以孤立的眼光去看待這兩段歷史,才能更清醒地關照、理解這段歷史。
(三)長安書法文化對西安書法發展的啟示
長安是一座古城,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瑰寶,論金文書法,與今西安相隔不遠的寶雞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論石刻書法,有始建于宋朝的碑林博物館,名碑巨作無數。這些瑰寶既屬于長安也屬于世界,是書法藝術發展的源動力,是長安書法文化的豐富遺產和歷史見證。在這些源動力的推動下,近現代乃至當代出現了一大批代表長安書法文化的優秀書家,有于右任、劉自櫝、衛俊秀、曹伯庸、吳三大、石憲章、鐘明善等。
于右任先生是陜西三原人,近現代著名書法家,善寫草書,引北碑入草,并開標準草書社,有當代草圣之美譽。劉自櫝先生和于右任是同鄉,劉先生書法以篆書見長,其篆書個性突出,自成一派,影響了一大批陜地青年書家。衛俊秀先生出生于與陜西相鄰的山西,其書法受清代書家傅山影響,善寫行草,氣韻高古,氣勢逼人。曹伯庸先生為陜西禮泉人,書法作品高古端莊,書卷氣息濃郁,對西北書法教育有很大影響。吳三大、石憲章二位先生均以善寫榜書著稱,所題榜書古樸沉雄,有漢唐遺風。鐘明善的書法作品清秀典雅,創辦西安交通大學書法專業,在書法教育方面影響較大。
近年來,隨著我國書法教學的蓬勃發展,西安許多高等院校也都開始重視書法人才的培養,先后有西安交通大學等十余所高校開辦書法專業,隨著書法藝術專業化發展路徑的逐步深入,長安書法文化必將在我國書法發展的進程中放射出耀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