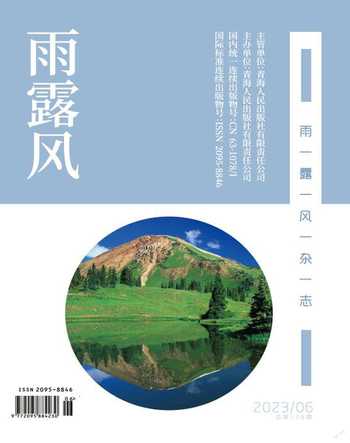以韓偓詩歌為例看唐末文人創作

以韓偓的詩歌為例來看唐末文人創作,有利于我們客觀評價這一時期的文人作品。從韓偓詩歌中能夠更好地了解唐末文人創作特點,了解唐朝末世詩歌創作風格。從詩歌賞析以及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掌握某個時代文學創作風格才能理解作品內容,體會到作品的藝術價值,達到促進文學發展的目的。
一、唐末文人創作特色
文學可以記錄一個時代,以不同的形式向同時代或未來展示作者對生活的理解。文學猶如一片森林,而每個朝代的文學猶如形態各異的樹,各個時代的文學名家如樹上的枝干,他們在社會政治、經濟的大環境下生長,他們窮盡一生,用自己的文學作品來感悟、澆灌和滋養后人。唐末亂世中的文人,唱著一首又一首末世的悲歌。
(一)幻滅、孤寂的情感特色
藝術來源于現實,又高于現實,文學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反映,并通過藝術創作手法,將作品升華,形成一部具有藝術價值的作品。因此文學創作往往和社會現實有著密切的關系。唐末文學的研究也應建立在唐末背景之上。唐末經濟衰落,政治不穩定,詩人仕途不順,也看到了一些凄慘的社會現象,因此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展現的情感也是冷寂、幻滅的,一方面抒發自己對當朝統治者的不滿;另一方面抒發對未來的惆悵,因此詩歌情感方面多以孤寂、幻滅為主。
如李商隱《賈生》作品中的名句“不問蒼生問鬼神”,表現的是對當朝統治者的不滿,統治者不關心時事政治,不關心民生,而是關心鬼怪的事情,表現了作者對當朝統治者的失望之情。又比如杜牧的《赤壁》《江南春》《泊秦淮》等詩歌作品,都流露出作者對現實的無奈,表現出失望、幻滅的情感。“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等詩句,都表現了作者對現實處境的不滿以及對當朝統治者的憤恨之情。
從作品中不難看出,唐末背景下,統治者治國不力,人民生活處境艱難。作者目睹這一切后有感而發,因此所表達的多為消極的情感,主要表現為對“現實的幻滅以及對統治者的失望之情”。
(二)憤世嫉俗的現實之作
唐末文人的創作心態早已經沒有了盛唐時期那種自信和自豪,這一時期文人的命運似乎更加悲慘。文人作為社會中的重要成員,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擁有建功立業的偉大抱負。唐朝鼎盛時期,是我國歷史發展中最為輝煌的時期,文人期望走入仕途,獲得更好的發展。唐末詩人也有積極的處事態度,渴望通過做官獲得個人發展。但是在唐朝末年,文人晉升的仕途被堵塞,統治者昏庸無道,不注重招攬人才,因此當文人墨客屢次碰壁之后,出現了憤世嫉俗的現實之作,表現出憤恨、失望之情,這種處事態度也體現在文學作品中。如杜牧《贈別》中,將人間離愁歸咎于道路,“門外若無南北路,人間應免別離愁”,這里把人間離愁歸咎于門前有路,看似毫無道理,但卻十分巧妙地表現了離愁別恨的情感,怨憤無處發泄而遷怒于道路,也表達了作者對現實的憤恨之情。天下不穩定,民不聊生,“文人對這種現象感到無可奈何,進而出現了憤恨的消極態度”[1]。
(三)借用典故諷喻當世
唐末時代背景給詩人提供了一個絕望、迷惘的現實處境,作品中所表達的情感多以冷寂為主,表現出對現實的失望之情。因此唐末的文學創作和盛唐時期的文學創作最大的不同表現為更傾向于憤恨情感的抒發,這種情感的抒發更為隱忍和朦朧,因此在創作手法上往往借用典故,用來諷喻當朝統治者。
李商隱和杜牧是唐末兩位重要詩人,其二人作品中也較多地運用了典故,比如李商隱的《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詩從一開始就感嘆“我來不見隆準人”,流露出對封建統治者的失望,敘寫這段時期困窘失意的境遇。另外引用燕照臺來表達自己懷才不遇的現實處境,并引入陶淵明表達自己不愿意歸隱,想要做一番事業,即“不賦淵明歸去來”,并表達自己建功立業的決心。又比如杜牧《赤壁》作品中也是將赤壁之戰作為典故來表達自己的情感。
二、以韓偓詩歌為例看唐末文人創作
“世為京兆萬年人。偓十歲能詩,商隱同登開成四年及第,又同為王茂元婿。死于患難,百折不渝……”[2]韓偓是一位始終心系家國的士人,有詩云:“事往凄涼在,時危志氣銷。若為將朽質,猶擬杖于朝。”又有“聞道復官翻涕泗,屬車何水在茫茫”,韓偓在唐末環境影響下的詩歌創作具有孤寂的藝術特色。
(一)冷艷、凄苦的藝術特色
韓偓詩歌作品也正是基于唐朝末期時代背景所創作的作品。在亂世、政治腐敗的社會背景下,作者的情感更加凄苦,更加冷寂。從韓偓詩歌中可以看出,他大量使用寒冷、寂寞等字眼,真實地反映了唐滅亡前的混亂局面和滅亡后作者內心的悲痛。韓偓在逃亡異地時寫下《避地寒食》:“避地淹留已自悲,況逢寒食欲沾衣。濃春孤館人愁坐,斜日空園花亂飛。路遠漸憂知己少,時危又與賞心違。一名所系無窮事,爭敢當年便息機。”詩中的“哀、冷、孤、亂”不僅反映了詩人的孤獨和不安,也表達了作者的憤慨,蘊含著無盡的哀傷之情。又如《即目》詩歌作品中“幾聲愁緒溺風光”,作者通過現實場景中的春草、夕陽等抒發了凄婉而沉重的情感。
(二)以花入詩,呈現凄美意境
韓偓善于通過描寫“花”表達傷別離以及憤恨、愁苦等情感。《全唐詩》三百二十首韓偓詩,其中一百七十多首有春意、涉春、花等內容,幾乎占了所有詩篇的一半。惜花、傷春是韓偓詩歌中必不可少的主題,這類詩歌將“無法排解的感傷情緒通過細小纖柔的題材表現出來,構成一種幽約低徊、纏綿徘惻的境界”。對韓偓三百多首詩作粗略地統計后發現,“花”作為意象頻繁地出現,而在以“花”為意象的詩中也常以“風”來襯托凄涼之感。在他的詩歌中“花”和“風”等字樣出現的頻率較高。面對唐王朝的衰敗之勢,杜牧發出了“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杜甫發出了“感時花賤淚,恨別鳥驚心”的末世之音。在韓偓以“花”為意象的詩中,有直接寫“落花”的,也有間接寫“落花”的,并非單純的寫景狀物,而是通過對“花”這一意象的描寫來反映詩人內心的無力之感。如《惜花》從殘花、落花、花落后的遭遇,一直寫到詩人的送花、別花和想象中花落盡的情景,充分展現了詩人面對春花消逝的流連哀痛之情。全詩緊緊扣住一個“惜”字,逐層推進,反復渲染。又比如《殘花》一詩中“蔫香冶態猶無窮”,描寫大雪中花的狀態,雖然下雪,但是依然能夠展現自己優美的姿態,通過描寫殘花映射自己的狀態,雖然自己現實處境并不理想,但是對未來依然充滿信心。詩人善于以“梅花”入詩。梅花自古以來就是文人墨客常寫的意象,代表著堅韌不拔、堅貞不屈的精神品質。韓偓詩中的“梅花”代表著詩人內心的精神世界,象征詩人不畏強權,不同流合污的精神品質。《亂后春日途徑野塘》一開頭就以“世亂”為始,在亂世中突見梅花凋落,詩人內心不免憂傷徘徊,詩人以梅為喻,抒發了他在亂世中的痛苦,以及他當時的艱難處境。此外,詩人還把梅花飄落與國家的興衰聯系在一起,在韓偓充滿悲情的口吻中,我們能感受到詩人慨嘆國家將亡的悲哀之情。
(三)借古諷今的感時之作
韓偓在入閩之后,詩中典故的運用較前明顯增多。在被貶以后涉及政局、社會動蕩以及抒發人生情志的詩中,詩人之意在于借用典故借古諷今,含蓄表達當時作者的情感。
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3]。唐末動蕩的社會變局中,文人常常通過一種價值的轉移,在作品中彰顯出時代性。韓偓赤膽忠心的人格,堅貞不屈的氣概和他矢志不移的決心,體現在文學作品中就是韓偓的時事詩。這一類詩歌從側面反映出來唐末亂世環境下的政治變遷以及動蕩的局勢。韓偓入朝的八九年間,皇帝孤立無援,權勢已去,劫亂驟起,韓全誨劫持昭宗前往鳳翔。又如《感事三十四韻》這首記事長詩,詩人用近乎血淋淋的方式,歷數了“昭宗后期宰相弄權、中人為禍、遞相傾軋,最終導致鳳翔劫遷、朱溫篡唐,對謀諸宦官過激,至養虎求全又引狼入室等一系列誤國決策”。并毫不遮掩地將朱全忠之輩等同于歷史上臭名遠揚的司馬昭、董卓。對崔胤養虎為患的誤國決策,給予批評“只擬誅黃皓,何曾識霸先”。整首詩帶有很深的反省意味,特別是詩歌的結尾句,除了抒發唐亡的悲傷之情,還流露出深深的無奈。韓握還有大量詩歌如《觀斗雞偶作》《火蛾》《有感》等,指斥那些趨炎附勢投靠朱全忠而為非作歹的人,對于朱全忠篡權立帝行為,更是進行了犀利而辛辣的諷刺。詩人生于晚唐,死于后梁。他將唐末與五代十國初那段動蕩的歷史納入詩中,將悲愴的情緒融入優美的詩句中,有杜甫的遺風,享有“唐末詩史”的美譽。
三、結語
“從整個唐代文學發展來看,唐末文學無論從成就還是氣象上,都無法與前面幾個時期相比,但作為亂世文學的典型代表,唐末文學有其獨特的時代內涵和文人心理。”[4]韓偓詩歌的藝術成就和他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因而韓偓的詩歌是其他文人在唐末文學環境中的集中體現。因此,對韓偓的詩歌創作進行探究,可以更好地對唐末文人創作及其成就與價值作出客觀的分析與評估。
作者簡介:彭迎兵(1998—),男,土家族,重慶酉陽人,貴州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學科教學(語文)。
注釋:
〔1〕方文晶.韓偓詩《已涼》[J].書畫世界,2021(11):57.
〔2〕韓偓.韓偓集系年校注.吳在慶,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3〕李定廣.國家不幸詩家幸[D].上海:復旦大學,2003.
〔4〕艾炬.唐末文人心態與創作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