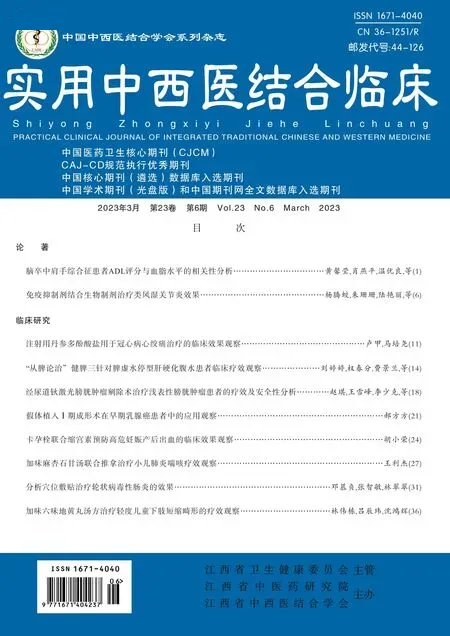卒中后痙攣發病機制及治療研究進展
龍穆麗 徐宏
(1 廣西中醫藥大學 廣西南寧 530001;2 廣西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康復科 廣西柳州 545001)
腦卒中是全球第二大、中國第一大死亡原因,同時也是全球成人殘疾的首要因素[1~2]。最近有學者預測,直到2040 年腦卒中仍將是全球前三位死亡原因之一[3]。我國腦卒中患病率和發病率呈上升趨勢,2013 年中國每年約有1 100 萬流行病例,200 萬新發腦卒中和100 萬腦卒中相關死亡[4]。在過去的30年里,腦卒中患病率和病死率存在明顯的地域和城鄉差異,反映了腦卒中危險因素患病率、腦卒中醫療服務可及性和質量的地區差異[5],許多卒中患者在卒中后數月至數年發展出各種醫療、肌肉骨骼和心理社會并發癥[6]。
痙攣是腦卒中患者發病后常見癥狀,表現為速度依賴性的肌張力增高伴腱反射亢進[7]。Persson 等[8]通過對年齡<70 歲,患急性腦卒中≥7 年的患者進行隨訪評估,發現年齡、手臂輕癱、失語、面癱是痙攣的獨立危險因素。Shin 等[9]對韓國3 056 例腦卒中患者進行調查,發現腦卒中后3 個月痙攣發生率為6.8%,6 個月為6.9%,12 個月為7.6%,表明痙攣程度越嚴重的患者,運動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等功能狀態越低。本研究對卒中后痙攣的發病機制、中西醫常見治療方法進行綜述。現綜述如下:
1 卒中后痙攣的發病機制
痙攣屬于上運動神經元(Upper Motor Neuron,UMN)損傷后的陽性表現之一[10],Lance[11]將其定義為速度依賴性的強直性牽張反射增加(即肌張力增高),并伴有過度的肌腱抽搐狀態,其特征是由肌肉的被動伸展觸發的不自主肌肉過度活動[12]。肌肉張力是由脊髓和脊髓上機制的復雜相互作用維持的,這些機制的破壞導致痙攣和僵硬[13]。有研究指出,導致痙攣患者肌張力增高的因素有以下幾個[14]。
1.1 脊髓運動神經元輸入的改變 來自肌肉的肌梭傳入反饋可以通過激活l g 傳出神經(肌梭運動纖維)系統增強肌梭的敏感性[15~16]。例如對于前臂伸肌,腦卒中患者紡錘體傳入的背景放電頻率為6.665,3 Hz(n=526),健康對照組為6.466,1 Hz(n=576)[17],這些數據表明,增強的腓腸肌驅動是不需要的,也可能不會發生在痙攣狀態。通過突觸前抑制調節傳入神經元與運動神經元突觸處的遞質釋放,來自外周的感覺反饋進入脊髓的突觸效能被突觸前抑制不斷過濾[18],這一機制涉及軸突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能突觸對傳入末梢的去極化[14]。研究認為在偏癱和脊髓患者中,突觸前抑制的降低是痙攣的主要驅動力。也有研究表明,在靜止與脊髓痙攣狀態下,突觸前抑制降低,但在偏癱痙攣狀態下,突觸前抑制并不降低[19]。另一種通過在Ia 類傳入神經與運動神經元的突觸上耗竭遞質[18],當Ia 類傳入神經在低頻(例如10 Hz)被重復激活時,運動神經元突觸處興奮性遞質的釋放受到抑制,這種異常與痙攣程度相關[20]。
1.2 運動神經元興奮性反射環路的變化 在靜息狀態下,偏癱痙攣患者的某些環路興奮性可能發生改變,但與痙攣程度的相關性較小,而且改變也常常發生在未受累的非癱瘓側上[14]。例如反復倫肖(Renshaw)抑制,也許是因為倫肖細胞從下行控制中釋放,復發抑制在卒中患者的靜息狀態下增加,而不是減少,導致在肌肉自愿收縮時正常的調節機制失衡[21];相互Ia 抑制,有研究顯示偏癱患者脛前運動神經元的相互Ia 抑制增加,通過神經阻滯可以改善背屈肌力[22]。互易性Ib 易化與夸張的踝關節抽搐同時出現,并可能導致痙攣的反射亢進[23]。在靜息狀態下偏癱受試者的下肢,雙側股四頭肌運動神經元的Ⅱ組易化通路中存在增強的傳導,這是電誘發Ⅱ組截擊的通常測試池[24]。這種增強被Ⅱ組神經元間環路中的選擇性傳導阻斷劑鹽酸替扎尼定抑制[25]。在運動過程中,股四頭肌運動神經元的Ⅱ組易化大于正常受試者[26]。但股四頭肌運動神經元的Ⅱ組易化增加與偏癱痙攣程度不相關,如Ashworth 評分[24~25]。
1.3 運動神經元內在特性的改變 有研究表明,運動神經元內在特性的改變有助于脊髓痙攣和屈肌痙攣[27~28],并為藥物治療脊髓痙攣提供了理論基礎。然而在受試者中,偏癱痙攣狀態的表現并不一致,有時在平衡狀態下是陰性的[29]。痙攣的原因和運動神經元損害相關殘疾在個別患者中存在差異。一般而言,靜息狀態下患者肌張力增高和腱反射亢進的主要原因是Ia 傳入與運動神經元之間突觸的同質性抑制減弱、運動神經元特性改變和肌肉特性改變,以及通過第Ⅱ組反射通路的過度傳遞可能是重要的,個別患者的其他脊柱環路可能存在重要改變。在運動過程中,存在通過所有或大多數脊柱回路傳輸的脊髓上控制缺陷,以及通過其他途徑自適應“分流”運動指令,這些變化導致運動神經元放電失去精細控制[14]。
1.4 小腦-丘腦-大腦皮層通路 肌張力障礙除基底節感覺運動環路異常外,也許同時與大腦皮層、小腦、腦干網狀系統相關,即小腦-丘腦-大腦皮層通路異常[13,30~31]。小腦作為調節運動及維持平衡的主要結構[32],Eline 等[33]研究發現,低髓鞘化伴基底節和小腦萎縮的患者幾乎都有突出的錐體外系運動異常,這種異常在低髓鞘患者中很少見。有實驗表明,對有肌張力障礙的小鼠選擇性剔除小腦的扭轉蛋白A(Torsin A)可以誘導肌張力障礙表現,發病程度與剔除的數量有關,而剔除基底節區的Torsin A 不會出現肌張力障礙[34],結果更傾向于小腦參與肌張力障礙發病過程。目前尚不清楚小腦與其他神經系統通過怎樣的方式產生聯系,但在基底神經節、小腦和大腦皮層發現了大量的神經信號變化。事實上解剖示蹤和電生理研究表明[35],感覺運動皮層、基底神經節和小腦組成了一個主要的平行多突觸(即傳入和傳出)皮層通路,小腦浦肯野細胞輸出通過雙突觸小腦-丘腦投射介導紋狀體神經元的興奮性,關于肌張力障礙的神經解剖學基礎的概念,已經從相對狹隘的關注基底節功能障礙演變為更廣泛的運動網絡模型[30]。因此,為了找到更適合不同發病機制肌張力障礙的治療方法,探索更多潛在結點是必要的。
通過以上研究,我們可以推測小腦-丘腦-大腦皮層通路可以作為肌張力障礙的潛在治療靶點。腦深部電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作為近年來受到較多關注的新型治療方法,已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認可用于治療肌張力障礙,迄今為止已有超過50 項不同研究評估了DBS 治療肌張力障礙的效果[36]。一項蒼白球刺激對孤立性肌張力障礙的療效結果顯示,遺傳性肌張力障礙和特發性肌張力障礙患者的運動功能、殘疾和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均有顯著改善,多個量表(Burke-Fahn-馬斯登肌張力障礙評定量表、多倫多西方痙攣性斜頸評定量表)也證實了這一點。數據表明平均有65%的癥狀減輕,且效果持久[37]。而DBS 治療的臨床成功為包括經顱磁刺激和聚焦超聲在內的其他形式的神經調節鋪平了道路,導致對光遺傳學、超聲遺傳學和磁遺傳學的興趣增加[36]。所以研究小腦通路對肌張力障礙治療方案非常有幫助。
2 卒中后痙攣的西醫藥治療
卒中后并發肌張力增高可引起疼痛、肢體畸形、關節攣縮、壓瘡等繼發性損害[38]。當患者功能受到影響或疼痛引起不適時,應考慮治療。治療目標是減輕患肢過度的肌張力,以增加患者的功能能力和減輕不適。目前有多種治療方案,包括物理、手術和口服藥物治療[39]。常用口服抗痙攣藥物有作用于GABA能系統的加巴噴丁、苯二氮類及巴氯芬,作用于α2 腎上腺素能系統的替扎尼定和鈣離子釋放阻斷劑丹曲林。針對101 項研究口服抗痙攣藥物的系統評價[40]指出,這類藥物缺乏高質量的試驗,并且發現替扎尼定、巴氯芬和丹曲林對痙攣狀態的療效證據有限,盡管這些藥物已在臨床長期使用。ACochrane[41]關于脊髓損傷后痙攣性管理的研究發現9 項試驗共218 名受試者,僅替扎尼定導致Ashworth 評分顯著降低。服用替扎尼定的患者服用安慰劑的不良事件也明顯增多,缺少充分理論支持抗痙攣藥物導致功能改善[41]。對469 例非進展性神經系統疾病患者的12項隨機對照試驗進行系統評價,口服抗痙攣藥物療效的證據“稀缺且薄弱”。在同種口服抗痙攣藥物中,替扎尼定導致Asworth 評分降低,但未改善功能[42]。巴氯芬被當作是口服痙攣藥物的首選,國家衛生與臨床優化研究(NICE)指南推薦巴氯芬作為一線藥物用于治療痙攣性多發性硬化癥的兒童和年輕人[43~44],第二線選擇替扎尼定和丹曲林。苯二氮卓類藥物與NICE 指南推薦第一、二類抗痙攣藥物具有相似的療效,但副作用表現得更加明顯,嗜睡以及行為副作用限制了在白天使用苯二氮卓類藥物。氯西泮對在夜間發作的痙攣癥治療特別有效,通常起始劑量為每晚250 μg,最大劑量為1 mg[39],約50%的成年人依從口服抗痙攣藥物治療[45]。大麻素是大麻中的藥理活性化合物[46],內酯大麻素受體(CB-1 和CB-2)廣泛分布在腦和脊髓中,四氫大麻酚主要作用于這兩種受體,可有效減少痙攣狀態,但會引起精神藥物和鎮靜副作用。大麻二酚對兩種受體具有較低的親和力,并降低四氫大麻酚的精神藥物和鎮靜作用。Nabiximols(一種口部噴霧劑,由9-δ-四氫大麻酚和大麻二酚的a1:1 混合物組成)在美國用于治療多發性硬化癥患者的痙攣狀態獲得允許,來自三項試驗的666 例患者原始數據的薈萃分析報告了耐受性良好,35%的治療組參與者僅對患者報告的測量結果有所減少[47],但如果在治療4~6 周后沒有改善,則應停止使用大麻素。肉毒毒素經常以肌肉注射的方式來使用,當被注入骨骼肌后,通過阻斷神經肌肉接頭處乙酰膽堿的釋放,從而削弱靶肌肉的選擇性,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沒有全身虛弱或鎮靜副作用的情況下,是一種局灶性降低。兩項隨機對照試驗,一項96例,另一項333 例成人卒中后肌痙攣,使用肉毒毒素治療后,改良Ashworth 評分降低,但功能無明顯改善[48~49]。鞘內注射相對小劑量的巴氯芬可使藥物在脊髓內達到較高濃度,從而產生良好的肌松作用,且無全身副作用,該藥物對脊髓損傷、中風和多發性硬化癥繼發痙攣的治療有效[50]。化學神經溶解術通過向神經內注射苯酚或酒精,使蛋白質變性凝固破壞外周神經,一項納入20 例患者的隨機對照試驗發現,神經內注射5%苯酚或50%酒精均可導致踝跖屈肌痙攣顯著減輕[51]。
3 卒中后痙攣的中醫藥治療
卒中后痙攣在中醫可歸為“瘛瘲、痙證、筋痹”等范疇,《難經·二十九難》中闡述:“陰蹺為病,陽緩而陰急;陽蹺為病,陰緩而陽急,人生于陽而根于陰,根本衰則人必病,根本敗則人必危矣,所謂根本者,即真陰。”中醫認為腦卒中后肢體痙攣狀態是陰陽失調所致[52],故調節陰陽平衡是治療的關鍵。陳瑛玲等[53]運用栝樓桂枝湯治療卒中后肢體痙攣患者,結果顯示治療組肌電積分(IEMG)及日常生活活動能力改善均優于對照組;姜美玲[17]通過對50 例患者比較發現,大秦艽湯配合康復治療在改善上肢運動功能方面較單純康復組效果更好。小續命湯出自《備急千金要方》,在唐代以前內風理論尚未興起,常用于治療正氣虛弱、外風侵襲之中風癥,劉薇等[54]運用其治療中風-風痰阻絡證后發現,上肢肌痙攣的試驗組與對照組肱二頭肌、肱三頭肌IEMG、肌電均方根(RMS)值均降低,且試驗組測試肌肉的RMS 值低于對照組(P<0.05);封桂宇[55]在中風患者偏癱側拮抗肌使用經筋刺法,以壓痛點為腧,結果表示該療法相較于傳統針刺法對抑制痙攣側亢進的肌張力增高作用更佳;柴豐超等[56]通過觀察對痙攣患者患側肩髃、曲池、外關、養老、陽陵泉、足三里、三陰交及局部阿是穴等穴位的火針治療效果發現火針組治療有效率為90%,優于普通針刺組的60%(P<0.05);李九席[57]研究中藥熏蒸聯合血府逐瘀湯治療中風后痙攣與西藥巴氯芬相比較,治療4 周后,研究組與對照組總有效率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12 周后研究組總有效率為88.10%,對照組為69.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孫秀業[58]通過試驗證明,電針聯合經筋刺法可有效改善中風后肢體痙攣四肢簡化Fugl-Meyer 運動功能(FMA)與日常生活能力(ADL),且對人體無副作用;劉雁等[59]證明在中風后痙攣期采用放血療法配合康復功能鍛煉可獲得比單純康復訓練更好的療效, 顯著降低患側肢體的肌張力,提高患者運動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
4 總結與展望
通過不斷探索、更新對卒中后痙攣發病機制的認識,對該病的發生發展進一步加深,并且對于新型有效治療技術的開發起到了推進作用。西醫治療存在見效快、運用廣等特點,但目前還沒有一種藥物能完全緩解痙攣狀態,且長期口服西藥可能對肝、腎帶來負擔。而中醫治療經過時間及實驗證明對該疾病治療有一定效果。痙攣是卒中后常見的一種并發癥,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了解其發病機制及治療趨勢,有助于更好地從中西醫結合方面提高治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