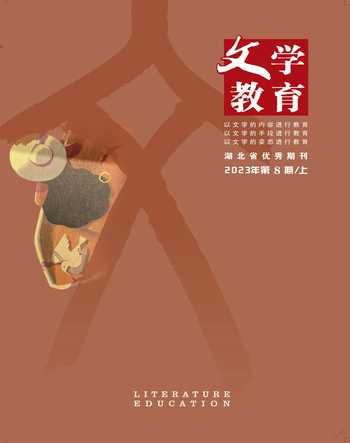論劉亮程散文作品的寫作姿態
王瑜
內容摘要:面對圍繞著劉亮程的爭鳴,本文從劉亮程的寫作姿態和散文世界兩方面入手,既分析了劉亮程真誠的寫作姿態和鄉村自然哲學的寫作立場,又對他的散文世界進行了剖析,肯定了劉亮程的哲學思考,也從社會發展和群體關懷的角度對其提出了批判和展望。
關鍵詞:劉亮程 寫作姿態 散文世界
自1998年劉亮程出版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起,作為一個曾經地地道道的農民,劉亮程幾乎創造了一個文壇奇跡。
2000年初,《天涯》、《北京文學》、《南方周末》等報刊對劉亮程的散文給予高度評價。2001年初,他和他的作品引起了諸多學者的研究和討論,并被一些評論家譽為“中國20世紀最后一位散文家”、“鄉村哲學家”。2001年4月,劉亮程被授予第二屆馮牧文學獎文學新人獎。2001年底,社會上掀起了“劉亮程熱”,與此同時散文界也出現了“劉亮程現象”的爭鳴熱潮,圍繞的關鍵詞為“詩意的鄉村”、“鄉村哲學家”和“鄉村神話”等等。
在散文界對劉亮程現象及其散文的爭鳴與反思中,有兩種觀點極端分化,一方認為劉亮程的散文是封閉與反現代性的,是鄉村哲學的“神話”,對其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另一方認為他是中國文學傳統詩意的“麥田守望者”,他的散文具有真正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并對其給予極高的贊譽。這兩種觀點主要見于《鄉村哲學的神話——“劉亮程現象”的反響與爭鳴》一書中。
因此,在評述當代散文作家作品時,劉亮程或許是一個頗有價值也繞不過去的存在。如何對劉亮程散文進行全面、客觀的研究和評述也就成為一件復雜和重要的事情。
一.劉亮程的寫作姿態
1.真誠與虛偽
劉亮程書寫的全部內容是關于一個村莊,這個村莊有一個真實確定的名字——黃沙梁。這是他的家鄉,他稱之為母親的地方。在長達半生的時間里,劉亮程在文學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描摹與懷念這個地方。同時這長達半生的時間,也是劉亮程一路遷移的過程。黃沙梁荒涼閉塞,劉亮程靠著自己,靠著一支筆,把家一步步從僻遠的黃沙梁遷到了靠近縣城的元興宮村,又從縣郊的元興宮村遷到了沙灣縣城,并最終遷到了首府烏魯木齊。這是一個農人向上遷徙的輝煌歷程。
文學與現實好似在此發生了赤裸裸的悖離,一路遷移,一路懷念。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懷念為何要不斷地遷移?既然已經遷移為何又還要懷念?我以為這看似悖離的現象,其實包裹了劉亮程作為農人和文人的雙重糾葛和憂傷。
劉亮程曾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在童年與青年時期,他長久地生活于黃沙梁,一個沙漠邊緣荒涼閉塞的地方。隨著世事變遷,這樣的村莊注定是養不住人的,尤其是有抱負的聰明人。在《一個人的村莊》——“家園荒蕪”那一輯中已經隱約暗示了村人遷徙,村莊破敗的事實。劉亮程一家不過是較早遷移的那一批。對于一個農民而言,劉亮程的遷移史,無疑是向上和輝煌的歷程。遠離偏遠、落后、貧窮,追求更好的生活,是每個人最基本的生活愿望。換做其他人,這樣的成功甚至可以當作炫耀的資本。
然而不幸,劉亮程還是一個文人。文人的敏感與聰慧,使他更深切地體會到了向上遷移的另一面——家園失落的傷痛。不斷地變換與遷移,使劉亮程成了一個沒根的人。一個外鄉人,要在一個新地方熟識與生根,是多么的艱難,它不只需要時間,還需要耐心,或許更要忍受心靈的巨大孤寂。
劉亮程的書寫,就是心靈還鄉的過程。而心靈還鄉的無實體性,注定依靠的只能是記憶、經驗、感悟和冥想。劉亮程曾說過:“我在這個村莊生活了二十多年,我用這樣漫長的時間讓一個許多人和牲畜居住的村莊慢慢地進入我的內心,成為我一個人的村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村莊。”[1]劉亮程筆下的黃沙梁,也就不再是那個真實的荒涼閉塞的小山村。雖然村莊里有名有姓的人不少,韓三、馮四、張五、馮三、韓老大、馮富貴……有靈性的事物也不少,大榆樹、牛、馬、羊、風、草、樹、野地……可是真正的人,面目清楚、有思有為的人卻只有一個,那個背著鐵锨在村里閑逛的劉二(劉亮程)。黃沙梁是他一個人的村莊,是他永恒的心靈家園。在文學上,在心靈中,這樣對于故鄉的皈依和懷念無疑是真誠的。
2.自足與現代
曾有論者質疑,劉亮程的寫作消解了鄉村的貧瘠和苦難,而展示給我們一個澄澈、樸拙、悠遠的地方,這不是那個真實的荒涼偏僻的黃沙梁。真正的農人,恐怕亦不會感覺到自己的生活有多少詩意,與之相伴的大多是辛勞、貧窮。在過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現代,或許還要加上越來越下降的社會地位和對城市生活的欣羨和向往。
詩意鄉村,無論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過去,它與廟堂功名相對;在現代,它與都市文明相對。“詩意”,本身即是一種態度,它是文人對鄉村冠以的稱呼。劉亮程對黃沙梁的心靈返鄉,本質上即基于對外界都市文明的對比。
鄉村無數次被人代言,卻又無數次處于失語的境地。它不知道有無數人在對它唱誦贊歌,也不知道無數人在對它表示向往。農人生活于自己的方寸之間,像一群靜默而麻木的存在。但在靜默之外,若有機會獲得利益,他們也會毫不吝惜自己的狡黠。從這一點看,劉亮程確實離鄉村很遠。
但是,這種質疑是站在現代理性基礎上的,強調的是現代觀念下對于鄉村的反思和觀照。而劉亮程使用的恰恰不是現代理性思維。劉亮程的哲思、語言和經驗,全部都是黃沙梁的,全部都是村莊式的。即使在外兜兜轉轉一圈,他奉行的依然是村莊式的自然哲學,就像老百姓說的“命”,或者說“存在即合理”。就是說一件事物即使不合理,在命定的自然軌跡下,到最后也會慢慢發現它的合理之處。從積極的角度說,它讓人更安心地面對命運、順應生活;從消極的角度看,這是一種靜態的向下的哲學,沒有任何前進的可能,甚至有消解苦難的危險。
例如《狗全掙死了》[2]一文中,因為村里有點兒本事的人都搬走了,輪到一幫尕小子輪換當村長。當過村長的人全富了,村里也被胡整的不像樣了。劉亮程對這件事情的態度卻是:“這個村莊真是幸運,幸虧聰明人全走了。若讓一個聰明人當上村長,村莊可能早變樣了。他會把難看的破墻爛房子推倒,把像把鉤鐮形狀的黃沙梁村規劃成長方形或正方形……如果這樣,這個村莊才真正地完蛋了。”[3]
劉亮程并沒有站在現代理性的角度,對這種現象給予批判,或者對遭殃的村莊表示悲憫,而是始終站在自然的命定的角度上思考。例如面對一件本來不好的事情,拿一件假想的更不好的事情來類比,也就從中看出好和幸運來了。這就是典型的鄉村自然哲學。
當代散文界對劉亮程現象的討論,聚焦點之一即是對他散文中的封閉與反現代性的批判,顯然,這是因現代理性思維和鄉村自然哲學這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而造成的沖突。
二.劉亮程的散文世界
劉亮程說:我全部的學識是我對一個村莊的認識。于他而言,村莊是一個完滿和自足性的存在。近百年來中國的思想動蕩、現代理性意識,并沒有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記。可以說,劉亮程全部的成功和缺陷,都與村莊緊密聯系。因此,村莊也就成為劉亮程及其作品研究的重要切入點。需要注明的是,這里的村莊并不是狹義的農民生活的地方,而更代表了一種認識自我和面對世界的方式,與中國傳統的哲學和美學相溝通。
因此,接下來本文將主要談論劉亮程以村莊為主體的散文世界,并試圖對他的價值和不足給出自己的評判。
1.鄉村自然哲學的圓滿與局限
劉亮程筆下的黃沙梁是一個真實而又虛幻的存在。在這里是沒有時間的,確切的說是沒有年代,它好像從遙遠的亙古就已經存在,是一個巨大的靜態。它與中國的社會,世事變遷毫無關系,就像懸浮于天空之上,孤立于黃沙之上。
時間的流逝、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在劉亮程的筆下都被抹平了。而當一個世界沒有了時間的衡量,抹去了差異與變動的可能性,那么一切事物的意義也就變成了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
在黃沙梁,稍細心點便會看到這樣兩種情形:過日子的人忙忙碌碌度過一日——天黑了。慵懶的人悠悠閑閑,日子經過他們——天黑了。天從不為哪個人單獨黑一次,亮一次。馮四的一天過去后,村里人的一天也過去了。誰知道誰過得更實在些呢。[4](注:馮四是村里最窮的人,家徒四壁,光棍一生。)
生命的現實奮斗意義被消解了,或者說與長久的重復的日子、與最終相同的死亡結局相比,它們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劉亮程轉而把關注力投向了人的心靈,他說:
長在人一生中的荒草,不是手中這把鋤頭能夠除掉的。在心中養育了多年的那些東西,和遍野的荒草一樣,它枯黃的時候,是不大在乎誰多長了幾片葉少結了幾顆果的。[5]
劉亮程站在生命的終極看待人生和世界,通過對外在差異與榮辱浮沉的抹平,他凸顯了心靈的意義并撫慰了一顆顆焦渴的靈魂。這是一種植根于古老農耕文明的哲學,它的前提是社會時間是重復的,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微小的。物質文明的窮困或富有并不會太過影響到各自的生活。但是今天,當現代文明飛速發展,時間變成金錢,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無限增大,我們又要如何無視甚至抹平這些現實差異而去專注于心靈?
顯然,劉亮程并不能給我們提供一種辦法。這樣的哲學不是讓人清醒的,而是讓人沉醉的。在現實生活中,這是一種靜態的和向下的生活哲學,通過抹平大與小、好與賴、勤勞與懶散、成功與失敗等種種概念,消解向上和奮斗的意義,而代之以心靈的關注。或許它會讓人一時忘記現實中的紛紛擾擾,然而無所依傍的心靈修煉,注定是一場幻想的烏托邦,剩下的只能是無盡的冥想與面對現實的虛空迷惘。
在這一點上,村莊成就了劉亮程,也限制了劉亮程。他的哲學,接續了傳統的老莊思想和自然的天道恒常,本質上說有著極為超越的人文關懷,然而村莊經驗限制住了他。在當代,村莊經驗面對世界的有效性是頗可懷疑的,但劉亮程對自己的知識和村莊,卻深負自信與迷戀,并試圖由此上窺天道。
那些我沒去過的地方沒讀過的書沒機會認識的人,都在各自的局限中,不能被我了解,這是不足以遺憾的。我有一村莊,已經足夠了。當這個村莊局限我的一生時,小小的地球正在局限著整個人類。[6]
這可以看作是宣誓的豪言,也可以看作是井底之蛙般的自大。所以雖然他的哲學站在超越的角度,有著生命終極意義上的人文關懷,但根植于村莊的生存背景和闡發基點,與當代社會發展的格格不入,都決定了它只能成為一劑安撫心靈的良藥,卻無法提供更切實的理性思考和指導意義。
2.鄉村的孤獨與憂患
劉亮程的寫作是經驗敘事,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鄉村生活的白描畫,這個村莊當然是詩意的,但浸透的卻不是人間幸福的溫暖,而是籠罩著村莊的一個人的巨大孤獨。
在這個村莊里,處處游蕩的只有一個“我”——這是一個扛一把鐵锨,在村外野地上閑逛的人。在《我改變的事物》一文中,他說:“我得給自己找點閑事,找個理由活下去。”于是他“會花一晌午工夫,把一個跟我毫無關系的土包鏟平,或在一片平地上無辜地挖一個大坑。”他會拉直一棵長的歪的樹,會把麻雀從一棵樹上趕到另一棵樹上。他說:“我相信我的每個行為都不同尋常地充滿意義”。這些閑事的意義,就是他活下去的理由。
這是一個孤獨的人,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鄉村貧瘠又辛勞的務農生活,不是他的志愿所在,他被村里的人說成是“閑錘子”。雖然身在鄉村,但劉亮程從不是一個真正的農民。他的心事與農民的心事不同,他的行為與農民的勞作不同。在心底里,他認為村人們日日的忙碌與勞作是無意義的,甚至說,他反對一切為了具體事務和功利的勞作。在他看來,那些常規的事——娶妻生子翻地種麥,早就結束了。他說:
我在村人中生活了幾十年,什么事都經過了,再待下去,也不會有啥新鮮事,剩下的幾十年,我想在花草中度過,在蟲鳥水土中度過。[7]
劉亮程選擇遠離人群,取而代之的是,他和驢說話,和螞蟻說話,和風說話。在城市,他反對現代人蠅營狗茍,追名逐利的生活方式;在鄉村,他蔑視一切日常的重復前人的事物與勞作。他選擇成為一個生活的旁觀者,在自我的獨行中,孤獨著,也發現著自我的意義。
無論是對于城市,還是對于鄉村,劉亮程都是一個特立獨行者。他和現實人群離得很遠,而和自然哲學靠得很近。他有著建立一套自己生活邏輯的信念。我想,我們在關注劉亮程時在關注什么?
是關注真實鄉村生活圖景嗎?不是,劉亮程筆下的鄉村和真實的鄉村生活相距很遠。
是關注劉亮程特別的人生經歷嗎?不是,描摹心靈之鄉在文學領域并非特別之事。
可能最特別的就是他對于自己鄉村自然哲學的建立吧,這套哲學孤獨、渺遠,對抗著世俗而又邏輯自洽。只是摒棄了人世的孤獨哲學,總是少了一點現實的溫度。
劉亮程在《寒風吹徹》中說:“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我們幫不了誰。我的一小爐火,對這個貧寒一生的人來說,顯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8]劉亮程的哲學也正如他文章中的這一小爐火,可以照亮他自己,但卻無法照亮真實的鄉村憂患。身為讀者,我渴望在他的個人經驗之外,看到更多群體的經驗,看到人類的意義,而不僅是個人的游蕩與獨語。
在劉亮程的散文中,有許多關于生命的哲思與感悟,它來自文化傳統,來自鄉村生活,來自個人經驗。而現在,不管是對于這種鄉村哲學的書寫,還是劉亮程的鄉村經驗,我認為都達到了瀕于極限甚至難以為繼的地步。如果不引入新的思想資源,新的敘說角度,那在他接下來的寫作中,無疑將有固步自封,自我重復的危險。
可敬的是2013年劉亮程從城市中離開,來到了新疆木壘縣菜籽溝村,結束了心靈的憶舊與漂泊生活,而是在與社會的聯系中建立起了木壘書院,在行動中踐行鄉村哲學,并推動鄉村發展。孤獨的鄉村哲學家終于落地,他以自己的行動結束了文學爭鳴,并在文學和現實領域,為我們呈現出了一份獨特的生活樣本和文學資源。
參考文獻
[1]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1
[2]賽妮亞.鄉村哲學的神話[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3
[3]林賢治.五十年_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J].書屋,2003年03期
[4]張國龍.關于村莊的非詩情畫意的“詩意”寫作姿態及其他——劉亮程散文論[J].中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四期
注 釋
[1]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1,209.
[2]同上,《狗全掙死了》,229.
[3]同上,《狗全掙死了》,229.
[4]同上,《馮四》,022.
[5]同上,《野地上的麥子》,084.
[6]同上,《黃沙梁》,053.
[7]同上,《剩下的事情》,026.
[8]同上,《寒風吹徹》,076.
課題項目:南京市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1年規劃重點課題(LZD/202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