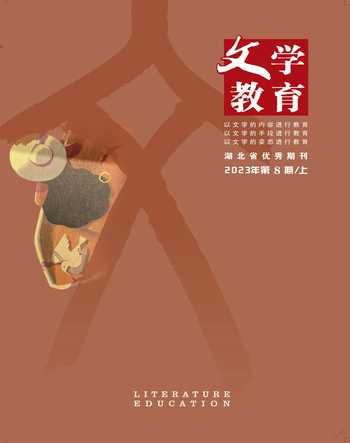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布魯克林》中的服飾與“愛爾蘭性”建構
唐力
內容摘要:愛爾蘭作家科爾姆·托賓小說《布魯克林》呈現了現代愛爾蘭人的移民境況及身份問題。從愛爾蘭“歷史”賦予的同一身份到布魯克林“現在“構建的多元身份,女主人公艾麗絲·萊西的服飾選擇體現了她身份的層層嬗變。文章以服飾作為切入點,結合愛爾蘭移民現象,以斯圖爾特·霍爾的文化身份理論為導向,深入分析艾麗絲身份的建構歷程,探究服飾與身份構建之間的可譯性,進而揭示全球化背景下“愛爾蘭性”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的位置選擇。
關鍵詞:《布魯克林》 愛爾蘭移民 身份建構 服飾 “愛爾蘭性”
科爾姆·托賓(1955-)是愛爾蘭當代著名作家之一,他關注正在經歷深刻變化的愛爾蘭并摹寫愛爾蘭社會中的流亡、宗教以及身份問題。《布魯克林》以愛爾蘭移民生活為主題,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的愛爾蘭,因為本土工業死亡,小鎮女孩艾麗絲無法在家鄉恩尼斯科西鎮找到工作,而前往布魯克林的經歷。在布魯克林,對家鄉的思念一直縈繞在艾麗絲心頭,當適應布魯克林的生活并打算和戀人托尼結婚時,她姐姐羅絲的死迫使她返回愛爾蘭,經過一番糾結之后艾麗絲選擇回到布魯克林。
學界從離散、女性身份和心理學等視角研究這部作品。愛德華·哈根認為《布魯克林》是對詹姆斯·喬伊斯《伊芙琳》的“拓展”和“延伸”。就像《伊芙琳》中的父女關系,艾麗絲陷入母親設置的陷阱被流放到布魯克林。在《布魯克林》中,艾麗絲與愛爾蘭的關系轉喻為艾麗絲與母親的關系,無法與母親斷絕關系的艾麗絲在美國和愛爾蘭兩個世界中構建自己的身份。安妮·弗朗索瓦運用隱性行為理論分析《布魯克林》中艾麗絲的沉默,認為艾麗絲通過訴諸沉默來獲得她想要的東西。“她微小的、安靜的和沉默寡言的行為最終產生了決定性的結果,甚至比任何冷靜的計算都更具決定性”[1]。托尼·揚通過保羅·里克爾的動作語義和表層語法理論來分析《布魯克林》中未披露的人物意圖。揚認為讀者和批評家對《布魯克林》中艾麗絲的行為分析暴露了其建立在外部觀察模式而非內部觀察模式的邏輯缺陷。從托賓對艾麗絲 “痛苦”生活的微妙描述中,可以發現移民經歷以及不同文化環境使艾麗絲受困于自我懷疑并且在生活中呈現出“表演”行為。正如揚提醒讀者,注意《布魯克林》中托賓設置的敘事線干擾,更多地關注發生在艾麗絲等角色周圍的事件本身。綜合以上評論,在托賓設置的敘事策略下,當艾麗絲以沉默以及手勢代替言語時,服飾更能展示主人公身份在移民經歷中的層層嬗變。
艾麗絲的身份建構以服飾變化為線索。整篇小說以主人公艾麗絲帶著愛爾蘭風格行李箱踏上布魯克林為始,期間帶著同個行李箱回到恩尼斯科西鎮,以及再次帶著那個愛爾蘭風格的行李箱前往布魯克林為終。艾麗絲在家鄉愛爾蘭、移民城市布魯克林以及返鄉后的服飾表現為從愛爾蘭風格到美國風格以及最后的混搭風格的演變,呈現出艾麗絲從同一到多元身份的建構。服飾作為小說的核心意象與艾麗絲身份的協商以及建構相互呼應,這體現出《布魯克林》中服飾與身份之間的可譯性。本文以服飾為切入點,結合全球化背景,深入分析以艾麗絲為代表的20世紀90年代愛爾蘭人的移民經歷,探究“愛爾蘭性”的現狀進而揭示“愛爾蘭性”在“過去”和“現在”中的建構。
一.愛爾蘭手提箱與身份的同一
小說以20世紀50年代早期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艾麗絲在家鄉愛爾蘭小鎮恩尼斯科西以及美國布魯克林的生活。在故事開頭描述了愛爾蘭恩尼斯科西鎮上傳統的生活以及人際關系。由于缺少經濟來源,在生活上艾麗絲一直以母親以及姐姐羅絲為導向,接受母親以及羅絲的價值觀念,以此尋求母親以及姐姐的認可。姐姐羅絲是傳統愛爾蘭文化鴻溝中的掙扎者,作為家中唯一擁有經濟收入的人,身為長女的羅絲是母親和妹妹的依靠也是她們溝通的橋梁。艾麗絲穿著的都是由姐姐羅絲購買或者贈送的衣服,這使艾麗絲在無意識中讓自己按照他者的意愿對自己的身份進行塑造。“各種物體本身均可擔當產生意義的能指功能,衣服也可兼作符號,它們構成意義并傳遞信息”[2]。姐姐羅絲贈送的服飾成為“愛爾蘭性”敘述中代表“共同的歷史經驗、共享的文化以及在其中形成的集體自我”[3]的文化符碼,為艾麗絲提供了同一和連續的文化身份。“愛爾蘭性”呈現為“無法自主的服飾”這一重要視覺意象,并以“依附性”這一核心價值存在。生活在母親和姐姐主導的愛爾蘭家庭中,艾麗絲處于客體位置,她的依附行為表現出自我認同的缺失,并將自己置于“穩定、不變、連續”[3]的“愛爾蘭性”。
與布魯克林熙熙攘攘的氛圍相比,恩尼斯科西鎮很安靜,甚至因為熟悉的小鎮居民們的“凝視”而令人窒息。“凝視是攜帶權力運作或者欲望糾結的觀看方法”[4]。在恩尼斯科西每個居民都處在其他人的凝視之下。凝視所暗含的權力壓力限制了“愛爾蘭性”的存在以及可能性。小說開篇描寫艾麗絲在窗臺看著姐姐羅絲下班回家,拎著新皮包披著羊毛衫,緊接著艾麗絲就身著羊毛衫出門去了。與其說艾麗絲是生活的參與者不如說她是觀察者,艾麗絲的凝視是模仿欲望的體現,艾麗絲的模仿不僅是對服飾的模仿還是對行為的模仿,在布魯克林艾麗絲時常通過模仿羅絲的說話方式以及行事方式來解決問題,缺乏自我認同的艾麗絲通過模仿實現身份定位。在艾麗絲到達布魯克林并適應布魯克林生活后,因為姐姐羅絲的突然去世,艾莉絲不得不回到了恩尼斯科西。幾天后,鎮上的人都知道艾莉絲回來了,母親告訴艾麗絲,“顯然整個鎮子都知道你在這兒……你最好穿上像樣的衣服,別太美國腔調了”[5]174。此時服飾已然偏離其直接意指,成為社會規訓的手段。無所不在的凝視將這個城鎮構建成一個“全景監獄”,在這里,社會權力使居民們習慣于日常生活中的凝視和規訓。生活在這種氛圍中,艾麗絲理所當然地接受了小鎮對女性的傳統期望,“一輩子住在鎮上,像她母親一樣,認識所有的人,有同樣的朋友和鄰居”[5]22。這種傳統的集體認同感形成了共有的集體身份并通過強烈的內在約束力使小鎮居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但共有的集體身份也攜帶非常清晰的界限,將他們與外部世界分隔開來。
全球經濟發展進程中愛爾蘭受制于傳統經濟而無法參與資本市場,昔日愛爾蘭的田園詩想象造成了今日愛爾蘭處于世界邊緣位置的生存困境,“愛爾蘭性”的“穩定”被扭轉為“封閉”及“落后”。與布魯克林美麗的富爾頓街相比,恩尼斯科西鎮仍然以傳統的個體經濟為主,例如小鎮上凱莉小姐家的雜貨店、海耶斯雜貨店、謝立丹雜貨店,吉姆家酒吧等。姐姐羅絲購買衣服都是等到都柏林商店一年中兩次大減價活動,從都柏林來帶回新外套、羊毛衫、裙子等。傳統的經濟模式使愛爾蘭無法搭上全球快速發展的經濟列車,對農業的堅持和對迷人田園風光的夢想限制了恩尼斯科西的經濟發展,阻礙了年輕人的機會,“至少在目前的恩尼斯科西,無論資質多好,也找不到工作”[5]8,這就是母親和姐姐羅絲希望艾麗絲去布魯克林的原因。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拉近了社區的距離,但同時拉遠了愛爾蘭與外界的距離。
艾麗絲身著的服飾反映了擁有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享的文化符碼的愛爾蘭人通過認同和依附的意義指涉來構建和維護“愛爾蘭性”。孤立的經濟模式下,傳統歷史在強化了連續的、不變的、穩定的愛爾蘭的同時,以鮮明的界限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系。以傳統歷史為標志的愛爾蘭社會形成了它的獨有的文化群落,并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家庭中,保持著其獨特的社會習俗和慣例。愛爾蘭的“歷史”就像艾麗絲前往布魯克林時所攜帶的愛爾蘭行李箱,里面帶著姐姐羅絲給她的衣服和首飾,獨特的風格使同船的喬治娜抱怨“太愛爾蘭風格了”,但是喬治娜建議換愛爾蘭行李箱時,艾麗絲又舍不得丟掉。相反,愛爾蘭手提箱帶著艾麗絲前往布魯克林也把艾麗絲帶回了恩尼斯科西。經過傳承和反復表征,“愛爾蘭性”被定型、被認同、被接受,成為無法艾麗絲無法丟棄的身份。
二.美國女人與身份的迷失
當前往布魯克林的機會出現時,羅絲選擇留守愛爾蘭而讓妹妹艾麗絲前往布魯克林。“羅絲在幫她辦妥出國之時,也放棄了真正的希望:離開這個家,有她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庭”[5]24。羅絲按部就班地過著模式化的生活,直到生命戛然而止。羅絲的去世隱喻著傳統“愛爾蘭性”在新時代的舉步維艱以至于最后被社會發展進程吞沒以至于喪失主體性的嚴峻形勢。身份屬于過去也屬于未來。預先給定和決定的方面只是身份的一部分,像所有歷史事物一樣,身份隨著時間、空間和文化關系而變化。“除了許多相似點之外,深刻和顯著的差異點構成了‘真正的現在的我們”[3],身份“斷裂和非連續”[3]將更好地書寫現在獨特的“愛爾蘭性”。
當艾麗絲踏上布魯克林時,她意識到了“新大陸”所帶來的差異,傳統的愛爾蘭身份受到挑戰,她站到了身份建構的門檻前。通過巴爾托奇商店入職面試后,艾麗絲得到了一件商店里的女孩必須穿的藍色制服。服飾成為“附加在穿戴者身上的社會關系的體現”[6]。藍色制服賦予艾麗絲以社會身份,意味著艾麗絲成為了巴爾托奇商店的中的一員,這是艾麗絲踏入美國社會的第一步。在布魯克林,艾麗絲和其他五個女孩作為房客住在基恩夫人的房子里,“潮流變幻和新趨勢是她的日常話題”[5]43。這些女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談論服飾,而在巴爾托奇商場的銷售工作為艾麗絲提供了融入她們的機會。在餐桌上,因為艾麗絲知道商場每一個新的趨勢,她總是有話可說。在基歐夫人和女孩們之間,服飾作為一個話題幫助艾麗絲獲得認同。布魯克林的“現在”打破了愛爾蘭連續的“過去”,布魯克林的“差異”賦予了“愛爾蘭性”持續建構的機會。
艾麗絲就職的巴爾托奇商店為了歡迎“黑女人”來購物,將售賣深褐色和咖啡色的紅狐牌絲襪,但是“紅狐牌絲襪必須和其他普通襪子分開”,并且要求負責該柜臺的售貨員要若無其事。但是每當有黑女人來買襪子時,艾麗絲以及其他售貨員總是會偷瞄她們。身份的建構存在于與當下的物質、文化以及社會關系中。不同顏色的襪子被消費時實際是在消費該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對意義符號的認同或不同界定著自我,區隔著自我與他人”[7]。在此背景下,艾麗絲認為“羅絲幫她買的裙子,看起來糟透了”[5]87,她對美國的服裝產生了好奇心,她想知道美國女人都穿什么,并且迫切地打算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美國服裝”。鮑德里亞認為“消費是一種符號的系統化操控行為”[8]。“美國服裝”作為美國人共享的符號被身在布魯克林的艾麗絲解讀為美國身份的象征。服飾成為了可以投射“自我”的鏡像,對美國身份的主觀認同和內在沖動驅使艾麗絲去尋找最適合自己的那種“美國服裝”。服飾通過表征呈現身份建構,對服裝的選擇指明身份“不是本質,只是位置”[9]596。
布魯克林的生活并沒有消解艾莉絲的愛爾蘭身份,反而加強了艾莉絲和愛爾蘭之間的內在聯系。到達布魯克林后不久,艾麗絲就想家了。“現在,所有這些似乎都無法和她家鄉、她的房間、弗萊瑞街的房子,她在那里吃過的飯、穿過的衣服相提并論。”[5]52。沮喪隱藏在布魯克林的喧囂中,她在這里微不足道,“此地無一物屬于她”[5]53。孤獨感激活了艾麗絲對故鄉的記憶,強化了她對愛爾蘭的認同和依戀。服飾成為連接愛爾蘭和布魯克林的橋梁。艾麗絲給她的兄弟們買的手表,給媽媽和羅斯買的羊毛衫和尼龍絲襪,以及在給媽媽和羅斯的信中分享布魯克林流行的時裝風格成為愛爾蘭文化和美國文化的交匯點。“歷史的源頭”是實現身份持續的前提。愛爾蘭文化給予身處布魯克林的艾麗絲歸屬感,兩種文化互相支撐并加強對方在身份建構中的力量,體現了身份認同的復雜性。
布魯克林是多元文化相遇的異質時空,在此愛爾蘭的“過去”與布魯克林的“現在”的碰撞反映在艾麗絲搖擺不定的自我與他者的身份定位上。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艾麗絲經歷不同文化的主導與壓制,無法做出抉擇的艾麗絲迷失在身份建構中。與之相對應的是,正是身份的不穩定狀態打破了艾麗絲固有的同一身份,賦予了艾麗絲建構身份的機會。這種不穩定為艾麗絲提供了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中“移民身上所具有的流動和多元文化身份得以發展”[10]。身份的建構不是以一種身份代替另一種身份,而是在“同一”的內部構建一種“并非是純粹‘他者的差異感”[9],因此需要布魯克林的“現在”與愛爾蘭“過去”在異質時空中不斷談判與協商。
三.混搭風格與身份的建構
全球化努力地將多維的時間和地點融合在一個全球共享的空間內,在這個空間“各種文化矛盾地融合在一起”[11],這種時代背景伴隨著“差異的擴散”[9]打破了舊的身份與新的身份的二元對立,使兩者結合在一起。當艾麗絲打算擁抱她的美國未來時,神父弗拉德給她帶來了姐姐羅絲去世的消息,艾麗絲決定回到愛爾蘭,但回到恩尼斯科西,故鄉在她看來既熟悉又陌生。與舊時朋友游玩時看到矗立在遠方的醋山時,艾麗絲想到布魯克林也有一座醋山并且就是以恩尼斯科西這座醋山命名的。醋山體現出布魯克林和恩尼斯科西的空間劃分不再那么清晰明確,而這也對應艾麗絲身上兩種文化體系的交織。經過醋山后,艾麗絲和朋友來到海邊,在艾麗絲換泳裝時,她心想,“如果是幾年前,從恩尼斯科西一路過來,她就一定擔心她的泳衣和款式了,她身材是不是不夠好……但是如今她已經和托尼同去科尼島時她就選好了泳衣以及在船上曬黑了,她有種莫名自信”[5]173。當艾麗絲回到恩尼斯科西,布魯克林的版圖也拓展到了恩尼斯科西,她身上一直帶著布魯克林的印記,艾麗絲身上流動的愛爾蘭血液不再通過白皙的皮膚清晰地顯現出來,而是掩蓋在被布魯克林日光曬黑的黝黑皮膚下。布魯克林的印記是對建立在血緣關系和共享的文化符碼上的同一的補充,又隱含著對傳統愛爾蘭身份的超越,二者相互滲透的關系構成了艾麗絲的多元文化身份,更重構了艾麗絲內化的愛爾蘭價值觀,在此基礎上艾麗絲樹立了以自我認同為導向的人生態度。
重回愛爾蘭意味著重回身份被壓制的愛爾蘭家庭。“在主導文化和從屬文化之間的縫隙處,壓制和反抗間的斗爭最激烈,文化身份認同最活躍”[12]。在家中母親更喜歡收拾羅絲留下的衣服,而不是討論她在美國的生活。“她說,她把所有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放了起來,包括衣柜和抽屜柜里羅絲所有的衣服”[5]164。當羅絲選擇留在恩尼斯科西,和她母親在一起,并仔細安排艾麗絲去布魯克林的時候,她就承擔了一個傳統愛爾蘭家庭的責任。然而,羅絲的死亡將家庭責任轉移到了艾麗絲身上,艾麗絲的母親理所當然地認為艾麗斯再也不會離開自己了,這成為艾麗絲身份建構的一個“壓力點”。“很難不認為她是羅絲的影子,母親在同一時間,以同樣的方式給她上早餐,對她說的話,贊美她衣服的話也和以前對羅絲說的一摸一樣”[5]175。母親努力說服艾麗絲接受并穿上羅絲留下的衣服,“我們明天早上把連衣裙和外套拿到裁縫店去,尺寸改好,看起來就不一樣了,會適合你新的美國身材”[5]171。羅絲的衣服代表“愛爾蘭性”蘊含的歸屬感但同時也代表著“愛爾蘭性”內化的特定的組織關系和規范,接受這些衣服意味著艾麗絲要永遠處于封閉的恩尼斯科西的規訓以及母親的監督下。服飾代表著從布魯克林歸來的艾麗絲身處的角力場,異質文化的沖突激化了艾麗絲的身份認同。原本分裂兩個人,“一個奮斗過布魯克林的兩個冬季和許多艱難時日”[5]175,“另一個是她母親的女兒”[5]75,在重回愛爾蘭后逐漸重合起來。姐姐羅絲生前就職的大衛公司老板布朗先生得知艾麗絲回家后熱情邀請在布魯克林獲得薄記證書的艾麗絲兼職薄記員。這是離家前艾麗絲夢想卻未能得到的工作,而在布魯克林獲得薄記證后,機會出現在了艾麗絲面前。“對受壓制的主體而言,通往過去的象征之旅有著特別的意義,因為回歸過去就是去尋根,去把握傳統”[12]。布魯克林的旅程松開了共同歷史與“趨同化”現在,返鄉之旅疊合共同歷史與“差異化”現在。相較于母親對艾麗絲美國服裝的不贊同,鎮上的朋友都說她“衣服漂亮、發型成熟和皮膚黧黑”[5]171。艾麗絲對整理羅絲的衣服感到非常厭倦,但同時,對自己走在街上而受到別人的注視而感到高興,“一個女人在看她的連衣裙、長筒襪和皮鞋,接著又打量她曬黑的皮膚”[5]168。被質疑、否定后,愛爾蘭與布魯克林文化沖突激化艾麗絲對身份的建構,“次日早晨,艾麗絲拒絕去裁縫店,終于對母親擺明她不想穿羅絲的連衣裙和外套,不管這些衣服如何雅致,多么值錢”[5]171。通過否定羅絲所代表的身份以及母親所施加的身份,艾麗絲逐步確定了自我,認識到同一的身份不過是傳統“愛爾蘭性”的幻想,“往事很快就會變成一場離奇、模糊的夢”[5]201。最后,在南希的婚禮上,艾麗絲修改了自己從都柏林阿諾特商店買的白色的棉布襯衫,并再上面搭配她從美國帶來的裝飾品。被修復、重構后,在艾麗絲身上美國的“現在”與愛爾蘭的“歷史“并存。
由于全球化趨勢加快,人口的遷移和流動產生了多元文化的社會,并導致“全球范圍內社會力量和關系的戰略性重新配置”[9]。因為差異不會消失,所以身份的建構永遠在路上而沒有終點。原始文化需要吸納不同的文化并與之協商來擴展它的界限。多元文化身份的建構是一個過程,其間不同的文化需要通過協商的方式更新傳統的價值觀和規范體系。多元文化身份表明的不是本質的身份,而是人們對希望融入的群體的位置選擇。
傳統文化獨特、同質、自成一體的文化作為認同點和依附點將社區成員緊密聯系在一起。傳統文化滲透到整個社區并為其成員提供了一種傳統的、穩定的文化身份。但身份作為是一個歷史和文化共同作用,空間和時間共同定位的過程,它受過去影響卻不會受制于過去。伴隨著艾麗絲從恩尼斯科西到布魯克林的多元文化身份建構,她的服飾呈現出愛爾蘭風格,混搭風格的變化,體現出服飾與身份構建之間的可譯性。艾麗絲多元文化身份根植于“愛爾蘭性”,但她的多元文化身份賦予了她與傳統“愛爾蘭性”協商的力量。布魯克林的“現在”正與愛爾蘭的“過去”不斷談判為艾麗絲構建了多元的文化身份,變化、非連續的身份為主體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多元文化身份表明的不是某種本質身份,而是對身份位置的選擇。在這個過程中,原生文化需要擴大其界限,不同的文化需要以協商的方式更新傳統的價值觀和規范體系。
參考文獻
[1][英]安妮-利斯·弗朗索瓦.公開的秘密:無數經驗的文學[M].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7:51.
[2]斯圖爾特·霍爾.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M].徐亮,陸興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7.
[3]WILLIAMS,PATRICK.&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A Reader[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223-225.
[4]陳榕:凝視.西方文論關鍵詞(第一卷)[M].趙一凡等,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349.
[5]科爾姆·托賓.布魯克林[M].柏櫟,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
[6]JONES, ROSALIND ANN. & PETER STALLYBRASS. Renaissance Clothing and the Materials of Memory[M].Edinburgh:Cambridge UP,2000:3.
[7]張孟玲,南健翀.論《杜蘭葛山莊》中服飾與女性身份建構[J].外國語文研究2021,7(4):50-58.
[8]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剛,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9]HALL, STUART. & DAVID, MORLEY.Essential essays.Volume 2,Identity and diaspora[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9:99-596.
[10]BHANDARI, NAGENDRA B.Diaspora and Cultural Identity:A Conceptual Review[J].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21,21:100-108.
[11]JONES,DONNA V,et al. North Atlantic Perspectives:A Forum on Stuart Halls The Fateful Triangle: Race, Ethnicity, Nation,Part I[J]. Contexto Internacional,2019,41(2):431–447.
[12]陶家俊.同一與差異:從現代到后現代身份認同[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2004(2):11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