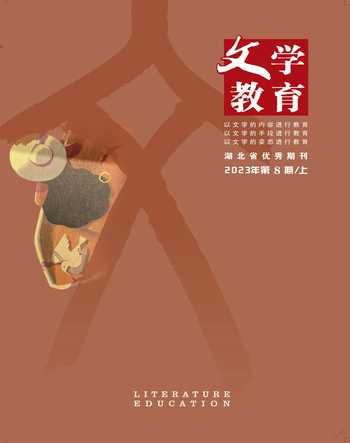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哀郢》中“冀壹反之何時”的精神實質及歷史語境
范昱杉
內容摘要:《哀郢》發出“冀壹反之何時”之嘆的情境是屈原不止“去君”,而且逾境“去國”;不是待召于郊,而是因罪被放逐。周代禮制,自疏去君之臣三月內等待國君召還,但臣子因罪被放逐的情況不在這一禮制范疇內。與作于去君待召時期的《離騷》等篇章相比,《哀郢》“冀壹反之何時”精神實質的獨特性在于,在希冀回返的目的層面,個人被國君重用的仕進追求讓位于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和對父母之邦的眷戀。兩漢九體擬騷作品對屈原“冀壹反”的心態進行了傳承與重構,其希冀回返的精神實質更多偏重于期待被國君重視,屬于個人進退、仕隱之抉擇的范疇,這種精神實質的差距從一個側面彰顯了屈原作品忠君愛國精神的純粹與徹底。
關鍵詞:《哀郢》 冀壹反之何時 待召之禮 屈原 九體擬騷作品
《哀郢》是屈原所作《九章》中的一篇,其中“冀壹反之何時”是此篇亂辭中的一句,這種希冀回返國都、再得面君的心態不僅貫穿于《哀郢》全文,而且多次出現在屈原創作的其他作品之中,構成其情感抒發的落腳點之一,被司馬遷概括為“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1]。應該注意的是,《哀郢》發出“冀壹反之何時”之嘆、抒發希冀回返的心態,其背景不同于《離騷》等篇目,因而也有著特殊的精神實質和文本建構方式。不過,這種心態總體上受到周代自放之臣等待國君召還這一禮制的影響,應該將其置入這一歷史語境中加以觀照。
本文重點分析《哀郢》中“冀壹反之何時”的心態有著哪種獨特的精神實質,是借助怎樣的文本邏輯進行傳達的,并探討這種希冀回返的心態產生于怎樣的歷史語境之下,對周代禮制背景、楚國政治現實和屈原遭遇等相關史實進行闡述和辨析。此外,漢代九體擬騷作家對屈原作品中希冀回返的心態進行了怎樣的傳承與重構,體現了楚辭與漢代擬騷類作品精神實質方面怎樣的區別,這兩個問題也在本文的考察范圍內。在周代待召之禮的禮制背景下觀照《哀郢》“冀壹反之何時”的心態,并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能夠幫助辨析《哀郢》創作的歷史背景,加深對屈原《哀郢》創作心態的認識,準確區分不同創作時期、不同作家在作品中傳達的希冀回返心態在精神實質上的差別,從一個側面精確把握屈原作品忠君愛國的“騷義”。
一.弱化對個人仕進追求的表達
“冀壹反之何時”[2]一句是屈原渴望回返國都、再得面見君主的心態在創作中的直接表達。流放在外而希冀回返的心態,在屈原各個時期的作品中經常作為貫穿全文的抒情落腳點被反復申述。《哀郢》按照遵循長江和夏水而漫游的空間順序,抒發流亡在外九年未能回返的憂悶與悲哀,“哀見君而不再得”“何須臾而忘反”“至今九年而不復”分別是作者回顧流亡路線、思念終古所居、講述窘迫的政治遭遇幾個抒情單元的情感落腳之處,長期流亡、遠離故鄉、仕途困頓在屈原作品之中統一歸于對回返國都、再得面見君主的希冀心態。與《哀郢》同理的還有《離騷》[3],作者借受女媭責備、向舜帝陳詞二事堅定了自己的政見,借一上昆侖與浮游求女二事寫期望彌合君臣分歧而不得,借靈氛之占與巫咸之告的矛盾寫自己在是否遠逝這一問題上的猶疑,希冀回返的心態貫穿于作者設計的每一個浪漫詭譎的藝術想象情境之中。
但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之中,屈原這種希冀回返的心態有著不盡相同的文本呈現。與作于屈原自疏去郢時期的《離騷》等篇目相比,《哀郢》對個人仕進的追求、渴望國君重用的心態明顯弱化。在接受上官大夫的讒言之后,楚懷王“怒而疏屈平”[4],這種情況下屈原由于“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5],不滿于楚懷王聽信讒言疏遠自己、不接受聯齊抗秦的諫議,因而選擇“遠逝以自疏”,王逸將屈原這種因諫不從主動疏遠君主的行為及心理動因概括為“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于世也”[6],指明作為《離騷》創作背景的流放在外是屈原因與國君政見不合、不被信任而作出的主動行為選擇。
在使得屈原作出上述選擇的心境支配下,屈原在《離騷》中對于希冀回返國都這一心態的表達,與渴望國君再度重用自己、采納聯齊抗秦的建議、實現自身政治抱負等個人仕進層面的追求關系更加密切。雖然聯齊抗秦這一主張的出發點是對楚國現實政治需要的考慮,包含著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憂慮,但從文本對比結果來看,相較于《哀郢》,作于自疏去君時期的《離騷》等篇目對于個人仕進追去的表達的確更加顯著。《離騷》的行文邏輯以與女媭、舜帝交流政治見解與遭遇,向昆侖之神求助卻受阻帝閽、周流求女卻終于無果,情靈氛占卜、向巫咸詢問建議作為藝術想象與情感抒發的三個環節,陳詞圍繞個人仕途中的主張與際遇展開,與神明溝通象征與國君溝通,是否遠逝的抉擇在當時的禮制背景下幾乎等同于國君是否再度重用自己——據《禮記》記載,“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7],兩周時期大夫三諫而國君不從,則自疏待命于郊,這種做法被稱為“以道去君”[8],如《谷梁傳》中記載:“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9],認為趙盾因與君王政見不合且入諫不被采納,出奔去君到郊外駐守,以求等待君命;再如柳下惠所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10],也是對這項禮制的反映。這一禮制的另一項內容是如果國君在三個月的限期內悔悟,決定聽取該臣子的諫言,可以“賜之環則還”[11],以玉環作為信物召還自放于郊的臣子。
反觀《哀郢》對于希冀回返這一心態的表達,極少流露渴望再度被國君信任而受到重視這種內涵,即不再將個人仕進追求作為希冀回返的目的,個人仕進追求在文本中的表達被弱化了。此篇第一處抒發希冀回返的心態是“哀見君而不再得”,此處作者主要是在回顧沿循長江、夏水一路漂泊流亡的經歷;第二處抒發希冀回返的心態是“何須臾而忘反”,此處作者主要表達對終古所居之故鄉的思念;第三處抒發希冀回返的心態是“至今九年而不復”,此處作者在為譴責“荏弱而難持”的令尹子蘭妨礙國事蓄勢——全篇消解了《離騷》中借助香草美人的比況與浪漫奇譎的幻想來表達遭受奸佞離間而仕途困頓的憤激。由《哀郢》文本的上述情感邏輯可見,在希冀回返的目的層面,強調的是對國家命運的擔憂與對父母之邦的眷戀,不再像《離騷》那樣,以諫言不從而自疏去君、期待再度被國君任用作為“冀壹反”心態精神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強調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和對父母之邦的眷戀
分析《哀郢》與《離騷》在希冀回返這一心態背后精神實質的差異,首先應該對《哀郢》的創作背景進行討論。王夫之認為《哀郢》作于秦將白起破郢的背景下,“哀故都之棄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離散,頃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12],即將“哀郢”理解為屈原在郢都被破后的悲哀心境,如果這樣理解,那么《哀郢》“冀壹反”卻不可得的原因是郢都被占領而無法回返。但是,這一觀點并不準確。《史記·楚世家》記載:“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13];《資治通鑒》也記載,白起破郢發生在“周赧王三十七年”,即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拔郢都、燒夷陵之后,“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14]。而屈原于頃襄王三年(前296年)自沉汨羅,《哀郢》不可能是白起破郢之后所作。實際上,《哀郢》作于頃襄王二年(前297年),此年楚懷王逃歸為秦追獲,再度被困秦國。并且,屈原已于楚懷王二十四年(前305年)被放逐于鄂渚,距離寫作《哀郢》已經有近九年的時間[15]。
此次放逐與楚懷王十六年時屈原“自疏去君”的性質已經不同,孔穎達曾在對 《詩經》的疏解文本中辨析兩周時期“放”臣的區別:“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逐之義。”[16]楚懷王十六年時屈原進諫不入遂“遠逝以自疏”應當屬于后者,而楚懷王二十四年屈原被放逐于鄂渚、九年不得復還則應屬于因罪被放。根據兩周時期的禮制,三諫之后國君“不用其言”而“自去”的臣子待放于郊,此時“爵祿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17],若國君三年內未召還這類臣子,或是“賜之玦則往”[18],那么臣子此時可以逾境去國。此外,如前所述,大臣三諫未從自放于郊三月等待君主召還是此項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放的原因是三諫而君主不從,再度被召還的情況往往是君主悔悟、采納其諫言,因此,自放的情況下希冀回返往往與個人得到君主重用的仕進追求密切相關,《離騷》中希冀回返的心態與個人仕進追求的表達密不可分這一現象可以視作明證。而《哀郢》的創作背景決定了,發出“冀壹反之何時”的感嘆不再屬于上述禮制范疇。從這一視角可以解釋,在屈原此時希冀回返的諸多目的中,再次得到君主重用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和對父母之邦的眷戀是更加緊迫、更具支配性的心理因素,也成為了“冀壹反之何時”之嘆的精神實質。
從《哀郢》作品文本來看,屈原對希冀回返這一心態的抒發總是與擔憂國家命運、眷戀終古所居的父母之邦相聯系。此篇以哀嘆百姓在戰亂中離散相失起首,這種哀嘆始終籠罩著第一個抒情單元回顧九年流放經歷的過程中,“哀見君而不再得”的感嘆由此發出。屈原將國都郢稱為“終古之所居”“故都”,表示自己漂泊的靈魂不曾有一刻停止向往回返。在交代了“至今九年而不復”的遭遇之后,屈原集中批判“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的子蘭,指責懷王聽信少子的主張“入秦不反”被困于秦、危及國家命運。
參考《史記·楚世家》可以發現,自楚懷王十七年以來,秦多次大敗楚軍,攻破楚國數城,齊、韓、魏等國與秦國結盟使得楚國外交上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態,楚懷王逃歸被抓獲復囚于秦[19]——屈原寫作《哀郢》時楚國正處于內憂外患的政治局勢中。屈原作為出身于楚國宗室的貴族,在楚國國運飄搖、自身被國君放逐九年未召還的條件下,本來可以選擇到他國另謀出路,“一言投合,俯仰卿相,士之欲急功名者,舍是莫是歸者”[20]。且先秦時期臣子不被君主召還而去國是比較普遍的行為選擇,《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21],孟子認為大夫三月未被君主召還則有權載質出境去其他國家;《毛傳》將《詩經·衛風·考槃》視為衛莊公時期的去君之辭,抒寫賢者不用于君的情況下“不復入君之朝”[22]的誓言,被概括為“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23];《鄭風·遵大路》中去國者直接申明“無我惡兮”“無我魗兮”[24],表示并非自己棄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屈原始終抱持著希冀回返的心態,這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其忠君愛國思想的有力彰顯。
三.兩漢九體擬騷作品對“冀壹反”心態的傳承與重構
兩漢九體擬騷作家也多次在作品文本中表達對于返回國君身邊的渴望,這可以視作對屈原所作的楚辭作品中希冀回返心態的傳承。具體來說,兩漢九體擬騷作品對希冀回返心態的傳承往往表現為渴望國君意識到應該采納自己的諫言。
以東方朔《七諫》[25]為例,作者借助屈原事跡抒發己意,在《初放》中“言我將方舟隨江而浮,冀幸懷王開其曚惑之心而還己也”[26];在《沉江》中慨嘆“安眇眇無所歸薄”,“言己放流,不得內竭忠誠,外盡形體”,認為自己流放在外是無所歸附的狀態;在《怨世》中講述自己在“賢者避而不見”的情況下打算“壹往而徑逝”,王逸注指出此處“言己思壹見君,盡忠言而遂徑去”;《怨思》“冀一見而復歸”處王逸注:“言己自憐身老,不足以終志意。幸復一見君,陳忠言”;《哀命》“念三年之積思兮,愿壹見而陳詞”,王逸注指明此處“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且《楚辭章句補》載糜信一位此言是“朔自為”。再度面見君主以陳忠言構成貫穿此篇騷體賦希冀回返心態的精神實質。
另一方面,兩漢九體擬騷作品借助對屈原希冀回返這一心態的重構,展示了兩漢政治生態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大部分作品中希冀回返心態的精神實質更多偏重于期待被國君重視,屬于個人進退、仕隱之抉擇的范疇。具體表現為將遠逝作為一種姿態而非最終結果。以嚴忌《哀時命》為例,全篇抒寫“不知進退之宜當”[27]這一出仕與入仕之間的矛盾,在欲進無門的情況下卻不甘于退遁,這種內心掙扎是其希冀回返心態真實目的的生動注解。并且,兩漢九體擬騷作品常將避世隱居作為希冀回返而不得的退路,如東方朔《七諫》中“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王逸注指明此處“言己懷忠信之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此外,部分九體擬騷作品鼓勵士大夫相信國君,不要輕易選擇遠逝,這可以視作在希冀返回而不得的情況下對士大夫仕隱選擇的反省和思考,王褒《九懷》在《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等部分接連抒發希冀回返心態下的悵然若失、心懷遺憾,最終“圣舜攝兮昭堯緒,孰能若兮愿為輔”[28]一句直接表明作者認為“竭忠信,備股肱”[29]是人臣抱持的正確心態,這對于前文希冀回返的心態是一種同義回應。
兩漢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治生態下個人進退、仕隱的選擇被更多地思考,仕途中“遇”與“不遇”的主題在漢賦、古詩中多有體現。漢代九體擬騷作品中對屈原希冀回返的心態進行重構,一定程度上是對兩漢政治環境和士大夫心態的如實反映。盡管如此,這種精神實質的差距依然從一個側面顯示出漢代九體擬騷作品“騷義弱而賦義強”[30],也彰顯了屈原作品忠君愛國精神的純粹與徹底。
正如王逸對屈原的評價:“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在《哀郢》一文中,屈原不僅是“去君”,而且越境“去國”了,這就是他在《哀郢》中發出“冀壹反之何時”之嘆的歷史語境——在當時的禮制背景下,屈原不是在城外等候君主召見,二是因被判定有罪而流放于國境之外。按照周代禮制,因政見不合或進諫不聽而選擇自疏去君的臣子必須在三個月之內等候國君的召見,但是因獲罪而被放逐的臣子不屬于這一禮制范疇,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其他的出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哀郢》“冀壹反之何時”之嘆精神實質的獨特性得到了充分彰顯——相對于《離騷》等寫于“去君待召”時期的其他篇章,“冀壹反之何時”在希冀回返的目的和主導動機層面,由受君重托的仕途追求轉變為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和對父母之邦的眷戀之情。東方朔、嚴忌、王褒等人兩漢“九體”擬騷作品繼承并重構了屈原希冀回返的心理,雖然這些作品章法、辭采更為精巧繁美,但其回返的目的和主導動機更多地體現在希望得到君主的信賴和任用上,這是一種個人進退、仕隱方面的抉擇。兩者精神實質上的差距從另一個角度彰顯了屈原忠君愛國之情的純粹與徹底。
注 釋
[1](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史記·卷八十四》,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485頁。
[2](戰國)屈原著,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485頁。后文所引《哀郢》原文皆據此本,不再另注。
[3](戰國)屈原著,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頁。后文所引《離騷》原文皆據此本,不再另注。
[4](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史記·卷八十四》,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481頁。
[5](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史記·卷八十四》,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482頁。
[6](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夏劍欽、吳廣平校點:《楚辭章句補注·卷第一》,岳麓書社2013年版,第42頁。
[7](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47頁。
[8](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六禮記正義·卷第九》,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833頁。
[9](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九.春秋谷梁傳注疏·卷第十二》,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236頁。
[10]陳曉芬、徐儒宗譯注:《論語》,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20頁。
[1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七》,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812頁。
[12](明)王夫之著,楊堅總修訂:《楚辭通釋·卷四》,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13頁。
[13](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史記·卷四十》,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735頁。
[14](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鑒小組點校:《資治通鑒·卷第四》,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46頁。
[15]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頁。
[16](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七.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二十一》,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049頁。
[17](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六.禮記正義·卷第九》,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822頁。
[18](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七》,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812頁。
[19]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頁。
[20]游國恩著,游寶諒編:《離騷纂義》,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77頁。
[2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十三.孟子注疏·卷第六》,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895頁。
[22](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三》,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78頁。
[23](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三》,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78頁。
[24](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四》,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719頁。
[25]東方朔《七諫》雖名為“七”,實為九體的格局。詳見曹勝高《屈原“遠逝以自疏”的歷史語境及其文本建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1年第5期。
[26](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夏劍欽、吳廣平校點:《楚辭章句補注·卷第十三》,岳麓書社2013年版,第235頁。
[27](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夏劍欽、吳廣平校點:《楚辭章句補注·卷第十四》,岳麓書社2013年版,第262頁。
[28](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夏劍欽、吳廣平校點:《楚辭章句補注·卷第十五》,岳麓書社2013年版,第267頁。
[29](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夏劍欽、吳廣平校點:《楚辭章句補注·卷第十五》,岳麓書社2013年版,第267頁。
[30]曹勝高:《屈原“遠逝以自疏”的歷史語境及其文本建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