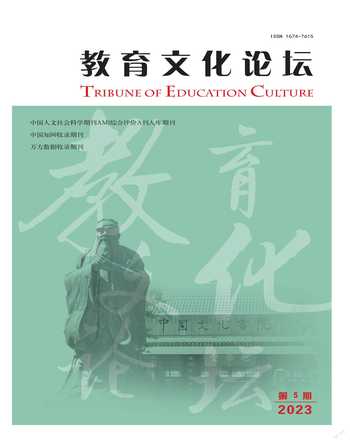面向文化治理的大學人文教育:何以與何為
何佩航
摘 要:作為國家治理模式的轉型方向,文化治理顯現出國家、社會、公民三種話語力量的動態博弈過程。但隨著當代中國文化治理格局中的結構性問題逐漸暴露,對文化治理的主體追問使大學人文教育應需而入場。大學人文教育作為培育時代新人的關鍵場域與青年話語匯集之地,應以人文滲透的育人過程、人文產出的形式與數字人文的實踐情境助推文化行動,提升話語力量,促進文化治理中共同體“有為”的實現。
關鍵詞:文化治理;人文教育;主體性;話語
中圖分類號: G64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7615(2023)05-0001-10
DOI: 10-15958/j-cnki-jywhlt-2023-05-001
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文化建設日益受到各界關注。隨之而來的文化治理,作為國家治理模式的轉型方向,也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文化治理呈現出隱性與柔性結合的特征,潛移默化卻深遠持久地影響著整個社會中的權力、制度與關系;另一方面,文化治理以文化為載體貫穿了整個社會的權力、制度、關系結構,是調整社會矛盾、回應社會訴求、穩定社會結構的內部邏輯。文化治理天生具有政治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內在邏輯,旨在平衡人、社會、國家三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態之間的文明互動關系[1]。但無法否認的是,“文化既是秩序的工具,又是失序的動因”[2]。在經濟全球化、信息高速化、風險流動化的今天,中國文化面臨著國家間爭端的風險與文化分層的落差等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文化治理的價值進一步凸顯,有必要思考如何在危機之中實現這一治理模式轉型。隨著實踐的推進,我國文化治理實踐中的結構性問題引發了各界對文化治理的主體追問,這使大學人文教育應需而入場。因此,基于大學人文教育面向文化治理的應然價值與時代意義,更基于大學人文教育助推文化治理的實踐可能,本文將以文化治理的三維格局為指引,探討大學人文教育如何為推進文化治理作出切實可行的貢獻,助力國家治理模式轉型。
一、 入場:文化治理與大學人文教育
(一)應然:當代中國文化治理的三維格局
文化治理這一概念來自西方。米歇爾·福柯對“治理性”、安東尼奧·葛蘭西對“文 化霸權”以及托尼·本尼特對“文化治理”的研究,使文化治理的理論逐漸成熟[3]。在文化治理視域之下,文化與權力相聯系。福柯指出,各種知識、話語等形式是廣義的政治支配性權力結構的表現,“控制的技術”將走向社會大眾“自我的技術”[4],并以“社會技術”對社會大眾進行行為引導與觀念塑造,即政府治理可以借助文化來實現。因此,文化不單單只是“文化”,而是表現為“權力彌散于文化結構”“言詞形式的領導權使群眾、政黨、領導集團緊密聯系”[5]。文化在社會互動中形成的統一意志使社會大眾、政黨、領導集團形成復合體并達成集體行動。但文化不僅僅是領導權的單向表達,“文化總是一種在場,并且是第一位的,存在于經濟、社會和政治實踐中,還從內部建構它們”[6]206。在文化治理視域下,社會作為一種文化有機體,需要形成“現代性共容”的文化土壤與文化治理場域,去適應、回應政治與經濟的改革,并形成文化、權力和市場的合理性關系[7],從而促成文化、權力、社會間的有機互動,實現政治、經濟、文化協同推進的應然圖景。
立足中國語境考察文化治理,從歷朝歷代的文化控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文化管理再到當代的文化治理來看,我國文化治理的轉向,從側面反映了國家權力的限縮趨勢與政府治理模式的轉型。文化治理于當代中國之所以重要,不僅由于文化治理自身的價值,也由當下特殊的國內外環境所造就。從文化治理的價值來說,文化是治理的手段、過程與目標的集合體,涉及意義生產、話語權建構乃至資源分配,不僅表達國家意識形態、理念與規訓教化,還涵蓋了民眾的文化權利以及背后的政治、社會權利方面的話語[8]。從國內外環境而言,我國面臨的競爭不僅是政治、經濟競爭,更是人才競爭與文化軟實力競爭。伴隨著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內部發展訴求以及外部競爭壓力都推動著當代中國文化治理的深化與轉型。
基于文化治理的現實價值,學界對文化治理的理論格局與結構進行了深入思考。從我國政策話語與相關學術研究來看,文化治理的三維格局逐漸明晰,包括政府維度、市場維度和公民維度[9]。其中,政府維度體現國家意志與主流意識形態,呈現為政治認同的國家話語[10];市場維度體現資源分配與要素流動,呈現為價值多元的社會話語;公民維度指向公民意志與主體性構建,呈現為自我賦權的公民話語。基于此,文化治理格局下的國家維度關乎文化的目標與取向,是文化治理的前提;社會維度關乎文化的價值與選擇,是文化治理的過程性保障;公民維度則關乎文化的訴求與表達,是文化治理在場的主體性回應。而這應然格局中三維對應的國家話語、市場話語、公民話語所代表的力量,則反映了我國文化治理的格局結構是否合理[10]。應然層面的文化治理格局意在使公民真正成為文化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體,形成和諧互動的三維結構,達成真正的合作共治,從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與模式的轉型。
(二)實然:當代中國文化治理的主體追問
在我國文化治理的推進過程中,國家話語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誠然,強勢的國家話語有利于體現國家的“家長責任”與“文化監護”,有助于構建以獨有文化為核心價值的文化中軸作為社會的穩壓器,從而潛移默化地使民眾心中生成具有民族特征、時代意義的“集體意識”。但隨著文化治理實踐的推進,當代中國文化治理格局中的結構性問題逐漸暴露。由于家長式政府所帶來的路徑依賴,公民在文化治理中存在習慣性接受、被動性參與、主體性缺失等問題,在文化治理在場中很難發揮應有作用。因此,在文化治理的背景之下,有必要發問:如何使公民真正成為文化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體?如何實現文化治理的主體性回應?如何達成文化治理在場中真正意義上的共治與善治?有學者指出,公眾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活動、積極表達意見是公民在文化治理中達成共治與善治的高階表現[9]。在強勢國家話語的歷史背景下,公民話語的有效表達,一方面需要突破國家主導的慣性話語機制;另一方面還需要激活公民的主體性,促使其主動行使權利,進行有效的話語表達與積極的文化行動。
一方面,隨著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與全面滲透,公民的文化需求已然呈現出爆發式增長,需求異質性越發凸顯,這有利于使公民話語作為一種反抗性力量推動文化治理格局下三種話語的再博弈;另一方面,我國在改革中獲得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文化相對被忽視,多種類型亞文化的悄然滲透和擴張使我國文化矛盾在個體間、階層間顯化[7],這使我國政府更加重視文化的功用,關注公民的主體價值。托尼·本尼特指出,文化的功用將“有利于在人們中培養一種自愿的自我控制力”[6]239,話語將“使我們更積極地參與到對我們自身的管理與監督之中,并促進我們自身的發展”[6]206。但“文化建構形成的謹慎的主體不是擁有一套信仰的主體——這樣的主體能通過贊同現存的權力而使其永存——而是作為一個行動者,通過要過一種新生活的行動實現權力運作的職能”[6]258。這意味著,文化治理的主體性回應并不是對領導權能的單純順應與贊同,而是以文化行動“作用于社會以調節社會,同時作為形成一種觀念即國家權力從屬于批判的理性形式的手段而發揮功能”[6]336。
一言以蔽之,文化治理的順利推進必依賴于公民的主體地位及其主體性回應,并在某種意義上達成公民文化自覺與行為自覺的某種治理性結果[7],由此從主體性走向主體間性,在對話交往中實現公民賦能,在文化治理中實現互動與回應,從而達成共治共享的理想局面。
(三)使然:文化治理下大學人文教育的入場
在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之下,文化治理的推進一方面更加凸顯出主體性建構的重要意義。主體性是培養擔當中華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的根基,這也意味著當代我國對人的培養應當重在人的主體性建構;其次,主體性也是社會共識和秩序凝結的內在紐帶[11],是達成文化自覺與行為自覺的養成性基礎。另一方面,主體性也是公民表達文化訴求等活動的參與基礎,是匯聚多方話語從而達成公民話語再博弈、實現共治共享的實踐性基礎。因此,文化治理格局下的主體追問使大學人文教育應需而入場,并力圖以其在文化、育人、治理方面的功用回應文化治理。
首先,從歷史視角來看,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人文文化特質:一是強調以人為本,要求保持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和獨立性;二是主張禮樂教化,強調自我管理,讓人自覺遵守社會行為規范[12]。文化本身就具有教育的意味,既是教育的工具,也是教育的目標,具有潛移默化且深遠持久的教育作用。“文化是一種道德教育學,將會解放我們每個人身上潛在的理想或集體的自我,使得我們能夠與政治公民的身份相稱,這樣的自我在國家的普遍范疇中得到最高表現。”[13]其次,教育是建構文化、革新文化、再生文化的重要場域,其中人文教育作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力量與方式[14],由里及外地存在于國家文明、社會生活以及育人場域三個層次中,而這恰與文化治理的三維格局相對應。歷史的經驗也表明,展現人之主體性的人文教育使公民具有與治理相匹配的素養,是把人從自然狀態解放出來的必由路徑,是社會治理最堅實、最持久、最本真的人文基石[15]。此外,文化和知識分子空間——類似大學的場所,將在發展和傳播社會與文化批判的特殊形式上發揮首要作用[6]336。知識分子具有“典范效應”,能以行動啟蒙社會大眾、關懷文化生活并推動社會發展。
基于此,大學人文教育作為人文素養培育與主體性建構、文化傳承以及話語表達的重要推手,將助力文化治理中各方回應與互動的實現。對于人文教育,托尼·本尼特指出:“人文學科需要重新定位,它們應該對現有的社會、學術、政治爭論和手段做出切實可行的有益貢獻。”[16]但基于大學人文教育對文化治理的應有之義,不應將其局限于對人文學科的重新定位,而應當基于時代背景,從目標、過程以及特有價值上與我國文化治理動態相呼應,從而探尋教育與治理的結合點,為全面實現“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奠定堅實的“軟支持”。
二、 何以:文化治理下大學人文教育的“三為”面向
在當代中國文化治理格局下,大學人文教育與文化治理在目標、過程與價值上呈現出高度的耦合與呼應,并表現為主體性賦能的個體之為、以文育人的行動之為以及話語表達與權力的治理之為。需要明晰的是,本文所指的大學人文教育并非人文主義教育或者狹義的大學人文學科,而是廣義上以人文育人理念提升青年大學生的人文認知以及人文素養水平的教育。因此,大學人文教育關注個體的自我修為與文化品性,意在使青年大學生能夠認識自我、真正“成人”[17],從而促進“人的主體性建構并實現文化治理中的主體性回應”這一理想的實現。
(一)主體之為:主體性賦能與德性培育
在文化治理視域下,公民話語的主體性表達之基礎必然與其主體性能力(抑或素養)密切相關,大學生作為具有“典范效應”的知識分子群體,更應具備較高的自我修為與道德素養。因此,當大學生作為文化治理格局中公民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時,文化治理目標與大學人文教育目標不謀而合。
從文化的主體之為來看,一是關注人的主體自我修為,實現人與自我統一;二是關注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在文化公共層面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圍,使人與社會相通[18]。正如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人文教育的第一要義即實現人與自我的統一,只有在人與自我統一的基礎上,個體才能真正親身參與、投入實踐從而進行社會創造。但人的主體性不僅是理性自我的充分顯現,個體有限性與無限性的通達可以轉化為個體向其他個體、群體和歷史的延續[11]。這意味著個體的主體性不僅體現于其自身,也體現于個體之間。也即,個體主體性的生成必然發生于社會之中,而個體與社會的共通正是文化治理的主體之為之一。這與人文教育在培養理性自我基礎之上欲達成的公共理性相耦合,也是達成群體認同與形成集體行動的基礎。
基于此,大學人文教育應致力于個體的主體性賦能與德性培育,從而塑造具有較高自我主體修為與德性氛圍的公民群體,繼而實現個體理性與公共理性互通與共融。一方面,大學人文教育的主體性賦能應當使大學生具有與文化治理相匹配的素養,從而具有對話與發聲的能力。大學生的主體自我修為不僅僅體現為人文認知水平,更體現其在公共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自我認知、理性思考與價值判斷等能力上。另一方面,大學人文教育的德性培育應超越私德,關注公共德性的內化,使大學生從主體性走向主體間性,將個體發展融入共同體發展。個體只有在自有、自發、自在的基礎之上,才能達成自覺、自為的治理結果。賦之以能力并喚醒其自發認同,才能使大學生確立順應時代潮流、堅守民族靈魂、符合國家價值的精神追求,從而實現個體與自我的統一、個體與社會的相通。
(二)行動之為:文化的動態建構與柔性塑造
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多元文化交流已成為常態。只有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已經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19]。這意味著,只有堅實的人文基礎才能使我們在日益動態多元的文化環境中堅守本心并理解他者。
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人類對民族、歷史、制度、文化等的認識之可能性都是基于自己的創造,而正是基于這種親身參與、親身創造的同質性,人才有可能從內部去認識、重構和理解社會歷史文化[20],并在認識、重構與理解文化的過程中實現自我的塑造與發展。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文化認識的異質性日益凸顯,文化也逐漸呈現出多元而動態發展的特點,這使文化的功用逐漸從縱向的時間維度轉向橫向的空間維度。在這個過程中,不僅需要認識、重構與理解本土文化,還要在文化市場化、文化全球化中建構與理解新的文化。這意味著,文化的革新與發展往往源于作為文化行動者的“我們”,而文化行動的發生又以文化對“我們”的影響為誘因。個體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脫離并再嵌入群體,并以文化產出的形式向外界傳播影響,而其他主體對客體性文化產出的理解或再造又意味著新一輪文化動態建構的開始。文化治理的主體性在這個動態建構過程中得到充分顯現,個體行動者既是文化的主體,又是文“化”的對象;個體行動者不僅需要“自識”,在此基礎上還需要“互識”,從而“再塑我者”,獲得“他者認同”。因此,只有具備較高的人文基礎,才能實現“自識”與“他識”的動態交互,并在文化動態建構過程中實現自我的塑造與發展。
基于此,大學人文教育將以學校體系的方式實現文化建構過程中的人文內化與文化交往過程中的人文堅守,從而幫助大學生在“自識”與“他識”的基礎上實現文化對話與交往。一方面,大學人文教育的過程正是認識自己文化的傳承過程,是對主體人文性與生命性的塑造。經典文化是人文教育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植根本土文化的人文積淀是文化治理中主體能夠認識、重構、理解自己歷史文化的前提。另一方面,大學人文教育的發生過程也是動態建構的過程,表現出主體交互性。大學人文教育的作用方式正是主體之間的動態交互,是教與學中的互相影響與互相成就,而非單向的師授生聽方式。此外,大學人文教育的作用體現在個體行動的過程中,表現出包容性與共通性。大學人文教育有助于大學生對文化進行選擇與判斷,也即進行文化心智模式的轉換;另一方面,在面對多元文化環境時,也有助于大學生學習從個體到群體的文化對話及交往過程[21]。
(三)治理之為:話語權力與文化共同體
在文化治理視域下,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過程必然意味著言語對話的產生,并在對話的基礎上實現權力的博弈。但在我國歷史進程中,國家話語體系之下的公民多表現為“沉默”或“失語”狀態,成為話語權弱勢群體,亟需一種一致性的力量使之形成行動共同體。一方面,由于具有強勢地位的國家話語以知識性文化輸送著價值體系,以“知識——權力”操縱文化治理機制中的具體規則,意在使社會公民中形成以專門知識建構社會的意識形態安全底線[22],但卻相對削弱了公民話語的聲音。另一方面,隨著文化市場的涌動,新媒體逐漸在市場話語中變成另一種“強勢話語”,具有彌散性和廣泛性的新興媒體話語伴隨著話語失度與失真,攜帶外來文化的價值沖擊[23],進一步消解了公民的話語權力。在這兩種強勢話語的影響下,公民的“沉默”逐漸演化為一種慣習。這意味著,作為新生代公民的大學生群體,不僅需要提升主體性能力,以主體的身份進入文化治理的場域;還需要超越“慣習”,以共同體的身份凝練新的行為方式與話語體系,作為一種文化動力應對市場話語的沖擊,張揚公民話語的價值。
因此,大學人文教育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個體發展之上,也同時彰顯于其構筑青年共同體的責任之上。共同的人文內核與價值觀將有利于大學生群體形成一致性追求,凝聚共識、合力行動,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從而以新生代的力量去破解公民話語困境。從個體層面看,大學人文教育著力于提升大學生個體的主體性修為與德性,從而成為“能為”的個體;從群體層面看,大學人文教育致力于提升大學生群體共同的人文情懷與價值認同,從而形成“自為”的狀態;從共同體層面看,人文教育旨在使大學生群體達成一致性追求與積極行動,從而實現“有為”的理想。正如托尼·本尼特的看法,“批判理性”與“積極實踐”是文化治理格局中知識分子群體的理想姿態。大學作為培育知識分子群體的場地,需以人文教育作為其“教育底色”,以知識賦能大學生,以人文聯結大學生,以話語賦權大學生,從而使大學生群體主動擺脫“沉默”的面具,以行動的共同體參與文化治理并投身社會主義治理實踐。因此,大學人文教育之于治理的價值,正是彰顯于培育大學生這一青年群體的主體性之上,從而聯結個體并形成共同體,有效增強公民話語力量。由此,文化治理格局下的三種話語力量才有可能實現結構性優化,繼而推動共治共享局面的實現。
三、 何為:文化治理下大學人文教育的行動路向
基于大學人文教育與文化治理的耦合關系,以及大學這一育人的關鍵場域,大學人文教育不僅具有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的傳統意義,也肩負個體主體性賦能、話語權彰顯的時代責任,更是凝結文化共同體、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紐帶。因此,從育人的視角來看,大學人文教育仍需探索將人文滲透育人全過程的路徑,從而實現個體的主體性賦能與德性培育,以個體“能為”推進文化治理;從文化的視角來看,大學人文教育還需探索推動文化認同的路徑,從而凝練核心價值的文化內核,以群體“自為”推進文化治理;從治理的視角來看,大學人文教育更需探索實現文化行動的路徑,從而打破公民話語的沉默慣習,以共同體“有為”推進文化治理。
(一)能為:以人文滲透的育人過程實現主體性賦能
基于文化治理的目標,大學人文教育應當在育人過程中體現人文滲透的特點,并在課程思政等政策引領之下構建起人文學科集群,通過文學、史學、哲學等人文學科集群,復歸人文學科的共通與互融,從而超越學科的局限性,使青年大學生能夠站在歷史和文化的高度去審視自身并實現個體的主體性賦能[24]。
一方面,大學人文教育應當以個體的主體性賦能作為目標,關注育人過程中的人文滲透。主體性賦能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只有將人文滲透育人的全過程,才能使個體在充滿人文關懷的教育環境中發展。但反觀現實,大學人文教育尚未實現全過程的人文滲透,甚至對人文教育的目標與過程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誤讀。其一,大學人文教育的主體性賦能不僅僅是對人文知識傳授的單向度關注。知識輸送并不意味著主體性的育成,學生的主體性往往被工具化評價體系所隱蔽。事實上,大學生的主體性表現為以人文認知水平為基礎的自我認知、理性思考與價值判斷等綜合能力,并體現為與治理相匹配的個體素養。其二,大學人文教育的德性培育不應局限于對政治德性的單向度關注,繼而異化為任務性的思政課程。無可否認,德育是大學人文教育的重要內容,但基于立德樹人這一大學的根本任務,大學人文教育需實現全方位的德性培育,促成公共德性的內化。在當前課程思政的政策東風之下,課程思政的推進為人文滲透課程提供了有益思路。由于課程思政建設與通識教育人文課程具有深層次的內在契合性,因此,以課程思政建設為指引[25],將人文特質與思政內容同步滲透、正向關聯。這是因為通識教育人文課程內容本身就具有人文特質,通過各類通識課程之中的人文滲透與思政互動,有利于使青年大學生的德性生成與人文認知提升融為一體,從而實現人文認知與德性的共生。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文滲透應當因課而化、常態推進,并在內容與方法上進行主體性設計,在評價上避免功利性傾向。
另一方面,大學人文教育應當突破學科間的壁壘,實現學科間的人文滲透。從當下教育環境看,大學人文學科邊緣化現象嚴重,極不利于時代新人的主體性建構。大學對專業化的追求使人文教育日漸式微,人文學科的細分使學科間被架構起人為的隔膜,學科競爭甚至使部分人文學科日益萎縮。例如,北京大學近年來以“專業+項目”的方式探索出古典文學、思想與社會、漢語國際教育等跨學科人文教育課程體系,有益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鍛煉其人文思維。因此,乘著新文科的政策東風,大學人文教育應當注重學科間的人文滲透,從而構建起人文學科集群,實現協同共育的教育生態。通過建構人文學科集群,不僅有利于集聚學科資源,實現學科間的互相支撐;更能以文化集群的形式發揮溢出效應,以充滿人文關懷的教育生態全方位提升個體的素養,從而助力個體“能為”的實現。
(二)自為:以人文產出的形式凝練文化核心價值
文化作為一個動態建構的過程,其必定發生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之中,并由某種文化形式承載。因此,大學人文教育應當反思如何通過人文產出凝練核心價值,以順應時代潮流的形式承載核心價值并擴散影響,從而構建起文化治理格局中穩定、包容的中軸力量。
大學人文教育要回應時代需求,增強其在文化市場中的話語影響力。從歷史的角度看,大學一直承擔著文化傳承與知識生產的重任,但大學人文教育的人文產出形式相對固化,主要體現為論文、報告等形式,這使人文產出在現實中常常被等同于學術生產。論文、報告等確有學術價值,但其話語表達不易被大眾接納。同時,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技術發展全面改寫了文化的傳播形式與速度。技術的自反性建構起知識的“定價”體系,變現的壓力使思辨傳統和人文理論研究被明顯邊緣化[26]。這也意味著大學人文教育需要更多的資源支持與財政投入,以面對市場經濟的沖擊。
大學人文教育需肩負時代責任,傳播中華民族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各類文化在技術邏輯的影響下或多或少地發生了形式上的變化,并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被建構、轉換,逐漸演繹出了更親近民眾的話語表達。但對形式的過度關注,往往意味著對實質內容的相對忽視,當下市場中部分“親民”形式的文化實際攜載著對核心價值的解構沖擊。碎片化文化、數字信息漫灌以及各類亞文化的沖擊使大學生群體更需要一種牢固的內心力量,以提升共同的人文情懷與價值認同,從而用人文的力量平衡當下市場話語的浮躁與功利,在“自識”的基礎上達成“互識”。
大學人文教育應積極供給優質精神文化產品,提升其人文產出水平。大學人文教育的產出形式不應拘泥于學術研究,可嘗試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與時代新意相結合,并以順應時代潮流的文化形式承載之。例如,在部分文化產出中利用新傳媒途徑,或者以大學生群體容易接受的流行話語、生活話語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闡發和創新,從而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話語親和力[22]。例如,云南大學的學術史話劇《魁閣時代》,以跨學科協同、師生構作的方式將人文、學術與傳媒融為一體,取得了較好的育人效果與示范效果。通過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練在親民話語形式下的文化產品中,有利于極大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力,使國家話語、主流話語逐漸融入大學生的日常學習生活中,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民族精神入腦入心。由此,大學生群體方能逐漸達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為轉化,從而以共同的人文情懷與價值認同投身于文化治理與社會主義實踐之中。
(三)有為:以數字人文的實踐情境鑄牢文化共同體
當下,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為文化建構了新的虛擬空間,大學人文教育需探尋文化治理中數字技術與人文堅守的平衡點,為大學生群體創設數字人文的實踐情境,從而促使其以一致性追求形成行動,實現共同體“有為”。以上海大學的“上大元宇宙”平臺為例,其集學術、講座、展覽、社交等功能于一體,學生們樂于在虛擬空間進行數字化學習、社交與生活,初步實現了虛擬技術下的真實共情與人文交往,這為數字人文的實踐情境提供了推進基礎。
一方面,借助數字技術,以大學數字人文實現人文培育、學術生產以及綜合實踐等功能的一體化,助力大學生的文化實踐。大學數字人文是對大學人文教育的堅守與延伸,這意味著大學生群體人文素養的培育過程不僅發生在傳統教育情境之下,也將進行數字情境下的轉化,例如學習方式的數字化、學習資料的數字化以及教學技術的數字化。此外,大學數字人文應當突破傳統大學人文教育的局限,為學術生產創造具有強大包容性的學術版圖[27]。人文學科的交叉與合作,有利于培育大學生跨學科思維,并以多元化的人文學術產出為大學生群體營造文化內核堅實且包容多元文化的環境。
另一方面,關注人文轉化,注重大學數字人文作為文化情境性機制的功能。當下,虛擬空間意味著文化作用的延伸與解構將同時存在,這使文化的動態建構更容易且更頻繁。然而,虛擬空間也意味著文化價值的多元與叛離將同時存在,這使話語的權力博弈更激烈且更分散。這表明,在數字技術邏輯的加持下,公民話語的異質性在虛擬空間中得到凸顯與放大。但與此同時,數字技術的蔓延也使公民話語分散,并出現表達失度與失序現象,這說明數字時代更需要人文柔性邏輯的堅守。在此背景之下,大學生作為虛擬空間的活躍分子,一方面需要促進人文素養的數字轉化,做虛擬空間的文化典范;另一方面也需積極參與虛擬空間的文化實踐,拒絕沉默與匿名。因此,大學數字人文應當以數字化技術促進人文轉化,從而激勵行動者有意識地在不同制度情境中轉變文化策略,并有效實現集體行動動員[28]。大學數字人文可嘗試以數字項目式研究作為實踐單元,以協同性、合作性的團隊實踐形式,使大學生群體在虛擬空間中為了一致的目標而行動。由此,大學生群體將以利益共同、責任同擔、積極行動的行為方式增強其話語力量,從而促進共同體“有為”的實現。
參考文獻:
[1] ??施雪華,祿瓊.當前中國文化治理的意義、進程與思路[J].學術界,2017(1):53-62.
[2] 齊格蒙特·鮑曼.作為實踐的文化[M].鄭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1.
[3] 李艷豐.走向文化治理:托尼·本尼特文化研究理論范式的轉型[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168-177+192.
[4] 福柯.性經驗史[M].佘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
[5]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M].曹雷雨,姜麗,張跣,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342.
[6] 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與社會[M].王杰,強東紅,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7] 張鴻雁.“文化治理模式”的理論與實踐創新——建構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為”[J].社會科學,2015(3):3-10.
[8] 張良.論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中的文化治理[J].社會主義研究,2017(4):73-79.
[9] 柯尊清.公共文化治理的理論維度、過程邏輯與實現路徑[J].理論月刊,2021(1):105-112.
[10] 廖勝華.文化治理分析的政策視角[J].學術研究,2015(5):39-43.
[11] 張鯤.新時代“時代新人”之主體性建構[J].思想教育研究,2018(10):24-28.
[12] 樓宇杰.中國文化的精神根基[M].北京:中華書局,2016:7.
[13] 特瑞·伊格爾頓.文化的觀念[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8.
[14] 王兆璟.新時代人文教育場域之突圍與再造[J].社會科學戰線,2019(8):228-233.
[15] 劉建軍,鄧理.基于人文教育的人文治理——理論建構及實踐進路[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2(2):60-73+194.
[16] 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與社會[M].王杰,強東紅,等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225.
[17] 馬智芳.論人文教育的三種內涵及其現實危機[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2,32(25):16-20.
[18] 徐椿梁.認知·實踐·主體:價值在文化存在中的三重意義[J].求索,2020(6):77-83.
[19] 劉謙.學校育人過程中文化自覺性的培養[J].教育研究,2011,32(3):13-16+20.
[20] 牛文君,張小勇.人文與詮釋——維柯人文科學奠基的詮釋學理解進路[J].社會科學戰線,2021(5):52-59+281.
[21] 廖文偉.文化自覺與社會行動者[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6(6):17-24.
[22] 劉莉.從“生命政治”到“文化治理”:對公共文化的一種定位與解構[J].思想戰線,2020,46(6):72-78.
[23] 肖薇薇,陳文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青年認同的話語賦能[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6,35(1):39-46.
[24] 李偉群,朱白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視域中的高校人文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16(9):86-89.
[25] 祝浩涵.論以課程思政建設推動通識教育人文課程質量提升[J].教育文化論壇,2022,14(6):79-83.
[26] 劉超.數字化與主體性:數字時代的知識生產[J].探索與爭鳴,2021(3):22-25.
[27] 孟建,胡學峰.數字人文:媒介驅動的學術生產方式變革[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41(4):24-28+54.
[28] 魏海濤.集體行動的形成:一個文化視角的理論模型[J].社會學評論,2019,7(4):75-87.
University Humanistic Education for Cultur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and Targets
HE Peiha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715)
Abstract:
As a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l, cultural governance reveals a dynamic game process among the three discourse forces of the state, society and citizens. However, as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in the patter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e gradually revealed, the inquiry of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governance has introduced the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 As a key field for cultivating new talents of the times and a place where young people's discourse converges, university humanistic education should promote cultural action through the nurturing process of humanistic penetration, the form of humanistic outputs, and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humanistic, so as to enhance discourse power and help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gain achievements.
Key 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 humanistic education; subjectivity; discourse
(責任編輯:梁昱坤 郭 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