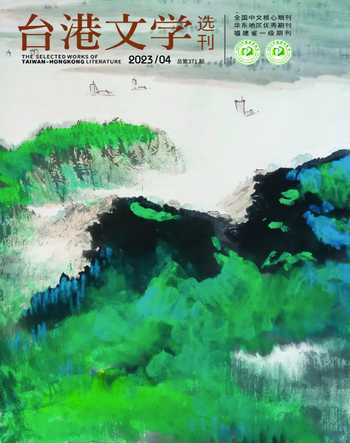驚蟄
李忠元
驚蟄一大早,陣陣雷聲驚起房前老樹上的一對烏鴉,發出清脆的啊啊叫聲,車老漢聽了叫聲,心里不免糾結起來。
因為在鄉下,自古就有一句諺語:烏鴉叫,不祥兆。
今天烏鴉叫,到底有啥不祥之兆,車老漢百思不得其解。
車老漢佝僂著腰身,整頓一下思緒,他不愿意再自尋煩惱了,走到院中,揮舞手臂,企圖趕走那兩只烏鴉。但烏鴉卻不示弱,依舊不停聒噪。
車老漢很生氣,但也沒別的辦法,只得折回屋,關好門窗,耳不聽為凈吧。然而,屋外烏鴉叫還是隱隱傳到耳膜,就像一滴又一滴水珠落入一泓水洼,在平靜的水面上漾起層層漣漪。
車老漢正在屋里捂著耳朵和烏鴉較勁,卻不想兒子車生悄然而至,手里拿了一沓錢,樂呵呵地說,爸,今年的地我包了,您就不用費勁往外包了,這是地兒錢,每坰地一千五,兩坰地正好三千,這是錢,您拿好!
聽了這話,車老漢的心一陣熨帖,愁結的眉頭頓時舒展,心里那只啊啊亂叫的烏鴉根本沒打一聲招呼,就悄無聲息地不見了蹤影。
車老漢轉怒為喜,他點了錢,麻利地裝進身后的紅匣子,坐下來,志滿意得地對車生說,這地價是有史以來最低的,你包下它,就等著掙錢吧!
也不怪車老漢絮叨,自從國家對玉米不再實行保護價,糧價降了兩毛,耕地頓時成了燙手山芋,對外流轉價一落千丈,去年還一萬元呢,今年一經炒作,竟狂降到一千五。
車老漢年老體弱,耕地一直轉包給車生,靠流轉金艱難度日,勉強過活。如今這地價一降,車老漢更感饑寒交迫。
確實,這點錢哪夠活命啊?
于是,車老漢天天關注《新聞聯播》,希望兩會提出新政,把糧價提上去,讓地價得以恢復,雖說不能大富大貴,但也能食以果腹。
可如今兩會都要開完了,糧食政策卻始終沒人提及,車老漢感到陣陣心痛。
本來,他是有低保的,但前幾年女婿花兩千元,買了一輛二手破車,民政部門就停了他的低保。
所以,承包地就是車老漢的命根子,沒了這點指望,他的活路就被堵死了,盼著地價上漲,不是貪欲膨脹,而是他的求生本能。
面對糧價下調,車生也有動搖,他也厭棄了土地,打算進城打工,擺脫糧價波動帶給自己的不安,畢竟他也要生存。但他一直猶豫,大批農民工涌入城里,崗位競爭激烈,到哪去找適合的工作呢?更何況,進城舍家撇業的,生活也更艱辛,這個挑戰需要足夠的勇氣。
車老漢知道兒子的那點出息,所以一再勸阻,希望他在家種地,今年這地價,即便是糧價不漲,也會賺個盆溢缽滿。
可車生不聽,依舊每天叫嚷要出去打工,總是拉出一副要走的架勢。
他一要走,車老漢就深感惶恐,萬一兒子出去了,這地一撒手可就沒了,下年再想抽回來,都不太容易了。
車老漢深知車生身體并不硬朗,重體力活未必能堅持多久,如果他打工前腳剛走,耕地就得馬上包給別人,畢竟眼下已是驚蟄,馬上就要春耕了。
古詩有云:微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車老漢當過十多年的民辦教師,這首詩今天依舊耳熟能詳。
可這地不包給別人,兒子走了,他把地擱那“放兔子”,就連個子兒也拿不到,生活就更沒指望了。
車老漢度日如年,一邊為自己的生計發愁,一邊為兒子的去向擔憂。
沒想到,經過多日的思想盤桓,車生終于開竅了,比往年痛快了許多,竟拿現金包下了自己的兩坰地。
今年這太陽是不是從西邊出來呢,車老漢惶惑地望了望天空。
車老漢想,人是會變的,我畢竟是他老爹,他懂得盡孝了。
想到這,車老漢一改悲涼的心境,他感覺天氣越來越暖和了,全身都是溫熱的。
車老漢感受到了親情的溫馨,雖然他仍舊面臨生活來源的嚴峻考驗,但在兒女親情面前,他已經變得很愜意了。
車老漢心里這一高興,就感覺身子骨一下硬朗了,他竟一反常態,忍著腰痛,走上東大道,和鄉鄰們聊起了家常。
沒想到,這一聊天,車老漢差點叫出聲來。原來,這兩天受兩會影響,糧價竟然大幅上漲,水漲船高,地價竟然上升到了四千五。
車老漢猛然醒轉,我說車生剛才怎么這么痛快呢,原來是先下手為強啊!
車老漢再也沒心情聊天了,他忍著腰痛,加快腳步,要回去問問兒子,父子爺們還用來這一招嗎?
可車老漢到了車生家門口,卻發現他家鎖頭把門。
這孩子哪去了?
車老漢在心里不住地默念,不覺走到了自家門前,他發現前院鄰居蘇南也走進院來,向自己和老伴詢問:你家的兩坰地都在哪啊,您兒子上午走之前已經把兩坰地以市價九千轉給了我。
聽了蘇南的話,車老漢腦袋“嗡”一聲,和身旁的老伴同時張大了嘴巴……
(選自《蘭州日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