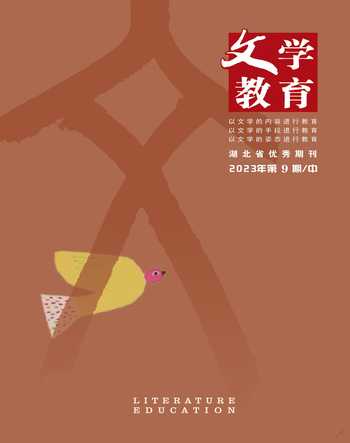以寧波之行為切入點看內藤湖南的中國認識
冀艷艷
內容摘要:近代日本人的來華游記,對于認識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以及了解當時的中國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本文把焦點聚集在內藤湖南的寧波之行上,從中了解當時寧波的部分風貌,從而進一步考察他對寧波的認知態度。此外本文也通過詳細分析內藤湖南的寧波訪書等活動,結合時代背景具體分析影響其中國認識形成的因素,捕捉到了他對中國文化的占有性欲求,窺探到他始終把日本利益放在首位的“畸形”中國觀以及為日本侵華服務的行徑。
關鍵詞:內藤湖南 禹域鴻爪后記 寧波之行 中國認識
研究近代日本人的來華游記,對于認識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及了解當時的中國有重大意義。本文試圖通過內藤湖南的紀行文了解其對中國都市的情感態度及中國認識。
本文研究的文學題材主要集中為內藤湖南第二次中國之旅的紀行文《禹域鴻爪后記》和《游清雜信》。通過他對寧波的記錄,了解當時寧波的情況,分析他對寧波的感情態度。接下來本文也將進一步通過分析內藤湖南的寧波訪書等活動,考察其訪書行為背后隱藏的真實目的。此篇文章對于進一步深化讀者對內藤湖南訪書行為的認識,深度了解其學術背后隱藏的政治性思想上會有所裨益。
一.內藤湖南的寧波行
內藤湖南是日本近代中國學的重要學者,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研究領域卓有建樹。內藤早期是記者,之后成為京都大學教授。他在《禹域鴻爪》中提到,去中國旅行,是向往已久的事情。他幼年便接觸漢學書籍,熟知中國的許多名勝古跡和地理人文,他的中國情結可以說是由此扎根。促成內藤第一次中國旅行的是1899年年初發生的一場火災。意外火災使內藤失去了日本國學、日本文化等方面的大量藏書。為了使內藤從打擊中走出來,朋友們進行了籌資,再加上報社的資助,內藤得以實現中國行的夙愿。以此次為開端,內藤此后以不同目的多次往返中國。
根據學者錢婉約的研究,內藤一生曾十次來過中國,旅跡遍及華北、東北、長江流域的所有主要大城市,像北京、天津、沈陽、上海、南京、蘇州等地,則是屢次游歷。在內藤湖南的十次中國之旅中,只有在第二次的旅途中,到訪過寧波,停留了4天。與交通便利、風景名勝眾多的北京、上海、武漢、蘇州等地相比,寧波并不在日本人來華的熱門路線當中,也并不受到重視。因此近代日本文人、學者到過寧波,在其游記中提及或介紹寧波的可謂不多。因此,作為“學者型記者”的內藤湖南的寧波之旅更加值得關注。
那么內藤湖南在寧波的主要活動是什么呢?筆者根據內藤湖南的《禹域鴻爪后記》和《游清雜信》,整理了他的行程。
1902年12月16日,在上海拜訪羅振玉;下午搭汽船赴寧波。17日上午在寧波鄞江下船,投宿永儀公旅社;赴天一閣請求參觀,未果;訪盧氏抱經樓,被拒;欲訪崇實書院,誤至中西學堂并觀之;至日新街之書肆汲綆齋等購書。18日賃民船往余姚。19日一夜過后,船行至不遠,始知被旅社老板誆騙。20日船抵余姚,登城內之龍泉山,拜王陽明祠、嚴子陵祠;觀山下之龍泉寺。
關于去寧波的緣起,內藤在游清雜信(再發自上海)當中提到:“與舊友羅叔韞氏(振玉)相晤,猶獲金石古書方面頗有價值之材料,并獲贈瓦當一枚,據氏相告,寧波舊藏書家范氏天一閣及盧氏抱經樓,今均收藏瓦當。因氏特意饋贈之四冊天一閣現存書目,加以彼處本為吾邦籌劃設領事分館之所在,故頗生浙東之游興趣,并詢及路程諸事。博愛丸二十七日發,時間似尚有余裕,即偕宮島農商務技師、狩野直喜君、本社之堀君及中國仆役二人,于十六日晚搭乘汽船江天號赴寧波,翌晨抵達。”
從以上材料我們僅能夠看出,內藤一行前往寧波似是臨時起意,原因大致如下:一是聽羅振玉提及寧波的天一閣和抱經樓,并從羅振玉處得到了四本天一閣的現存書目;二是當時日本有在寧波設置領事分館的計劃,也一并生發了游歷考察的興趣;三是時間尚有余。
這其中,天一閣及抱經樓應是引起了內藤的極大興趣,才會讓內藤在即使無人引薦天一閣主的情況下,仍決意直接赴寧波。那么,天一閣和抱經樓究竟是什么樣的存在呢?
天一閣乃明代寧波進士范欽建立的藏書樓。據記載,范氏的藏書,不是收藏宋元的珍本名刻,而是收藏有明一代的典冊書籍,像明代的地方志書、詔令、制誥、登科錄、邸報各項文件,以及明代雜史和詩文集,又收藏明代新拓的漢、魏以來碑刻拓片。天一閣的藏品中最珍稀的是明代的地方志和科舉錄,其數量也是最多的。羅振玉所列四冊書目中必然會有地方志。內藤漢學素養深厚,更是深知地方志的重要價值和意義。他直接奔赴天一閣的行為,更是證明了天一閣所藏書目的珍貴性。
抱經樓是清代浙東著名的藏書樓,主人是盧青厓,當年藏書之富,可與范氏天一閣、鄭氏二老閣相媲美。據記載,盧氏藏書中保存有多種珍本秘籍,如宋刻本開慶《四明續志》十二卷、宋乾道刻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金刻本《經史類證大全本草》二十三卷;抄本有《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等。
據現有材料,內藤并未從羅氏處得到抱經樓的具體書目。內藤的欲訪抱經樓之舉,自然不是考察羅振玉所說的“瓦當”。從抱經樓的藏書書目中,我們能夠推斷出內藤欲訪的乃是我國古代的古籍珍本。在無人推薦抱經樓書目情況下,內藤卻目標明確,天一閣訪問不成,便轉場抱經樓,可見內藤并不像他在《游清雜信》中書寫的那樣,羅氏的推薦是他游歷天一閣及抱經樓的契機,而是他早已對其關注且頗感興趣。這點我們從他寧波旅行前的1901年3月寫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他提出《應向中國派遣奇籍采訪使》,主張到中國收錄珍貴史籍,其中也提到聽說寧波的馮氏藏有宋本《修文殿御覽》,此書引用古書更多、更古老且卷帙浩瀚,若用鋅版凸版技術來影印這些書,并不難吧。
從中可見內藤認識到《修文殿御覽》的學術價值且異常“熱衷”獲取此書,而抱經樓便有《修文殿御覽》的抄本。因此內藤的抱經樓一行絕對不是巧合,而是熟知中國古典及其動向的內藤刻意行動的結果。抱經樓中也收藏有地方文獻。據記載,盧青厓還注重地方文獻的收藏,先后收藏有開慶《四明續志》十二卷,及全祖望的《四明文獻》三十二冊一百四十卷,還有其他四明地方文獻,計數百種。且歷史上江浙一帶的藏書樓多收藏地方志。內藤除了對中國的珍奇異本格外留意外,他的天一閣及抱經樓的探訪計劃也能窺探出他對中國的方志也很有興趣。此外,據學者巴兆祥考證,內藤湖南收集了眾多地方志,比如:《廣輿記》24卷、《大明一統名勝志》208卷、《漢南紀游》1卷、(乾隆)《黔南識略》32卷、(宣統)《新疆圖志》等,目前保存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和關西大學等處。在內藤第一次旅行后的紀行文《燕山楚水》中,也提及了參考引用的各類地方志書。由此可見,內藤熟知中國的地方志,且一直有在關注和收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內藤到訪寧波,不只是朋友推薦下的表面的偶然之舉,更是必然行徑。他來寧波以訪書為主要內容;主要活動是去書肆購書、觀藏書樓;欲訪的書目主要是中國的珍貴史籍及地方志。
二.內藤湖南的寧波訪書活動
近代日本中國學家來華訪書,作為一種普遍性的學術活動,開始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學術風氣和學術方法的影響下,日本學者開始更加注重對研究對象進行實地探查、文獻調查、搜集文獻等工作來開展深度的學術研究。日本中國學的教授、教員和留學生們,在中國進行學術調查、訪書就是最好的明證。
伴隨著日本近代化的發展,地方志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得到日本各界人士進一步的認可。日本諸多研究機構、學者及社會人士開始有意識地大批量地收集、采購、掠奪中國方志。地方志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社會、經濟資源問題所必須的一種重要資源。學者巴兆祥認為,近代日本實行“大陸政策”而侵略中國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的。為侵略而搜集地方志,又利用地方志為其侵略服務都是不爭的事實。
內藤寧波訪書的真正緣由一是探求珍貴古籍;二是搜尋地方志。內藤之后在中國學和史學上取得的學術研究成果,正是建立在對中國古籍的搜求考證上。表面上看,內藤通過訪書,搜集地方志實現個人的學術抱負。但事實上是內藤的學術研究內容一直與日本時政相關聯。這點我們從學者錢婉約的研究中也能看出,內藤多年來訪書活動的重心是滿蒙史料,而滿蒙問題與日本的侵華密切相關。還有“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最關注的是滿蒙問題,日本學界則興起了滿蒙史地研究熱。據學者巴兆祥的考證,1919年內藤湖南與稻葉巖吉等編輯出版《滿蒙叢書》,收集了《口北三廳志》《龍沙紀略》等志書,以三年為期,每年8冊,計劃出版24冊。
由此,我們便可以清晰探察出內藤的訪書及收集地方志除了個人的學術研究外,更多地是在為日本當局政府的政策服務。
三.內藤湖南的中國觀
內藤來到寧波后,關心的是什么呢?我們先來看內藤自我闡述的去寧波走訪的另外一條理由:加以彼處本為吾邦籌劃設領事分館之所在,故頗生浙東之游興趣”。可見,內藤時刻關注日本的在華利益。由此,我們更不能只停留在表層去審視內藤的江浙訪書行為。學者錢婉約認為,“在內藤眼里,到中國去學術調查,關注晚清中國動亂中古籍珍本的動向,不失時機地獲得而收歸日本藏有,是應該視作一項政府的時代文化策略來重視的”,“其潛意識中,或正欲以日人當下的積極赴中國訪書搜書,為將來之再編《佚存叢書》,居功于中國文明乃至東洋文明而興奮不已!”
內藤作為一名漢學家,喜愛中國傳統文化,可在中日相關問題上,卻滿眼只顧日本利益,不能保有一個公正客觀的態度去看待。
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戰爭的勝利后,內藤甚至發表了以下言論,暴露了其學術工作的本質:奉天這座學術寶庫的開啟標志著可以開展滿洲史料的探查,這將成為最有意義且有趣味的工作。這也是作為學者最為應該從事的,因為只有從事這樣的事業才能與我軍所取得的赫赫戰功相提并論,此項工作能夠促進吾輩大有作為。內藤考察中國的學術史料,卻將其與日本的“戰功”相提并論,體現了內藤在學術工作中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思想及對中國文化遺產的占有欲望。
上文所提及的內藤編輯出版《滿蒙叢書》、收集中國各類志書、向日本傳播中國重要信息情報的行徑更是直接在為日本政府的侵華計劃服務。日本學者子安宣邦對于內藤《支那論》一書的評價為:此書從數千年中國歷史及其演變脈絡的內部出發,抑或僅以其歷史識見,論盡了辛亥革命及之后現代中國的變遷與局勢,這不正是日本帝國大學的“支那學家”內藤湖南對現代中國在認識論上的干涉或曰介入嗎。由此,我們得出內藤始終把日本的利益需求放在首要位置,喪失掉作為一名學者應持有的客觀立場和良知。
在此有必要考察一下對內藤湖南中國觀的形成有重要影響的事件。內藤是隨著明治維新成長起來的。學者渡辺和靖認為,明治時期思想的特征是西方思想和傳統思想的二重性。內藤擁有著深厚的漢學素養,受儒家“經世致用”思想頗深。明治中期的時代課題是關于探索“臣民”像和“國民”像的思想課題。特別是內藤所任職的政教社主張國家主義、國民要持有國家觀念去行使參政權。社內人思想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也會影響內藤的中國觀。中野目徹認為,“臣民”和“國民”可以說是明治后期思想(1888年前后至日俄戰爭)的關鍵詞。日本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勝利以后,“臣民”像和“國民”像互相抵消、互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日本人的形象。一方面戰爭的勝利,增強了日本人的“國民意識”,另一方面也內化了日本人的“臣民意識。”這跟甲午中日戰爭以前,日本進行的“忠君愛國”的教育也有深切的關系。由此看來,內藤湖南只顧日本利益的“畸形”中國觀,與當時日本社會大環境的思想有莫大的聯系。
因此,內藤只考慮日本的利益,為日本現實政治服務,站在所謂的“文明人”“文明國”的角度對當時中國的政治進行“指手畫腳”的行為,更會錯誤地引導日本國民認識中國。
本文通過分析內藤湖南的寧波之行,得知他的主要活動是在寧波搜集珍奇籍本和地方志。通過進一步分析內藤的寧波訪書等活動,窺探到他始終把日本利益放在首位的“畸形”中國觀:特別是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文人、學者站在所謂的“文明國”的立場,對當時中國社會進行批判,對中國的政治提出“指導性”的評論。從其行為我們能夠窺探出其背后反映的是日本民族的狹隘心理、畸形的民族意識以及不平等的對華觀念。其次是文化占有和侵略的中國觀:內藤湖南目標明確地長期訪書、搜集地方志以及稀世珍本的行為體現地正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占有”心理。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日本文人學者搜集、索取、強取豪奪中國珍貴典籍、地方志的行為是對華文化的一種明目張膽的掠奪行為,更是侵略中國文化的重要體現。同時,我們也能探查出內藤為日本侵華服務的行徑:內藤湖南積極搜集中國地方志,編輯出版方志叢書,為日本方提供中國地情、礦產資源等情報是直接在為日本的侵華服務。
總之,內藤湖南一方面搜集中國珍貴古籍、地方志等情報資料,實現個人研究志向抱負、建立“文功”,試圖讓日本居功于東洋文明的同時,更是為日本的軍事侵略提供信息情報的支持;另一方面內藤的學術著作,拋開應有的公正立場,鼓吹所謂的“興亞論”,在歷史中尋找“合理性”依據,為日本侵華進行宣傳。這一切都與內藤湖南的民族主義有關,無論他是記者身份,還是京都大學教授身份,內藤都持有對社會政治的關懷。他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讓他喪失了作為學者應保有的基本良知以及理性公正的態度,走上為日本侵華服務的道路。
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本身就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近代日本文人、學者持著對中國輕蔑、傲慢的態度,打著“文明”的旗號寫就的文章,進一步傳播到日本民眾,造成更惡劣的影響,更為之后日本的侵華戰爭提供理論上的支撐和服務。學者王向遠認為,“內藤史學”在20世紀上半期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過程中,起到了制造輿論、獻計獻策、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誤導了一般日本讀者對形勢的判斷和對中國的了解。今后,對于內藤湖南的相關著作和文章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
參考文獻
[1]巴兆祥.中國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內藤湖南.內藤湖南全集:第四卷[M].筑摩書房,1969-1976.
[3]內藤湖南.吳衛峰譯.燕山楚水[M].中華書局,2007.
[4]內藤湖南.李振聲譯.禹域鴻爪[M].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
[5]內藤湖南等著.錢婉約譯.中國訪書記[M].九州出版社,2020.
[6]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M].中華書局,2004.
[7]錢婉約.此生成就名山業 不厭重洋十往還—內藤湖南中國訪書及其學術史意義述論—[J].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別冊=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2008,3: 135-159.
[8]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M].昆侖出版社,2015.
[9]謝國楨.江浙訪書記[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10]周達章,周嫻華主編.寧波藏書文化[M].寧波出版社,2017.
[11]子安宣邦.王升遠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觀[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
[12]佐藤弘夫主編.概說日本思想史[M].ミネルヴァ書房,2005.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