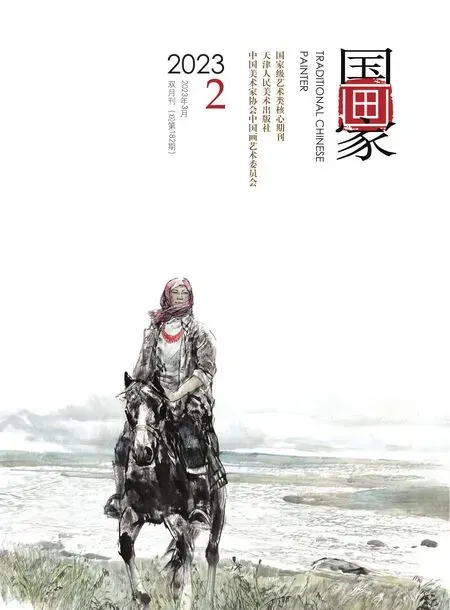北宋中后期文人畫家的游戲精神
南開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蒯豐
北宋中后期,由于黨爭問題造成社會環境和政治生態急劇惡化,“出世”成為當時文人士大夫階層普遍的文化心態,體現在文藝觀念與繪畫創作上,則傾向于托物寄情,表現孤獨悠遠、天地蒼茫、靜謐荒寒等多重意象。縱然被現實籠罩,文人畫家的藝術活動也與“游戲精神”所內含的自由與創造的體驗相一致,在藝術創作中實現了理想與現實的平衡。
一、游戲精神與文人畫家
對于游戲,人們總有原初的熱情和渴望,“游戲”也是歷來諸多思想家及學者關注的論題。就當代社會而言,游戲之于生活,不僅在時間和力度上,而且在文化構成和“喂養”受眾的方式上,都與我們息息相關。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中寫道:“如果把游戲看作是復雜社會情景的活生生的樣子,游戲就可能缺乏道德上的嚴肅性,這一點是必須承認的。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使高度專門的工業文化迫切需要游戲,因為對許多頭腦而言,它們是唯一可以理解藝術的形式。”[1]由此反觀,游戲與生活的關系早已在人類文明的積淀中升華成了一種精神,游戲與藝術、游戲與藝術家的關系,同樣成為人類精神活動的特殊表征,是人們達到“詩意地棲居”的一種中間形態。
根植于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土壤,中西方對于游戲理論的闡發邏輯差異較大。孔子《論語·述而》中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莊子·逍遙游》中描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的形象,皆傳達了人們超越“自我”、獲得身心自由時的狀態。在繪畫領域,宋代對于游戲思想的表達最為直接,如蘇軾在《題文與可墨竹》中寫道:“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以游戲的心態施加在墨竹繪畫創作之時,或可得到自在。“自在”的先決條件便是“游戲”。由此可見,文人畫家的游戲并不是戲謔,而是在“游心”精神的引導下,從萬事中解脫出來,感知“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的空靈,達到游于藝、游于天地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西方,游戲精神主要被描述為關于主體和靈魂的自我決定,以及自由的本體界的建構問題。當人們把審美與自由畫等號時,游戲便成為創造美的方式。康德美學通過“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與“無功利的純粹愉悅”等觀點,證明藝術無須借助其他力量也可以擁有非概念普遍性。席勒在康德之后,對“審美游戲說”進行了充分的理論闡發,即人對于世界有兩種沖動——感性沖動和理性沖動(形式沖動),兩者相互對立,必須依靠第三者——游戲沖動,實現統一。在審美游戲中,感性沖動與理性沖動達到了平衡,使人獲得自由,成為真正的人。相較于西方,中國古典文人畫家群體的藝術精神雖有超逸之態,但也昭示出中國傳統語境之“游”缺少了一些積極的、能動的和主觀反思的精神。這一時期,以蘇軾、文同等人為代表的文人集團,運用和創造新藝術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改革傳統繪畫,形成了融詩、文、書、畫于一體的文人“墨戲”,使“墨戲”成為士大夫群體表意抒懷的非功利的超造型藝術的文藝形式。[2]在這種革新下,北宋中后期文人墨戲也具有了隱喻性、敘事性和反思性的特點。
二、現實生存與文人墨戲
宋朝的士大夫兼具文人和官吏雙重身份屬性,他們或參與,或被卷入政治斗爭,其社會地位和仕途的沉浮,對個人的情感狀態及審美心理會產生深刻的影響,進而直接體現在創作中。北宋中后期這一特殊歷史環境下,士大夫的藝術創作為中國文人畫之風貌鐫刻了濃重的歷史印記,為后世文人畫的演進開辟了新的發展之路。
(一)抗爭與托物
北宋王安石變法致使士大夫集團分裂,當權者為清除異己不擇手段。然而,擁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在獨立人格包裹之下的宋人,以“與天子共治天下”為己任,忠信仁篤,修齊治平,其“為天地立心”之氣雖屢受沖擊,但并未幻滅,轉而表現為藝術創作,借書畫寓托不屈的抗爭精神。蘇軾被貶黃州后,用詩詞抒發憤懣,別抒懷抱;黃州之后,其所畫枯木樹石皆瘦硬曲折,并無常規法度,米芾認為此類意象正是蘇軾胸中塊壘的外化:“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郁也。”[3]文人畫家表現反叛也未必都像蘇軾這般,借乖張拗怒的枯木頑石,以孤傲的姿態含蓄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屑,比如文同就常用意象較為中和的墨竹托物言志。在北宋文人畫家群體的藝術實踐中,梅、菊、松、竹、枯木、怪石等內含抗爭意象的自然物象成了繪畫的創作要件,承擔了救贖內心的重擔。
(二)內斂與出世
宋代士大夫雖向往廟堂,但在中隱觀念的支撐下,找到了調節“仕”與“隱”之心理矛盾的方法。文人畫家以一種內斂化的意象呈現,表達渴望且矛盾的心理,畫面傾向于表現蒼茫悠遠,尤以山水更為常見。畫家喜點染扁舟、大雁、遠水之類的物象,使畫面形成空間張力,同時加大留白面積,如蘇軾《瀟湘竹石圖》,除左下角伸出幾叢竹子外,其余皆留有大片空白,表現水天茫茫、眾生如滄海一粟之感。黃庭堅亦持有此種審美觀照的態度,他從“遠”的角度評判山水畫,如《題陳自然畫》中“水意欲遠”[4],《題花光畫》原注“此平沙遠水筆意,超凡入圣法也”[5]。黃庭堅的評述表明,宋人已將“遠”作為藝術品評中的重要尺度。此外,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三遠”法,韓拙又提出新“三遠”說,將闊遠、迷遠、幽遠列為新三遠,更加強調了宋人對于描繪象外之意的偏重。宋人黃休復又將繪畫分為逸、神、妙、能四品,以逸品為上。宋代的文人畫家將心靈寄托于天地大美之中,將出世之心與入世之意灌注于山川性靈,流露出畫家試圖突破現實壁壘、奔向全新語境的渴求與企圖。
(三)孤憤與超逸
李澤厚評論蘇軾后期詩文說:“(蘇軾)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6]蘇軾的孤憤和歸隱之心,已不僅僅是對政治的逃避,而是對待社會、對待歷史的深切愴痛,進而內化為一種富有悲劇性和創傷性的超逸與孤獨。這種情感在文人畫上最突出的表現則是山水寒林意象,它不僅呈現了士人對人格精神的高尚追求,同時也構建出了不同于現實世界的彼岸——一個不受侵擾的世界。文人畫家多用孤峰、獨樹、野鶴、獨舟入畫,又常作寒江垂釣、云峰遠眺等題材,與天地合流,與萬物為一,在超脫中飽受悵惘與孤獨。這般情緒未必需要排遣,對于能用自己的人生哲學對抗苦難的士大夫而言,如蘇軾所云,在“變”與“不變”的人生中,“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荒寒并非生命的消亡,而是創作主體對以往歷史的思索及對生命本質的探詢;荒寒亦非心靈的死寂,而是創作主體熱烈的生命情懷的獨特表達。”[7]文人畫家將內心放逐于荒寒之境,宣示一種與歷史共同生長的有限自由。
三、文人“游戲”的有限與無限
如果將藝術作為一類“游戲”,至少有兩種狀態,一種有限,另一種則無限。有限的藝術以完成表達為目的,無限的藝術以延續“游戲”和創造永恒為期許,北宋文人的“墨戲”則趨向于無限的游戲,同時也包含著邊界與有限性。這并非偶然,不論身處任何時代,總有人想讓主體的生命劇本化,提供一個由他者撰寫的腳本,如何與“在場的他者”相處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宋代文人畫家創造的“墨戲世界”承載了主體性的生產與再生產,同時也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藝術創作中的有限性。宋人不斷嘗試打開世界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但忽略了基本前提,即這個世界無論如何都是被社會話語建構出來的。他們嘗試把握共同體的心理取向,但選擇權有限,因為藝術世界也被社會和歷史的總體建構所規定。現代世界追求擴張與無限,一味突破邊界將帶來失序和無度,通過藝術創作,對有限性進行實踐與反思也是對現實的平衡。在藝術上,我們更應該思考藝術創作中“他者建構”與“自我建構”的關系、“角色身份”與“現實身份”的差異和關聯等問題。二是藝術與生存世界的無限性。宋人將面臨失序的人生寄托在藝術活動之上,重新構建出豐富的精神生活世界,這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具有同一性的主體身份是否仍然可能?藝術場域中我的“真身”與現實的我之間的裂隙,某種意義上否定了西方哲學的一類主體想象,而這種否定在何種程度上改變著當代人的自我觀念,改變著當今盛行的個人主義文化?我們何以通過藝術實踐,反思人與人、人與萬物、人與生命之間的關聯?何以通過重新建立聯系,實現人的社會性共存,達到一種無限?
注釋
[1][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99頁。
[2]劉崇德,《從“以文為詩”到“以詩為畫”——北宋士人畫體的形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3]米芾,《畫史》,《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3冊,第12頁。
[4]黃庭堅,《黃庭堅全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38頁。
[5]黃庭堅,《山谷詩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72頁。
[6]李澤厚,《美學三書·美的歷程》,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96頁。
[7]吳增輝,《北宋黨爭與文人畫的精神內涵》,《文藝評論》,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