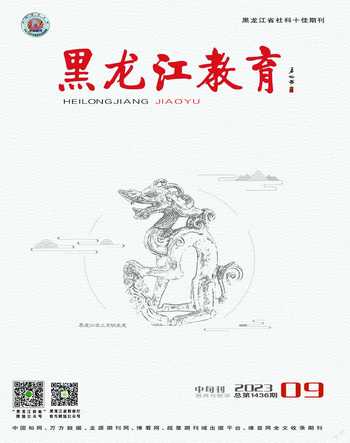深度學習下高中歷史學科教材商榷式備課探究
孫豐鑫
摘要:一線教師長期脫離學術研究,日常授課往往成為枯燥單調的活動,倘若教師不能獲得持續的專業性成長,其授課積極性便會降低,引導每一位教師走上從事研究的道路是保持教師教育熱情高漲的有效途徑。商榷式備課不失為保持教師良好研究能力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有效途徑之一,教師在備課過程中站在“對立”的角度面對教材,以批判的方式使用教材,嘗試以“糾誤”的方式梳理教材的備課方式。通過融合教材內容,更新教師知識結構;商榷文本材料,提升教師研究能力;理論實踐結合,強化教師研做結合,希冀在基于深度學習的教師專業成長方面提供一些借鑒與參考。
關鍵詞:高中歷史;深度學習;商榷式備課;教師成長
當代教育理論倡導教師“用教科書教”,而不是“教教科書”[1]。教材是教師上課的工具,教師應當重視教材的作用,同時,教師在備課過程中也應加入自己對教材和課標的理解與設計。自新教材投入使用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并嘗試對其進行剖析,也提出了許多專門針對新教材的備課策略與備課方式。受新教材通史性和適用性影響,現有的教學方法和教學策略理論性過重,對學生和教師的素質要求較高,甚至部分教學設計與教學策略只能應用于特定的課堂。部分學者注意到“糾誤”這一類教學方式,但也僅是從教材某一課或某一單元出發,尋找其中有爭議或是不合理之處,尚未提出系統、有效的備課方法。
一、當前高中歷史教師備課存在的問題
由于高中階段學業壓力大,部分教師缺乏主動研究的意識,同時也缺乏整體教學觀以及從整個課程過程把握教學的能力,學生的實際學習情況得不到科學分析,教材資源的挖掘程度有限。
新版教材使用時間不足三年,《中外歷史綱要》(以下簡稱為綱要)的課堂實踐使用中仍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方面,教師對新教材的熟悉程度不夠,舊版教材經過反復研究與探討,教師對其有充分的了解,備課時能夠清楚地認知課或單元的重點難點,在設計教學時也能有效地利用教材所給資料,完成課堂目標。部分教師未理清課目單元的授課脈絡而繼續按照傳統課堂的方式授課,甚至有部分老教師消極對待教材整合和大單元教學模式,造成了新教材與課堂教學的割裂,新教材的優勢無法發揮。另一方面,新教材中是否存在著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知識性問題、圖文搭配不合理及材料未及時更新等,這些問題也需要教師在日常備課中加以注意。
二、基于深度學習的教材商榷式備課的概念及流程
教材商榷式備課指的是教師本著嚴謹的學術態度對待日常備課,正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教材也同樣適用。在備課過程中,教師不僅需要對史實和材料進行查證,還應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并記錄教材中沒有提及或未深入講解的重要知識內容,此過程既加深了教師對新教材的理解,也提高了自身的專業技能,對于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是巨大的。
在教學實踐中,教師應注意教學的動態過程及學情的重要性。在三新背景下,固有的教學策略并不能滿足所有課堂,新課改要求教師必須轉變舊有的教學觀念與方法,以適應學生需求,這就要求教師在備課中嘗試更多、更新的策略,以科研的標準要求自己,建設高效課堂,進行深度學習,而教材商榷式備課模式為其提供了有效路徑。
教材商榷式備課的流程為:深度研讀新課標及教材—教材內容梳理及考證—整理考證文本—改進教學設計(如圖1)。

三、教材商榷式備課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價值
1.融合教材內容,更新教師知識結構
教材商榷式備課首先要求教師對課程內容十分熟悉,應當在了解歷史課程標準的要求和研究課題的立意及地位的基礎上,對整堂課的內容進行深度分析,基于此確定教學目標和教學方式,設計教學活動、準備教學資源、編寫課時教案。新教材是新的知識體系,教師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知識和理念上的盲區,在教材商榷式備課的過程中,教師以批判的方式使用教材,嘗試以“糾誤”的方式對教材內容進行嚴格的梳理,考證教材內容的出處及來源,并將其與教材內容進行核對,在此過程中勢必會對教材內容進行深度解剖,可以極大地加深教師對教材內容的理解,從而可以深度把握重難點,更好地融合課程內容,以便將其重新解構,適應大單元教學的需要。
以“遼宋夏金元的文化”這部分內容的教材商榷式備課為例,教研組經過嚴密論證,認為程顥為理學學派的說法是錯誤的,嚴格意義上說程顥應屬于心學學派,部分論證(截取)如下:
程顥與心學代表人物王陽明的觀點具有極大相似性。程顥認為天理在心內,而不在心外,故不必向外尋覓求索。這與心學的觀點不謀而合。
程顥與王陽明都認為不能離卻人心來談天理,天理自不外在人心,這是心學與理學最基本的表征差異。“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程顥曾如此論述。在《定性篇》中也有相似論述:“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而明代學者及近現代史學大家也將程顥思想歸為心學。
明代學者李之藻在《頖宮禮樂疏》卷二中寫道:“宋儒陸九淵學術生而清明、學術純正,自孟子沒而心學晦,至周敦頤程顥追尋其緒,陸九淵繼之心學復明。”
綜上所述,教材中將程顥歸為理學的創始人是不恰當的,程顥應屬于心學學派。修改建議:在教材第66頁第一子目“儒學的復興”中“其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顥、程頤兄弟……”中的“程顥”刪去;在教材第85頁15課第二子目“思想領域的變化”中“明朝中期,王守仁在南宋陸九淵的基礎上,提出一套以‘致良知為核心的理論,形成陸王心學”一句改為“明朝中期,王守仁在北宋程顥、南宋陸九淵的基礎上,提出一套以‘致良知為核心的理論,形成陸王心學”。
論證的過程更新了教師的知識結構,不僅加深了對心學的理解,還將理學的知識進行了深入探究,拓展了教師的知識面,使得教師對教材內容的理解更加深刻,以便于對教材進行深度整合。一次一次的備課與教材內容研究,見證了教師在知識結構上的成長與蛻變。
2.商榷文本材料,提升教師研究能力
教師在對文本內容提出質疑后,需要查閱各種文獻資料進行嚴密的論證,在此過程中,教師發現問題的能力、專注力、文獻查閱能力、總結歸納能力以及科研能力都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以《綱要》(上)第10課的糾誤過程為例,教師首先通讀教材,斟字酌句地對教材內容進行檢查,這無疑能夠提高教師的問題發現能力與專注力,在此過程中,教師的批判性思維也得到成長。經過通讀教材,認為子目二“金朝入主中原”的第3段:“1114年,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舉兵反遼,次年稱皇帝,建立金朝,定都會寧府,也稱上京。”存在表述錯誤之處,對定都會寧府進行了糾誤,并建議改為“定都皇帝寨,后升為會寧府,也稱上京”。在論證過程中教師先后查閱了《中國古代史》《金史·地理志》《金史·太宗紀》《金史·熙宗紀》《燕云錄》以及《呻吟語》等相關史料,極大地鍛煉了教師的文獻查閱和史料實證能力。教師梳理資料形成論證文本,部分示例如下:
首先查找會寧府這一地區在完顏阿骨打時期的名稱。根據閱讀的資料,了解到金初的國都沒有州府名稱、京師名號,將以會寧府為中心的生女真(沒有編入遼國戶籍的女真人)的發祥地稱之為“內地”、御寨和皇帝寨。據《金史·地理志》可知,會寧府是金源內地,在金熙宗天眷元年升為上京[2]。
再從宋代文獻中看金初國都的記載,趙子砥在《燕云錄》中說:“御寨去燕山三千七百里,女真國主所居之營也。”趙子砥在靖康之變時隨徽、欽二帝北遷,后于建炎二年遁歸南宋。《燕云錄》是趙子砥在金朝的所見所聞,其中對金朝國都的記載反映了當時人的稱呼,應該可信,所以對金朝都城的稱呼應是御寨。除此之外,黃裳在《地理圖》中把金上京標記為“御寨新京”。由此可推論出,天眷元年會寧府建號上京之前應當為地圖的成圖年代。除此之外,“御寨”在宋文獻中也叫“皇帝寨”,翻閱《三朝北盟匯編》可知:阿骨打建號,曰皇帝寨。至亶,改曰會寧府,稱上京[3]。
上京路,是女真興起之地,金初稱“內地”,天眷元年(1138年)京師稱上京,設上京路……會寧府,上京路首府,治所在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白城。完顏阿骨打建國時,女真人忙于伐遼戰爭,無暇顧及京城的營建,金太祖時都城稱為“御寨”。金太宗年間,設會寧州,后升為會寧府[4]。
根據上述史料的論證,事實為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定都御寨(金源內地),后升為會寧府,在金煕宗時加號為上京。課本應尊重歷史的時空對應性,故應將其改為定都皇帝寨,后升為會寧府,會寧府也稱上京。
論證文本可以裝訂成冊由學校制作精美裝訂后進行成果展示,以對教師進行正反饋,保持教師的教學和研究熱情。教師長期耕耘于教學一線,游離于文獻查閱等學術活動之外,教師的學術能力也逐漸淡化,而教材商榷式備課克服了這一問題,教研組內教師輪流負責一子目或一課的商榷與糾誤,既鍛煉了教師的學術能力,也使得教師在備課中體會到自己的專業成長,使教師在成長體驗中重新燃起了教學熱情。
教師在進行備課的過程中,歸納總結教材商榷中遇到值得探究的問題,如說法不一、圖片溯源等。在日常授課過程中,課堂展示部分教師備課提出的商榷問題,引導學生運用商榷方法對教材部分內容進行探究,讓學生嘗試分析所給史料,對教材內容的來源與表述進行深層次的剖析,以判斷史實信息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從而培養學生對待歷史問題的批判性思維。一方面,加強學生的信息獲取能力與材料概括能力,另一方面,培養其史料實證與歷史解釋能力。
教師將商榷內容與授課有機結合,讓教研服務于教學實踐,并在研究狀態下進行教學,對實踐中遇到的問題進行反思,教師的專業能力一定能夠得到實質性的提升。
參考文獻:
[1]于友西.中學歷史教學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26.
[2]脫脫.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2020:59.
[3]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26.
[4]程妮娜.金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120.
編輯/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