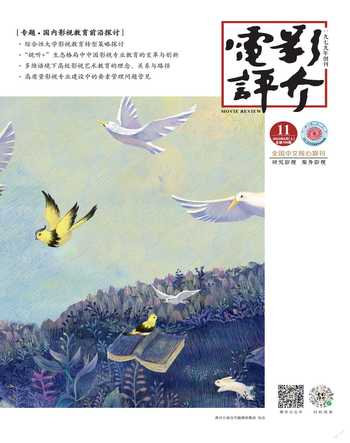復合審美與審美的復合性:新時期中國軍事題材電影的多維美學體系建構與思考
鐘菁

隨著短兵相接的大規模戰爭時代的結束,現代軍隊的職能、現代戰爭的形式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和平與戰爭的邊界不再涇渭分明,各國圍繞軍事題材所創作的游戲、電視劇、電影等正在媒介戰場上以另一種隱蔽的方式博弈。美國學者提姆·萊諾(Tim Lenoir)和盧克·卡德韋爾(Luke Caldwell)提出“軍事—娛樂復合體”概念,給全媒體時代下的軍事題材電影賦予了獨特的雙重身份。[1]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軍事—娛樂復合體”的提出,代表著當代學者對于軍事電影功能性由單一走向復合的一種反思,反映出新時期軍事題材電影的審美范式、審美觀念出現了復合性傾向。
一、“規訓”與“娛樂”:軍事電影審美功能的復合性
(一)政治美學的“規訓”耦合
美學是先驗范疇與感性經驗的雙面耦合,這種雙面性使得軍事題材電影中充盈著“美”與“丑”的對立思辨,這種思辨同時影響了美學的歷史嬗變、審美意識、審美范疇及審美理念等多重維度的美學辯證體系。軍事電影的美學體系轉向具備政治美學的范式體征,而政治意義的美丑判斷則與權力概念的泛化“規訓”不謀而合。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中說道:“它既不會等同于一種體制也不會等同于一種機構,它是一種權力類型,一種行使權力的軌道。”[2]軍事與政治的天然膠著決定了戰爭美學必然受到政治體制的規范化引導,純藝術領域的美學理論難以切實涉及政治領域、意識形態領域電影的美學邏輯。尤其對于軍事題材電影而言,涉及有關根本的生死觀、是非觀、正義觀及合法性的問題判斷時,國家意志總是傾向于將評判的權力潛移默化地予以控制,借助美學的共識性將戰爭審美與道德倫理相掛鉤。
從藝術發生論和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任何美學思潮的產生及衰退都與特定歷史時期的人類文明變革息息相關。中國軍事題材電影的美學演進與中國社會現實的發展軌跡緊密契合,同時也受到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深刻影響。譬如,傳統中國軍事題材電影普遍習慣通過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來表現人民軍隊的光輝形象,通過演繹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歷程來見證和書寫國家歷史。“十七年”電影、主旋律電影、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皆被主流意識形態賦予了超越電影本身的社會功能。飽含愛國意識、憂患意識、救亡圖存愿景的中國電影人,將軍事電影的創作與激勵民族團結一心、弘揚正義道德理念、鼓舞軍民戰斗士氣、啟蒙和解放思想等合目的性的現實使命結合在一起。“功利主義美學主要基于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文藝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政治功能的學說,融含著儒家傳統思想中‘詩以言志和‘文以載道等觀念。”[3]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爭年代,功利主義美學以“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為人民服務”、黨性意識、典型性方法論等形式體現于具體的電影創作中,以政治美學的顯性姿態教育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觀眾,使其通過觀看軍事電影,接受崇高精神的洗禮,感受革命史詩的雄渾壯闊。進入和平年代,隨著社會現實和藝術環境的轉變,功利主義美學的政治功能性顯示出局限性。作為一種藝術形式,電影畢竟不能用于直接實現階級立場和國家意志的鞏固,在面對審美多樣化、個體化、差異化的當代電影觀眾時,政治“規訓”開始尋求通過間接的、可能的道德倫理,以一個個或悲壯、或崇高、或浪漫的革命故事,打破刻板的“神化英雄”形象和“無沖突論”思維,傳播軍事美與人性美,以期獲得大眾的共情和審美體驗。
正如康德所言:“美是道德觀念的象征,把審美范疇的崇高對象定位于客體的無形式”[4];“美感不是用知識和推理的方法去尋求客觀事物的知識,而是用想象力去感受客觀事物得到的趣味”[5]。至此,軍事題材電影的美學體系逾越了純電影藝術的美學范疇,而與政治美學指導下的倫理敘事相結合,不斷闡釋著德性倫理、道德傳統敘事的正義神話,旨在從穩定的民族心理層面取得一定的敘事認同和情感共鳴。美學的轉向實際上是一種審美經驗的空間拓展,一種從淺表感知層面上的本能體驗向具備理性思考、邏輯思辨的深層審美活動的轉變,同時也是一種對于合規律性、從善從美的審美慣性的逾越。
(二)暴力美學的娛樂表達
軍事電影,尤其是戰爭片,與暴力的膠著關系是天然存在的。戰爭以暴力的形式展現,而暴力程度的強弱直接影響著戰爭規模的大小。從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論來看,人類對于生本能與死本能(暴力)的渴求是本能欲望的體現。[6]暴力在電影中被視為非理性的原始沖動、教唆青少年犯罪、荼毒社會的洪水猛獸,即便真實戰場上的軍事活動也處處充斥著極度震撼的暴力,電影中也不能如實呈現三分。特定的歷史環境和美學訴求導致過去的軍事電影,無論在敘事亦或是剪輯上都著力于塑造觀念和書寫意義,甚少將注意力集中在通過暴力表達操控觀眾的情感體驗、追求各種感官刺激的興奮強度上。
電影對于暴力表達的欠缺在當代大眾引領的泛娛樂化大潮中迅速反彈,由于“性元素”的呈現始終是國家嚴格把控的高壓線,暴力成為軍事電影追求娛樂強度和審美體驗最好的途徑。越來越多充滿血腥的屠殺場面被毫不避諱地呈上銀幕,槍戰的特效場面甚至比真實戰場上更為激烈兇殘。有關軍事題材的影像制品向著現代戰爭的仿真復刻方向不斷靠近,追求真實戰場上緊張刺激的暴力體驗,敘事剪輯風格迅速而凌亂,模擬第一人稱視角的戰斗畫面呈現出失控的抖動和逼仄的局限感,觀看時令人不由自主地聯想到類似《使命召喚》《美國陸軍》《反恐精英》等戰爭游戲。新時期軍事題材電影的畫面普遍是直接的、震撼的,大眾對于電影審美的認知也變得無意識和條件反射,“這種認知由感官體驗帶來的無意識的副現象——情感、激勵、刺激和抑制、愉悅和痛苦、震驚和適應等組成。電影跨越了一般認知的門檻而成了一種新型的認知,它要么低于人類的認知水平,要么高于人類的認知水平。它是具體的,與生俱來帶有前反思性,但缺乏深度和內化”[7]。現代軍事題材電影對于暴力美學的直白追求不僅體現在諸如《軍情五處》《24小時》《勇者行動》等國外影視作品中,同時在近年的國內軍事題材電影如《戰狼》《紅海行動》《八佰》《長津湖》《長津湖之水門橋》《狙擊手》等作品中也得到了佐證。在2021年票房冠軍電影《長津湖》中,表現作戰場面的鏡頭絕大多數都采用手持跟拍,并且畫面伴隨著美軍戰機的炮彈轟炸而產生強烈震顫搖晃,仿佛將觀眾視野代入一個身陷炮火的士兵身上,大量運動鏡頭的快速組接使觀眾的視聽感官在短時間內受到的刺激程度大大提升,對于戰爭暴力的審美方式也變得感性而直接。
同時,科技主義的蓬勃興起也為戰爭影像的暴力書寫增添了無限仿真現實的可能性。僅《長津湖之水門橋》一部影片中,多家公司參與戰場特效制作,從宏大的全景展現到微觀的作戰武器、交火場面表現上,影視特效的大量植入都強有力地推動了新時期軍事電影的美學觀念產生了革新。暴力美學的興盛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電影中意識形態敘事的份額,壓縮了觀眾思考戰爭的空間,同時平衡了傳統軍事電影過分追求“意義”和“主義”的傾向,使意識形態與審美話語在內容與形式層面上都產生了復合式的互動發展。
二、“結構”與“范疇”:軍事電影復合審美的雙重維度
(一)電影美學:悲劇美感與倫理救贖
戰爭是無情的,是丑陋的,一切戰爭對于生命個體來說都是悲劇。暴力摧殘生命,戰爭美學的審美同時是一種審丑。殘缺的肢體、破碎的家庭、悲鳴無力的哀嚎及飛濺的鮮血“都表現了人生內容的欠缺性和不安定性,所以它們與美的本質相對立,都意味著丑惡的東西”[8]。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在論述悲劇的本質時說:“悲劇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悲劇是人的苦難或死亡,這苦難或死亡即使不顯出任何‘無限強大與不可戰勝的力量,也已經足夠完全使我們充滿恐怖和同情。無論人的苦難和死亡的原因是偶然還是必然,苦難和死亡反正總是可怕的。”[9]
但在戰爭中,“丑”的東西處在特定歷史境遇下也會與美相轉化、相融合,成為一種異相之美。猥瑣、卑鄙、意志力薄弱的敵人在遭受暴力時不堪一擊、毫無抵抗之力,從而襯托出正義方的強大與力量。弱小無助的平民在炮火中成長,猶如沖破厚土、頑強破殼而出的嫩芽富含勃勃生機,最終獲得反抗壓迫的力量,這也是一種充實生命力和體現,具有厚積薄發的美感。馬克思(Marx)在論述悲劇的本質時指出:“新的社會力量雖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但是面對著強大的傳統的力量,卻顯得弱小,因此在斗爭中必然會有犧牲和失敗,在實踐中逐漸壯大自己。這種力量對比是歷史形成的。這是形成悲劇的客觀現實基礎。”[10]新生力量在壯大的過程中所遭遇的阻礙與創傷是悲劇產生的源泉,也是戰爭產生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軍事戰爭電影塑造了無數為了正義犧牲的悲劇英雄,無論是《狼牙山五壯士》中為了保護大部隊轉移死守在棋盤峰抵抗日軍3500人,最后抱著對共產主義信念跳崖犧牲的5位八路軍戰士,還是《淮海戰役》中華東、中原野戰軍為了抵抗敵軍的猛烈進攻,與國民黨交戰中全部犧牲的我軍一個營的指戰員,都具備了濃厚的悲劇感染力。如果僅從客觀力量對抗結果的比較上,犧牲的一方自然是在體能上弱小的,在戰斗力上低下的,但是何以在悲劇中重生,使得人的力量在毀滅中重生,使得肉體的弱小顯現出精神的崇高,便是依靠意志美、精神美及人性美得以升華。此時,戰爭敘事中所蘊含的倫理道德成為使廣大觀眾對于戰爭電影中的悲劇賞析從單純的恐懼轉化為敬仰,從審丑轉為審美的重要工具。
魯迅先生說過:“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11]所謂有價值的東西,是指那些符合社會倫理道德規范、體現群體道德的高標準、代表全人類利益和進步要求的東西;而“毀滅”是指人類共同的道德象征,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所遭受的挫折和失敗。倫理道德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隱形準繩。它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處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社會經濟基礎之上,即便是最堅硬的道德準則也會潛移默化地發生改變。軍事電影的特殊身份決定了在所有電影之中,它將必須最堅定地遵守一切道德上的、倫理上的、法律法規上的游戲規則,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其他電影的表率與榜樣。誠然,從生命的尊嚴角度而言,每個戰爭中被炮火剝奪的個體都是悲劇,但卻并不是每個消失的生命都具有審美價值。只有代表正義理想,符合道德倫理的犧牲才具有悲壯美。
道德倫理實際上代表了一種意志精神和人性本質,它是賦予軍事電影以審美價值的關鍵。“不是所有帶著悲劇意味的英勇豪壯的軍事行為,苦難、頑強與犧牲,都是軍事悲壯美。只有那些腳踏苦難、征服苦難,在苦難中奮起,以生命推翻暴政、用熱血祭奠真理、以暴力換來和平與安寧的軍事行為和戰爭行為,才是軍事悲壯美。”[12]悲劇英雄的普遍共性體現在倫理道德上,他們是自覺的真理捍衛者及斗爭者,他們的犧牲與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他們的肉體在巨大的戰爭苦難中被無情地粉碎碾壓,但他們在面對死亡時表現出的無畏與激情,使得死亡行為本身成為微弱的真理之光,最終照亮黑暗的希望,成為新世界取代舊世界的轉折點。
(二)戰爭美學:軍事智慧的美感與韻律
戰爭不僅是體力的正面對抗,而且是頭腦的激烈博弈。“美的基本含義,在古希臘哲人那里有二:一是智慧;二是技巧。軍事美的基本含義,就是軍事智慧和技巧。軍事藝術美,是軍事智慧和技巧美的集中表現。”[13]戰爭的智慧美,是指戰爭本身作為一門藝術所展現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有機統一之美。不論是軍事知識、治軍思想、戰爭倫理或是戰斗方式、戰役指揮都彰顯著人在戰爭中所綻放的不同于野獸搏斗的理性智慧之美。戰爭智慧在影視作品中的展現使得戰爭脫離了純粹蠻荒的廝殺與毀滅,使戰爭影像表達脫離了單純血腥刺激的技巧,而上升到了一種充盈著人性力量的生存博弈。
近幾年,軍事題材電影對于戰爭場面的刻畫,以及對戰術、戰略的還原更為謹慎求實。《長津湖》《長津湖之水門橋》《狙擊手》等影片中大篇幅表現了抗美援朝時期中國志愿軍開展的冷槍冷炮運動。在敵我裝備武器水平及作戰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大批志愿軍特等射手、狙擊手(實際由于志愿軍所配發的武器落后,根本沒有真正的狙擊槍和光學瞄準鏡,嚴格意義上他們只能被稱作“步槍手”)、游動炮兵穿插迂回于前線戰場,配合主力部隊進攻,破壞封鎖陣地內的交通,把火力對戰的焦點推向陣地的前沿。在電影《長津湖》和《長津湖之水門橋》中,志愿軍第七穿插連的多次進攻都展現出了非凡的戰爭智慧和鋼鐵般的戰斗意志。該連使用的裝備主要有駁殼槍、三八大蓋、布朗式輕機槍和M2型60毫米輕型迫擊炮,以及少量從敵軍處繳獲的卡賓槍、巴祖卡火箭筒等。而美軍出現的裝備有大八粒M1加蘭德、M3式沖鋒槍、M2式勃朗寧大口徑重機槍等。美軍的火力壓制強,射程遠,后勤糧草彈藥補給充足第七連戰士缺衣少食,后勤補給線被美軍轟炸機多次炸斷,作戰武器簡陋匱乏,戰場傳遞信息只能靠吹口哨和喊話進行。即便如此,穿插連戰士依舊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利用一切優勢,從側面或縫隙中迂回包抄,阻擊敵人后撤,擾亂敵方進攻。美軍士兵盡管戰斗實力十分強悍,對重型武器的操作爐火純青,但一旦脫離了空軍和重型火力的配合,很容易就會失控崩潰。打穿插對于執行任務的部隊來說困難極大,穿插的過程中,要長時間暴露在敵人的火力封鎖線上,而一旦穿插成功,到達敵人身邊,又會陷入被前后夾擊的圍攻中,幾乎沒有全身而退的可能性。能打穿插的隊伍都是士兵里精英中的精英,但即便如此,仍會首當其沖受到最兇猛的進攻,死傷最為慘烈。《長津湖》中小戰士伍萬里的編號是第677號,也就意味著在他之前,這支連隊已經在過去的戰斗中陣亡了好幾輪戰士了。
相較于《長津湖》史詩般的全景戰場刻畫,2022年上映的《狙擊手》則更側重于以小見大,以抗美援朝戰爭中一次小規模戰役為表現對象,細致刻畫了敵我雙方八次你來我往的戰斗過程。片中有一幕對戰的場景,生動詮釋了志愿軍“趕鴨子上架”戰術的神機妙算:一片寂靜的雪地中,美軍狙擊手藏在戰壕死角,易守難攻。五班班長劉文武和小戰士大永為了引誘敵人主動暴露,雙人配合,一人一槍拉開距離,埋伏兩側,并在兩人間的雪地上悄悄平均間隔開來,放置了另兩把上好膛的備用槍。戰斗開始,劉文武首先對著敵人戰壕開了第一槍,趁敵人尋找開槍方位時,原地發射第二枚子彈。此時,敵方狙擊手躲在戰壕中,鎖定了目標,開槍還擊。劉文武迅速滾到第一把備用槍處,換槍打出第三發子彈,隨后滾到第二把備用槍處,換槍打出第四發子彈,然后帶著第二把備用槍滾到大永身邊,打出第五發子彈。緊接著,大永用自己的槍開出第六槍,敵軍被一槍斃命。對于不大熟知軍事的觀眾來說,這一幕戰斗場景可能不容易理解。劉文武和大永之所以要如此布局進攻,是因為在這場戰役中,敵方狙擊手使用的是M1941狙擊步槍和M1C半自動狙擊步槍,而且皆配備了當時最高端的八倍光學瞄準鏡;而中方戰士使用的槍支是1944式莫辛納甘短槍管步槍,沒有瞄準鏡,僅能靠肉眼瞄準,有效射程短。這款俄羅斯研發的旋轉后拉式步槍為整體式彈倉,打一槍要上一次膛,而且彈倉只能容納五發子彈。敵軍狙擊手深知這點,因此在劉文武開前四槍時,敵人盡管立刻都予以了還擊,但仍死死躲在戰壕中,不暴露位置。直到劉文武滾到大永身邊,開出第五槍后,敵人誤以為我方只有一人一槍,五發子彈已經全部用完,必須要重新給彈倉填充彈藥,因此想趁著這個停火空隙伸出頭來,好徹底看清戰場局勢,一槍解決我方狙擊手。卻沒成想,前五發子彈都是用來迷惑他的煙霧彈,而大永在五發子彈結束后也終于看到了探出戰壕的敵人,果斷瞄準目標開出第六槍,贏得了最終勝利。
戰爭智慧并不單純是一種對于戰爭技巧的贊揚。萬韋崗戰役、平型關戰役、黃土嶺戰役,以及眾多的游擊戰、運動戰可以運用智慧巧勝,而孟良崮戰役、上甘嶺戰役、淮海戰役等更多的大型戰役卻只能強攻。面對強敵,有堅強的意志與毅力抓住時機,同樣是戰爭智慧美的表現。“軍事藝術美實際上是軍事主體辯證心理過程的流動的美。它是隨客觀實際的變化而采取自由靈活的方法,來處理復雜多變的軍事與戰爭問題,克敵制勝的軍事手段和技巧的美。”[14]戰爭思維、技巧、觀念、信仰都屬于戰爭智慧之美的表現形式。技精而成藝,中國共產黨在百年的革命斗爭史中領導著中華民族創造了一場場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神話。這些戰爭神話中所蘊含的智慧之美為軍事電影的美學觀念維度拓展了廣闊的空間,為電影的美感創造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結語
中國軍事題材電影的美學體系是一個涵蓋廣闊的集合體,它不僅涉及軍事學、戰爭學、電影學、敘事學、美學等有關于藝術本體的學科,而且與人類學、文化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諸多有關藝術語境的學科相聯系。復合審美范式和審美的復合性傾向形成,既是一種歷史維度的發生歷程,也是一種觀念維度的感知融合。盡管新時期軍事題材電影在當代泛娛樂化的浪潮中愈發自覺或不自覺地降低了國家主流意識的“規訓”意味,隱藏了社會功利主義的審美訴求,弱化了過去電影中那種簡單直接的政治立場表達和高昂飽滿、無往不勝的戰斗姿態展示,且從宣傳工具向消費藝術品的身份上不斷轉化,朝著電影的娛樂本性不斷發展,但它終究是以表現軍事戰爭、表現與軍事緊密相連的意識思想的一種電影形態。政治美學、電影美學、道德美學的多維互動融合,將成為新時期中國軍事電影美學理論發展的指導方向和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美]提姆·萊諾,盧克·卡德韋爾.軍事——娛樂復合體[M].陳學軍,譯.北京:后浪出版公司,2021:2.
[2][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241.
[3]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學[M].北京:中華書局,2002:52.
[4][5][德]康德.判斷力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65,172.
[6][奧]弗洛依德.精神分析論[M].北京:商務出版社,1997:57.
[7][美]Steven Shaviro.The Cinematic Body[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26-27.
[8][日]笠原仲二.古代中國人的美意識[M].魏常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33.
[9][俄]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活與美學[M].周揚,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102.
[10]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美學與美學史論集[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10.
[11]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178.
[12]田立延,劉晉生,亦村.軍事美學[M].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49.
[13][14]方振東,宋海英,李學明.軍事美學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5.338.
【作者簡介】? 鐘 菁,女,陜西西安人,成都大學影視與動畫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