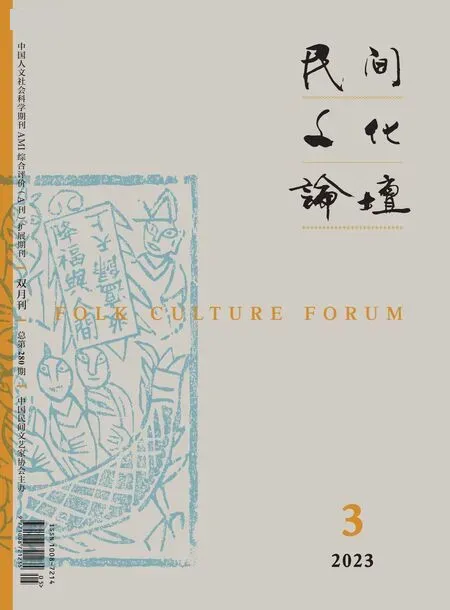中國社會科學實地研究的必要性*
李安宅 著 周小昱文 譯 岳永逸 校
在西方,對社會科學中田野工作(field work)重要性的任何強調,聽起來都像是在重復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尤其是在人類學家中間,實地經驗是其突出的特點。但在中國,圖書室研究在傳統上一直是學術界唯一的研究形式,我們需要開展一場偉大的運動,把知識分子的創造力從書籍的沉重負擔中解放出來,使其在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實主義研究中得到體現。在這個領域的任何創造性工作之前,我們必須普遍認識到實地研究(field research)之于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實驗室研究之于自然科學。
如果中國沒有這種意識取向,那么將會出現學術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二分。這種二分讓學術工作變得徒勞無益,而現實生活則是一個沒有洞察力或控制可能性的偶然。盡管這種情況并不唯一,但在中國這種混亂最為明顯,且最不受人關注。當然,這樣的觀察并沒有降低我們對今天的中國和她實際正在進行的為重生而英勇斗爭的贊賞。正是基于此般贊賞,我們才更加迫切地需要改革和改變我們的科學興趣。
在實地研究中,我們可以找到上述二分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案。社會文化領域的實地研究可能有兩種用途。首先,這些發現可以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一個基礎,并幫助我們從社會科學傳統的權威類型中解脫出來,這種社會科學要么是簡單的形式,要么是圣人的語錄集,以前是中國人的,現在越來越多的是外國人的;不過,它們可以作為扎實教學的重要基礎。教學應該從直接的、已知的到遙遠的、未知的,而不是像中國傳統的教學形式那樣,主要以牽強附會的外國文本為基礎。其次,這些發現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進行整合,以便真正洞察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使明智的和有意識的生活方向成為可能。這可能表現為立即適應各種現有沖突,或為未來規劃一個更為永久的建筑。通過此方式,我們可以將自身從其他國家借鑒制度公式或從社會歷史背景中采用某一 “主義”的習慣中解放出來。
眾所周知,除了因文化接觸而產生的正常轉變之外,在今天的中國還有兩個過程融為一體,成為國家生活的一個整體轉變,即從農村的自給自足到工業和世界經濟的演變過程,以及從殖民地到獨立國家地位的解放過程。工業主義是外部強加于我們的。與此同時,從一個經濟階段到另一個經濟階段的任何自發的和正常的演變,都受外國干預的制約。中國不可能解決一個問題而不介入另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考慮到工業革命的歷史,或其他國家的人民在面對外國干預時,為創造一個現代國家而進行的斗爭歷史,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時候都足夠了。在同時處理這兩個問題時,我們中國面臨的困難可能很容易理解。這些問題,的確,這個組合問題,不是獨特的。因此,智慧之路,就是向其他國家學習經驗。雖然我們意識到,要付出的代價將與問題的重要性成正比,但或許我們可以使我們的改造成本低于其他國家。而社會科學家,如果想證明自己的任何用處,那么他們必須是動態導向的,而不僅僅是“學術性的”。在這樣的危機中,固守學術性意味著死亡,而動態導向則意味著重生。以此為導向,發揮社會科學家的作用,最好的方法似乎不是埋首書本,而是從動態的實地研究中學習。唯有實地經驗才是富有創造性的與務實的。
考慮到中國幅員遼闊,任何田野工作,都不是一個人的工作。只要有可能,都必須作為一項共同事業來完成,以便全面而有意義。因為中國是一個處女地,國際同行有機會同時幫助中國及其科學。在這里,認真的工作必然會產生有意義的成果——無論它碰巧屬于歷史學派、功能學派,或者任何一種興趣——即獨立起源、傳播、文化與人格的關系,以及其他。無論他們的興趣是什么,中國為社會科學家提供了檢驗其理論的土壤,并以豐富的研究成果振興他們的科學。其他偉大的文明已得到較為充分,有時甚至是過度的研究。那么為什么不系統地、更積極地嘗試在中國做研究?
國際社會科學家,通過為其科學服務,也可以幫助中國。而且,他們在中國的研究越科學,對中國的社會科學和社會規劃越有利。國際科學家不僅以超然態度,幫助中國工作者對自己的社會文化現象保有一種更有意識和客觀的看法,而且通過他們在其他文化模式中具有的經驗和知識,幫助訓練被指派與他們一同工作的中國學生。反過來,中國社會科學家和學生可以消除語言,以及與中國社區建立聯系的所有困難,這些困難可能會推遲外國學者積極參與這樣的合作事業。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和學生可以消除一切語言的,以及與華人社區建立聯系的困難,這可能會緩解外國學者積極參與此種共同事業的顧慮。與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在中國進行田野工作絕對花費更少,且更有利可圖。任何在其他國家有定期田野工作預算的人,如果在中國使用這筆預算,比如兩年,會發現中國其實并不遙遠,甚至可能省下足夠的錢來支付其來回的路費。只要合作研究產生的出版物是用不同語言編寫的,那么在任何形式的合作中都不可能發生沖突。如有任何疑問,燕京大學和本期刊很高興能作為一個交流平臺,服務于與此類事業相關的問題。
一系列全面的社區功能研究,將為中國的系統社會科學和明智的社會規劃奠定堅實基礎。因此,學術世界和現實世界間的二分,將被證明是二手的產生于搖手椅上的理論與源于直接經驗的具體洞察力間的對立,而非理論與應用間的對立。一手知識將產生創造性的理論與建設性的社會工程。
在對一個社區進行抽樣時,一個單獨的村莊或相當于一個村莊,極可能不是一個相對自給自足的單位。最有可能的是,我們被迫研究城鎮及其周邊的村莊,或更廣為人知的“村鎮社區”(village-town community)。這類綜合性研究不僅為其自身目的服務,而且還為那些更專門和獨立的研究提供機會,然而它們本身,雖然數量眾多,并不構成真正的社會學分析(sociological analysis)。因此,在對一個社區進行社區研究時,在提供功能分析,顯示社區生活各個階段相互關系的同時,也不能排除對有關社區的發展過程和外部關系的研究。在這樣一項合作性的工作中,每位專家都將發揮重要作用。當他自由地專注于自己的專業時,他將不可避免地為描繪整個社區生活形態做出貢獻。例如,一旦制定了涵蓋研究不同階段的大綱,每個研究人員就既有一般職責又有特定職責。其一般職責使他了解整個情況,其特定職責要求對他在共同分工中所承擔的階段進行專門的調查。他所關注的特定領域,同時也是其余研究階段的工作人員的協調中心。他還可以通過同事們的具體立場來確定自己與整個研究的關系。換句話說,每位專家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都扮演著主要角色,并在與同事研究興趣相關的領域中扮演著次要角色。在不妨礙對特定主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同時,研究結果將是一個更高層次上的綜合整體。可以預見,這種合作性研究,在強化每一門具體社會科學的同時,將鼓勵一種真正的整合趨勢,這可能使社會科學本身超越具體社會科學的傳統本位主義。
為促進開展規模足夠大的田野工作,滿足上述設想的迫切需要,準備工作必須完成。這樣的準備工作是給所有參與此工作的人,編輯一系列小冊子。這套叢書可由兩套專著組成,一套關于世界文化區與模式的描述,為中國學生提供必要的文化視角;一套是在理論上涉及方法論和典型專題,如財產、親屬關系、儀式、政府等,為學生提供解釋的建議。有了這些基本手冊,不僅使教學變得系統,材料容易獲得,學生也會得到適當指導,而且全國各地的其他專業人員,如新聞記者、傳教士、學校教師等,也可能會對社會科學產生業余興趣,并幫助以統一的方式收集數據。這些數據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積累到如此巨大,以使世界上此部分的科學變得豐富和重要。
由此可見,無論是積極參與實地研究,幫助編輯基本的系列專著,或提供獎學金和助學金,世界各地有共鳴的學者和科學機構都有機會,在他們的直接利益范圍內幫助中國,以促進這兩類工作在中國的開展。中國社會科學第一手資料的積累,將給世界圖景本身一個新的視角,從而為純科學的利益和我們的實際利益服務,使世界更如我們所愿。
如果這些說明能引發對所提出的一些問題的探討,那么其目的就達到了。我們不能聲稱已完全處理了此處所表達的觀點。因此,我們希望那些感興趣的人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感受,例如,關于合作研究的整體想法,或者描述他們自己在田野工作中的經驗與建議。也可以提出社區研究應該包括什么的問題。我們樂于接受意見、建議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