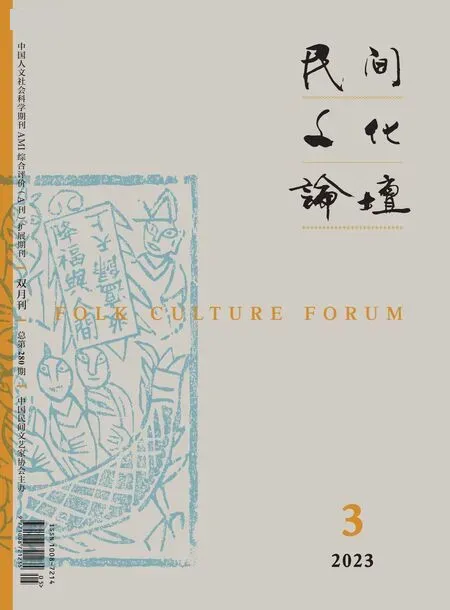“國家”與“邊地”之間
—— 清代以降滇西儀式背后的鄉村權力
張柏惠
學界以往在討論明清時期地方文化發生改變的過程時,往往強調的是士大夫文化的以“禮”化“俗”。在其描述中,這個“禮”是王朝標準化的禮制(廣義上包括禮拜儀式、服飾、建筑風格,以及文書格調和標準等),是國家在文字權力擴張過程中“強加”給地方的“禮”;“俗”則是地方舊有的禮儀傳統,他們代表著地方民眾的世界觀和宇宙觀。然而,隨著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不斷推進,可以看到,在明清時期,之所以國家的“禮”能順利地在地方推行,主要是因為民間的“俗”選擇“主動”靠近,而地方也往往形成“禮”“俗”共存的格局。那么民間的“俗”是經由什么媒介從而與國家的禮教產生關聯的?國家與地方之間是否存在著一些“文化中介”群體?這些中介是什么樣的社會群體?明清時期,各地文化中介之職能由不同的社會群體承擔,中介的機制也有相當大的地域差別。其中,以何炳棣、張仲禮、費孝通、吳晗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士紳群體是王朝國家與地方之間最重要的媒介。①何炳棣著,徐泓譯注:《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張仲禮:《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費孝通、吳晗:《皇權與紳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在區域社會史的相關研究中,通過士紳等中介群體的帶動,地方文化向精英化靠攏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然而,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士紳等中介群體為何甘心扮演皇權執行者的角色?這些中介群體為什么要讓地方文化向精英化靠攏?精英化的過程對于各地方的歷史意義究竟是什么、有何不同?對于這些問題,研究者從不同的觀察點切入并對不同的區域展開研究時,往往會得到不盡相同的答案。
社區的廟宇(或是神明信仰)是地方之“俗”的重要標識,而圍繞著這些廟宇(或是神明信仰)所建立的拜祭系統在空間及社區人群的生活中通常是通過儀式來體現的。因此,儀式是研究者觀察地方文化的一個切入點,通過儀式分析不僅能夠勾勒出社區內部的關系,還能夠看到超越社區邊界更大的地域社會關系,更重要的是,儀式發生變化的過程本身也與社區歷史發展中各種社會關系的變動以及地方所經歷的歷史過程相呼應。
對于地方儀式的歷史解讀,劉志偉、羅一星等學者圍繞著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北帝信仰儀式所展開的研究是一個經典的案例,就筆者上述的提問,在他們的討論中能夠找尋到一些回答。羅一星通過對佛山地區四大祭祀儀式的細致論述展現了社區內部的關系:北帝坐祠堂的儀式與八圖土著之間的共享關系和社區特權;北帝巡游與佛山社區的等級關系;“燒大爆”與不同地緣群體的關系;鄉飲酒禮與僑居者、土著民的關系。①羅一星:《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劉志偉則通過對北帝儀式的分析討論了地方與國家的互動關系。②劉志偉:《神明的正統性與地方化——關于珠江三角洲地區北帝崇拜的一個解釋》,《中山大學史學集刊》(第二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07—125 頁。他談到,祭祀北帝的儀式既展現了上層士紳和下層鄉民之間不同的文化行為和態度,同時也體現了兩者互相影響、互相適應的一面。
華南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答案,那么對于西南而言,答案又是如何的呢?本文旨在通過對現今依舊留存于滇西綺羅鄉的“打保境”儀式的考察來探尋上述問題的答案。
一、綺羅鄉與打保境儀式
綺羅鄉現今隸屬于云南省西南部的騰沖市,其下轄三個自然村——上綺羅村、中綺羅村及下綺羅村。③綺羅鄉所在的滇西地區對于中原王朝來說是一個“極邊區”,然而,對于東南亞地區而言,卻是一個通往內地的“核心”地區,是東南亞往來貿易的中心之一。歷代統治政權將騰沖設置為管理滇西地區的行政中心,視其為滇西地區的門戶。綺羅鄉早期的歷史較少有文字等記錄留存,村落所在的大盈江流域,在明王朝入駐西南以前已有土人進行開發并形成了一些聚落。④陳文纂修,李春龍、劉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圖經志書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342 頁。萬歷《云南通志》以及《徐霞客游記》中均有“矣羅村”的記錄,可推知,在明代時,“綺羅”已經發展成為眾人熟知的規模較為完備的聚落了。⑤李中溪纂修:《(萬歷)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觀·永昌軍民府》,《西南稀見方志文獻》第二十一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影印本,第309 頁;徐弘祖:《徐霞客游記·卷九上·滇游日記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1002 頁。入清后,騰沖全境被劃分為十八個“練”,“綺羅練”便是其中一“練”,而綺羅鄉則是該練的主體部分。進入民國后,騰沖地方改設五個大區,綺羅鄉分屬于第二區。民國三十三年(1944 年),騰沖光復后,綺羅鄉改為直屬騰沖縣政府,新中國成立后,又歷經幾次行政劃分的更改。
隨著定居人口的增加以及村落規模的拓展,“矣羅村”在清朝初年時便已分劃為由東北向西南延伸的上、中、下三個部分。村落中的一部分巷道使用姓氏來命名,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前巷道舊名的延續。綺羅鄉現留存的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主要公共建筑為上綺羅村的妙光寺建筑群、段氏宗祠,中綺羅村的觀音寺,下綺羅村的文昌宮建筑群、水映寺、靖瀾寺(現只殘存房屋的梁架部分)、綺羅圖書館、河邊李氏宗祠、青齊李氏宗祠以及尹氏宗祠。
在自然地理上,綺羅鄉位于騰沖城東南4 公里處,地勢北高南低,東西為開闊的田野,是一個平壩地區。自明代至今,綺羅鄉大部分鄉民的生計方式以務農為主,種植作物多為水稻,一年一季。①騰沖西邊的德宏地區,即明、清時期的土司地區,同樣以水稻種植為主,因氣候條件不同一年則可以收獲兩季。為了補貼家用,一部分鄉民會選擇在冬春之際往返緬甸進行貿易。②李根源、劉楚湘纂,許秋芳主編:《民國騰沖縣志稿·卷十七·農政·土壤及農時》,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4 年,第324 頁。從騰沖城出發,經過綺羅鄉之后,便是多條通往緬甸的主要交通干線,因此,該鄉“走夷方”從事商業貿易之人頗多。③李根源、劉楚湘纂,許秋芳主編:《民國騰沖縣志稿·卷二十四·禮俗·習尚》,第441 頁。
綺羅鄉每年最重要的儀式是立秋前的“打保境”。“打保境”又喚作“秧苗保境”“消災保境”。舉行該儀式是為了祈禱風調雨順,秧苗長勢順利,無病蟲害,能夠獲得豐收,同時達到消除地方災禍、清吉平安的作用。該儀式每年在立秋前的兩三天舉辦,與農事緊密相連。立秋前的日子是騰沖地區插完秧后的農閑時間,因此鄉民得以有時間參與地方上的祭祀活動,同時也可以為此后的秋收做準備。在綺羅鄉鄉民的記憶中,新中國成立以前舉辦打保境時,四鄉八鄰齊聚,人山人海,轉經隊伍所過之處,人們夾道觀看、歡呼。屆時還有賣小吃、小玩意兒,走親戚,談生意的,場面十分熱鬧。然而,打保境既不是綺羅鄉獨有的一個儀式,也不是整個騰沖地區的鄉、鎮都舉辦的儀式活動。打保境儀式主要由城關鎮(即騰沖城)及其周圍的和順鄉、綺羅鄉、洞山鄉、玉璧村以及個別雖然遠離騰沖核心區,但是人口稠密且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固東鎮的順利村等舉辦。
關于打保境儀式,官方史書以及歷代民間文獻中均沒有確切且詳細的記載。同樣,騰沖其他舉辦打保境儀式的鄉、鎮亦不知儀式確切的起始時間。打保境儀式的一個核心部分是洞經隊的演出,綺羅鄉洞經隊的成立則可以明確地追溯到清代的道光年間。據此可以判斷,綺羅鄉舉行打保境的儀式最遲不會晚于道光時期。
早期的儀式,現在不易得見,但從如今保留下來的科儀文書、儀式表演以及對洞經隊老成員的訪談中,仍然能夠辨析儀式中所表達的地域社會關系,從儀式的變化中也能看到社區歷史發展中各種社會關系的變動。④筆者在田野考察中共搜集到綺羅鄉洞經隊用于舉行打保境儀式的科儀文書共34 本,這些科儀文書均為老舊的手抄本,大多年代不詳。其中《打保境功德名錄》為光緒六年(1880 年)抄本;《大洞治瘟寶錄》為民國八年(1919 年)抄本;《太上洞玄靈寶拔度救苦談章》為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抄本。因為民間信仰儀式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借助身體動作、語言表達等形塑的一種社會文化。在儀式中,地域社會里的不同人群依照其所掌握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源,分別表現其各自的身份、地位與訴求。不同人群在不同時間依序登臺演出,這便是地域社會人群關系、權力變遷的一種表達。
綺羅鄉每年打保境多在立秋前的兩三天開始舉行,整個打保境儀式共持續四天。儀式第一天的內容包括“熏壇”“蕩穢”“禮請諸真”,即清理經壇,蕩除污穢,并將請帖送往天上的眾神,請眾神第二天來參加保境大會,目的是為第二天打保境活動的正式開始做準備。第二天的儀式意味著保境活動的正式開始,主要內容包括“宣讀儀注榜”“迎神”“談演《大洞仙經》上卷”“讃燈”“接亡”“設諸天科”。第三天的儀節包括“開壇”“談演《大洞仙經》中卷”,期間包括“迎十供養”“轉經抬閣”“談演八卦”“設齋(或是設醮)”。第四天是打保境儀式的最后一天,主要包括“開壇”“談演《大洞仙經》下卷”“拔亡”“送亡”“送圣”。除了“轉經抬閣”這個部分,所有的儀節均是在同一廟宇中主要由洞經隊成員及承首來完成,1918 年以前,主要儀節是在下綺羅村的文昌宮內完成,1918 年以后至今則改為在上綺羅村的妙光寺內舉行。
整個打保境儀式過程中最熱鬧且最能體現社區整合并明確其“邊界”的環節便是“轉經抬閣”。①因騰沖縣政府的安全管理要求,2000 年前后綺羅鄉被迫取消了“轉經抬閣”,所有儀節表演改由在廟里進行,因此現今已看不到“轉經抬閣”的表演。轉經前,經長宣讀“起朝”表文,示意諸位神仙也跟著一起轉經,焚表后正式開始轉經。轉經隊伍所要經過的鄉里的主要巷道都會提前擺好香案。轉經隊伍沿村邊大路轉走,按順序依次經過上綺羅村的妙光寺(起點)、中綺羅村的觀音寺以及下綺羅村的文昌宮和水映寺(終點)。走在轉經隊伍最前面的人群舉著皇傘,扛立著風旗,邊走邊敲鑼打鼓。洞經隊成員同樣列于隊伍前端開道,并隨走隨演洞經音樂,承首則手捧香爐緊隨其后。除此之外,巡游的隊伍中還包括高抬閣②高抬閣的構造,用木料堆成假山的形象,再用細鐵絲互相連接起來,假山配置花草。下面是四方形的木架,中間立一根用鐵做成的拐桿。上面放置一個小臺子,供人站在上面。臺桿上以十二三歲的男童裝扮成白蛇、仙女、姜太公等人物。,地抬閣③即地上走著的裝扮人物,人物選自戲曲中的角色,如唐僧、笑和尚。,水讖棚④用一個木架子搭著,前后各一個人抬著,中間搭成一個篷子。外面一個人打著大缽,棚里的那個人打著鼓。,大提爐四個,香亭⑤用竹子扎成的亭子,中間放著香爐燒香。,以及人裝扮的馬、趙、溫、康四帥⑥“馬”即馬天君(馬靈耀);“趙”即趙公明(財神);“溫”即溫天君(雷神化身,消除瘟疫);“康”即康元帥。四帥各騎一匹馬,手持刀槍、寶杵等法器。、太歲和鬼王。在轉經抬閣的過程中,巡游隊伍要轉到當年擔任承首的家里上一道“鎮宅表”。轉經隊伍每經過一個大巷口,承首都要進一炷香,并鳴鐵炮三響。待由上綺羅村轉到中綺羅村的觀音寺時,隊伍停下,由經長去寺里上一道表文,后又轉到下綺羅村的文昌宮同樣上一道表文,最后隊伍到達下綺羅村的水映寺,上完表文后,抬閣、四帥等裝扮者卸裝,巡游隊伍解散,表示轉經結束。據鄉民們回憶,轉經游行的隊伍浩浩蕩蕩,全鄉的男女老少都會夾道觀看,場面十分熱鬧。
二、國家禮儀的地方化與士紳的文化中介功能
參與整個打保境儀式籌劃、表演的人員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整個儀式每年主要、固定的參與者,洞經隊成員。第二類是承首、相邦者、轉經隊伍扮演者等不固定人員。綺羅鄉洞經隊的成員是儀式專家,負責指導祭品擺放等準備工作,引導整個儀式過程,使得四天的活動井然有序。同時,他們還是各部經典的唱誦者以及洞經音樂的主要演奏者。
根據筆者對綺羅鄉洞經隊新、老成員的訪談以及綺羅鄉歷任洞經隊經長的記錄,綺羅鄉洞經隊最初成立于下綺羅村,組織創立者以及第一任經長名叫李含英。⑦李含英是下綺羅村河邊李氏宗族的成員,道光初年的舉人,在他的主持下河邊李氏亦在道光年間開始正式建設宗族。洞經會成立時取名為“桂香會”,新中國成立前充任桂香會會員者除了必須是綺羅鄉人士外,還必須具備儒生身份。洞經隊現任成員均擁有“一技之長”,而這些技能往往都受教于老一輩的洞經隊成員。新成員中的一部分人需要向老會員學習如何撰寫祭文以及行禮(包括唱禮和誦讀祭文),另外一部分則需要學習如何彈奏樂器以及奏唱洞經音樂。成為洞經隊成員并不意味著是選擇了一個職業或是從事一個行當,綺羅鄉洞經隊成員大多是“兼職”參與桂香會的活動。在整個打保境期間,他們是溝通神明的儀式專家,并以文昌帝君座下弟子自居,這種能夠與神明溝通的資格便是借助“入會”以及“師承關系”進行傳遞的。洞經隊成員在儀式中的地位,類似于道士在道教科儀,僧侶在佛教科儀中的地位。
從道光年間開始,以李含英為首的士紳群體便借助洞經演奏參與到了這個本地的重大儀式當中,成為儀式表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此以后,他們通過主持儀式強固了這個群體在鄉里的權勢。根據鄉里的老人所述,新中國成立以前鄉里的讀書人家都會爭相把小孩送去洞經會學習,而洞經會成員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更受到鄉民們的尊敬并且在鄉里擁有很高的地位。
傳說李含英將洞經引入綺羅鄉的契機是其離鄉赴京參加會試,他在離鄉期間習得洞經后便引薦回鄉。故事的真實性無法考證,但這個傳說卻透露出洞經不是騰沖本土而是外來事物的信息。騰沖地區同樣擁有洞經組織及打保境儀式的,如和順鄉、洞山鄉等,他們關于洞經會成立的傳說亦大致表明洞經是由外地傳入騰沖的。①對于洞經傳入騰沖地區的時間與地點各鄉的說法均不同,但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南京傳入說”,即明朝初年由南京到騰的移民傳入;二、“鶴慶、大理傳入說”,即清代中葉由大理地區傳入。(參看郭朝庭、閔承龍、毛三:《保山洞經初探》,《今日民族》2007 年第12 期;騰沖縣文管所、騰沖縣民族民間傳統文化普查組:《騰沖打保境調查報告》,2005 年5 月20 日。)以往的研究顯示,洞經音樂以及洞經會自明代以來便在云南流布開來,談演洞經具體起于何時以及源于何方均無明確的史料記載。②據學者們的調查研究,云南最早成立的洞經會大概是洱海地區下關的“三元社”和大理的“葉榆社”,兩會成立于明中期,此后洞經會組織便逐漸擴散到云南諸地。一般的說法是隨著明朝在云南開疆拓土后,洞經音樂及洞經組織便由南京、四川等地傳入云南,隨后以大理為中心向周邊傳播、拓展,云南的洞經會組織因談演《文昌大洞仙經》而得名。③關于洞經會在云南的緣起,從現有的學術成果看主要有三種說法:一、以王興平《文昌崇拜與洞經音樂》(《音樂探索》,1996 年第2 期)一文為代表的著述認為元末明初時由江南移民和士兵帶入洞經音樂,隨后云南相繼組成了洞經會;二、以張興榮《云南洞經文化:儒道釋三教的復合性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一書為代表的著述認為洞經傳入云南的時間大約在明初洪武年間,由南京、四川等地傳入,在嘉靖九年時大理率先成立了三元社和葉榆社兩個洞經會,隨后洞經會組織擴散到云南諸地。三、以何顯耀《古樂遺韻》(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為代表的著述認為洞經音樂與洞經會起源于云南大理。
根據一些學者對云南昆明、大理、楚雄、建水等地洞經會調查的情況來看,云南地區洞經會的成員在明清時期幾乎都是有功名的儒生。④參看張興榮:《云南洞經文化:儒道釋三教的復合性文化》,第1—16 頁。同樣,新入會的洞經會成員向老一輩的成員學習,老成員以口傳心授的方法教學工尺譜,鑼鼓經或“朗當譜”。有些成員采取跟班聽學的方法,修習滿三年后便可當選司事,邀人擺壇,參加洞經會內部組織的“考試”合格后才算正式會員。⑤張興榮:《云南洞經文化:儒道釋三教的復合性文化》,第27 頁。
洞經隊成員在儀式中的分工都十分明確,一人擔任“通贊”,該人需精通禮儀程序,負責發號施令,引導禮儀的完成。一人擔任“陪贊”,負責協助通贊發號施令。一人擔任“糾儀”(或稱“監經”或“督壇”),該職位通常多由老成公正的紳耆充任,負責糾察違規者。洞經隊其余成員擔任首座、副座、上座、下座等,負責樂器的彈奏。⑥“首座”一般位于左班之首,實為談演的總指揮,負責起調畢曲、曲牌轉接等談演。“副座”位于右班之首,實為談演之副指揮,該人精通經籍,負責經典談誦講讀,散引領唱等。上席位置一般在堂內左、右班第2—6 座,操演各種樂器(武樂)。下席位于堂外左右班第1—4 座,操演各種樂器(文樂)。(參看張興榮:《云南洞經文化:儒道釋三教的復合性文化》,第27—28 頁)綺羅鄉洞經隊的成員在打保境儀式中雖然幾乎沒有這些“專稱”,但是他們的“分工”卻都帶有上述那些“普遍性”的特征。四個“朝席”是談演的總指揮,負責曲調的節拍以及經文的誦唱。其中右班的首席是整個儀式中最為關鍵的人物,他負責起調、畢曲、曲牌轉接、散引領唱以及儀式的表演與主持。整個綺羅鄉洞經隊除了有在堂上參與儀式表演的成員外,另有專門負責書寫文書的“文書長”,負責各個儀節供品、經場布置的專員,引導承首及善信進行拜祭的專員以及糾儀的“督察員”。這些綺羅鄉洞經隊成員在儀式中的“職責分工”又與州縣層級王朝禮儀中的“通贊”“引贊”“司正”“樂生”等十分相似。
如若翻檢明清《會典》以及明清地方志所記載的州縣層級所舉行的儀式規程,可發現綺羅鄉的打保境儀式和明清王朝禮儀涉及的程式與司儀所喊的口令等多有相似重疊之處。州縣層級所舉行的儀式是民眾最容易接觸到的王朝禮儀,如祭祀孔子、關帝、社稷的儀式,鄉飲酒禮儀式等,在明清各種政書與地方志中都有詳略不等的記載。①明清王朝的祭祀禮儀及其儀注可參看《明會典》、《大清會典》的記載,對于州縣層級的禮儀,地方志中的記錄較之《明會典》與《大清會典》更為詳細,云南方志中乾隆十四年所編《新興州志》對鄉飲賓禮的程式作了詳細的記錄。(任中宜纂修:《(乾隆)新興州志卷八典禮》,《中國地方志集成·云南府縣志輯》第26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第550—551 頁。)明清時期州縣層級的眾多儀式的程式有很多相似之處,比較打保境儀式與鄉飲賓禮儀式,可以看到從司儀的選用與職責,禮儀的程式以及口令都十分相似。只不過在時間上王朝禮儀的一個過程完成往往比較短暫,整個打保境儀式完成持續時間較長,如果仔細分析不難發現,打保境的儀式在循環往復的上演明清王朝禮儀的基本程式框架。但是,打保境的儀式又并非都是照搬王朝禮儀。從儀節來看,打保境儀式又與文廟的釋奠禮等王朝禮儀有所重疊。文廟釋奠禮的主要儀節包括:迎神、三獻禮、飲福受胙、徹饌、送神、望燎(焚祝帛)。②劉永華:《明清時期的禮生與王朝禮儀》,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著:《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9 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245—257 頁。而打保境的主要儀節中也包括迎神、三獻禮(雖然獻的都為素食)、飲福受胙、徹饌、送神、焚表文等。即使打保境儀式期間穿插了其他儀節,但是其主要的儀節安排及順序仍然與王朝的禮儀有諸多重疊之處。當然,將地方與國家禮儀的儀式作比對,并不是說打保境儀式就是對明、清王朝禮儀的直接復制,而是說它的形成受到了王朝國家禮儀的影響或是借鑒了國家禮儀。從儀式的結構看,文廟釋奠儀式和明清時期的其他朝廷祭祀儀式比較相似,釋奠儀大體上是郊祀儀的簡化。③劉永華:《明清時期的禮生與王朝禮儀》,第245—257 頁。無疑州縣層面舉行的儀式成為了王朝禮儀向民間滲透的最重要的渠道。
既然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充任桂香會的洞經隊成員都必須是地方儒生,那么他們其中一部分人或多或少都參與或是觀摩過地方衙門所舉行的祭祀孔子、關帝、社稷、鄉飲酒禮等王朝禮儀,自然對官方祭祀的程序耳熟能詳。王朝禮儀的公開性與易復制性又讓這些地方精英得以將這套禮儀運用到地方的儀式當中,而這個過程也是國家禮儀地方化的一個過程。
但是,必須注意到的是這些儒生對于王朝禮儀的復制顯然也是有限度的,從打保境儀式中選用的科儀文書、所拜請的神明以及經場的布置等來看,打保境儀式更多的是融合了大量道教、佛教以及民間宗教的禮儀傳統。從洞經隊隊員所使用的各種科儀文書的內容來看,大多都是從道教的各種“經典”中直接抄錄使用的,儀式的幾個重要儀節(例如“八卦”的談演)也是源自道教。
雖然洞經隊成員均自稱所屬儒教,但是從整個打保境儀式期間要求斷絕葷茹、停止俗事以及向各位圣真獻上的拜祭品來看,是與儒教的“血祀牲祭”截然不同的。設醮(設齋)、度亡等儀節安排同樣也與儒家的祭祀無關。因此,這些士大夫雖然將王朝的禮儀“挪用”了一些加入到打保境儀式之中,但是綺羅鄉地方儀式的主體內容仍雜糅了道教、佛教以及民間宗教的禮儀。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由于綺羅鄉洞經會的成立使得綺羅鄉打保境儀式帶有了濃重的“精英化”色彩,如上所述,這體現在了洞經會的成員極力地將地方儀式與中原儒家文化以及王朝國家的禮儀建立某種關系,主動讓其“精英化”。從下綺羅村文昌宮中所保留的明清歷朝儒生的題名碑可以看到,自乾隆以來,綺羅鄉的儒生人數迅速增加,而嘉慶、道光時期更是綺羅鄉乃至整個騰沖核心區域宗族建設蓬勃發展的時期。①《科甲題名碑》,現存于下綺羅村文昌宮內。若將地方的種種變化與洞經會在村落儀式中的加入關聯起來,或許可以認為地方儀式的“精英化”是此時士紳階層擴張的另一個產物,更是因為乾隆中期爆發“清緬戰事”后,致使滇西邊地族群關系緊張,從而使內地人群對于漢人身份以及國家認同的不斷加強。
另一方面,之所以這些士紳愿意充當“中介”并借助洞經會談演等活動融入地方的信仰儀式之中,是因為他們心中有數,知道中央的權力可以為地方所用,于是模仿著王朝國家的禮儀來向村落人群展示他們在社區中的至高地位,由此開始獲得對于地方“掌控”的權力。
三、儀式背后的權力更替與地域社會關系
整個打保境儀式中除了洞經隊成員外,“承首”是另一類關鍵人物。承首的人選每年都不是固定的(不同于洞經會成員的長期選任),通常在儀式開始前的半個月就已選定,一般由一到兩人擔任。他(或他們)在儀式中充任主祭者,是獻祭主體,更是整個社區的代表。每年打保境活動的經費大部分由當年的承首以及村民捐獻,其中承首為主要的出資者。雖然擔任承首對被選任者自身的財力要求較高,但是并非有錢的人家都能被選為承首,承首的選任還要看該戶是否在村落內乃至地方上具有威望,品行是否端正等。鄉民們認為,能夠擔任承首的人都是在社區中有權勢并且掌握話語權的人,反過來說,充任承首亦是在打保境儀式中公開向鄉民們顯示其宗族在社區中地位的一種表達方式。
整個打保境儀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承首與洞經隊成員的密切配合,他們是整個儀式中最為重要的兩個能動主體。在承擔“引贊”職責的洞經隊成員的引導中,承首代表社區通過上香、點燈、獻祭等方式與神明進行直接地溝通。雖然洞經隊成員在實際生活中為社區的成員,但是在舉辦打保境的儀式時,這些洞經隊成員的身份是文昌帝君在人間的弟子,他們作為第三方,是連接神明與社區的橋梁,職責是組織、主持、表演整個禮儀,而不是像承首一般以社區代表的身份與神明進行溝通。
據洞經隊成員以及鄉民們的回憶,新中國成立前,綺羅鄉的承首多出自那些建有宗族者,那么,充任承首亦是宗族顯示他們在村落中擁有權威的方式之一。在打保境儀式的轉經抬閣儀節中,轉經的隊伍在巡游時要特別繞到當年擔任承首的家門處,并由洞經經長上一道“鎮宅表”,這是擔任承首者享有的“特權”,意在向社區人群表明承首所屬的宗族在社區的地位。
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必定包含著不同人群的興衰隆替,承首及洞經隊成員的選任即是社區內部權力更迭的表現。
按照綺羅鄉洞經隊成員的追溯及歷任經長的記錄,第一任洞經會經長李含英去世后,并沒有人立即接任會長一職,直到“咸同事變”平息后的光緒年間,才有名叫許莊廷者接任經長職位。許莊廷為中綺羅村許家巷人,此人是李含英麾下的洞經學員中最為出色者,他先后在騰沖地區傳教洞經。但是后來由于許莊廷赴緬甸經商,再未回綺羅鄉,于是蕭應祉接任,成為第三任經長。蕭應祉是中綺羅村貢生蕭琇如的次子,曾在光緒年間獲得監生的功名。①《科甲題名碑》,現存于下綺羅村文昌宮內。繼蕭應祉后,第四任經長為黃興忠,他是上綺羅村黃家巷人,生于清末,在新中國成立前后亦赴緬甸經商,未歸。新中國成立前,上綺羅村栗樹園人李大綱接任了第五任經長,然而在他接任后不久,洞經隊便發生了分裂,分為兩隊,即上、中綺羅村一隊,下綺羅村一隊。
兩個洞經會在當時約定,由上、中綺羅村的洞經隊負責每年的打保境儀式,下綺羅村的洞經隊則負責村里的另一個重要儀式——朝斗。但是,新中國成立不久后由于各種“浪潮”,鄉里的儀式被迫停辦,兩個洞經會也停止了活動,直到1979 年,在第六任經長楊正林的組織下,上綺羅村的洞經隊才得以恢復,自此他們重新開始負責整個鄉里所有儀式的舉辦。自1979 年以來,共有5 人擔任過綺羅鄉洞經會的經長,他們均為上綺羅村的村民。
從綺羅鄉洞經隊自清中期至新中國成立后擔任經長人員的來源以及桂香會的裂變來看,掌控地方權勢以及話語權的力量從清中期的下綺羅村逐漸轉移到了民國末年的上綺羅村。這種權力的更替一部分是由于社區內部的激烈競爭所使然,另一部分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隨著國家新一輪的政權更替,下綺羅村的大部分精英勢力遠走他鄉、逐漸消逝,從而導致社區人群權勢重心的轉移,而這種社區權力重心的轉移顯然投射在了洞經會的組織變動之上。
放眼騰沖地區,同樣,大部分財勢較大的宗族在民國年間相繼移居緬甸,隨著人群勢力的轉移,在緬甸地區,洞經會組織逐漸成立。至民國末年,騰沖人在緬甸成立的洞經會組織有“當陽桂香會”“瓦城(曼德勒)桂香會”等。②楊大禹、李正:《歷史和順》,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85 頁。新中國成立后,騰沖地區的洞經活動逐漸停辦了,而在緬甸的活動則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緬甸的洞經會與騰沖地區的一些洞經會一直保持著往來關系,洞經會成為了身在國外的人群與本土家鄉聯系的一道橋梁,也成為緬甸地區華人在異鄉維系關系的一個紐帶。
回到打保境儀式,雖然現今已不再舉行轉經、抬閣的儀節,并且由于市政道路的改建已經無法再復刻出當年巡游的路線。但是,無論村中的道路怎么變化,十分明確的是,巡游隊伍必從上綺羅村的妙光寺出發,且順次經過中綺羅村的觀音寺和下綺羅村的文昌宮和水映寺。從這些廟宇留存的碑刻中可知,清初至清中葉時綺羅鄉的鄉民對它們進行了一番修復擴建工作,這些修建活動不僅明確了綺羅鄉中大姓家族對于各寺廟的掌控,更明確了妙光寺、觀音寺和水映寺分別作為上、中、下三個聚落核心廟宇的地位。③乾隆四十八年《常住田碑》,碑存上綺羅村妙光寺內;《妙光寺碑記》,碑存上綺羅村妙光寺內,該碑為2007 年新立。乾隆三十二年《重修觀音寺碑記》,碑存中綺羅村觀音寺內;乾隆三十年《水映寺碑記》,碑存下綺羅村水映寺內;乾隆五年《文昌宮常住田碑》,碑存騰沖市綺羅鄉下綺羅村文昌宮。清初至清中葉時,綺羅鄉還未開始建構宗族,因此人群的關系多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組織;清中葉開始建構宗族后,人群的關系則逐漸變為以共同祖先作為依據的地域群體,于宗族組織而言,祖先只是依據,重點是成員對祖先的認同而不是成員是否與祖先有相同的血緣。然而,不同于前三者,下綺羅村的文昌宮是跨越社區內部邊界的存在,是整個綺羅鄉共享的一個廟宇,但是,它在功能上只屬于村落中的士紳階層。
因為四個村廟是綺羅鄉的核心廟宇,所以成為儀式巡游路線的必經點。當巡游隊伍達到村落的核心廟宇時,都要由洞經經長進入廟中上一道表文。這一舉措既明確了綺羅鄉內部各村落的存在又建立了它們之間的關聯,使得社區祭祀系統得以統合。另外,轉經隊伍在巡游時每經過村落的一個大巷口,承首都要進一炷香,并鳴鐵炮三響,這一舉動亦是社區在地理空間上統合的表達。
顯然,在清初時,社區內部已經開始產生分化,但綺羅鄉為何還能保持其整體性呢?明清鼎革后,騰越州全境被劃分為十八個練,按照《州志》所載,各“練”下直接統轄各“甲”,而每個甲之下又有一個到幾個不等的村、寨,從十八練各甲的相對地理位置來看,幾乎都是按照地域進行劃分的。①屠述濂纂修:《(乾隆)騰越州志》卷二《疆域·村寨》,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本,第28—32 頁。綺羅練是騰越州十八練的其中一練,其下囊括了好幾個村寨,除了現今綺羅鄉的主體部分,還包括了距離綺羅鄉較遠的田心、栗柴壩、瞿家營、冷飯寨等四個村寨。行政的設置使得綺羅鄉在清代時仍保持成為一體。轉經抬閣的儀節整合著社區內部的“三村”與“四廟”,使得綺羅鄉在實質上還是一個整體并以此呼應“練”的格局。至道光年間,由于邊地野夷滋擾過甚,騰越廳為了加強防范,以各“練”為基礎采取了一些措施。②趙端禮纂,陳宗海修:《(光緒)騰越廳志》卷十一《武備志·邊防》,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本,第181—183 頁。“練”的格局因為地區局勢的動蕩及設置的補充、增加而變得越發重要。
在社區發展中必定包含著很多的沖突與矛盾,祭祀儀式的安排,則可以成為村落不同人群用于調整和確認相互關系的一種手段。轉經、抬閣儀節的安排,除了擁有其功能性的表達——強化綺羅練作為一個整體外,更是全鄉人一年一度的一個狂歡節日,社區成員在此儀式中增加著彼此之間的認同感。
四、結論
綺羅鄉的士紳在道光年間成立了洞經“桂香會”并成功加入到村落的儀式之中,此舉改變著村落權力的體系,更是士紳階層力量擴張的體現。洞經隊成員將王朝禮儀的元素引入到打保境儀式之中,成為了儀式主持的主體,由此參與到村落內部人群關系的建構當中。
清初綺羅練的設置使得綺羅鄉內各個村落在行政上以一個整體而存在,但從各大姓對妙光寺、觀音寺與水映寺等村落中心廟宇的修建活動又可以看到,綺羅鄉在發展的過程中實際上逐步分化為上、中、下三個聚落。鄉民們通過舉行打保境儀式整合著“三村”與“四廟”,從而增加了全鄉人對于彼此之間的認同感,使得綺羅練在實質上保持著整體性。同樣,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也必定有很多的沖突與矛盾,儀式的舉行則可以成為村落不同人群用于調整和確認彼此關系的一種手段。
前輩學者所提出的士紳功能論的一個缺陷在于過度強調士紳階層的中介作用,從而使得研究者在理解和認識鄉村權力關系的時候往往容易局限在對國家政權與地方精英之間權力變動的討論之上。士紳功能論者對于鄉村權力運作的討論主要是將關注點放在國家與士紳之間的關系之上,并沒有橫向考慮村落內部的其他權力結構以及他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由此自動忽視了村落中其他的權力關系。顯然,士紳功能論不能完全解釋鄉村權力關系的運作。
在綺羅鄉的歷史發展中,這些介于國家與地方之間的鄉村精英——不論是士紳還是其他身份者,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個人利益和宗族利益,促使他們去參加科舉從而擁有儒生身份的動力大多不是對國家效忠,而是這個身份所帶來的社會地位以及地位所代表的權力。雖然洞經會的成員完全是由參與科舉考試的儒生組成,但是洞經會成員的選任與國家、地方政府完全無關,同時他們所進行的活動也并不是以替國家控制鄉村為目的。因此,由儒生組成的桂香會并不是王朝教化的推行者,王朝的禮儀以及國家最上層賦予他們的地位只不過是這些儒生能夠成功參與到村落的儀式之中從而掌握話語權的籌碼。國家與地方的關系并不是絕對的控制關系,鄉村精英們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也并不是與地方對立而趨附于國家政權的存在。
帶有儒生身份的洞經會成員以本地的方式將國家的“禮”融入到地方的“俗”之中,不是國家強權的干預,而是地方社會給國家以應有的尊敬與認同,并且將之整合到地方的禮儀之中,“地方社會心中有數,知道中央權力可以為地方所用,于是屈從于中央”①科大衛:《明清社會和禮儀》,曾憲冠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112 頁。。在蕭公權所描述的中國鄉村中,國家權力必須無處不在,這是帝國控制想要達到的一個目標,但是應該看到,這個目標的實現必須有民眾的主動參與,而在實際的歷史過程中也確實是在村民們的“主動與共同的行動下”完成的。地方用來維護傳統與利益的行為,經常以拉近自己與國家關系的方式實現,而民間性的文化創造與地方認同的營造,往往就是國家整合機制的形成過程。②劉志偉:《講述鄉村故事》,收入《借題發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第123 頁。此外,從綺羅鄉的案例中亦可以看到,導致鄉村權力變遷的因素是多元的,鄉村權力存在于錯綜復雜、不同維度的社會關系之中,國家與鄉村的關系只是這眾多維度中的一維,不同時期、不同因素所形成的權力關系才共同形塑了那時的鄉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