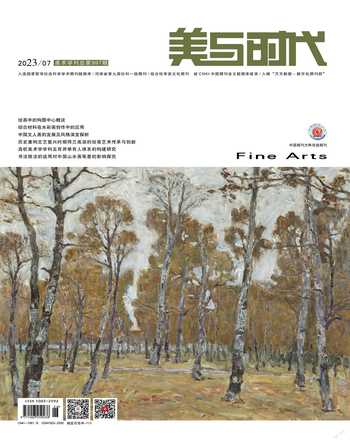黃公望對明清山水畫的影響
摘 要:作為“元四家”之首,黃公望的繪畫創作與理論對明清山水畫多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結合沈周、董其昌、“四王”等明清時期藝術家的創作,闡述黃公望對明清山水畫意境、設色、技法的影響,分析后人對黃公望山水畫藝術的繼承和發展。
關鍵詞:黃公望;山水畫;明清山水畫
一、黃公望繪畫的藝術特點
黃公望(1269—1354年),字子久,號大癡道人。研究黃公望的繪畫藝術,很難從一個固定角度入手,因為黃公望沒有將自己限定在一個框架中。這恰是他最智慧的地方,也是其精神源泉。用框架的方法只能得到被限制的黃公望,得不到自由灑脫的大癡。
朱良志教授在《南畫十六觀》中表示,黃公望之畫,“最重這全然之悟”。也就是說,正是因為領悟,才會有子久的藝術創作。他認為黃公望只是一個“懵懂人”,借助兩只朦朧醉眼窺探這世間萬物,做到了忘記凡塵,忘記自己。這說的是非常貼切的。如果不能從這個角度了解黃公望,僅僅從筆墨入手,是絕不能懂大癡的。
汪砢玉說:“水紋風皺,花影月翻,此不染畫事也。觀大癡畫不當于筆墨中求之。”說的很有道理。黃公望在《寫山水訣》中言及很多繪畫中應當注意的問題,卻又說“畫不過意思而已”。結合黃公望的藝術來看,會發現這句話十分貼切。黃公望作畫常常不是一揮而就,而是要反復修改,有時一張畫要歷時幾年才完成。這種繪畫習慣成了他畫面中的不確定因素,使得畫面保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意味。其繪畫創作,是建立在不確定的狀態下不斷地樹立明確的形象再不斷使其模糊的過程。
混沌不分明也是黃公望立畫的精神立足點,在這個立足點上他真正超脫那些煩惱,進入自由的物我兩忘之境。黃公望說的“畫不過意思而已”,又何止是“畫不過意思而已”,“畫”成了一個代稱,他所要言說的是“一切都不過意思而已”的透徹境界。而黃公望可以這樣進行創作的原因,應是受到自身藝術觀的影響。
黃公望在《寫山水訣》中說,“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為上”。他認為畫可改可救,自然出手“輕松隨意”,內心更為從容,這也是他可以將一張畫歷時幾年完成的心理基石。而這些“可改可救”的痕跡,也反映在他的繪畫之中。他經常會有復筆,錯開原先淡的筆觸,用新的不同質地的筆觸去調整畫面關系,使畫面達到渾然無我的境地。如果說“畫不過意思而已”是黃公望創作的綱領,那么“可改可救”就是他的實踐心路歷程,最后都落在他創造的真山水之上。
黃公望繪畫正是在這樣的“綱領”指導下繪就而成的,他這樣的藝術思想的形成與他晚年隱入全真有很大關系。“全真”的本意就是“去虛妄,存本真”。而縱觀黃公望的山水畫,不同面貌下流露出的“人生三味”,才是畫背后的“意思”。若只在筆墨中追尋,終究陷入形而下的執迷。這里不是要否定從筆墨入手對黃公望的研究,而是強調筆墨之外的黃公望是如何借助這些筆墨來繪寫心中境界的。黃公望“畫不過意思而已”,正是他渾然物我兩忘境界的寫照。
二、黃公望對明清畫家的影響
黃公望在繪畫風格上,崇尚自然,講求寫意。黃公望關注技法造詣,時常會觀察自然景觀,仔細留心風、雪、雷、電、光等自然界的改變,了解季節更替帶來的不同美景,挖掘山間深谷、溪流樹木、泉水的美。對明清時期的山水畫來說,黃公望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一,就創作原理來說,黃公望提出山水畫創作理當靈活多變,畫作的風格需一致和諧,倡導將墨色作為重點,彼此協同。其二,就設色問題而言,提倡淡著墨作為關鍵方式,淺絳法中墨和色彼此對照。其三,通過作品推動明清時期山水畫模式的優化。黃公望向往簡單無邪的心境,這對于明清時期山水畫的發展意義重大。
(一)繪畫意境的影響:以沈周為例
沈周的山水畫法與董源一脈相承,不惑之年沉迷于黃公望的畫作。文征明曾經為沈周的畫題詞,表示他曾經研習過黃公望的畫作,沉溺于此。《沈石田山水冊》里曾收錄了一幅借鑒黃公望風格的作品,畫上題詞:“溪山好處行難盡,風日佳時趣自長;聊寫癡翁醉余筆,坐收煙靄作閑忙。”除此之外,書中還收錄了一幅與黃公望風格相仿的作品,沈周自己在作品上寫道:“畫在大癡境中,詩在大癡境外;恰好百二十年,翻身出世作怪。”沈周曾仿畫過一幅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他在畫卷末尾處寫道:“大癡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設,平生不見多作,作輟凡三年始成,筆跡墨華當與巨然亂真,其自識亦甚惜。”由上述大量題跋可知,沈周非常推崇黃公望。
沈周曾有一幅模仿黃公望的作品《仿黃子久連山夾澗圖》,這幅畫的意境相對柔和、淡然,每一處細節都展現出作者對黃公望的推崇與重視,不管是構圖,還是意境,都與黃公望的風格相似。和《富春山居圖》這一幅出自黃公望的作品相比,兩幅畫之間有許多共同點。首先,二者均為長卷,表達的都是淡然、平和的意境。其次,黃公望的畫作中石頭多用披麻皴,而沈周的仿圖里,大多也是用披麻皴與荷葉皴結合,風格灑脫,更顯隨意。黃公望山頂多畫礬石,沈周在此圖中也是山頂多作礬石。再看山腳,黃公望山腳多畫碎石,而在沈周圖中,山腳也多碎石。沈周的畫作中一列列高低不一的樹木、類似蟹鉗的枝杈,都與黃公望作品中的樹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后來看遠山的畫法,《富春山居圖》與《仿黃子久連山夾澗圖》都用淡墨勾出遠山輪廓,借助淡淡的墨色展現遙遠之地,連綿的山峰讓人覺得隱約可見、琢磨不定,甚至山峰的構架與外觀都大致相同。沈周大多數的畫作里都能見到黃公望的筆法,《魏園雅集圖》里和刀劈斧砍一般的群山外觀和黃公望所畫的《水閣清幽圖》里的山大致相同,用點苔方式點綴石頭。可見,黃公望對沈周的畫作風格影響巨大。
(二)設色技法的影響:以董其昌為例
董其昌把從唐到元的著名山水畫家分為南北兩個派系之說,并且有崇南貶北之意。其中,董其昌對黃公望非常崇拜,將黃公望視為南宗文人畫體系的重要一員。董其昌在《畫旨》中曾表示,“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畫道亦爾。馬遠、夏圭輩,不及元季四大家,觀王叔明倪云林姑蘇懷古詩可知矣”。他還于《畫禪室隨筆》一書里寫道:“余少學子久山水,中復去而為宋人畫,今間一仿子久,亦差近之,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后大成。”
董其昌的一生都極為推崇黃公望的藝術風格,他收藏黃公望的藝術作品多達三十余件,其中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真跡和沈周背臨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都曾被他收藏過。其獲得沈周所繪《富春山居圖》的次年,想起沈周仿黃公望畫作的事情,并為表達對黃公望的崇敬,當時已經古稀之年的董其昌仿了一幅《富春山居圖》,并為這一畫作題詞:“《富春大嶺圖》,黃子久畫卷,在予家,時一仿之,不必盡似,石田亦爾。”此仿卷縱28.5厘米,橫297厘米。整個畫卷中山巒疊嶂,江水圍繞在山旁,村落彼此掩蓋著,樹木蔥蔥郁郁。圖中同樣運用披麻皴,只是變黃公望的長皴為細筆短皴。董其昌甚至給其臨摹的畫作添了色彩,赭色作為底色,在上面增添些許石綠色,用螺青汁綠點綴。此填色模式與黃公望所繪《天池石壁圖》的模式大同小異,讓畫卷靈動明亮,柔軟厚重。這些都得法于黃公望。
明末清初的畫師大多學習董其昌的繪畫理論,受其影響,一時間畫師們爭相模仿黃公望的畫作,研習黃公望的繪畫的風格,如吳振等人。
(三)對繪畫筆法的影響:以“四王”為例
王時敏與王原祁、王翚、王鑒三人共稱為“四王”,他在山水畫方面造詣較高,其著墨蒼勁有力,柔潤秀麗,厚重卻灑脫。年少時,王時敏曾研習董其昌的畫作,之后了解到黃公望的繪畫風格,十分震撼,從那時起就沉心鉆研黃公望的風格。在《仙山樓閣圖》中,王時敏所用的就是研習黃公望筆法所得的繪畫風格,作此圖時,王時敏已過古稀之年,當時為了給好友高堂拜壽,才創作了這樣一幅畫作。畫面中小山重疊,樹木茂盛,溝壑間小河蜿蜒,房屋彼此掩映,水面泛起霧氣,猶如瑤池圣地。王時敏曾作《南山積翠圖》一畫,對下筆的力道極為關注,要求內斂有力,石頭樹木的繪畫方式與黃公望有異曲同工之妙,畫面的灑脫、山頂的點綴,細節之處皆可見黃公望之風格。這幅圖著墨完美,濃淡得當,虛實相合,可看出黃公望的筆法精髓。受黃公望的影響,全圖筆墨蒼潤雄厚,工整細膩,意境幽遠淡雅。
王鑒的臨摹功底十分深厚,基礎也相對扎實,山水畫是他所長。其著墨以烘染為主,擅長華潤的風格,曾研習董其昌的筆法,但是更熱衷于“元四家”的筆法,尤其喜愛黃公望。因此其很多畫作都是模仿黃公望的筆法,像是風格蒼勁的《煙浮遠岫圖》,正是總結黃公望繪畫精髓所得。這幅畫包括遠、中、近三處景色,借助長披麻皴表現了石頭的堅韌、高山的巍峨,畫面物象相互承接,栩栩如生。此畫用筆蒼勁,用墨淡雅,配以赭石、汁綠等色,畫出了山勢的延綿不斷、樹木的蔥郁茂盛,顯示出大自然的勃勃生機,頗有黃公望“山川渾厚,草木華滋”之態。
年少時期,王翚曾拜王鑒為師,學習繪畫,之后臨摹了很多前朝宗師的畫作,其中最喜愛的便是黃公望的畫作。因為喜愛,王翚臨摹了三遍《富春山居圖》,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精進。后來,王翚作《仿黃公望山水圖》一圖,并為其題字:“大癡畫法超凡俗,咫尺山河千里遙。獨有高人趙榮祿,賞伊幽寂近清標。山莊清夏,午睡初起,檢古人法書名畫鑒閱一過,極人間清曠之樂。隨興臨仿,至彌月始竟。”這幅圖是王翚嘔心瀝血之作,他不看畫作,臨摹了原《富春山居圖》,借鑒黃公望一般使用的點苔與披麻皴等方式,下筆有力瀟灑,抓住了黃公望的繪畫精髓。除此圖外,他還臨摹過黃公望的多幅作品。惲南田曾評論王時敏與王翚研習黃公望繪畫風格的行為:“癡翁畫,林壑、位置、云煙、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非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臻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一峰耶,石谷耶,對之將移我情。”
王原祁也表示:“余弱冠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余年矣。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王時敏、王原祁是祖孫關系,二人的繪畫風格都源自黃公望。由于家世良好,王原祁在弱冠之年便有機會見識并模仿黃公望繪畫作品。他一生繪制過很多模仿黃公望風格的畫作,下筆極具黃公望的風格,畫意淡然,引人深思,筆墨深厚。王原祁曾探摹古跡,把二十四幅古跡縮本裝訂成冊,以備出行時方便臨摹,這二十四幅縮本中就包含了黃公望的古跡,可見王原祁對黃公望筆墨格法的誠心學習。
三、后人對黃公望藝術的繼承和發展
黃公望的筆墨語言對明清以來的文人畫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董其昌曾給予其極高的評論,并把黃公望當作南宗一脈山水畫中的領軍人物。董其昌以身作則,把黃公望畫作挺拔俊朗、繁簡有度等風格融入個人風格,還將這種風格傳承給了徒弟王時敏,從而讓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愛黃公望的畫作風格。了解他們的山水圖,不管復雜的構圖,還是簡單、瀟灑的勾皴,墨色的淺淡,處處彰顯出黃公望的風格影響之大。
我國的山水畫必須關注畫中不同物體間的搭配與位置,黃公望的價值恰是其給我國山水畫的物體分布設定了比較健全的模板,且發展出嶄新的黃公望風格,也就是很多畫師口中的“富春樣”。黃公望的風格與觀念對學習山水畫的后輩而言意義重大,之后傳承并將其風格發揚光大的畫家有很多,比如王時敏、沈周等人,從他們的著墨中能夠看到黃公望的觀念與風格,且以其風格為前提,持續促進繪畫技藝的提升,并衍生出許多嶄新的繪畫模式。每一代畫師都持續深化,把我國傳統的山水畫技藝提升至更高的水平,深刻影響了我國明清時期山水畫領域的發展。為此,研究和分析黃公望的理論成果和繪畫實踐有利于認識和借鑒傳統。明清時期的畫師們大多延續這一道路,通過傳承和發展,持續健全我國繪畫的表達方式。其創新性、實踐意義讓我國的傳統畫作由原本的客觀朝著主觀發展,推動了很多主觀情緒明顯、能夠展現江南風格的繪畫風格出現,讓我國的傳統繪畫面貌產生了巨大的改變,讓我國傳統的山水畫迸發出強大的生命力,進入新的發展境地,并領導了中國山水畫今后六七百年的發展。這對開創我國傳統山水畫新風格來說意義重大,具有深刻歷史價值。
身為“元四家”的第一人,黃公望開創了我國山水畫的新局面。黃公望作品中蘊含的藝術性具有較強的召喚性和傳播力,不僅限于元、明、清三朝,也不局限于近現代時期的我國,還突破國家間的壁壘,影響多個國家,成為我國美術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
[1]陳瑞燕,谷雨.黃公望繪畫理論及對明清山水畫創作的影響[J].蘭臺世界,2015(21):140-141.
[2]趙啟斌.從南京博物院部分藏品略論“黃公望畫派”的藝術特征[J].書畫世界,2008(6):4-11.
[3]原秋妮.從設色的角度簡述黃公望的淺絳山水畫[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6.
[4]王元元,徐鴻平.論地域性因素對黃公望山水畫風形成之影響[J].藝術大觀,2020(1):33-35.
[5]魯鵬琳.倪瓚與黃公望山水空間表現的差異性對后世的影響及藝術價值[J].藝術評鑒,2020(8):56-57.
[6]黎斌.清逸蕭淡 以我觀物:從黃公望代表作品看元代山水繪畫風格[J].黑龍江科技信息,2007(8):166.
作者簡介:
岳琛喆,蘇州科技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