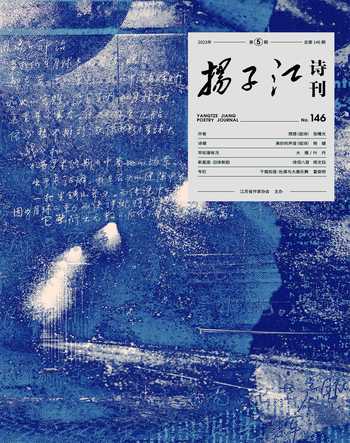美妙的聲音(組詩)
楊鍵
灰色不會變
山里是否有一條河還是只有灰色,
我感覺兩者都有而且同時存在,
灰色不作聲,是籠罩式的,
河水有聲音但不會給你聽到,
兩個都是非常神秘的生者,
你走在其中不會感覺到,
你感覺到了也很難說出來。
灰色里有一切顏色,
很干凈,沒法窮盡。
成為灰色的目的沒別的
就是向后退,一直退,
退到人跡罕至的時間深處,
重新成為幽僻的山水,
又是你眼前的山水。
但你很難進入那幽僻的山水,
你只能看見眼前的山水。
因為你無法進入幽僻的山水,
灰色一直在那里,
它有讓你進入幽僻山水的使命,
因為灰色是一座橋。
少年時代
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事情,
現在講出來無人相信,
那還是他做放牛娃的時候,
他大概七八歲的樣子,
有一天他放牛進了山溝,
一邊放牛一邊睡著了,
等他醒來睜開眼的時候,
看見遠處一條大蟒蛇慢慢飛起來,
飛到天空的最高處,
駕著一朵白云消失在藍天深處了。
他親眼見到了一條蛇脫去了蛇身,
無法不相信對困境的轉化,
時有發生,
在少年時代。
送葬
天氣陰冷,
正適合送葬,
田埂上三十來人一字排開,
小孩子活蹦亂跳,
跑在最前面,
稀稀落落三十來人,
也能送出浩蕩凄清的感覺。
隊伍很長時間好像走不動,
忽然就到了墳前,
把那一小袋安頓好就結束了。
送葬雖然結束了,
但送葬的隊伍依然在行進,
有目的地,
但是并不到達。
背景已經足夠陰冷,
腳底也有足夠的稀泥,
但是隊伍依然在行進,
一刻不停。
當所有的人都散了,
一列送葬的隊伍還在田埂上行進。
我感覺到冷,
于是鉆進了被窩,
但也能看見那墳墓,
那在家門口都能看見的墳墓竟有一種遠意。
兩棵樹
冬天是最適合畫素描的季節,
有兩棵樹正在用心畫著。
一棵是老榆樹,年逾古稀,
瘦瘦高高,把自己十分精細地畫在路邊。
沒有一根枝條被它茍且放過。
另一棵是老柳樹,死去多年了,
細弱的枝條仍然披拂下來,
它把自己感人地畫在了水邊。
哪里是它們最初的第一筆?
哪里又是它們結尾的最后一筆?
兩個人在樓上爭論其中奧秘。
但兩個人不是兩棵樹,
兩棵樹又不是兩個人,
這究竟是幸運還是遺憾?
美妙的聲音
我病了,
躺在床上
聽五歲的兒子在樓下數數,
那聲音那么好聽,
好像破天荒生平第一次聽數數,
第一次聽,
人的喊叫,人的奔跑,
從來沒有想過,
天籟就是從樓下,
我兒子的喊叫奔跑里發出,
不是從別處。
山樹
當我站在院子里,
看山上的樹,
感到嚴酷的生長正在發生,
風吹樹木,發出浪濤的聲音,
就是沒有人的聲音,
這就是它們如此之美的要義,
一棵棵,站在斜坡上,
就像在平地上一個樣,
死了一次或多次才能這么美,
還得看不出它們曾經死過。
它們的語言就是沒有語言,
因此我們很難說清楚它們。
它們沒有出發更無歸來,
它們打的是原地戰,
有些精瘦的樹長得極為復雜,
其樹枝的轉折穿插非一般巧手可以再現,
但無論是大樹還是小樹老樹還是死樹
全都在一種巋然不動的氛圍里,
灰灰的木然的調子,
外表很蕭瑟可是巋然不動,
無數的樹木就長在這種巋然不動里,
或者說,巋然不動長出了這些樹木。
不時有幾只鳥飛出來,
巋然被打破,瞬間又閉合了,
長久地存在但是悄無聲息。
在陽臺上
媽媽讓我坐在她身邊,
聽她講,
江邊砸過的礦石,
廢品站拉過的報紙,
火車上卸下的煤炭。
她讓我坐在她身邊,
聽雨聲,
在耳邊沙沙沙。
媽媽說過的這些事,
很快就變成了雨聲。
雖然在下雨,
但媽媽看上去像衰老的蠶,
已經很透明了。
她最近總是說起她小時候常常去的村里的廟,
說她小時候聽著那廟里的木魚聲睡得很香,
那老和尚愛吃臭咸菜,
說上會兒她就停下來,
聽著雨聲,
在耳邊沙沙沙。
媽媽說過的小時候的寺廟,
很快就變成了雨聲。
結尾
在我如煙的靈魂深處,
一高一低走著我們母子二人,
我是那樣小,牽著媽媽的衣袖。
我倆都是黑白的也是彩色的。
在我如煙的靈魂深處。
在我如煙的靈魂深處,
一高一低走著我們母子二人,
媽媽是那樣小,我牽著老了的媽媽,
去尋找我們的歸處,
在我如煙的靈魂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