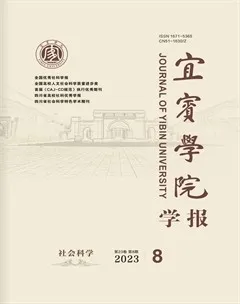論“內容”的著作權法歸屬
郝江鋒
(澳門科技大學 法學院,中國 澳門 999078)
知識產權法作為民事規范的具體內容,與民事原則有著一脈相承的特征。我國侵權行為法規定了一般侵權中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1)損害事實:要求損害事實的“客觀”存在。即侵權人的侵權行為造成了他人人身或財產權益的損失。(2)行為特征:行為具有違法性,即凡是違反了法律禁止性或命令性規定的行為才應承擔法律責任。此處的違法行為有作為和不作為兩種情形。有些行為事實上侵犯了他人權利,由于其存在法律規定的阻卻其違法性的情形,如職務授權行為、正當防衛行為、緊急避險行為,不具有違法性。(3)因果關系: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即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系。(4)行為人有過錯,即行為人存在故意或者過失的錯誤,當然也排除其他特殊責任形式。只有當四個條件均具備時,行為人才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具體到知識產權法領域的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仍然延續著民事侵權認定的規制路徑。在知識產權侵權歸責中,同樣需要滿足損害事實、行為特征、因果關系以及行為人過錯的條件。知識產權是在物質基礎滿足生存條件后的精神產出,因而知識產權客體存在非實體性(也作無形性)特征,其流動領域也帶有大量的經濟活動特征。由于其非實體性的特征導致對其侵權的行為存在自身的特殊性,排除了實體的物質層面的器具破壞、功能減損,更多的是帶來人身以及財產方面的損害。諸如對人身層面的發表權、署名權的侵害,以及經濟層面的復制權、改編權、注釋權的侵害。所以,對于無形的知識產權客體的侵害,不能沿用對傳統的有體物的歸責方式來規范,立法者通過對侵權四要件的變通,完成了從有體物的要件式規則到無體物的“接觸+實質性相似”規則的轉化,即存在損害事實,把損害行為與因果關系調整為需要行為人對知識產品有接觸的行為要件,同時有爭議的知識產權客體達到了實質性相似的程度,才可能被認定為是侵權。
一、“接觸+實質性相似”規則
之所以“接觸+實質性相似”作為判定侵權的核心要件,是因為在侵權判定要件中“主體條件”與“損害事實”屬于“事實層面”,不存在價值判斷以及判斷方法的技術性問題。不論是從正面來看,事件內部的涉及人員來作判斷,抑或反向的事件外部的第三視角,其主體資格與損害事實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即主體是否具有民事能力以及免責事由,或者損害事實是否已經存在等,所以該內容的判斷誤區相對較少。但是對于“接觸+實質性相似”而言,兩個法學詞匯本身即帶有高度的抽象特征與不確定性:何為接觸?何為實質性相似?達到如何的程度即認定為接觸以及實質性相似?心理學概念上的“潛意抄襲”算“抄襲”嗎?作品的哪些內容需要通過對“復制”行為的控制以實現保護?以上問題不一而足。
(一)關于“接觸”
1.詞匯本身。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作為漢語詞匯的法學用語“接觸”有著高度的凝練特征以及豐富的法學內涵。接觸,在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為:①挨上;碰著②(人跟人)接近并發生交往或沖突。在法學領域中的接觸概念則被解釋為行為主體是否對在先作品有過看、聽、觸的行為。其中,這里的“接觸”行為僅考慮事實上的接觸,對于心理層面的幻想,對于非法途徑的獲得以及合法途徑的轉述描繪等不做探究。實際上,判定規則對“接觸”的要求是考察行為人的主觀心理,即通過行為的表現來推測心理,雖說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表達上高度相似的耦合也并非不可能。所以對“接觸”的探討有必要延伸到對法學以及司法實踐的高度進行理解。
2.事實與價值。學習法學專業的第一要務便是明晰客觀事實與價值判斷的區別,具象司法活動中同樣如此。從利益分配論的視角來看,利益判定的終極現場——法庭審理中,最重要的事項是舉證質證階段。法官作為客觀判斷的第三方,不在事發現場,也不可能從頭到尾地經歷整個事件。因此對于事件本身的判斷是基于證據,即在訴訟過程中,法官通過雙方對證據的出示與檢驗,盡可能推測并還原事實的真相,借助邏輯判斷、第三方客觀的角度和法律所賦予的職權對案件進行審理裁判。也就是說,出于公平原則與客觀事實,法官也只能通過出現在庭審中的證據盡可能推理推導出實施的真相,至于“真相”是否為真,我們已經無從得知。
3.接觸程度。人對事物的認識存在認知速度的差別,對接觸的程度以及接觸作品后的理解程度也有所差異。結合法律是對日常生活的規范來理解,瞥一眼是接觸,拿捏著細細把玩也是接觸;偷瞄片刻是接觸,把作品內容詳細記錄學習也是接觸。因而從結果論的視角出發,泄露商業秘密的事實不以行為人對商業秘密的理解記錄程度而改變;同樣的,侵權判定規則:“接觸+實質性相似”同樣不以行為人對在先知識產品的接觸程度有所變化。因此對于上文以及個別學者所提到的“潛意抄襲”是否可以作為抗辯,就目前來看,筆者以為“潛意”本身即為接觸的一種,不能作為抗辯理由來免除侵權責任。當然,從法律規范的影響與性惡論角度來看,“潛意抄襲”的否定難度極大,任何涉及“接觸+實質性相似”規則的侵權均可被其否定,進而對知識產權制度產生根本性的沖擊。
4.接觸本身。信息傳播是信息(information)的根本特征,信息產生的目的就是要進行傳播。而對于信息傳播過程中的“接觸”則成為信息傳遞過程的必然經歷。人,作為信息的動物,從物質、能量到信息,當然需要與外界進行交流。而“接觸”也成為人之所以進化為人的生物特征,可以說是基本人權,是天賦人權,因此接觸本身是不應也不能禁止的。因而在司法判斷中,在耦合式的侵權判定規則中,實質性相似成為判定侵權與否的核心因素。而回顧接觸本身,信息的傳遞過程構成了巨大的信息網絡,如分子運動般把信息傳遞到信息網的各個角落。另外,接觸這一客觀行為,取證存在著巨大的難度。接觸是對知識產品的信息交換,由于知識產品的無形性特征導致接觸本身同樣也帶有非實體的屬性。在“瓊瑤于正案”中,于正方對瓊瑤《梅花烙》的接觸是自認的[1]。那么實踐中關于接觸的判斷,也需要由法庭結合案件事實對舉證責任進行分配。
“接觸”作為高度凝練的法學詞匯和侵權規則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體現,不論是對“接觸”本身的內涵理解,抑或是對“接觸程度”的理解分析,仍然有著十分的必要。對“接觸”的事實判斷僅做行為的考察,不做感知層面程度的探究,因而潛意抄襲不能作為抗辯理解。
(二)關于實質性相似
所謂“實質性相似”,其內涵為侵權作品復制或部分復制了原作品的獨創性部分,因而造成了涉嫌侵權作品與在先作品具有同一性[2]。此項理論是認定“侵害民事權益”這一侵權責任的知識產權成立要件的前提。既然在司法實踐中接觸作為較為隱匿的行為難以舉證,那么實質性相似就成為案件審理的核心。
在實質性相似中,“實質性”作為“相似”的修飾詞表明了對相似程度的要求。既然存在“實質性”,當然存在與之對應的“初步性”以及“模糊區”等概念[3],即描述在爭議作品之間,作品相似程度僅達到初步性相似或者介于彼此的模糊程度。法學,作為傳統的社會科學,缺乏定量的分析,那么對于“初步性”與“實質性”之間的界限似乎并不明確。而從知識產權侵權判定規則來看,初步性相似并非侵權判定的構成要件,在學理上的分析是為了對“實質性相似”進行更為透徹地理解。
1.實質性相似與獨創性問題。首先,獨創性是一個漢語詞語,也稱原創性或初創性,是指一部作品經獨立創作而具有的原創性。英文中獨創性為originality,原意為原始創造、源頭創作的意思。而在中文中,獨創性可以分解為“獨”與“創”,可文義解釋其為主體單獨、不受外界影響以及對物質世界的改進、創造。質言之,一部作品只要不是對一部已有作品的完全的或實質的模仿,而是作者獨立構思的產物,就可以視為具有獨創性。其理論層面可抽象為:(1)是否由作者獨立創作完成,(2)對表達的安排是否體現了作者的選擇、判斷。由此觀之,獨創性概念是從作品產生的角度來闡釋的,而實質性相似概念則是演化自知識產權侵權判定[4],即作品外部的判斷角度。
2.實質性相似的“量”的問題。知識產權法作為調整社會因創造、使用和保護智力成果而產生的法律關系,以及在確認、保護與行使智力成果所有人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必然存在著大量的文理學科交叉現象[5]。以實用工程技術科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理工學科,其特征必然包含高度確定性的定量分析。受限于文科定性分析的法學與高度精確的理工科學之結合成為了一個重大難點。數學邏輯的裨益在于將無法解決的問題轉化分解為可以解決的問題,所以至少可以參考同類涉及創造性標準的規定:(1)在畢業季,高校的論文審查中,通常以20%為界限,相似度超過20%的論文應當修改后進行答辯。(2)在專利實質性審查時,倘若存在新專利包含于在先專利的情形,則駁回該專利申請,但具體包含的數量有多少并未提及。需要解釋的是,在學術規范的論文查重中,被檢測的論文需要與所有在先論文、報紙、網絡文章甚至境外文章進行比對,范圍之廣令人咋舌;而專利權申請中,被比對的專利要素僅需要與相關領域的近似專利進行比對。所以實質性相似的量的問題,仍需要在日后的研究中進行深化。
3.實質性相似質的問題。“質”,顧名思義,對在先作品的復制,應當是獨創性較高的部分,或者爭議作品之間相似的部分,應當是高質量的模仿,而非貶損或者改劣。對于復制部分的創作水平判斷,是實質性相似與初步性相似的關鍵;而對于復制模仿水平的判斷,則是“內容”水平的分析,這也是下文中“內容”歸屬于表達的理由之一。關于實質性相似質的判斷,在文學與藝術領域適用較多。典型如“瓊瑤于正案”,該案中法官羅列的相似性理由[6]包括核心道具、人物設定、劇情線以及劇情之間的起承轉合等。此案中,法院經庭審認為于正《宮鎖連城》(簡稱《宮》)構成與瓊瑤《梅花烙》(簡稱《梅》)構成實質性相似,《宮》侵犯了《梅》著作權中的改編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也就是說,“內容”部分也屬于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進而需要對作品侵權判定的邏輯前提——思想表達二分法進行重新解釋。
二、思想表達二分法
(一)思想表達二分法的內涵釋義
思想表達二分法是個舶來品,《TRIPS 協定》第9 條第二款規定:“版權的保護僅延伸至表達方式,而不延伸至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數學概念本身。在著作權法中,“思想與表達二分法”是一項重要原則,該原則將作品分為思想與表達兩方面,著作權法只保護對于思想觀念的獨創性表達,而不保護思想觀念本身。美國1976 年《版權法》第102條(b)規定: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論作者在作品中是以何種方式加以描述、表達、展示或顯現的,對原創作品的版權保護都不擴及作品中的一切屬于想法、程序、過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及發現的部分。
從經濟學領域來看,此原則有著非常清晰的解釋。在經濟學視野中,理性人假設是最基本的擬制之一。在理性人主體下,思想的發現者對思想有著法理上控制的正當性,不論是出于經濟追求抑或社會追求,發現者可以通過自行或委托公力救濟的方法實現對各種利益的獲取與保護。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已經論證人類發展的有其偶然性與必然性,對于其中的必然性,發現者可以“一招鮮,吃遍天”。不僅如此,該理念與思想的應用都需要經過發現者的授權,其中必然會有大量的資源浪費,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反而帶有巨大的副作用。法作為平衡的藝術,是在利益的保護與調整中做到動態平衡,不能一味地保護權利人,同時也應當為后來者留下充分的探索空間與適用范圍,這也是知識產權相關法律中合理使用與權力限制的經濟學邏輯[7]。另外,在對思想的適用方面,從保護的成本角度也可以作出很好的解釋。倘若按照思想受保護的邏輯下,人類社會有著巨大的適用環境與實施主體,不論是公力救濟或是私力救濟,僅在權利適用的發現環節便存在著巨大經濟成本,更無論鑒別、救濟過程了。所以從哲學層面來歸納,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相應的上層建筑對物質基礎有反作用。先進的意識可以指導推動社會發展,而落后的意識只會起反作用。
法是調整人類社會規范,是對現實世界的平衡。法不處罰思想,“追究傾向的法律不僅要懲罰我所做的,而且要懲罰我在行動以外所想的”[8]是非法的。所以法律對社會的規范是停留在客觀層面,對于捉摸不定的,無法相對確定理解的事物不做規范,這也是為什么著作權法對作品的規定有“一定形式表現的智力成果”的要求。那么“內容”①在思想表達的安置則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二)“內容”的提出
我國著作權法所規定的權利內容中有“改編權”“攝制權”以及“翻譯權”等權利,按此羅列方式的立法思路進行設置條文有利于社會實踐的具體應用,卻無法回避一個問題:即客觀形式上的不同與主觀內容近似的問題。具體在拋開思想之外的表達中,不同形式下的作品之間對于作品的思路、個別獨創性表達、陳列安排以及其他內容的“改編”或稱之為“挪用”,對于此類行為該如何規制。
另外,“內容”的存在必要性是對分類問題的一個梳理。就“分類”而言,是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分別歸類。分類是對事物研究的開始[9],區別于其他研究,分類在實證科學與關乎生命健康的醫學中尤為明顯[10]。因而對概念分類的研究實際上代表了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路徑的選擇[11]。因而在“思想”與“表達”的分割中,我們是否在對保護對象的劃界問題中完成了足夠精細的析離,關于這個問題的界限是否足夠清晰。換句話說,在“思想”和“表達”之間是否還有空白地帶需要進一步探索,此即本文所論述的重點——內容。而之所以選擇“內容”作為論述的重點,即因為“內容”本身是人腦對信息處理后主觀的理解,是生物意識的體現之一,因而在接下來的探討中將作“內容”融于現行理論體系的試探以及另起爐灶的嘗試。
(三)內容的思想歸納試探
歸納于思想表達二分法的“思想”是法學的高度凝練結果,“思想”內涵豐富,字面解釋上包含思想、思路、觀念、構思、概念、原則等,結合知識產權法與社會發展的妥協平衡等,思想的解釋應該采取廣義理解,即除了上述包含項以外,還有客觀事實、科學發現、創意、管理程序、技術思路、工藝和方法等項。
初看“思想”一詞,似乎并無“內容”部分,那么內容是否“應該”或者說“可以”安置在“思想”部分?
內容,從文義解釋可以被理解為:1.物件里面所包容的東西。這條解釋是從物理層面來闡述的。2.事物內部所含的實質或意義。本條解釋含有法學層面的蘊意,即內容可以被理解為是作品的實質或意義。3.哲學名詞,指事物內在因素的總和,與“形式”相對[12]。世界上任何事物沒有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二者互為依賴②。此條解釋是內容的高度概括,對思想與表達的分割產生沖擊。內在因素的綜合即從元素主義出發,將事物機械地分割為各類與各個元素的集合體,因而可以將上文提及的視聽作品中“人物設定、劇情線、核心道具”等元素理解為“內容”,這般也是雙方主張將“內容”歸納在“思想”部分的主要原因。另外,內容本身區別于客觀形式的表達。對于“表達”,不論是視覺、聽覺,平面或是立體的呈現,均是現實的客觀的,不帶有人的個性化的特征;相反,內容的判斷則帶有明顯的個性化表現,在“瓊瑤于正案”中,對劇情線、核心道具以及人物的設定和情感的表達,不同的人當然的會有不同的理解,畢竟“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法律是要在不確定與確定性中實現相對確定的衡平[13],實現對創作者權利的保護。那么結合內容的不確定性特征,思想(非客觀)與表達(客觀)的特征來看,內容似乎可以歸結到“思想”部分且此理解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四)內容的表達歸納試探
歸納于思想表達二分法的“表達”同樣是法學的高度凝練結果。據詞典釋義,表達(expression)是將思維所得的成果用語言等方式反映出來的一種行為。具象在知識產權領域,表達是將智力成果傳播給外界的行為,以交際、傳播為目的,以物、事、情、理為內容,以語言為工具,以聽者、讀者為接收對象。那么表達的形式需要一定的載體,王遷教授曾撰文專門討論現場直播表現形式的“固定”[14]。也就是說,表達,作為司法判斷的對象應該具有現實客觀性特征,可以被普通民事主體所大致無差別地認識、判斷。
內容,作為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的保護對象,支持者認為其理應歸屬于思想表達二分法中的“表達”部分。首先,思想表達二分法的劃定即為對思想部分不做保護,而表達部分才是保護的對象;其次,將內容歸入思想部分會陷入理論矛盾的境地,倘若對“思想”部分不做保護,那歸入思想部分的內容則必然帶來理論無法自洽的境地;最后,將內容歸入表達部分,僅需要對“表達”進行擴張解釋,在立法滯后性的背景下可以通過靈活的司法解釋工具實現對內容的保護。既實現對作者權利的保障,又完成了對法律規范中“注釋權、改編權”的保護,同時完成了作者權益與社會利益的協調。
(五)“內容”設立的解釋標準
如果將“內容”在形式上得到司法實踐的承認則需要對思想和表達進行法學方法上的重新解釋。也就是說,在思想和表達之間,是否存在一個可被稱之為“內容”的中間地帶,猶如黑色白色之間存在灰色這一客觀色彩。或是出于保護法學體系的穩定性,可以將事實上存在的“內容”歸納到“思想”或者“表達”。
在現行法學研究體系中,如果將“內容”解釋到思想或表達任何一個部分,都有擴大“月暈輪”解釋的嫌疑,因而關于“內容”的安置,筆者傾向于可以單獨設立“內容”的保護部分,但不排除將內容解釋入“思想”或者“表達”。
倘若設立“內容”的保護部分,對于“思想”與“表達”的解釋則應當以嚴格標準進行理解,即思想的涵蓋范圍包含作品的主題與主旨、展示的價值、呈現的原則以及精神等;對“表達”的理解,即表達的涵蓋范圍包含作品的客觀呈現,包括聽覺內容、視覺內容、觸覺內容以及其他人類對信息的感知。而內容則是需要一般自然人對輸入信息的有意識的理解后所產生的信息稱之為內容,具體包含“整體觀感法”中所談到的感覺、情感波動、劇情線索以及高度概括的“思想”與具體呈現的“表達”所不包含的內容,即人類主觀能動性所產生的對信息加工的結果,統一稱之為內容。如此即可實現對現存作品保護邏輯的圓滿,同時可以為司法實踐提供一定的裁判理論,而無需利用司法解釋或者裁判說理。當然也可以通過解釋的方法,將“內容”解釋到“思想”或者“表達”,以最大限度的實現對作品中“模糊區”的保護。
三、內容與思想表達的并列構想
(一)內容保護的現實意義
作為創作者思想體現的內容,凝結著現實且等價的勞動。人人生而平等不能僅停留在口號上,現實中的勞動同樣應當是平等的,勞動的種類千差萬別,勞動的效率各有不同,但仍然是等價的平等的。就內容而言,內容的主題選擇、編排方式與呈現、核心道具與人物設定甚至是作品內詞句的表達,無不是創作者的精心構思。
矛盾是運動發展的,事物也在不斷變化著。從文字作品形式的小說改編為視聽作品,其主要的矛盾便從文字的表達轉化為了視覺與聽覺以及綜合內容的感知藝術。改編權作為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權種之一,其保護理念的背后便是矛盾的運動規律。具體而言,文字作品是通過文字的描述來實現對內容的表達,其核心造詣在于作者對文字拿捏以及事物特征的表達。其典型侵權模式類似學術規范系統的“查重”功能,此篇“復制”了多少彼篇的段落或者字樣等。相反,就同樣的“邊塞”和“思鄉”主題來看,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涼州詞》,與段奕宏飾演的龍團長:“走啊,我帶你們回家!”由于不是兩組品的跨度之大以及該劇并非改編自《涼州詞》,其“表達”當然是不同的。感受層面,《涼州詞》是一首四言詩歌,并無圖像畫面的固定,也就是說受眾在讀罷后對于作品“內容”的想象力不受限制,這也是文學給讀著留下充分想象空間的魅力③。相反,視聽作品通過視覺、聽覺以及其他感知途徑來表達作品內容的方式,從表達方式上限制了受眾的想象力。談到豬八戒,我們腦海中浮現的多是馬德華老師所塑造的憨態可掬的家豬形象,但原著中對豬八戒的描寫卻并非影視演繹的那般可愛④,甚至不是畫面呈現的白皮“家豬”,而是“黑毛野豬帶獠牙”形象⑤。那么結合現實的判例來看,“瓊瑤于正案”中,瓊瑤于2004 年創作了文字作品《梅花烙》,于1993 年改編并完成攝制的《梅花烙》(又稱“梅花三弄”);在2014 年上映作為編劇人的于正的《宮鎖連城》,同年瓊瑤訴之侵犯改編權;2014 年12 月25 日,北京市三中院判決《宮鎖連城》侵犯了《梅花烙》的改編權,認定其人物關系及情節來源于《梅花烙》,令其停止傳播,賠償原告500 萬元。也就是說,作為復雜程度較高、制作難度較大的綜合作品,其各個“元素”部件都應當對獨創性保持應有的高度。類比到專利制度中,復雜程度較高的汽車作品,汽車的外觀設計存在專利,汽車內部的發動機也有專利。在視聽作品中,作為伴奏的音樂作品不能侵權,作為表達的視覺畫面不能侵權,作為內容呈現的劇情、人物、道具也不能侵權。而在文字作品內部,直觀侵權的文字復制是最容易識別的方式。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進步以及侵權方式的多樣化,“洗稿”活動亦粉墨登場。由此觀之,文字作品之間的侵權停留在確定性較高的文字層面,而跨種類作品之間的侵權類型則是紛繁復雜且作品間聯系盤根錯節,對其之間爭議的厘清需要裁判者殫智竭力方可。
(二)內容設定的理論協調
在判斷作品實質性相似的法學方法中,“抽象分離法”(亦稱“抽象過濾比較法”)是對內容部分較為接近的方法。抽象分離法首先將作品中屬于思想的抽象部分抽離,再過濾掉爭議作品中相同但又屬于公共領域的部分,最后將爭議作品剩下部分結合獨創性要求判斷是否達到實質性相似。其中,“抽象”和“過濾”正是對思想和表達之間的界線劃分,“比較”便是對兩者之間相似性的認定。
有學者認為抽象分離法是思想表達二分法適用的重要方法,但筆者認為恰恰是抽象分離法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內容”部分回歸著作權法的必要。
在“瓊瑤于正案”中,有學者認為非文字性作品元素主要表現為小說或劇本中的人物關系、故事情節以及作品結構,這些都是文學作品創作過程中極為重要的思想發光點,倘若著作權法一味將其排除在外,勢必會影響著作權人的積極創作[15]。因此,對于單純的人物關系和故事情節,著作權法不應給予保護。比如瓊瑤于正案中認定侵權成立的9個故事情節(橋段),如“偷龍轉鳳”“鐘情饋贈,私訂終身”等情節,可以說是愛情古裝劇里面常用的橋段,不應該受到著作權的保護。但實際上,北京三中院恰恰是依據此9 個故事情節以及人物設定、角色關系以及矛盾沖突的劇情線進行認定的[16],也就是通過通俗意義上的“內容”。不僅如此,周靜(筆名秦簡)的《錦繡未央》抄襲案12 名作家的16 部作品,2019 年6 月20 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依法對《錦繡未央》小說涉嫌抄襲11 案進行一審宣判,法院認定《錦繡未央》侵權成立,其中網絡版270 萬字左右的《錦繡未央》被判定共侵犯來自12位作家的16部作品共11.4萬字,侵權語句共計763處(句),侵權情節共計21處[17]。
從司法審判來說,以上兩案的審判也形成了寶貴的裁判思路。有關法院采用了“相同或實質性相似”標準,將《錦繡未央》中被指控的侵權語句、背景設置、出場安排、矛盾沖突和具體的情節設計,與權利作品進行比對,具體評判是否構成了侵害。這樣評判標準,無疑是對之前“思想表達二分法”和“接觸+實質性相似”等標準的切實補充。雖然我國是成文法國家,但判例仍有著不可忽視的力量,當然也提供了可貴的借鑒,有利于在類似案件中作出對作品保護程度較高的判決。
相反的,在“李霞訴周梅森案”中,李霞作為一位有著22 年工作經驗的基層政法系統公務員,有著豐富的體制內生活體驗。2010 年,李霞的小說《生死捍衛》在《檢察日報》連載。2017 年,根據周梅森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熱播進而引起廣泛關注。李霞認為《人民的名義》構成對其小說《生死捍衛》的剽竊,具體包括破案線索的推進及邏輯編排、角色設置、人物關系、情節、具體描寫五個方面[18]。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小說的故事結構、故事情節、人物設置及文字描寫中的獨創性表達可以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當事人舉證證明的被訴侵權作品與原作品在非獨創性表達層面的相似內容不屬于實質性相似的比對范圍”。也就是說“小說的故事結構、故事情節、人物設置及文字描寫中的獨創性表達可以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但是本案中,法院是從反方向來進行判斷的,即“18處人物設置、50處具體情節、78處文字描寫中的獨創性表達層面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并未構成實質性相似”,一共具有多少人物設置、情節和文字描述未有表述,但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反證法在司法領域適用的弊端在于“入罪”與“出罪”的混淆,而這種混淆會明顯的帶有主觀色彩的擴大或者縮小保護范圍。倘若在“瓊瑤于正案”中,審判人員的出發點是爭議作品中的人物設置、情節和文字表述存在一定數量的不同,因而不能認定為實質性相似,進而不構成侵權,想必此種說法必然貽笑大方。相應的,陜西“猴壽案”,任新昌與李中元在對畫作“猴壽”圖的著作權爭議中,李中元創作的《太極猴壽》與任新昌所作《猴壽圖》在內容上均是“猴”與繁體“壽”的巧妙結合,原告任新昌訴稱:“顏色、線條與元素的布局與原作的相似度達90%”,其中李中元畫作與在先作品僅在尾部的擺動和猴頭的角度有所改動,法院認定兩幅作品不構成實質性相似,因而不屬于侵權。但當事法院或許忽略了作品在知識產權法學層面上的多重含義,即“作品”概念包含現實物質層面的畫作,也包括非實體的著作權層面的畫作。在后作品李中元的《太極猴壽》的確是一副新的現實的畫作,而該作品事實上與任新昌的《猴壽圖》的確存在高度的相似,我們不能因為爭議作品在細節上存在些許的改動而忽略了大篇幅的相似[19],已經超過了合理使用的“學習、致敬、借鑒”的范圍,而應該是“抄襲、改劣、照搬、仿冒”等行為。換句話說對于作品相似度的判定上應當由相對寬松的要求轉變為相對嚴格的標準。社會意識與主要矛盾是在不斷運動變化的,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之后,社會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以對處于模糊區的相似作品,其判定應當以有限當事人利益保護為原則,對社會作品貢獻次之。
(三)內容設定的實踐規范
2021年12月,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出臺了《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2021)》(簡稱《審核細則》),在常規規范之外的醒目條款包括,網絡短視頻不得出現如下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社會道德規范的內容:未經授權自行剪切、改編電影、電視劇、網絡影視劇等各類視聽節目及片段的;違規播放國家尚未批準播映的電影、電視劇、網絡影視劇的片段,尚未批準引進的各類境外視聽節目及片段,或已被國家明令禁止的視聽節目及片段的;引誘教唆公眾參與虛擬貨幣“挖礦”交易、炒作的。
除了極具時代特色的“挖礦”內容,其他較為醒目的條款仍然是對視聽作品傳播的規范。其中,未經授權不得自行剪輯、改編電影、電視劇和網絡影視劇的條款,實質上是對“內容”層面的規范。詳細來看,胡戈《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下稱《饅頭》)是對陳凱歌《無極》的剪輯與改編,畫面上幾乎通篇截取自《無極》,內容上的聲音呈現通過胡戈的變聲、截取以及其他方式予以完成,但是內容上的劇情展開、角色再造以及矛盾運動等都有著全新的特色。該惡搞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惡搞”內容,丑化了張柏芝女士飾演的“傾城”與之不良癖好,把陳紅女士飾演的“滿神”塑造成專門打擊他人的惡趣味角色,把真田廣之飾演的“光明”塑造為歸化中國的城管隊長。但由于對劇情內容的全新“改編”演繹,作品之間是否達到“實質性相似”來說則不然,但事實上《饅頭》侵犯了《無極》畫面、劇情內容的改編權。所以我們需要來做一個完整回顧:《饅頭》由于畫面的摘用以及劇情的改編,侵犯了《無極》的改編權;由于《饅頭》的全新劇情、角色設定與角色改編,對《無極》不構成整體上的實質性相似,主要理由是內容上存在較大的差異;《饅頭》和《無極》兩個作品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獨創性。所以在著作權法層面,來自作品內部的獨創性、從作品外部判斷的實質性相似、跨種類的侵權是不同的問題⑥。
《審核細則》的出臺單位是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該組織是注冊于民政部,按自愿結成原則組成的全國性、行業性、非營利性社會組織。也就是說,該組織既不是政府機關,也不是司法系統,其性質為行業協會。按照我國權力領導與分配原則,行業協會不是立法、司法機關,沒有立法權與司法權,其所謂“審核細則”的實質是具有倡議性質的行業自律。雖說該細則不具備司法效力以及其他公權力,但結合歷史特色與社會文化,該細則卻能說明一定的問題:即使不是商業使用的免費表演⑦,“內容”上的剪切、改編與解說在其看來亦不應準。這樣一刀切雖然省事,但卻帶來了實踐上的難題,如此嚴苛的規定是否會很大程度地限制文藝發展,原著作權人難以聯系,縱然沒有惡意的改編與解說,必然存在溝通上的成本;縱然此項規定有其現實的合理性,但行業協會替行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職權,頗有越俎代庖的嫌疑。而相應的,在著作權侵權的種類上,“內容”部分已經被行業和公眾所接受。換句話說,法作為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的意志,當然應該反映特定物質條件下的客體“內容”和“內容”已被社會廣為接受的事實所做出必要的調整。從學理上看,立法論思潮或已被解釋論所替代,但不代表解釋論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雖說社會科學的檢驗不同于自然科學一般的嚴謹與顯著,但事實上對“內容”部分的承認與適用已是板上釘的事實。理論是否為大眾或法學界接受是一方面,實踐是否為人所用則是另一方面。恰如魚不知水鳥不知云,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四、內容在實踐上的適用伸縮
(一)意識活動與意識的自我調整
意識產生于自然篩選。人是生物的一種,凡所生物均為有機物與自然環境的特殊產物。作為自然界的組成部分,對外界環境的刺激做出反應的應激性便是生物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而意識也成為應激特征的自然選擇結果[20]。意識是自然界中人類進化的產物,是對自我認知與環境認知的前提[21]。生物的基本特征在于生存與傳承。相較于生存,自私的基因會將傳承作為優選。為了保障基因的傳承,生物在龐大基數的前提下是依靠“感覺”生存,而非“邏輯”。也就是說,作為生物之一的人類,活下來的動因是基因傳承的自然選擇,活下來的判斷是感覺的自然選擇,真正的“硬傷”都在自然選擇中做了排除⑧。
自然選擇的強大在于它會把不適應當前環境生存的特征篩選出去,而對于其他非致命特征做了保留[22],譬如先天肢體殘缺或者智力障礙的相較于整體來看仍屬于小概率事件,但是自然選擇并未把現代意義下的胖瘦、美丑進行篩選,也就是說所謂“胖瘦美丑”對于生存與傳承來說不是主要矛盾。另外,科學是人類對世界認識的總結,對于存在時代局限的科學其工具與認識水平同樣受到環境與對象的限制。換句話說,科學是階段性的認識工具,對于復雜事物的研究也是存在階段性特征的,因而對于人的意識的認識,當然也存在必然的局限性。這也是司法活動中,對作品實質性相似判定中群體的“整體觀感法”存在的現實依據。
回顧心理認識層面,對于事物變動特征的理論歸納便是“內容”適用的邏輯前提。人是感覺的動物,對人類感覺的研究大多在生理學與心理學領域。德國生理學家E.H.韋伯通過對重量差別感覺的研究發現的一條定律:人類為了適應惡劣的自然環境,不論是對疼痛的體會以及快感的把握,感覺的差別閾限隨原來刺激量的變化而變化,而且表現為一定的規律性(見圖1和圖2),刺激的增量(△X)和原來刺激值(X)的比是一個常數(K),用公式表達即K= △I/I,這個常數叫韋伯常數、韋伯分數或韋伯比率。通過數學推導可得出S=k·logX+C(S為感覺量、K為常數、X為物理量,C是積分常數)。

圖1 刺激量與感覺強度的坐標表達

圖2 刺激強度與新力量的坐標表達

圖3 猴壽案爭議作品對比圖(左:任新昌,右:李中元)
所以通過圖1和圖2的直觀表示可以發現,人類對于刺激的強度與心理的感覺是呈對數模式遞增的。對于常數K的數值,經過實驗發現最小可覺差為1∶40,即在原基礎上的1/40 才能對其感知,而且對于感知的遞增,需要對數增長的刺激才能引起反應。在可以量化的外部感受中質量(重量)與分貝(音量)層面尤其明顯,同樣適用于內部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與快感的神經類藥物的計量,甚至可以延伸到先秦法家商韓對于制度的設計。后續的研究中,德國物理學家、心理物理學創始人G.T.費希納進一步通過數據實驗的方法得出感覺強度按算術級數增長的時候,刺激似乎是以幾何級數增長的,也就是說,人類對于外界的感知更加重視的是比例,而非絕對值。鑒于本文研究對象為法學問題,更為詳細的實驗數據請讀者在場外閱讀。
(二)“內容”法學適用的伸縮
人類對于外界刺激的感知規律被描述為“韋伯定律”,那么作為人組成現實社會以及司法實踐同樣的適用該規律,群體測驗如是,法官判斷亦如是。在視聽作品實質性相似的判定中,聽覺部分的主要表現形式是音樂作品。音樂作品主要是以旋律、節奏與和弦為組合的聽覺藝術,其本身是通過旋律的波動來進行情感的抒發或內容的表達,也就是說,旋律的波動是音樂作品的主要矛盾,而對于和弦、聲調與聲部的選擇,演奏的樂器以及節奏等屬于作品的次要矛盾。
對于普通的音樂作品,對其主要矛盾——旋律的感知也要適用“韋伯定律”,即對于爭議部分的旋律而言,其不同部分與相似部分的比例應該至少達到1∶40,一旦小于這個比例的話則通過“整體觀感法”可能難以識別,需要進行更為細致的“扒譜”來進行比對。同理,對于平面美術作品而言,同樣的需要大于1∶40。陜西“猴壽案”中,原告任新昌訴稱良作品之間顏色、線條與元素的布局與原作的相似度達“90%”,但當事法庭認為此比例不能作認定作品實質性相似的證據,對此學界也頗有爭議。
而對于電視劇《梅花烙》與《宮鎖連城》,兩部劇的整體劇情線存在高度相似的情況。《宮鎖連城》在有關偷換來的男孩、送出去的女孩、公主三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三位主人公的出身背景,社會身份、主從關系、情感交織和變換等故事情節上,都與《梅花烙》完全一致。在故事情節的支線方面,《宮鎖連城》將軍府中的將軍、福晉、側福晉、庶出兒子等相關內容,除了姓名改變以外,人物關系亦與《梅花烙》中的一致。具體來看,偷龍轉鳳的故事情節和基本內容基本相似,被送出去的女孩的職業身份看基本相似,男孩與女孩的關系看基本相似,被送出去的女孩做了使女來看基本相似,在推動劇情變動的核心道具“梅花烙”與紅色胎記存在相似。對于如此大規模的相似存在,已經超過了1∶40 的可識別比例,因而對兩部作品熟悉的受眾均有“抄襲”之感。2015 年,北京高院認定于正《宮鎖連城》侵犯《梅花烙》改編權,爭議自此始有定論。
對于篇幅較短的作品,譬如已審結的“敖包相會與月亮之上案”中,作品《月亮之上》涉嫌對《敖包相會》的6 小結高度相似。此案中的焦點則集中于此6 小節是否達到實質性相似的程度。將“內容”限定在音符與音符的波動上,被告辯稱爭議部分來自蒙古民歌《韓秀英》,但經過法官對此微觀“內容”的辨析,其結果認定為滿足侵權的構成,判令《月亮之上》著作權方進行相應的民事補賠行為[23]。
通過以上或判或和的事實來看,對于爭議作品的相似性問題,人有著靈活的識別基準,通過生理學與統計學的研究說明了人對于自身的感知是比例原則,而非絕對值。在內容方面,對于視聽作品的內容標準當然的要區別于平面美術作品、文字作品等,而“內容”的涵蓋范圍應當包含在“思想”與“表達”之外的部分。將此法做進一步推廣到其他作品范圍,可簡單概述為文學藝術作品在于劇情相關而非客觀上的文字與表現,音樂作品在于旋律的波動而非音符的相同,如此相關不一而足。對于爭議作品而言,人類的生理規律是不自知,人類的認識規律是比例原則,對于作品的詳細探查應當以整體觀感為基礎,在此之上以類似“扒譜”的仔細程度對作品進行比對。
五、內容在著作權法上的歸屬
通過上述分析與探討,我們發現了內容其實在司法運用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對于思想表達二分法來看,內容的法律歸屬似乎缺少理論淵源的支持,但法律是社會存在的能動的反應,對于現實的已被適用的法律元素,尤其是文藝領域的內容,應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對于建設工程施工圖、計算機程序代碼抑或是其他領域的作品,在實質性相似的判定中,內容在法官自由心證的比重則必然會有所下降。但需要澄清的一點,占有比重與存在與否是兩個命題,立法與否與使用情況也是區別于彼此。
其次,人為地割裂作品思想、內容和內容的表達,頗有機械主義與形而上學的不妥。內容是作者通過作品所表達的核心,通過人類能動地對爭議作品的期待值調整進而完成對作品之間實質性相似程度的判別是人類自有的生物機能。在科技相對不成熟時期,作品的種類、制作的工具以及作品的傳播均受到物質條件的限制。而在科技大幅進步的當今,制作方法與技藝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新媒體與計算機生成作品得到了全面的推廣。我們當然不能用一成不變的眼光來看待相對穩定的法律規章,但是對于新生事物的回應理當是法律人所應有的態度。時代是進步的,社會是發展的,與時俱進才是我們對待法律文化與法律現象的應有之義。
最后,知識產權法是相對前沿的一門法律學科,對于前沿知識與變革動因,知識產權法學界相較于其他部門法而言,有著較強的革新動力[24]。人工智能與生成物的著作權問題,元宇宙與社會規范的協調問題以及內容與意識在多種類作品相似性判定的問題上,知識產權人都有著不可回避的前進使命。因此,對于“內容”的著作權法歸屬,對于思想表達二分法原則的再審視以及實質性相似判定規則的新發展,知識產權人應當敢做學科的排頭兵。在文理交叉的學科特點下,在“新文科”建設的時代背景下,適時地回顧當前立法與實踐,進而有力地推動理論的創新,方為知識產權發展的自然之理。
注釋:
① 之所以選擇“內容”一詞做探討,在“瓊瑤訴于正案”中,終審裁判的第六部分、第七部分、第八部分都有談到相關定語的“內容”一詞,在裁判說明中以及其他部分僅提到“構成高度相似”,因而筆者擬采用“內容”進行說明。詳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5)高民(知)終字第1039號。
② 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賴內容更多,并隨著內容的發展而改變。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內容,影響內容,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對內容的發展起有力的促進作用。內容和形式是辯證的統一。
③ 元素主義由心理學中的構造主義所引出,即在心理學中,各個“構造”部分均有負面情緒的傾向,衍生為在著作權作品中,各個元素均應當有與其相應的藝術水準。
④ 原著對豬八戒的描寫:是一條黑胖漢,后來就變作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呆子,腦后又有一溜鬃毛,身體粗糙怕人,頭臉就像個豬的模樣;黑臉短毛,長喙大耳;獠牙鋒利如鋼銼,長嘴張開似火盆。
⑤ 據考證,白豬最早于20世紀50年代從歐洲引入國內,最有名的是丹麥長白豬以及英國的約克夏豬。也就是說,吳承恩描述的豬八戒形象應該是中國本土馴化的獠牙黑豬。
⑥ 著作權侵權、實質性相似、獨創性都是著作權領域的事項,但分屬三個問題。
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24條第九款。
⑧ 譬如恐高癥與恐蛇癥,凡現代人幾乎都有此二癥,因為在遠古時期的人類,“高”與“蛇”通常代表危險,而對此無應激性特征的人大多被自然所篩選,故而現代人幾乎都有恐高癥、恐蛇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