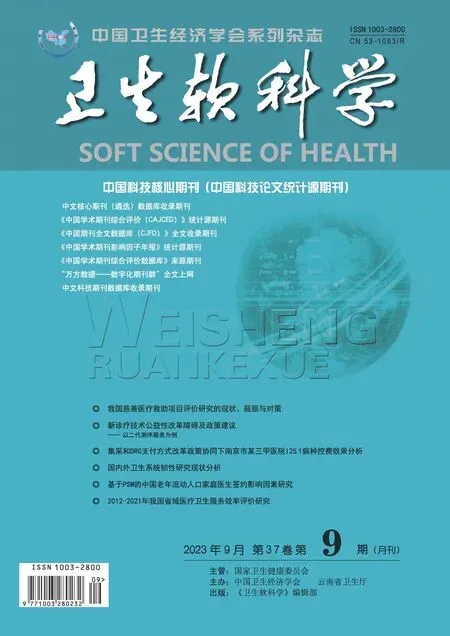基于Andersen行為模型的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及影響因素分析
冉甜甜,吳 爽,2
(1.華北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河北 唐山 063210;2.華北理工大學衛生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河北 唐山 063210)
《“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中提出,開展居家社區養老服務工程,引導日間照料中心等養老服務機構依托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和社區公共服務綜合信息平臺,為老年人提供精準化個性化專業化服務。《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網絡,對推進日間照料中心等居家社區養老服務設施建設作出部署。日間照料中心作為社區居家養老模式下重要的養老設施,可以補齊機構養老的短板,讓老年人可以繼續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保留老年人自身的生活歸屬感和穩定的社交網絡,符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同時老年人能夠有人照料,減輕子女的照料負擔,與他們的經濟能力相適應,成為家庭養老強有力的支撐與補充。然而大力推動日間照料中心發展時,很多農村地區卻出現了場所設施設備閑置、照料中心老人寥寥無幾的狀況,與此同時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1],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億人、占18.70%,其中農村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23.81%、17.72%,比城鎮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鎮總人口的比重分別高出7.99個百分點、6.61個百分點[2]。農村的老齡化水平明顯高于城鎮,在此背景下,研究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對推動日間照料中心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目前對日間照料中心的研究方法比較單一,缺乏理論模型支持,并且調查對象多以城市老年人為主,對農村老年人群體關注較少,本研究基于改進后的安德森模型分析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為科學應對農村老齡化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文以天津市寧河區為調查地點,于2022年9~11月,在寧河區豐臺鎮、板橋鎮、苗莊鎮、俵口鎮等13個鎮進行調研,每鎮內抽取1~2個村,再從各村抽取20~30名60歲以上的老年人作為調查對象,統一培訓調查員,按照知情同意的原則,在征求調查對象的同意后,村委會的協助下,現場調查及填寫問卷。發放問卷520份,共回收問卷490份,有效問卷490份,有效回收率94.23%。
1.2 理論框架
1.2.1 安德森行為模型
為更深層次地歸納、挖掘影響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本研究以ANDERSEN等[3]提出衛生服務利用模型—Andersen 行為模型為理論基礎,國內學者已有少量關于養老意愿方面的研究使用了該模型,適用效果良好,參考以往研究成果[4,5],將可能影響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各類因素作為自變量。根據模型的理論分析框架,將自變量按照三類因素進行劃分,具體為:傾向因素,包括人口學特征、社會結構和養老觀念,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文化程度、居住情況、退休前職業、養老觀念的開放程度;使能因素,包括經濟來源、家庭月收入、子女數量、子女關系、鄰居關系、醫療保險類型、長期護理保險、養老保險類型、家人的態度、步行到日間照料中心的時間;需求因素,包括生活自理能力、慢性病患病種類、生活滿意度、孤獨感(見圖1)。

圖1 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影響因素模型
1.3 統計學方法
將收集的問卷整理后,Excel 建立數據庫,如實錄入數據庫中,利用 SPSS 26.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的描述性分析,利用卡方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歸模型進行多因素分析,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正式調查前對60名老年人進行預調查,預調查完成2周后再次測試,保證問卷具有較好重測信度;問卷在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基礎上,經過專家評估、論證、修改后形成,5名專家評定后內容效度CVI>0.90,表示問卷內容效度較好。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基本情況
調查的490名農村老年人中,男性232名(47.35%)、女性258名(52.65%);60~69歲、70歲以上年齡組分別有170名(34.7%)、320名(65.3%);婚姻狀況中335名(68.37%)老年人有配偶;有子女的老年人457名(93.27%);文化程度為小學及以下者377人(76.94%);387人(78.98%)的老年人是農民,經濟來源為勞動收入及儲蓄的老年人242人(49.39%),老年人患慢病比例高達308人(62.86%);愿意日間照料中心養老的老年人270人(55%),不愿意日間照料中心養老的老年人220人(45%)。
2.2 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單因素分析
按照不同的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將對象分為兩組,采用卡方檢驗比較組間差異。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居住情況、退休前職業、養老觀念的開放程度、家庭月收入、長期護理保險、家人的態度、子女關系、鄰居關系、步行到日間照料中心的時間、慢性病患病種類和生活滿意度在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婚姻狀況(P值=0.291)、經濟來源(P值=0.413)、醫療保險類型(P值=0.751)、養老保險類型(P值=0.411)、子女數量(個)(P值=0.108)、生活自理能力(P值=0.363)、孤獨感(P值=0.128)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單因素分析
2.3 各模型預測概率及擬合優度分析
Hosmer-Lemeshow檢驗結果顯示,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的Cox &Snell R2值分別為0.368、0.562、0.579逐漸接近于1;Nagelkerke R2值分別是0.492、0.752、0.774逐漸接近于1;-2LL分別為449.66、269.29、250.512逐漸變小,說明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逐漸提高,對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解釋能力在逐漸增強,表明整個模型可信度較高。在模型Ⅰ基礎上加入使能因素后,Nagelkerke R2上升增幅較高,在模型Ⅱ基礎上加入需求因素后,解釋上升增幅較小。由此可見,使能因素對本研究影響最大,其中,模型Ⅲ對的擬合優度最好,模型Ⅲ的Nagelkerke R2>0.600,解釋度>60%,表明模型Ⅲ納入的變量對于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預測能力和解釋度最高(見表2)。因此,本研究采用模型Ⅲ進行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

表2 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影響因素各模型的預測概率及擬合優度情況
2.4 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安德森行為模型理論為分析框架,探討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以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作為因變量(愿意=1,不愿意=0),將單因素分析中有意義的傾向因素、使能因素、需求因素所包含的變量篩選出來(P<0.05)作為模型自變量納入模型Ⅲ,對單因素分析中具有統計學意義的14個自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診斷,方差膨脹因子(VIF)均<10(VIFmin=1.063,VIFmax=1.863),表明14個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即可全部納入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養老觀念的開放程度、家人的態度、子女關系、步行到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時間、慢性病患病種數是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3。

表3 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Logistic回歸結果
3 討論
3.1 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一般
天津市寧河區農村普遍文化程度較低,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其中使能因素的影響最大。樣本中,有270位農村老年人表示愿意日間照料中心養老,占55.1%,而其余220位(44.9%)表示不愿意日間照料中心養老,低于2022年西北農村老人市場化居家養老服務的意愿調查情況(74.49%)[6],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天津市近年來提出一系列加快養老服務發展進程的條例,通過政策引導以及資金支持,大力扶植日間照料中心發展取得初步成效;另一方面,說明農村老年人受傳統養老觀念影響較深,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孝道文化和“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相輔相成,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大多數老年人更傾向于宅在家里,子孫繞膝、盡享天倫,所以對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一般。
3.2 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
3.2.1 傾向因素
性別(OR=2.477,P=0.019)是影響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女性老年人對日間照料養老意愿是男性的2.477倍;這與國外學者研究結果一致[7],與唐藝藝、支夢佳[8,9]的研究一致,女性情感細膩,更善于溝通,更傾向于在日間照料中心尋求幫助和支持。
養老觀念的開放程度中越贊同日間照料中心養老的意愿越強烈,與周雪陽[10]的研究結果類似,老年人的養老觀念越開放,老年人自我感覺狀態良好、樂觀豁達,越能認同養老應該借助家庭以外的力量的說法,接受由子女以外的照護人員照護,更愿意嘗試新型養老模式,對日間照料中心的認知度和接受度較高。
3.2.2 使能因素
家人的態度(OR=89.204,P<0.05)是影響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家人贊同日間照料中心養老的老年人是家人不贊同的89.204倍,這與王嫻、孫鵑娟[11,12]研究一致,這可能是因為農村子女多外出打工,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父母,其對老年人使用日間照料服務的理解和支持度增加;同時在中國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老年人選擇養老方式,往往并不是個人全權決定,而是照護與被照護人共同決定,甚至很多時候是由主要照護人決定[13]。
與子女的關系是影響農村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關系良好,節假日均會探望的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低于與子女往來不密切的老年人(OR=0.255,P<0.05)這與張鈺穎、鄭娟[14,15]研究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農村老年人深受“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影響,對日間照料中心帶有抵觸情緒,同時與子女關系越融洽、情感越親密的老年人,獲得的家庭的生活照料、精神陪伴更充足,自然不需要尋求社會服務。
步行到日間照料中心的時間在30~45分鐘和45分鐘以上的老年人比步行時間在15~30分鐘的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意愿更低,分析原因,農村老年人步行時間長,離開熟悉的居住環境,加之老年人對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服務的運作流程缺乏清晰的認識,日間照料中心政策宣傳力度也不夠,使得老年人意愿下降。
3.2.3 需求因素
患有3種及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低于沒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意愿(OR=0.173,P<0.05),這與楊光媚[16]研究結果相似,農村老年人多病共患,受到一定的疾病或功能障礙困擾,日間照料中心對于疾病照護、康復訓練等方面缺乏專業的服務保障,為老年人提供的醫療、康復、護理等規范化和專業化的服務,不能完全顧及到具有較大照護需要的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無法滿足這類老年人的需求。
4 建議
4.1 積極轉變傳統養老觀念,加強日間照料中心宣傳
調查發現,仍有相當一部分老年人對日間照料中心養老知曉率低、認知度低。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作為一種新型的社區居家養老方式,在提升日間照料中心居家養老服務能力的同時,政府應引導人們轉變傳統的養老觀念,加大養老文化宣傳力度,將“尊老、敬老、養老、助老、愛老”宣傳列入鄉鎮新時代文明實踐活動工作中;通過各村微信群、大喇叭小廣播等信息媒體,定期推送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政策與內涵,擴大日間照料中心在老年人及子女等家屬中的知曉率和認可度;從子女方面入手,鼓勵老年人享受幸福的老年生活,通過對子女其進行動員,逐漸形成多樣化的尊老、敬老、愛老的社會風氣,改變固有的“養兒防老”觀念,讓廣大農村老年人及其家人認可社會化養老、市場化養老和專業化養老。
4.2 擴大日間照料中心覆蓋面,服務輻射到更大范圍的老年群體
擴大日間照料中心覆蓋面,增強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服務的可及性。《天津市促進養老服務發展三年行動方案(2019~2021年)》指出,到2021年,提升健康養老服務保障水平,老年人日間照料服務中心增加300個,97%的老年人享受優質便捷居家養老服務目標,這一政策是引導各區擴大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的覆蓋面、推廣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模式的重要舉措。在實施過程中,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的地理位置規劃需要被老年人所感知,老年人步行到日間照料中心時間縮短,使老年人有獲得感;與此同時,日間照料中心養老服務的設置需要在有限資源下統籌協調,對于地理位置毗鄰的村莊可以聯合開展配餐服務,優化各村之間的資源配置,避免由單個村莊提供的資源浪費、成本過高、老年人參與度不高等問題,切實滿足老年人的實際需求。
4.3 拓展醫療護理服務范圍,滿足老年人多樣化養老服務需求
可建立護理等級分類制度,拓展服務范圍,日間照料中心在引入醫療護理專業人員的基礎上提供治療、護理及康復相關的咨詢及指導服務,逐漸開展專業慢性病管理,在保證老年人活動安全的前提下,對本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日間照料服務,減輕其家庭或照料者負擔;為老年人提供預約、就診的“一站式”服務,開展健康教育、醫療衛生知識普及等服務;與日間照料中心有合作的醫保定點醫療機構,可設立“老年人就診服務處”,為老年人提供專門的雙向綠色就診通道,保證日間照料中心能夠將存在醫療服務需求的老年人及時轉移到專業的醫療機構當中,從而為老年人提供醫療、康復、護理等規范化和專業化的服務。
4.4 完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提升家庭疾病風險抵御能力
長期照護險主要是為被保險人在喪失日常生活能力、年老患病或身故時主要提供護理保障和經濟支持。因此擴大長期護理保險在農村地區的覆蓋率,提高在養老方面的投入力度,有利于農村地區的經濟負擔緩解,在最大限度內實現“老有所養”。在對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的實踐經驗進行總結與歸納的前提下,進一步拓寬籌資渠道,精準衡量與評估基本護理服務和資金需求,在此基礎上推動長期照護保險覆蓋面擴大到全體農村居民;同時重視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拓寬籌資途徑,從而維持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穩定運行與發展,提升家庭疾病風險抵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