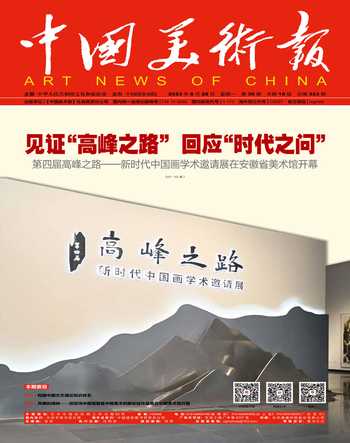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應該積極回應新時代要求
李超德
論及學理性很強的“文藝理論知識體系”構建,實則無法同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討論截然分開,更無法單純抽象談論文藝理論,必須要和門類藝術學研究相結合加以探討。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就更應該從實踐出發,突出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正確理解以作品為先導的“史、論、評”的關系,探究其“三大體系”的歷史脈絡與生成發展。
文藝理論知識體系構建,突出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應該以具有中國“原創性”美術理論知識體系的新構建作為突破口。
我們強調要用正確的文明史觀確立民族文化自信,從不反對汲取世界范圍內人類文明共同優秀成果作為自身成長的養料。然而,在當今“文藝理論知識體系”的構建中,長期以來卻一直被西方學術體系主導的所謂“主流”文藝理論話語所掌控,有些文藝理論家對中國自成體系的文藝理論少有涉獵,對其應時而變的理論思考充耳不聞,熱衷于轉譯西方文藝理論著作。而強調文化自信與具有中國特色“原創性”文藝理論和美術創作理論話語權式微。
中國傳統經典美術理論如何能夠完成現代表達和活化?相關美術理論知識體系如何回應當代美術創作重大理論問題?確實還存在著體系結構松散乏力、重大研究成果鮮見等不足。好的美術作品必須要有優秀的理論和知識體系作為支撐,在作品中既能反映出美術家內在品性和筋骨,又要有觀照人民群眾現實生活的溫度和溫情。因此,以傳統畫論和文論為基礎的中國美術理論知識體系,尤其值得探討其獨創性的理論源流,并完成現代話語的闡釋。
近40多年來,美術研究總結了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美術創作與理論建設的經驗,借鑒了西方較為前沿的“新實用主義哲學”“圖像學”“社會學”“藝術人類學”等學術研究方法,形成了一系列的學術成果。進入了大數據、互聯網和智能化時代,關于美術創作與美術知識理論體系構建又有了新的思維觸角,拓展了新的學術研究視野和知識體系構建基礎。但是,關于中國美術理論知識體系研究,卻少有人從中國“原創性”理論視角出發,探究知識體系的自我生成與構建。我們通常將中國傳統文人美術理解為“詩、書、畫、印”的必備之學,將民間美術看成是勞動人民樸素情感和豐富心靈的外顯,也經常將西方語境中的“文、史、哲”打通,古代文人的學識因此成為通人之學。今天,談論美術理論知識體系,不僅要通古今,還要融中外,既要著重圍繞本民族的文化和美術實踐本體展開思考,又要突破美術理論知識體系固有的認知障礙,將知識體系的構建置于宏闊的社會大背景下加以歸納與總結。如果僅僅以某幅古代繪畫作品之外的“知識生成”做研究,雖然有其積極意義的一面,也豐富了文獻研究的學術內涵,在某些特定的環節,也確實為鑒定古代畫作的真偽提供了不可缺失的文獻支撐,卻只能是從屬性和輔助性的。
作為學術話語體系的頂層設計研究,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不應該僅僅陶醉于古代文論和畫論中傳統士大夫的雅俗觀辨析和哀怨彷徨的自言自語。
中國當代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不僅是闡述美術創作的歷史總結、理想藍圖和理論歸納,還應該是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中國美術創作方法和理論路徑的不斷探索、評價與完善。
如何理解文藝創作以人民為中心?如何聚焦現實美術創作所倡導的內容?藝術的文化主張是什么?藝術的表達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是什么?在西方現今美術創作語境中,以塑造人的美好心靈、表達人的美好生活的寫實主義美術和再現性藝術,被西方主流美術逐漸拋棄。西方當代藝術宣揚的“以人為中心”,著重強調藝術家個人主觀偏狹的小我之“人”,迷茫于藝術界在現行社會中的歷史方位,拒絕于表達現實生活的光明和宏達敘事的美術實踐,遠離高揚民族歷史文化的根脈和魂魄,單純強調以個人眼光看世界,疏離于大時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囿于抒發極端自我的精神迷思。作為時代命題,如何高揚時代精神主旋律?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突出美術創作的“人民性”,我理解必然包含著真正關心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以及把握時代節律、彰顯人文關懷的胸懷和心靈。這是新時代的客觀命題,只有將美術家個人風格和興趣轉化為時代要求的主觀自覺,才能真正體現“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觀。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體悟,既是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的必要組成部分,也作為美術創作如何展現文化自信、自強的深沉底色。我們既要尊重“與古為徒”的學術堅持,認真分析農耕經濟時代中國傳統士大夫繪畫浸潤于詩、書、畫、印的文人之學,又要“與古攜新”,理性分析自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建立在工業革命基礎之上西方文化占領主流文化前沿的歷史、規律與現實;既要看到國際藝術潮流的發展趨勢,又要復觀再現藝術如何在中國大地上尋找滋養生息的土壤。
當代美術理論知識體系的構建,我理解應該是更為開放的系統。
藝術是時代發展的一面鏡子,又是社會變換的縮影。見證這一偉大實踐的每一位參與者,既要認識到美術創作與理論建設的無限性和有限性,又要包容和吸納全世界范圍內先進文化的精華,這是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的必然要求。時代之變一定有時代影響下的精神氣象,美術作品必然是時代精神的真實寫照,必然烙印了時代的典型性話語特征。古代社會時空間隔很長,因此有了“虛空”“思念”和“離愁”,產生了許多經典作品。今天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應該積極回應時代變革中的新要求。特別是年輕人對傳統藝術表達的審美情感確實有陌生感,他們真實的思想情感想表達什么?應該褒揚什么?揭露什么?我們又如何以“守正創新”為原則,加強傳統文化的熏陶,將時代氣象用飽含東方美學精神的現代藝術語言展現出來?
美術創作和理論研究不可否認會強調藝術的自由創造。但是,所謂的創作自由并不可能有超越于特定社會制約的絕對自由,更不能回避社會道義和文化責任。在復雜和多重社會條件下,每一個人都有家國情懷、公序良俗、道德倫理的要求。作為美術家,藝術實踐活動和理論研究時刻蘊含在自律和他律的矛盾之中。美術家的“自律”往往是指美術創作和美術理論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內在邏輯和本體規律,以及美術家在創作和批評過程中對美術規律的依從。而所謂“他律”,我理解則是指美術創作過程中,受到諸如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社會進步等他者因素的影響而產生的約束。美術創作與理論研究的自律和他律,兩者既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又是共同推動當下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的平衡點。
用正確的文明史觀看待美術發展和理論知識體系構建,我們應認識到新時代美術理論知識圖譜必然會有新的理念、新的圖像和新的表達。人的審美情感以人的正常情感為基礎,人的情感又隨著的時代變化而變化,進而發生嬗變。如何在新時代打造新的理論知識體系,為文化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支持,確實是每一位美術理論工作者和創作者的責任。
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仍然要堅持從實踐中來,再回到實踐中去。
應該承認,我們面臨著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主流學術話語和文化滲透的挑戰。我們需要直面世界,用高度的文化智慧和文化理性,強調在全球化時代文化與文化、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融合。“一切過往,皆為序章;所有未來,皆為可待。”必須承認,中國文化發展正處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轉型期這一特殊的社會現實,中西方學術界不同的學術觀點應該互為他者,更應該強調文化與文明的互鑒。學術界既要警惕“從工具到工具”“技術中立”的民族虛無主義惟技術論和泛文化論的身份焦慮,又要避免為談弘揚中國文化精神而唯我獨尊的鴕鳥心態。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的立足點,應該超越一般傳統文人士大夫津津樂道的“雅俗觀”討論,積極吸納全世界優秀民族的文化與文明成果,在與當今藝術界進行廣泛的國際對話與交流中才能實現。
“星辰大海,滄海一粟”。我們既無需為湯因比的“文明交融論”“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而過于樂觀,也不用為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而杞人憂天,更無需為賽義德的“東方學”控訴西方文化霸權無理而沾沾自喜。無論是強調中西方優秀文化的互鑒,還是在和世界當代美術創作與研究的對話和交鋒中真正實現“話語體系”的重生與構建,都需要聚焦于中國的美術理論知識體系如何“吐故納新”,真正打造契合于時代發展的“有為之學”。美術家的責任使命就應該是這個時代的先行者和先覺者,就應該用自己的藝術才華抒寫勞動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偉大時代的華彩樂章。守正與創新互為關系,如何以新的視野、新的狀態,倡導真善美的價值追求,破除傳統美術界固有的門派之見、理論界常見的幫閑游雜狀態,確立新知識體系的科學圖譜,建設美術理論的學術新生態,我想這也是美術理論知識體系構建積極回應新時代要求的最好精神指引。
(作者系蘇州大學卓越人才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蘇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