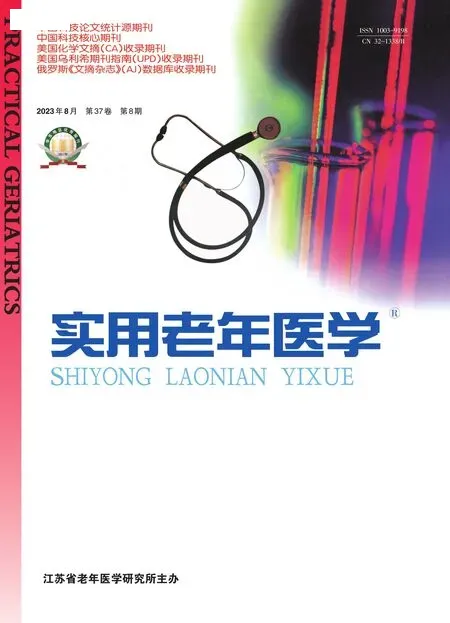以脾切除后血小板增多為首發表現的老年慢性粒細胞白血病1例
張莉 劉思岑 唐艷
慢性粒細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是起源于造血干細胞的骨髓增殖性腫瘤,特征為受累細胞系可見Ph染色體和(或)BCR-ABL融合基因。CML慢性期多數表現為白細胞水平明顯增高和脾大,可伴有血小板水平升高[1]。慢性期病人出現單獨血小板明顯增多臨床較為少見,但也偶見報道[2-5],而脾切除后出現血小板增多較為罕見,因脾切除后血小板增多通常被認為是繼發性血小板增多,常被臨床醫生忽略,未進行骨髓檢查,導致漏診誤診。本文報道1例以脾切除后血小板增多為首發表現的老年CML。
1 病歷資料
病人,女,72歲,因“頭暈、視物模糊2月余,發現血小板增多10余天”于2022年10月8日入院。病人2個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頭暈伴視物模糊,并逐漸加重,10余天前就診于我院眼科,診斷為“白內障”,擬行手術治療,術前血常規檢查發現“血小板增多”,故就診于我科門診,以“血小板增多癥”收入院。既往反復心前區疼痛病史7年余,未曾系統診治;5年前因車禍致肩關節、肋骨骨折及脾破裂,行切開復位內固定術及脾切除術;有甘露醇過敏史;無高血壓、糖尿病史;無煙酒及不良嗜好史。查體:體溫:36.5 ℃;呼吸頻率:18次/min;血壓:120/84 mmHg,一般狀態尚可,左上腹可見約10 cm手術瘢痕,淺表淋巴結不大,心肺聽診未聞及明顯異常。血常規檢查:白細胞總數為16.7×109/L,中性粒細胞計數為9.60×109/L,淋巴細胞計數為6.2×109/L,嗜堿性粒細胞計數為0.26×109/L,紅細胞計數為3.74×1012/L,血紅蛋白含量為117 g/L,血小板計數為868.2×109/L,平均血小板體積為13.1 fL,血小板壓積為1.14%,血小板分布寬度為17.5%。腹部彩超示:膽囊息肉樣變,脾切除術后。骨髓涂片示:增生明顯活躍,G=78.5%、E=14%、G/E=5.61∶1;粒細胞系增生明顯活躍,以中幼以下階段為主,易出現嗜堿性粒細胞;紅細胞系增生活躍,以中晚紅細胞為主,可見巨幼樣改變,成熟紅細胞形態無明顯異常;全片共見巨核細胞超過300個,血小板呈大堆。血涂片示:白細胞總數明顯增多,粒細胞呈核左移,可見嗜堿性粒細胞;血小板呈大片狀、簇狀分布。(骨髓)檢驗診斷:血小板增多,建議進行骨髓增殖性腫瘤(myeloproliferative-neoplasms,MPN)相關檢查。骨髓活檢結果示:骨髓增生活躍,粒紅比例增大,粒細胞系增生,各階段細胞均可見,以偏成熟階段細胞為主,紅細胞系各階段細胞可見,以中晚幼紅細胞為主,巨核細胞易見,部分分葉少。(骨髓)病理診斷:粒細胞系比例增高伴部分巨核細胞形態異常,請結合其他。JAK2基因V617F突變定性檢測為陰性,MPL基因第10號外顯子、CALR9號外顯子、CSF3R基因及EXON14熱點突變未見突變。BCL-ABL1融合基因定性監測報告:BCL-ABL1(P210) 陽性。BCR-ABL1 P210型融合基因定量檢測:BCR-ABL1拷貝數為941 300,ABL1拷貝數為578 900,BCR-ABL1/ABL1為162.601%,IS為130.081%。染色體核型分析報告:46,XX,t(9;22)(q34;q11)。根據上述檢查結果,確診為CML(慢性期)。2022年10月30日開始在我院給予甲磺酸氟馬替尼靶向治療,治療1個月后復查血常規恢復正常,3個月時復查血常規正常但病人拒絕骨髓復查,目前病人規律隨訪、監測中。
2 討論
CML起病緩慢,多數病人因在體檢中發現脾腫大或白細胞增多而就診,或因脾腫大壓迫而產生上腹部不適、食后腹脹就診。其白細胞水平一般>30×109/L,有些甚至>100×109/L[1]。本病例就診時并無上述表現,而以白細胞輕度增多伴血小板明顯增多為主,結合頭暈及視物模糊等病史考慮不除外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癥(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 ET),其特征為骨髓巨核細胞異常增生伴血小板持續增多,同時伴有其他造血細胞輕度增生,常有反復自發性皮膚黏膜出血、血栓形成和脾臟腫大;神經癥狀也較常見,表現為頭痛、感覺異常、視力障礙或癲癇樣發作。但入院后追問病人病史,發現其為脾切除術后5年,一直未監測血象,不清楚術后血小板情況,因此該病例首先應考慮為繼發性血小板增多。繼發性血小板增多癥是指由感染、藥物、惡性腫瘤、脾切除術等病因引起的血小板增多,其血小板增多一般≤600×109/L,原發病控制后血象即可恢復正常。對于脾切除術后,血小板升高一般在1~3周內恢復正常,但也有部分病人表現為持續增高[6]。為規范、明確診治,本研究對病人進行了骨髓檢查,結果顯示BCR-ABL融合基因及Ph染色體均為陽性,從而確診為CML(慢性期)。
脾切除術后血小板升高的機制目前尚不清楚,可能原因一是人體每天血液內的衰老血細胞都會被脾臟內的吞噬系統吞噬,脾臟切除后這些細胞特別是血小板會因無法清除而明顯升高;二是脾臟會產生一些抑制骨髓產生血小板的因子,脾切除后這種抑制解除[6]。本病例在脾切除5年后,首次發現血小板增多,首先考慮繼發性所致,但骨髓涂片表現卻符合MPN、ET等表現,經基因及染色體檢查確診為CML。另外,繼發性血小板增多癥骨髓象一般僅為輕度巨核細胞增生,與本病結果不符;骨髓活檢提示部分巨核細胞形態異常,也不支持繼發性血小板增多癥[6]。
因ET病人中JAK2/V617F突變基因陽性率僅有50%~70%,即JAK2/V617F突變基因等陰性也可診斷ET,對于僅僅以血小板增多為首發而沒有典型CML表現但BCR-ABL融合基因陽性的病人,應該歸類為ET還是CML,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但2008年WHO明確指出:診斷ET,其Ph染色體及BCR-ABL融合基因均要為陰性,故此類病人應該診斷為CML[7]。多數報道認為,與經典CML相比,僅以血小板增多為主要表現的病人尚處于CML的早期階段[2-4],這也可以部分解釋為何這些病人不出現典型CML的表現。另外,僅以血小板增多為首發表現的CML脾臟多不腫大或僅輕度腫大,白細胞正常或稍增多,外周血及骨髓細胞分類中無中、晚幼粒細胞異常增生,骨髓以巨核系增生為主,未檢出JAK2 V617F突變,給予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KI)治療多數能取得較好的療效[5]。而且,CML病人容易伴骨髓纖維化,且均為女性,目前尚不清楚原因[3]。本例為老年女性,除脾臟切除及無骨髓纖維化(網狀纖維染色MF=0)表現,臨床資料與上述文獻報道基本一致,其中骨髓涂片易見嗜堿性粒細胞及部分巨核細胞形態異常可能與CML有關。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針對血小板增多的病人,無論臨床上考慮為原發性或是繼發性血小板增多癥,均應積極行骨髓檢查及BCR/ABL融合基因、Ph染色體、JAK2、CALR、MPL等MPN相關突變基因檢測,盡快明確診斷,進而及早采取有效的治療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