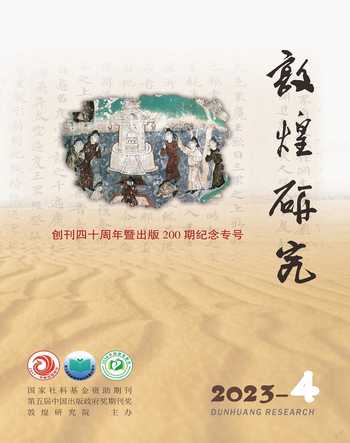云蒸霞蔚的四十年
李焯芬
敦煌藏經洞于1900年被發現之后,受到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的高度重視。專家學者們開展了敦煌文獻的研究,逐漸發展成“敦煌學”。早年參與敦煌文獻研究的學者,包括了在香港的饒宗頤。20世紀50年代初,饒宗頤開始在香港大學任教。為了開展敦煌文獻的研究,他托朋友在英國買到了英藏敦煌文獻的一套縮微膠片(microfiche)。在深入研究及考證的基礎上,他發表了一些論文,受到國際漢學界的重視,并獲邀到巴黎去研究法藏敦煌文獻。于是他利用每年的暑假到巴黎去,住在法籍學生汪德邁(Leon Vandermeersch)的家;白天到法國國家圖書館去細閱被伯希和(Paul Pelliot)帶到法國的敦煌文獻,晚上回到住處后,經常挑燈夜戰,工作至深夜。他用楷書撰寫的多份研究報告,至今仍收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內。他亦不斷找機會到其他國家,找尋和參閱流失海外的其他敦煌文獻,并作深入研究。饒宗頤的敦煌研究成果十分豐碩,曾獲國家文物局及甘肅省政府頒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
20世紀80年代中葉至本世紀初,饒宗頤曾兼任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的學術委員會主席,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推動敦煌學研究。有感于“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和“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國外)”這些話,他很希望能為推動敦煌研究、培養敦煌研究人才作點貢獻。于是,他先后邀請了二十多位內地中青年學者(包括榮新江、郝春文等)到香港,進行研究和交流。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已出版,收錄在兩個系列的學術專著,包括《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11種)及《補資治通鑒史料長編系列》(8種)。他還鼓勵我們成立了“香港敦煌之友”,支持敦煌石窟的保護、壁畫的數字化和相關的研究工作。
讓饒宗頤晚年感到特別安慰和開心的是,他看到我們國家的敦煌研究專才一代代地茁壯成長,繁花滿園。敦煌研究蔚然成風,碩果累累。用饒老晚年的話說,我國敦煌研究呈現云蒸霞蔚的好現象,明顯已居世界超前或領先的地位。國際間的敦煌研究合作,亦呈十分可喜的現象。
從這一角度看,《敦煌研究》這部高水平學術期刊的四十年,是促成、見證我國敦煌研究達至云蒸霞蔚局面的重要歷史進程,值得我們由衷地喜悅和贊嘆。衷心感謝敦煌研究院、各院校和研究單位學者們的默默耕耘和不懈努力;特別要感謝期刊編委會和編輯部同人的長期辛勞和奉獻,把期刊辦成國際頂尖的敦煌學刊,實在無量感恩!
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