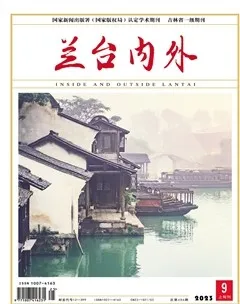“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探析
王倩 史小青 袁暢 孫婷婷
摘 要: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民族團結的根本,文化共同體又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核心與靈魂。通過解讀徽州家譜檔案,挖掘并分析其中蘊含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溯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徽州家譜檔案中的表現,為探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路徑提供新的可能。
關鍵詞:徽州家譜檔案;中華民族共同體;譜牒學
1902年,梁啟超最早命名和使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此后,在學術界理論探索與社會發展實際需求的雙重引導下,“中華民族”的概念呈現出了“超民族”的狀態。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涵在實踐過程中得以不斷豐富和發展。由“中華民族”衍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體現了中華民族由救亡圖存的集體發展至民族大團結的有機整體,涉及范圍更加寬泛,個體之間的聯結與歸屬也得以強調。
徽州家譜檔案的纂修最早可追溯至宋元,發展至明清時期逐漸成熟。作為宗族社會尊祖敬宗、追本溯源的憑證,徽州家譜檔案也蘊含著中華民族整體的道德追求與情感認同。目前,明清徽州家譜檔案數量眾多、內容豐富和保存較好上海圖書館館藏有1500余部,安徽省圖書館等機構以及民間個人也留存有一定數量,因此,利用徽州家譜檔案研究徽州宗族整體具有可行性。徽州宗族整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都體現著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情感互動,據此,筆者擬通過解讀徽州家譜檔案,探尋這種聯結和歸屬的深層涵義,探求“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徽州家譜檔案中的表現
1.“家國認同”:徽州家譜檔案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個人修養理論
徽州家譜檔案在形成之初就對本族成員起著教化與約束作用,徽州宗族個人修養尤重視“修”與“行”。在“自我”的維度上,首先,涉及人格要求方面,主要包括知恥向善、修身正己和責任理想三個部分。在知恥向善層面,徽州宗族主張忠孝節義的價值觀念,在此基礎上指導著“可行”與“不可行”。徽州宗族多以“積善”為訓,認為“常寸善心行善事,此敬祖宗之心也”。其次,在修身正己層面,徽州宗族強調要加強自身修養,做到博學多才。徽州宗族尤其推崇教育,《西關章氏族譜》中記載“年六七歲,即令親師教以詩書,使知禮義”,鼓勵人積極向上,“職業當勤”。最后,在責任理想層面,徽州宗族推崇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觀。徽州家譜檔案中體現了徽州宗族將匡時濟世視為人格修養的重要內容,這也成為有識之士的價值追求和人生理想。
由人格要求擴展至行為要求,主要包括為人處世和責任義務兩個層面。一是為人處世層面,較為典型的要求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秉持與人為善的原則,重視與鄉鄰構建和諧友好的關系,“睦族之次,即在睦鄰”“睦鄰之道,一切小忿,說過便消,仍復舊好,不留宿怨”;二是責任義務層面,家譜檔案中常以典型人物的事例來引導美俗良風,如《康熙周氏家譜》中的爾奇公關懷鄉里,對于所遇災害“每煮粥以振饑,施藥以療疾,立郵亭、設義漿以解渴”。家譜中刻畫族人向善行善的群像,其教化傾向不言而喻。
2.“和宗睦族”“尊宗敬祖”:徽州家譜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宗族倫理觀
基于宗族同屬的觀念,徽州人將“宗族與吾一本”的思想融入宗族內部日常交往中。若百姓和睦是王道的開始,則“教民親睦之道始于宗族”,家譜發揮的教化功能正是治國治民的根基。秉持和宗睦族的品質,宗族成員在面臨困境時才能做到團結一致,將“患難與共”的準則落到實處。《汪應美公傳》中的汪美公“遇義所當為者能罄所有以濟入,無幾微吝色”。族人之間的相互扶持,成為人們自發的生活信條,讓徽州社會處處彌漫著濃濃的人情味。而將“宗族以和睦為貴”推及至家族治理中,則要求家庭成員要有敦睦之心。《金山洪氏宗譜》中載:“男正外,女正內,無致反目,皆居家之首務也,吾族勉乎哉。”夫妻以家庭為基礎進行分工,有助于營造和睦的家族關系。既然是同宗一本,親族之間便休戚相關,映射在徽州家譜中的群體意志和宗族情感,對于維系宗族凝聚力和宗睦族起著重要作用。
徽州宗族社會家族規模龐大,內部結構復雜,家譜在傳達“和宗睦族”觀念的同時還承載著對族人日常行為的規范。木瓜坦洪氏家訓的《祭典十禁》為規范族人行為,詳盡列出不得入祀的種種情形,包括為官不仁、亂倫敗節、盜賣祖業和為非作歹等。此外,徽州的宗族等級秩序還強調敬重在世的長輩。例如,《金山洪氏宗譜》中強調尊卑有分和長幼有序,“慎毋踰尊凌長,毋暴弱欺貧”,無故犯上者必將受到家法懲戒。家族中個體的日常行為是家風規范的載體,在徽州家譜維護區域共有秩序的背景下,宗族組織化和制度化進一步加強了宗族的治理功能,強化了族人精神共識,凝聚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涵的制度規范縮影。
3.“愛國愛民”“為商不恥”:徽州家譜檔案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社會倫理觀
徽州宗族從其發展淵源來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倫理以“仁”為核心,孔子解釋仁即為愛人。愛人不僅僅愛自己的宗族和親人,還要愛其他人。首先,徽州宗族在社會實踐中表現出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在保證家族發展的情況下,盡其所能濟世利人。歙縣潘氏第二十三世孫潘玉溪涉足商業并形成一定規模之后,積極從事家鄉的公益事業。《故弟玉溪公行略》中記述道:“會宗祠圮,慨然捐數十金,以佐完善;道路傾欹一,因之修葺。”徽州宗族這種樂善好施的品行也得到了鄉黨們的贊賞和認可。其次,徽州宗族認為族人應當盡好國民的義務,按時繳納稅款,在國家危難之際及時提供援助。“朝廷國課,小民輸納,不得故意拖延”。婺源人許達“業商于江淮”,在國家建立之初,“率諸商宣力以資國榷”。
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徽州人傳統職業觀念是“士農工商”,學而優則仕已經成為徽州宗族培養后代的最高準則,很多家庭是因為貧困才不得不棄耕從商。但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徽州人逐漸轉變了對商人的看法,“士、農、工、商,皆是本職”。但這并不意味著一些徽州宗族徹底放棄了入仕之路。徽州作為科舉風靡之地,崇文重教已然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對于徽商而言,從商獲取的經濟利益只是實現入仕理想的一種手段。一些徽商在致富之后,會捐資興修書院,為同族子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并設立義莊,為家族子弟的教育提供資金支持。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徽州家譜檔案中的溯源
1.家國一體與長幼有序維系的政治因素
徽州家譜檔案在追憶祖先收攏族人的名義下有著維系宗族等級秩序、統一宗族思想、強化宗族控制以及維護統治階層利益的深層需求。《大阜潘氏支譜》提道:“適庶之辨,辨于所生適出。雖次,直稱為嫡子”。體現族內的嫡庶之分與尊卑有別。在宗族中處于統治與領導方的族長和鄉賢,一方面,在家譜檔案中滲透秩序思想;另一方面,也將宗族共同體中個體對于族群的歸屬進一步延伸至對宗族與社會統治的認可與維護。
同時,徽州家譜檔案的編修也體現著官方的意志。《文堂鄉約家法》“請申禁約,嚴定規條,俾子姓有所憑依”,請求徽州地方官府的許可與支持。官府的告示也表明官方對修譜這一穩定家國行為的認可,使宗族修譜的民間行為上升為官方意志,增強其權威性和政治性的同時,拓展權力操縱范圍,也為保障宗族群體利益謀取一定的保障。
2.宗族意識與身份認同建構的物質基礎
徽州屬于丘陵山區,耕地稀少,自然環境封閉,易守難攻,大量中原人遷居使其從原先的蠻荒之地成為融合中原文明的移民社會,經過漫長的發展形成各大宗族。在人多地少的現實環境下,部分徽州人維系著并不能完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并不斷拓展著生存版圖。個體的生存保障需要宗族社會的穩定,因而,各大宗族以擬構譜系的方式,建構對中原祖先的集體記憶和強化身份認同,如《祁西二都東源葉氏宗譜》“葉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武王母弟季聃之后”,即是對宗族祖先進行擬構。
同時,徽州人在農業之外另辟出路。經濟中心南移使得徽州土產的需求激增,在宗族組織的互幫互助下,徽商得以興起與發展。徽商尊祖敬宗的情感使其商業利潤又會輸送至其所屬的宗族,用以修譜建祠和置田興丁,如“挾鉅貲貿易于海上”的海商羅汝“不忘子侄輩”“聲歷苦勤善治家產”,對家譜“復總修之”。在此互動過程中,徽商的宗族意識得以提升,身份認同得以進一步建構。
3.自我約束與公序良俗建立的文化環境
與社會相匹配的倫理道德對宗族社會的維系具有重要作用,既能營造和諧的宗族秩序,又可凈化社會風氣。儒家文化在徽州地區的思想文化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重文興教的社會文化氛圍長期影響著本地居民。南宋以來,徽州鄉賢作為徽州傳統社會治理的引領者與主導者,充分吸收儒家文化資源,其中,茗洲吳氏注重禮法,所編制的《茗洲吳氏家典》從“忠、孝、節、義”四方面對個人行為進行約束。在此種社會文化氛圍的長期熏陶下,徽州人對儒家文化更加認可與尊崇,優秀價值觀念代代相承。
明清時期,徽州社會還存在著賭博和奢靡等不良風氣,且在眾多鄉村地區,官府權力鞭長莫及,道德是個人行為的重要約束。歙縣南屏葉氏宗族嚴禁賭博,并在《祖訓家風》中表示禁止賭博已有百年,若有賭博者嚴厲懲罰,“士庶老弱,概不少貸”。宗族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教化了民眾,強化了對不良風氣的管控,從而在預防宗族內外矛盾中起到重要作用。
三、徽州家譜檔案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啟示
1.守護集體記憶,增強身份認同
徽州地區的集體認同感是區域共同體得以塑造和維系的重要支撐,家譜檔案起到了保留宗族記憶和增強身份認同的作用。集體記憶是連接集體過往與集體認同的紐帶,集體記憶的凝聚是產生集體認同和集體歸屬感的必然邏輯。對于擁有悠久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而言,民族形象是在歷史過程中塑造出來的,最終沉淀為集體認同和集體記憶。挖掘共有的文化符號和守護好集體記憶,為增強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提供了現實基礎。
2.探尋文化基因,強化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有助于在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中形成情感歸屬。徽州地區共同享有的文化記憶塑造著人們的價值觀念,維系著人們的情感聯結,這些文化通過家譜代代相傳,其教化功能甚明。中華民族共同享有的文化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情感維系和文化認同的重要紐帶,源源不斷地為共同體意識注入動力。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增強文化認同需要以情感共鳴堅守文化認同的情感凝聚力,通過開展多樣文化交流活動調動民眾堅守文化的積極性。
3.建設共有家園,加強交流互嵌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由各種社會紐帶相交織而成,在整體上呈現出互嵌的狀態。在徽州地區,共同體意識很大程度上是在內部互嵌的過程中逐步融匯而成的。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應進一步推進互嵌,要確保在個體層面給予成員安全感與意義感,加強族際交流,多途徑打造交往場景,提升交流意愿,從而加深相互之間的文化了解從而逐漸消除刻板印象和隔閡。
結語
家譜檔案是一個家族歷史發展和文化底蘊的見證,又是一個社會和一個時代的投射和縮影。徽州家譜檔案中深藏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基因,是維系民族情感和加強文化認同的重要工具,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嶄新的思路。因此,作為新時代的檔案工作者,必須牢牢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主線,深化對于徽州家譜檔案的價值認知,加快推進徽州家譜檔案的研究開發,把“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凝聚意識從徽州家譜檔案中提煉出來,并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方法。
參考文獻:
[1]李大龍.中華民族共同體屬性與建設途徑探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43(03):1-8.
[2]明清徽州家譜檔案[J].檔案,2022,342(5):66.
[3]姚 碩.從徽州家譜看徽州家風建設——以績溪家譜為中心[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3(01):22-25.
[4]祝 虻.明代徽州家訓述論[J].徽學,2020(01):58-73.
[5]《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詩·示兒戩》[M].四庫全書存目全書本,第511頁.
[6]陳雪明.明清徽州族規家訓中的“好人教育”理念及其當代啟示[J].地方文化研究,2020,8(04):57-64.
[7]張令影.《康熙周氏家譜》卷十六《清處士前太學生爾奇公傳》[M].
[8]方弘靜.《千一錄》卷二十三《家訓一》[M].續修四庫全書本,第429頁.
[9]羅翔宇.論宗法觀念在古徽州宗族社會中的傳承與發展——以徽州家譜為中心[J].皖西學院學報,2018,34(06):121-125.
[10]朱慧敏.明清家譜人物傳記的宗法思想——以徽州家譜為中心[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38(02):66-70.
[11]黃忠鑫.清代徽州佃仆的宗族意識與族譜書寫[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46(6):32-39.
[12]張 凱.《蘇州“大阜貴潘”研究》[M].合肥: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07:234頁.
[13]周夢云.清代徽州周氏家譜傳記研究[D].安徽大學,2018.
[14]朱莉濤.《茗洲吳氏家典》研究[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54(03):18-24.
[15]李曼曼.明代壽縣正陽關的許氏徽商研究[J].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22,24(04):32-36.
[16]《袁氏族譜》卷首《家規》[M].1921.
[17]武 倩.明清績溪婚姻問題研究[D].安徽大學,2022.
[18]卞利.明清時期徽州的鄉約簡論[J].安徽大學學報,2002(06):34-40.
[19] 《祁西二都東源葉氏宗譜》卷四《葉氏宗譜序》[M].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