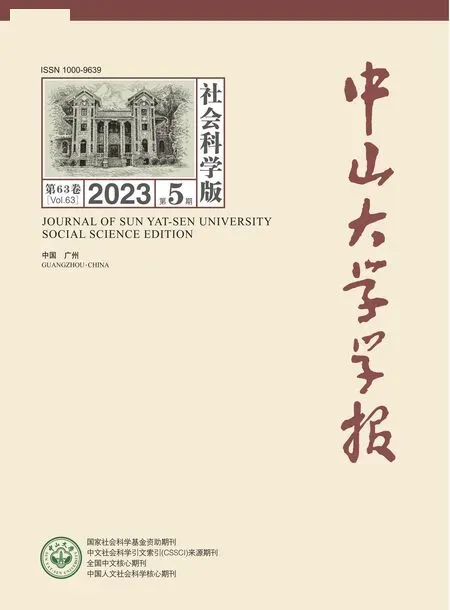被翻譯掩蓋的西方詩歌真相*
王東風
西方詩歌譯入中國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對中國當代的詩歌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于學術界一直有一個共識,認為中國的白話新詩就是受西方詩歌的影響而產生的。自新文化運動以來,西方詩歌在國人的心目中就是自由詩。這種詩體剛一出現的時候,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持否定意見的人認為那不是詩,只是一種分行散文。但隨著白話文和白話新詩的普及,人們慢慢也就接受了這一詩體的存在。然而,有一個簡單的事實卻一直被人們忽略:西方詩歌也有格律詩和自由詩之分,為什么深受西方詩歌影響的白話新詩卻只有自由詩一枝獨秀?西方格律詩有那么多的詩體為什么僅有十四行詩在中國詩歌界偶有所見?而如果按西方十四行詩的標準,卻又沒有一首原創的漢語十四行詩能夠達標。既然白話新詩是受西方詩歌影響而產生的,那么在新文化運動期間,這樣的影響必定是通過翻譯而形成的。然而,這一百多年來的詩歌翻譯是不是準確地譯出了西方詩歌的詩體特征?如果真的譯出來了,為什么只有一個自由詩和并不達標的十四行詩被引進到了中國?由于新文化運動以來主導詩歌翻譯的那批譯者,幾乎個個都另有一個著名詩人的身份,這是一個讓當今翻譯者和翻譯學者望塵莫及的學養,因此一直以來學界對他們譯文的評價多是溢美之詞、膜拜之態,少有理性的反思。然而,拂去這層溢美的浮塵,從詩學和翻譯的角度對比那些譯詩的原文,我們卻不無震驚地發現,原來西方詩歌的詩學真相被翻譯牢牢地掩蓋了、壓制了、改造了乃至扭曲了:中國讀者看到的那些譯文原來并沒有真正展現原詩的詩學真相。本文將從詩學與翻譯的角度撩開掩蓋在西方詩歌之上的這層由翻譯編織的面紗或偽裝,通過分析與更加合乎詩學原理的重譯盡可能地再現西方詩歌的真容。
一、從十四行詩的變形說起
十四行詩,亦譯“商籟體”,后者是英文術語sonnet 的音譯,而“十四行詩”這個術語則是根據這種詩體多為14行的特點而意譯的名稱。這種詩體起源于13世紀的意大利宮廷,后流傳到歐洲各地,產生了多種變體,不同的變體有其韻式和節奏的嚴格要求,是西方的一種格律最為嚴謹的詩體。
最早的十四行詩的漢語譯文見于1854 年的香港,發表在一個叫《遐邇貫珍》的刊物之上。表1 是該詩的前四行原文和譯文:

表1 早期漢譯十四行詩原文與譯本對照
原詩是彼得拉克體的十四行詩,韻式是ABBA ABBA CDE CDE,節奏是抑揚格五音步,即:
以上分析圖標中的“x”為“抑”音,“/”為“揚”音。英語格律詩的節奏,跟漢語格律詩一樣,也是通過音節之間二元對立的音差組合及其有規律的重復來構建的,雖然具體表現有差異,但也并非只有差異而沒有共性。英語格律詩最典型的音步(foot)由兩個音節構成,這是它的節拍,兩個音節前輕后重,故稱“抑揚格”(iamb),亦稱“輕重格”,這是它的聲律。節拍與聲律的有機結合形成音步,音步的有規律重復形成節奏。但這里所說的“輕重音”并不完全是口語或詞典中所標注的輕重音,而是根據格律的要求分布或認定的,非詩語境中的輕重讀是所謂“口語重音”(speech stress),詩歌中的輕重讀是“節奏重讀”(metrical accent)③James McAuley,Versification:A Short Introduction.East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6,p.3.。上面這首詩的譯文是詩經體的四言詩格式,原詩的韻式、節奏乃至十四行的特征均被譯文所掩蓋。
該詩的譯者并沒有說明這是十四行詩,只說是一位叫“米里頓”的“英國顯名詩人”的作品,既沒有譯出標題,也沒有給出這位詩人的英文名。對當時的讀者來說,這僅僅是一首詩經體的譯詩而已。經查,這位“米里頓”就是彌爾頓(John Milton);詩的標題是On His Blindness,今譯《論失明》。由于這首譯詩發表在當時已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地區,因此對中國內地的主流詩歌文化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第二首十四行詩的漢語譯文出現在1911 年的日本,即蘇曼殊翻譯的印度女詩人陀露多(Toru Dutt)的《樂苑》,收在蘇曼殊的詩集《潮音》之中,最初在日本出版,1925年才在中國由湖畔詩社翻印。以下是這首詩的前四行原文和蘇曼殊的譯文:
A sea of foliage girds our garden round,
But not a sea of dull unvaried green,
Sharp contrasts of all colors here are seen;
The light-green graceful tamarinds abound
萬卉帀唐園,深黝乃如海。嘉實何青青,按部分班采。①[印度]陀露哆著,蘇曼殊譯:《樂苑》,朱少璋編:《曼殊外集——蘇曼殊編譯集四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第87—88頁。
原詩的韻式是ABBA ABBA CDCD EE,節奏仍是抑揚格五音步。在譯文中,十四行詩的特征被悉數掩蓋,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傳統的五言古體詩。
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后,白話新詩出現,其基本特征是所謂的自由詩,實乃分行散文體。白話詩人不僅在詩歌創作時用這一體式,在翻譯包括十四行詩在內的各種西方格律詩時也采用這種文體,因此詩歌翻譯開始告別過去的“舊詩化”翻譯階段,進入到“自由化”的翻譯階段。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十四行詩翻譯當數郭沫若譯的雪萊的《西風歌》(今譯《西風頌》)。原詩是由五首十四行詩組成的組詩,表2 是該詩最后一章前六行的原文和郭沫若的譯文:

表2 雪萊《西風歌》節選英澤對照
原文是一種叫三韻體(terza rima)的十四行詩,韻式是ABA BCB CDC DED EE,節奏仍是抑揚格五音步。但原詩的這些格律特征在譯文中均不見蹤影,唯一體現出來的十四行詩的物理特征是行數:譯文也是十四行。
后來,新月派認為譯詩還是要盡可能地再現原詩的韻式和節奏。在新月派眾多詩歌翻譯家中,唯有朱湘翻譯的一首十四行詩可以說在格律上與原文最為接近,表3是英國玄學派詩人多恩(John Donne)的一首十四行詩Death(死)的前八行原文及朱湘的譯文:

表3 多恩十四行詩英漢譯文對照
原文的韻式是ABBA ABBA CDDC EE,節奏是抑揚格五音步。朱湘譯文體現了原詩的韻式和縮行特征,節奏上也十分接近,但受其安徽安慶方言的影響,押韻時前后鼻音不分現象比較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在節奏上,該譯詩絕大部分節奏單位都是由兩個字構成的。但可惜的是,朱湘未必是有意識地以二字逗來對應原詩的雙音節音步,因為譯文中還有三行沒有達到這個標準,其中一行就是上面引文中的第六行:“我們并喜歡他來到人間。”而在朱湘翻譯的其他十四行詩中,這種節拍不對應的情況則更多,能在絕大多數詩行中實現節拍對應的譯詩僅此一首,因此可以視為是其“以字代音節”的譯法的偶然所得。但是,英詩音步除了雙音節組合形成的節拍之外,還有輕重讀構成的“抑揚”聲律,這個特征在譯文中沒有體現出來,略顯遺憾。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如此接近原詩格律的譯文已經是非常難得了。而真正遺憾的是,他的這首譯文在方法上的突破一直沒有被學界所注意,因此他在這首譯詩中所體現出來的這一獨特的詩歌翻譯方法,以及由這一方法所初展的十四行詩真容,也就被長期地埋沒在故紙堆里了。
其他新月派詩歌翻譯者,則在聞一多“音尺”觀的影響下,開始嘗試用口語中的自然音頓來構建新詩的格律,并把這一理念用到了詩歌翻譯之中。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最后在新月派詩人卞之琳的倡導之下,終于形成了“以頓代步”(簡稱“頓代化”)的詩歌翻譯規范,至今盛行于詩歌翻譯界。以下是卞之琳翻譯的《西風頌》最后一章的前六行:
請拿我做你的瑤琴,就像你拿森林:
縱然我也要木葉盡脫也成!
蕭蕭騷騷的你這種雄偉的和音
會從兩方面撥出深湛的秋聲,
凄涼而甘美。激越的精靈,你就做
我的精神!你做我,蕭殺的莽神!①[英]雪萊:《西風頌》,卞之琳編譯:《英語詩選:莎士比亞至奧頓(英漢對照)》,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55頁。
按“以頓代步”的規則,前兩行的節拍結構如下所示:
請拿我 | 做你的 | 瑤琴 |,就像你 | 拿森林 |:
縱然 | 我也要 | 木葉 | 盡脫 | 也成 |!
卞之琳嘗試用漢語口語中的“頓”來體現原詩的音步,但原詩的音步是雙音節結構,輕重音組合,而譯文雖然每行有五頓,但頓內的字/音節數卻是忽二忽三的無規律組合,明顯對不上原詩的節拍,聲律也被無視,因此十四行詩的節奏真相仍然被掩蓋。
就格律詩的節奏而言,最理想的譯法是既要譯出原詩的節拍,還要譯出其聲律。翻譯界以往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從韻律學的角度看,這并非不可能。西方詩歌多是利用音節的長短或輕重來構建聲律,如希臘語詩歌的音步是通過音節的長短來組合,其中一種音步就是短長格(iambus)。英語詩歌的音步是通過音節的輕重來營造聲律,形成抑揚格(iamb)。從希臘語的iambus(短長格)到英語的iamb(抑揚格),即可看出這一節奏特征的跨語演變:iambus源自希臘語詩歌,當英語引進這種節奏時,根據英語詞匯的語音特點,就將其本地化為了輕重格或抑揚格。同理,如果我們要譯出這一節奏,也完全可以根據漢字的語音特點來做本地化借鑒,即用“平”代“抑”,用“仄”代“揚”,這就是本文作者所提出的“以平仄代抑揚” 的詩歌翻譯方法②參見王東風:《以平仄代抑揚,找回遺落的音美:英詩漢譯聲律對策研究》,《外國語》2019年第1期。。雖然平仄與抑揚的音型完全不同,但詩學功能是一致的:都是用以構建有規律的節奏。考慮到英語中絕大多數格律詩都是抑揚格的,僅有少數詩歌是用揚抑格(trochee)的,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采取這種“以平仄代抑揚”的方式來對應英詩的聲律。至于英詩音步的其他組合,如揚揚格(spondee)、抑抑揚格(anapest or anapaest)、揚抑抑格(dactyl)、抑揚抑格(amphibrach)、抑抑格(pyrrhic)等等,實際上都是作為抑揚格或揚抑格詩歌的“節奏變體”而出現的,可以說極少有一首詩歌是全部用這些音步寫成的,即便有也不妨用“以平仄對抑揚”的方式來做對應。試以此法譯《西風頌》第五章的前六行如下:
把我權當一把豎琴彈撥:
弦鳴音起猶似風掠莽林,
撩落殘葉幾許又能若何!
你的宏大合奏嘹唳深沉,
秋意蕭颯,悲戚而又甜蜜。
多想如你,我的狂暴天神!①王東風:《論“以平仄代抑揚”的可行性:再譯〈西風頌〉》,《中國翻譯》2022年第4期。
譯文盡可能準確地體現了原詩的意象和思想,同時盡量保留了原文的韻式和節奏。在節奏方面,每行五個二字逗,對應原詩的五個雙音節音步;絕大多數節奏單位做到了“平—仄”組合,以對應原詩的抑揚格,因為英語格律詩并不要求每個音步都是嚴格的抑揚組合,只要絕大多數音步達到這個要求就可以了,因此譯文只要保證絕大部分節奏單位都是“平—仄”組合,就基本實現了聲律的對應。
十四行詩進入中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但因為翻譯掩蓋了其格律真相,廣大讀者,甚至十四行詩譯者本身,都深受變了形的十四行詩的譯文的誤導,乃至國產的十四行詩沒有一首能夠達到西方十四行詩的設計標準。在此不再具體列述。
二、被扭曲的莎劇
英語格律詩中,產量最高的品種是“無韻詩”(blank verse),另譯“素體詩”。無韻詩的節奏也是抑揚格五音步,但不用押韻,也沒有行數限制,因此比較適合于寫史詩、敘事長詩和詩劇;此外,在用無韻詩寫的詩劇中,節奏變體(metrical variation)使用得比較多,詩行多一個音節少一個音節,乃至多一個音步少一個音步,是一種常態化的現象,這是因為詩劇中有大量的人物會話和獨白,節奏不能太呆板,必須要有一定的自由度方可適合表演。
英漢格律詩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即英語格律詩可以不押韻,而漢語格律詩必須押韻,因此在英語詩歌話語中,所謂的“格律”(metre)僅指節奏的規律化模式,與押不押韻無關。
英語無韻詩譯入中國最多的當數莎士比亞的戲劇。莎劇有37 種,都是用無韻詩寫的,因此莎劇就是詩劇。但包括莎劇在內的無韻詩在中國的旅程,也同樣始終遭遇了翻譯的困擾,始終沒有露出她的真容。
莎劇在中國公認最早的譯本是田漢1921年在《少年中國》上發表的《哈孟雷德》第一幕;完整的譯本是1922年出版的,劇名改為《哈孟雷特》。以下是《哈孟雷特》第三幕第一場中“哈孟雷特”的那段著名獨白的原文前10行: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To die:to sleep;
No more;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The heart-ache,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That flesh is heir to,'t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d.To die,to sleep...①William Shakespeare,The Tragedy of Hamlet.Ed.by Edward Dowden.London:Methuen & Co.1899,pp.98-99.
這段獨白原文有33 行,格律是抑揚格五音步,不押韻,內有大量的節奏變體;變體詩行中最多的是11 音節詩行,以上10 行引文中就有8 行都是11 音節詩行,僅第6 和第10 行是10 個音節,即抑揚格五音步。以前兩行為例,試分析如下:
最后一個音節上斜體的x處于第11個音節,位置在行末,這是一個輕讀音節,即“抑”音。英語格律詩的詩行如果是以抑音收尾,叫“陰尾”(feminine ending),是一種叫“超音步音節”(hypermetrical syllable)的節奏變體,簡稱“超步式”變體,即最后一個超出規定音步數的音節不計入音步。這是莎士比亞使用得最多的節奏變體,也是英語詩歌中歷史最悠久的詩歌寫作技巧之一。以下是田漢的譯文:
還是活著的好呢,還不活的好呢?——這是一個問題:所謂豪杰之士者,到底應該忍受著“暴虐的運命”的矢石呢,還是應該在和狂波駭浪相抵抗死而后已呢?死,——和睡,——差不多;假若一睡可以解脫我們心里的悲痛,和一切附屬于肉體上的苦惱,——那真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好事。死,——等于睡……②[英]莎翁著,田漢譯:《哈孟雷特》,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22年,第73—74頁。
田漢沒有把原文當詩來譯,而是將其譯成了白話散文體。該譯本還有田漢作的一個“譯序”,但并沒有提及原文所采用的體裁是無韻詩。此后的一系列莎劇翻譯大多都是按田漢這個體裁模板來翻譯的。但有識之士還是看出了其中的問題,如孫大雨。在他看來,原文是詩,就應該以詩譯詩。于是,1931年,他在《詩刊》第二期發表莎劇譯文《黎琊王》片段,以下是該譯詩前三行的原文:
Lear
Blow winds,and crack your cheeks! Rage,blow!
You cataracts and hurricanoes,spout
Till you have drenched our steeples,drowned the cocks…③William Shakespeare.Shakespeare's King Lear.Ed.by A.Schmidt.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879,p.130.
原文依然是無韻詩的格律。作為新月派一員的孫大雨采用了新月派慣用的頓來做詩歌的節奏單位:原文是一行五個音步,譯詩則是一行五頓。以下是他的譯文:
Lear 刮啊,大風,刮起你們的狂怒來!把你們的頭顱面目刮成個稀爛!
汪洋的大水,暴雨同颶風,倒出
你們的狂濤,打透這些屋尖……①見孫大雨:《譯King Lear》,《詩刊》1931年第2期。
孫大雨將他所用的節奏單位稱為“音節”,并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了一個音組論,主張用漢語的“音節”來對應原詩的音步,以構建詩歌的音組。在他的話語體系中,“音節”對應的是英語的“音步”,音組對應的英文術語是metre②參見孫大雨:《詩歌底格律》,《復旦學報》1956年第2期;《詩歌底格律(續)》,《復旦學報》1957年第1期。長期以來學界一直以為他說的“音組”差不多就是“字組”或“頓”的意思,其實是一個誤解,參見王東風:《被冤枉的何其芳,被誤解的孫大雨:新詩節奏單位起源之爭》,《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22年第6期。,即英詩話語中所說的格律。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新詩詩人們用“音節”來指涉節奏單位,相當于聞一多所說的“音尺”,但與如今語言學所說的“音節”不是一回事,后者對應于英語的syllable。不難看出,孫大雨的“音節”跟卞之琳的“頓”基本上是同一個性質:節奏單位內的字數忽多忽少,沒有規律,更沒有聲律設置。從莎劇傳播的結果來看,真正贏得讀者之心的還是散文體的莎劇翻譯,尤其是朱生豪的散文化譯本。以下是他所譯《哈姆萊特》中那段獨白的前幾行: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斗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死了;睡著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這一種睡眠之中,我們心頭的創痛,以及其他無數血肉之軀所不能避免的打擊,都可以從此消失,那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結局。死了;睡著了……③[英]莎士比亞:《哈姆萊特》,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63頁。
然而,原詩的詩學真相并非如此,而漢語也并非譯不出原詩的節奏。用“以平仄代抑揚”的方式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原詩的格律。考慮到原文中有大量的節奏變體,譯文也應以變應變。試譯哈姆雷特這段獨白的前幾行如下:
如此,還是那般,問題就在這:
惶對時運箭石頻射無所為,
還是直面無盡愁苦拔劍迎,
何種方式才顯高貴豪邁風?
如果能死:當會一睡無醒時;
一切皆可終止;一睡而去,
頭痛遂釋,還有肌體無盡傷,
從此一了百了,何樂而不為。
如果能死,當會一睡無醒……
譯文采用“以平仄代抑揚”的方式對應原詩的節奏。為應對由11個音節構成的節奏變體,譯文也仿照原文的節奏結構譯出,絕大多數節奏單位都是“平—仄”組合,達到了這一翻譯方法的設計要求。針對大量出現的11 音節詩行,對應的方式要么是二二二二二一,要么是二二二二一二,結尾處的“二一”或“一二”跟漢語傳統詩歌的三字尾相近。這一點下文還會談及。
語義方面,譯文的第一句與以往所有的翻譯都不同,這是因為原文這第一句的語義本身就是含糊的,需要與下文聯系起來的方可得到解讀;更重要的考慮是,哈姆雷特當時正在裝瘋以自保,說的是莫名其妙的瘋話,因此譯文在此也應該以含糊對含糊,方能更符合語境的要求。
三、被毀容的六行體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影響最大的一首譯詩莫過于拜倫的《哀希臘》(The Isles of Greece)了,這是一首六行體(sestet)組詩。譯名有多種,以蘇曼殊所譯的《哀希臘》著稱。以下是該詩的前一節:
The isles of Greece,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except their sun,is set.①Lord Byron.Don Juan.Boston:Philips,Sampson,and Company,1858,p.117.
《哀希臘》有16 節,每節六行,共計96 行;韻式為ABABCC,節奏是抑揚格四音步,即每行八個音節,四個抑揚格音步;二四行縮行而寫。
這首譯詩的名氣很大,因為20 世紀多個著名的詩人兼翻譯家都翻譯過這首詩,如梁啟超、馬君武、蘇曼殊、胡適、柳無忌、聞一多等,他們在翻譯這首詩的時候紛紛用自己所喜愛的詩歌形式替換了原詩的詩體,但也正因為如此,相信那些期待從這些名人筆下見證拜倫詩歌真容的人,一定會很困惑。
梁啟超的譯文:
(沈醉東風)……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平和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兩神名。)榮光常照。此地是藝文舊壘,技術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卻太陽光線,萬般沒了。②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第1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631頁。
馬君武的譯文:
希臘島,希臘島,
詩人沙浮安在哉?
愛國之詩傳最早。
戰爭平和萬千術,
其術皆自希臘出。
德婁飛兩布英雄,
淵源皆是希臘族。
吁嗟乎!
漫說年年夏日長,
萬般消銷剩斜陽。③[英]裴倫撰,馬君武譯:《希臘島》,馬君武:《馬君武詩稿》,上海:文明書局,1914年,第20、22頁。
蘇曼殊的譯文:
巍巍西臘都,
生長薩福好。
情文何斐亹,
荼輻思靈保。
征伐和親策,
陵夷不自葆。①[英]拜倫撰,蘇曼殊譯:《哀希臘》,朱少璋:《曼殊外集——蘇曼殊編譯集四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第206頁。
胡適的譯文:
嗟汝希臘之群島兮,
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
詩媛沙浮嘗詠歌于斯兮,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長夏之驕陽兮,
紛燦爛其如初。
我徘徊以憂傷兮,
哀舊烈之無余!②[英]裴倫撰,胡適譯:《哀希臘歌》,胡適:《嘗試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95頁。
柳無忌的譯文:
希臘的群島,希臘的群島!
那里熱情的莎嫵愛著歌著,
那里揚起戰爭與和平的藝術,——
那里涌現了迪羅,生長著飛勃!
永恒的盛夏仍舊照耀群島,
但是,除了太陽外,萬般都已銷歇。③柳無忌:《希臘的群島》,《從磨劍室到燕子龕——紀念南社兩大詩人蘇曼殊與柳亞子》,臺北:時報出版社,1986年,第245頁。
聞一多的譯文:
希臘之群島,希臘之群島!
你們那兒莎浮唱過愛情的歌,
那兒萌芽了武術和文教,
突興了菲芭,還崛起了德羅!
如今夏日還給你們鍍著金光,
恐怕什么都墮落了,除卻太陽?④[英]拜倫撰,聞一多譯:《希臘之群島》,孫黨伯、袁謇正編:《聞一多全集》第1 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0—301頁。
卞之琳的譯文:
希臘群島啊,希臘群島!
從前有火熱的薩福唱情歌,
從前長文治武功的花草,
涌出過德羅斯,跳出過阿波羅!
夏天來鍍金,還長久燦爛
除了太陽,什么都落了山!①[英]拜倫撰,卞之琳譯:《哀希臘》,卞之琳編譯:《英國詩選:莎士比亞至奧頓(英漢對照)》,第137頁。
再往后的譯文大致就都是在聞一多這種形式上的微調了。
以上各種譯文雖出自同一原詩,卻完全看不出原詩的詩體特征,甚至在聞一多之前,連原詩的韻式都沒有體現出來。譯文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卻又都聲稱是譯自拜倫,而實際上,原詩的藝術形式被這些形形色色的翻譯粗暴地毀容了。從發展的角度看,該詩的譯文經歷了三個階段:舊詩化階段(從梁啟超到胡適)、自由化階段(柳無忌)、頓代化階段(從聞一多到卞之琳)。不難看出,原詩的那種每行八個音節、每兩個音節為一個抑揚格音步的節奏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一直被各種各樣的譯文所掩蓋。這對于希望了解西方詩歌卻又不能讀原文的人來說,想要通過這些譯詩來了解西方詩歌的格律特征,是不可能的。
從理論上講,最接近原詩格律真相的譯法就是“以平仄代抑揚”,而這個譯法并非只是脫離實際的理論空談,實踐上看也完全是可行的。試譯該節如下:
希臘群島,希臘群島!
薩福如火歌美情濃,
文治卓越兵法精妙,
提洛昂立飛布②提洛:希臘基克拉澤斯群島中的島嶼的一個島嶼,在希臘神話中,它是女神勒托的居住地,在這里她生育了太陽神阿波羅和月亮女神阿耳忒彌斯。飛布:太陽神阿波羅的別稱,“飛布”系沿用馬君武的譯法,另有多種譯法。神勇!
長夏無盡群島灼亮,
天下傾毀,唯有殘陽。
英語名詩中有很多六行體的作品,如華茲華斯的Daffodils(《水仙花》),但也與《哀希臘》的命運一樣,在進入中國之后,難逃被譯者毀容的宿命。
四、被無視的節奏變體
所謂“節奏變體”,是西方格律詩寫作的一種常見技巧,指的是在詩中與基本節奏不同的局部變化,且有多種變化的形式。
上一節的案例顯示,在莎劇中,這樣的節奏變體十分常見。其實,在絕大多數英語格律詩中,都會有節奏變體的出現,只不過有的是偶然的,有的是密集的。偶然性的節奏變體,在翻譯中可以不予考慮,但密集型的節奏變體就不能視而不見了,畢竟是作者的一種選擇,有其特定的審美目的。
然而,西方格律詩中的節奏變體問題卻從未受到過譯界的關注。這也不足為奇,因為以往的翻譯就連節奏都沒有體現出來,節奏變體被無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以雪萊的名詩To a Skylark(《致云雀》)為例,這是英語中的一種叫“英式五行詩”(English quintain)的詩體,并不是很常見;韻式為ABABB。《致云雀》是一首長達21節、105行的格律詩。該詩的一大特點就是大量使用揚抑格音步,每節五行,前四行為揚抑格三音步,第五行變換成抑揚格六音步。該詩的基本節奏模型如下:
但在該詩中,完全采用上面這個節奏模型的詩節也只有8 節,也就是說,另有13 節都采用了與音節增減有關的節奏變體,但變化都不是特別大,因此由這8 節所建立的基本節奏就成了該詩的主旋律,其他變化都是圍繞這個主旋律所做的微調。由此也可以看出,該詩中的節奏變體是十分頻密的。這與該詩的主題密切相關:該詩描寫的是云雀的飛翔,詩中不斷變化的節奏表現的是云雀飛翔時的忽高忽低、忽快忽慢的靈動。因此,像這樣的節奏變化,譯者就不能視若無睹了。遺憾的是,以往的翻譯對此就是直接無視了。該詩有四節非常精彩的比喻,即第8 至第11 節,表4 是其中第10 節和第11 節的原文和江楓的譯文:

表4 《致云雀》英漢文本對照
譯文采用的是“以頓代步”法,即用長短不一的頓來對應原詩雙音節音步所構建的節拍,詩行中的字數全部超出原詩詩行的音節數。至于原詩的抑揚聲律和不斷出現的節奏變化,譯文則完全沒有理會。如此譯出的詩句,雖然本身也很優美,但對于不懂“以頓代步”的詩歌翻譯游戲規則的人來說,其實與自由詩無異,完全看不出原詩節奏工整之中有變化,節拍之外還有聲律的配合,原詩的節奏及伴隨其中的音樂性基本上沒有體現出來。
如果說,譯文與原文在節拍上的不對應是“以頓代步”這種譯法的一個結構性缺陷的話,那么這一方法對聲律的無視就是它的一個結構性的硬傷了。江楓的譯文雖然在努力營造一種節奏,但這種建立在自然音頓上的節奏完全不是格律化的節奏。英國著名詩人和詩論家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對節奏的定義是:“某個有規律的音節序列的重復。”①Gerard Manley Hopkins,The Journals and Papers of Gerard Manley Hopkins.Ed. by Humphry Hous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00.這里所謂的“音節序列”在英語格律詩中就是“音步”,在漢語格律詩中叫“逗”②聞一多:《律詩底研究》,孫黨伯、袁謇正編:《聞一多全集》第10冊,第148頁。,但“以頓代步”中的頓卻并不符合霍普金斯對格律詩節奏單位的界定。雖然“以頓代步”法要求用等量的頓來建行,但長短不一的頓卻沒有達到“某個有規律的音節序列的重復”這一格律性節奏的前提條件。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對于“頓”有過深刻的研究,他說:“各頓的字數相差往往很遠,拉調子讀起來,也很難產生有規律的節奏”。③朱光潛:《詩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239頁。
其實,漢語的表現力和可塑性是十分強大的,完全有能力譯出原詩的格律。尤其是這首詩,因為很多采用了節奏變體的詩行都是奇數音節詩行,尤以五音節詩行為多,七音節詩行也有不少,這種五七音節的詩行跟中國傳統的五七言詩在節拍上非常相似。
中國傳統詩話對五言詩的節奏劃分是“上二下三”或“二二一”,七言詩的節奏劃分是“上四下三”或“二二三”,但在王力看來,“最后一個字單獨成為一個節奏單位”④王力:《詩詞格律》,第133,137—138,133,133頁。,即二二一或二二二一,在實際吟誦的時候則形成一個三字尾⑤王力:《詩詞格律》,第133,137—138,133,133頁。。王力認為,漢語格律詩的三字尾既可以是二一式的組合,也可以是一二式組合,五七言詩的最后一個字是一個獨立的節奏單位。從節奏的發生機制來看,這正是按照“聲律單位”⑥王力:《詩詞格律》,第133,137—138,133,133頁。來劃分的,而不是按“意義單位”⑦王力:《詩詞格律》,第133,137—138,133,133頁。來劃分的。從這個角度上看,原詩針對末尾音節所采取的節奏變體就往往會形成奇數音節詩行,留下一個二一式的結尾,這與漢語傳統詩歌中的三字尾就形成了一種妙合,因此在翻譯時可以將最后的單音節音步和前面的雙音節音步合成一個三字尾,以體現這種節奏感,但不必苛求一定是二一式,一二式也完全可以,因為二者的聲律單位都是二一式。然而,中英詩歌之間這一難得的妙合卻一直以來被翻譯掩蓋了,讓人無法通過譯文來體驗來自異域詩歌中的這種親近感。
為找回這種真實存在的親近感,可以采用“以平仄代抑揚”的翻譯方法來處理:用“仄—平”的組合譯前四行的揚抑格詩行,用“平—仄”組合譯第五行的抑揚格詩行;至于節奏變體,則以變應變:以五言對五音,以六言對六音、以七言對七音,等等;原文有標點處,也按停頓處理。如此,盡可能地再現原詩節奏如下:
十
有如火螢金曳
隱約露凝谷,
順風撒播云天色
不拘也無束
花草叢中任逍遙,蹤影行跡全無:
十一
有如玫瑰掩面
避藏綠葉后,
熱風催花片片
但留謦香久
花賊不耐濃郁,戢羽又暈頭:
譯文按原文的節奏譯出,平、仄與抑、揚互換,可見其詩行時而五言,時而六言,時而七言,頗有宋詞的韻味,但這并非是譯者刻意歸化或舊詩化的結果,而是原詩的節奏原本如此。
其實,詩歌翻譯也應跟宋詞的填詞一樣:宋詞的作者如果要創作出某個詞牌的詩歌,必得要按那個詞牌的要求對號入座才可構建出那個詞牌所特有的節奏。譯詩也應該如此:原詩的格律猶如特定詞牌的格律,翻譯時平仄與抑揚互換,對號入座。如此,譯詩的節奏自然會更加貼近原詩,英漢詩歌的異同由此也會看得更加真實。
結 語
具有現代意義的西詩漢譯始于新文化運動,但一百多年來,因為翻譯的方法不得當,致使西方詩歌的節奏沒有得到應有的重現。詩歌不同于其他文學體裁之處在于詩在傳情達意之外,還有其獨有的音樂性,而節奏正是營造詩歌音樂性的最重要的元素。詩之所以能更高效地傳情達意也正是因為有著音樂性的加持,因此,詩歌是一種有聲的藝術,尤其是格律詩,其音樂性更是詩歌不可分割的風格元素,一旦失去,其實詩已不成詩,誠如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譯成“床前的月光很明亮,以為是地上下了一層霜”一樣索然無味。凡做文學翻譯和研究的都知道文學翻譯的重中之重就是對原文風格的保留,否則千人一面、千人一腔,不僅美感不足,而且還誤導讀者,因此文學翻譯成敗的關鍵就是要看譯文是否能夠盡可能多地保留原文的風格,這已是翻譯界和文學界的共識。
然而,有了共識不一定等于就有了有效的翻譯方法。就詩歌翻譯而言,誰都知道音形意兼具的詩歌翻譯是“妙合”①參見龔剛、趙佼:《“妙合”:文學翻譯的佳境》,《當代外語研究》2020年第1期。之品,但實際操作起來,就會發現,兩種語言之間的距離貌似近在眼前,實則遠隔千山萬水:語言不合,文化不同。因此,詩歌翻譯欲達求真之彼岸,難于上青天。詩歌翻譯史上曾經有過的不多的妙合之譯往往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合,究其原因乃是以往翻譯的方法不符合詩學的原理,說白了,就是譯者大多只是查查詞典,順順意思,頂多控制一下每行的頓數,安排一下韻腳,就算完成一首詩的翻譯,從而使得原本難度極大的詩歌翻譯變成了一個極為容易的文字轉換,完全沒有復制“吟安一個字,捻斷數根須”的詩歌創作過程,這正是導致大量詩歌翻譯嚴重失真、缺乏詩意的原因所在。
為了還原英語詩歌的格律之美,本文作者提出了“以平仄代抑揚”的翻譯方法②參見王東風:《以平仄代抑揚,找回遺落的音美:英詩漢譯聲律對策研究》,《外國語》2019年第1期。,并用實際的翻譯驗證了這一方法的可行性③參見王東風:《論“以平仄代抑揚”的可行性:再譯〈西風頌〉》,《中國翻譯》2022年第4期。。從詩學的角度看,這一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詩的格律:音形意兼顧,既合得上節拍,又對得上聲律,押韻自是默認的操作程序。根據這一方法,可以以“平”對“抑”,以“仄”對“揚”,因為從發音效果上看,這樣的對應最為接近兩種音型的特征,尤其是英語中的重讀音節(揚),其典型聲調是降調,這跟漢字的去聲十分接近,而英詩中的輕讀音節(抑),其典型聲調是平聲,則與漢字的陰平十分接近。當然,這樣的對應與其說是建立在音型的對應上,不如說是建立在二者共有的詩學功能(poetic function)之上:抑揚也好,平仄也罷,都是構建格律化節奏的語音構件;抑揚或平仄所構成的“音節序列”,只要能滿足有規律的重復這一條件,就可以生成格律化的節奏。這也是這一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與原文節奏妙合的理據所在。一百年前,詩人兼詩歌翻譯家朱湘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國如今尤其需要譯詩。因為自從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只有些對于西方文學一知半解的人憑借著先鋒的幌子在那里提倡自由詩,說是用韻猶如裹腳,西方的詩如今都解放成自由詩了,我們也該趕緊效法,殊不知音韻是組成詩之節奏的最重要的份子,不說西方的詩如今并未承認自由體為最高的短詩體裁,就說是承認了,我們也不可一味盲從,不運用自己的獨立的判斷。我國的詩所以退化到這種地步,并不是為了韻的縛束,而是為了缺乏新的感興,新的節奏——舊體詩詞便是因此木乃伊化,成了一些僵硬的或輕薄的韻文。倘如我們能將西方的真詩介紹過來,使新詩人在感興上節奏上得到鮮穎的刺激與暗示,并且可以拿來同祖國古代詩學昌明時代的佳作參照研究,因之悟出我國舊詩中那一部份是蕪蔓的,可以鏟除避去,那一部份是菁華的,可以培植光大;西方的詩中又有些什么為我國的詩所不曾走過的路,值得新詩的開辟?①朱湘:《說譯詩》,《文學周刊》1928年第5期。黑體著重為筆者所加。
顯然,朱湘在當時已經清楚地看到了詩歌翻譯方法的不妥。在他看來,我們翻譯西方詩歌的目的之一是要引進“新的節奏”,從而為我國的詩歌發展提供借鑒。從這個角度看,用“以平仄代抑揚”的翻譯方法所譯出的西方詩歌就可以實現朱湘的這個目的,因為用此法譯出的英語格律詩就明顯呈現出了一種“我國的詩所不曾走過的路”。以十四行詩的翻譯為例,譯文所生成的那種“平—仄”簡單重復的節奏結構,與漢語近體詩中平仄同類相聚、交錯推進的節奏模式就形成了一種有趣的詩學對比。但以往的那種舊詩化的、自由化的和頓代化的譯文均無法直觀地體現出這種“新的節奏”,因而也就無法譯出朱湘所說的“真詩”。
看看一直以來被翻譯掩蓋得嚴嚴實實的西方詩歌的真容,再聯想到學界的一個共識,即中國的白話新詩是受西方詩歌的影響而產生的。這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明顯存在著一個缺環,值得我們反思。胡適的關門弟子、美國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在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大會上做了一個發言,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回顧過去八十年新詩的發展,我們向洋人去東施效顰,可說是一項也未學會,最后終于學會了一項,這一項便是‘一項未學’”。②唐德剛:《論五四后文學轉型中新詩的嘗試、流變、僵化和再出發》,歐陽哲生、郝斌:《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54頁。究其原因,正是因為我們通過翻譯來學習西方詩歌的方式出了問題:如果那樣的翻譯掩蓋了西方詩歌的詩體,那么我們最終還能學到什么呢?如果我們從中學到的僅僅是胡適所說的“詩體大解放”③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星期評論》1919年第5期紀念號。,那可真的是“一項未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