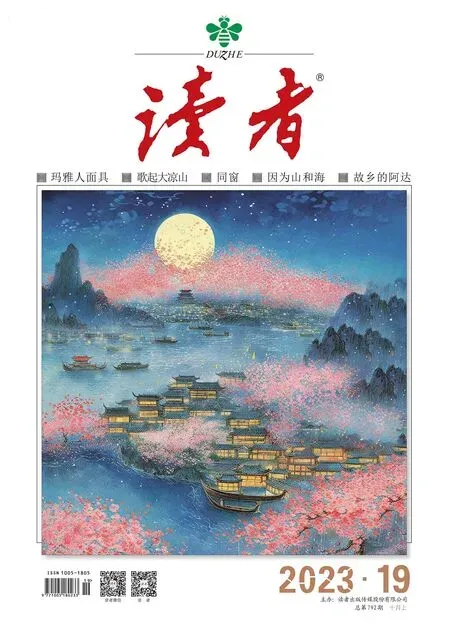歌起大涼山
☉王秦怡

妞妞們放聲歌唱
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有這樣一個神奇的組合——妞妞(彝語,女孩)合唱團。歌聲為妞妞們插上了夢想的翅膀,讓她們走出大山,登上中央歌劇院、中央音樂學院等國內一流的音樂殿堂。音樂對妞妞們還意味著什么?在海拔2000 多米的普格縣大槽鄉中心小學,妞妞合唱團的發起人、小學老師吉布小龍,在講起這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時說,女童命運的改變,更能體現一個地方的人文底色和思想進步。
小龍老師的合唱團
我不怕森林深處兇猛的豺狼,我翻過高山深谷看見了彩虹,爸爸媽媽不會永遠陪在我身旁,星星月亮伴著我,聽蟋蟀歌唱……
——《勇敢的妞妞》
認識吉布小龍的最好方式,是走入他的排練日常。
“我辦合唱團,首先是希望妞妞們能從中獲得自信,尊重別人,看見世界,做一個有愛的人。”這是吉布小龍對妞妞合唱團的理解。自信、見識、愛,任何一點都比表演的專業性更為重要。
在排練現場,妞妞們不用刻意保持隊形,想甩頭就甩頭,想跺腳就跺腳,想扭屁股就扭屁股。剛開始練歌時,有人捂著嘴哼哼唧唧,害怕自己唱錯音被聽見;有人一直摳手,掩飾自己的緊張;還有人把頭別到一邊,不看老師,肢體僵硬。吉布小龍就逗她們,故意做一個很丑的表情,等她們笑了以后,問她們:“你們覺得唱歌快樂嗎?如果覺得快樂,你們為什么不笑?”
大槽鄉多樹,也多山,螺髻山脈綿延整個鄉里,一年四季綠意蔥蘢。有時,吉布小龍會偷偷帶妞妞們離開學校,到大自然中去。當她們觸摸春天的泥土,看樹木抽出嫩芽,閉上眼睛感受森林的氣味,傾聽河流的聲音時,再害羞的孩子似乎也會被自然的氣息感化,興致勃勃,扯開嗓子唱一唱。
這種頗具前瞻性的教育,和吉布小龍有關,更和當地孩子的成長環境有關。
“現在物質條件越來越好,但鄉里很多孩子是留守兒童,爺爺奶奶只關注孩子的吃喝和安全,哪兒也不讓去。孩子們很孤獨,沒自信,也禁不住誘惑,看到回鄉的年輕人穿得光鮮亮麗,就想輟學去打工。”吉布小龍說。
吉布小龍想起自己的童年。學校在山路那頭,需要徒步1 個多小時才能到達。他常常滾著鐵環去學校,放學了就瘋玩,掏鳥窩,摘野果,在河里游泳。“很快樂,感覺自己無所畏懼。”他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正源于此,直到現在,他作曲的習慣還是想象那些畫面,或者到自然中去,“跟著云朵的形狀,就會哼出旋律來。躺在松林里,聽風吹松濤鳴,旋律浮現也在腦海里”。
妞妞合唱團唱的很多歌曲都是吉布小龍寫的。他希望孩子們有屬于自己的歌,而不是唱網絡上常見的“口水歌”。
所有歌中,他最喜歡《勇敢的妞妞》。那原本是他寫給合唱團里某個妞妞的——她住在另一座山里,父親已經去世。有一天,母親生病,她打著手電筒來鄉里抓藥。“她告訴我,好像身后有什么東西跟著她,她特別害怕。”吉布小龍寫下《勇敢的妞妞》來鼓勵她,用歌聲為她加油打氣,沒想到妞妞們都很喜歡。
聽見她們
哦嗚哦嗚,啊呀啦,到底向誰訴說。哦嗚哦嗚,啊呀啦,誰都聽見了。聽見了你呀,聽見了她,聽見了我們的夢。聽見了夕陽,聽見山風,聽見了我們的歌……
——《聽見妞妞》
現在,妞妞合唱團有30名學生。9 月開學后,因為初中在普格縣里,距離大槽鄉中心小學很遠,高年級的妞妞將離開合唱團。同時,更多低年級的妞妞將加入合唱團。
但在最初“招兵”時,孩子們可沒有現在這份熱情。那是2016 年,吉布小龍剛來到大槽鄉中心小學,他考的是音樂教師的崗位,卻受制于學校教師缺乏,成了數學老師和語文老師。最初更多是出于個人興趣,他拿著一個小本子,一個班級一個班級地跑,興沖沖地說了自己的構想,問有沒有人現場報名。一陣靜默。孩子們你戳戳我,我戳戳你,就是沒人舉手。
轉機發生在2018 年。具體彈了什么歌,因為什么,吉布小龍都忘記了。他只記得自己心情不好,拿了把吉他在操場邊的樹蔭下,自彈自樂,沉浸其中。彈著彈著,4 個孩子圍在他身后,跟著他輕聲哼唱起來。他心頭一動,問孩子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唱。孩子們點了點頭。吉布小龍給這個合唱團起名“陽光合唱團”。
之后,合唱團在音樂教室排練時,常常有孩子出于好奇,趴在窗戶上看,膽大一點的則直接蹲在門口。對于這些圍觀者,吉布小龍逮著了,就一定要問一句:“來不來?”就這樣,合唱團漸漸壯大起來。
排練之余,吉布小龍喜歡和妞妞們聊天,了解她們的家庭情況和理想。他發現,孩子們的夢想很局限,走不出這一座座山——有想當警察的,這樣自己家的牛羊丟了,就可以把小偷抓起來;有想開養豬場的,這樣就可以天天吃肉;還有想去鎮上開超市的,這樣就能賺很多錢。
在山區,相較于男孩,女孩更難掌控自己的命運。彝族女孩在15 歲到17 歲之間,有一場換裙儀式,換上成年女子的裙子,宣告步入成年,可以定親了。吉布小龍就有兩個16 歲的女學生,被父母或哥哥許給了同鄉。
越和妞妞們相處,吉布小龍越希望她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去北京參加演出,走在北京的街頭,看著燈火璀璨的摩天大樓,他告訴妞妞們:“你們看,哪一個人不是行色匆匆,為夢想奔波。你們也想來大城市吧?但沒有知識、沒有過硬的本領,待不了幾個月就得回家。”
如今,再問她們:“你們將來想做什么?”她們有的說想當警察,“因為想保護人民”;有的說想當音樂老師,“像小龍老師一樣”;一個皮膚被陽光曬得黝黑的女孩,等其他人都說完了,才語速緩慢地說:“我想當森林消防員。”她眼睛很大,說話怯怯的,但雙眼發亮:“因為我想讓小動物有一個安康的家。”
跟著音樂去過遠方,她們人生的夢想終于跳出了大山。
一個圓
阿甘拉仁,朋友很多。阿甘拉仁,總在忙碌,酒肉朋友把他拋棄在街頭。阿甘拉仁,偷偷在哭泣,這是為什么?阿吧吧,孩子哭著哭著就笑了。阿吧吧,大人笑著笑著就哭了……
——《阿甘拉仁》
越走近吉布小龍,越會發現,他與合唱團、與大涼山的故事像極了一個圓——他和孩子們的成長經歷高度相似,他是山里孩子的教育者,同時也是受益者。
在童年很長一段時間里,吉布小龍都很好奇:那些大卡車都開去了哪兒?車上的人呢,他們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作為土生土長的普格縣螺髻鎮人,他從小就看著各種大巴車、大卡車在鎮上來回穿梭。在讀大學前,吉布小龍的生活半徑僅限于縣里。
1999 年,吉布小龍升入初一,是村里當年小學畢業的25 個孩子中唯一繼續念書的。在填報高考志愿選擇專業時,吉布小龍想學音樂。父親不同意,拒絕支付他參加藝考的路費。母親悄悄塞給他800 元,那是她賣花椒的所有收入——那時,在山里人看來,把音樂當營生是不務正業。
等到了成都,吉布小龍才知道800 元太少,根本不夠吃和住,但他還是覺得“外面的世界太好了”。他長了很多見識——音樂專業藝考有“練耳”一項,老師背對著學生彈奏,學生要馬上回答出準確的音階。“老師彈完了,我沒說話。他又彈了一次,我又沒說話。老師就問我是怎么回事,我這才知道,練耳就是要把這幾個音都說出來。”
可能是彝語民謠打動了藝考老師,18 歲的他進入四川音樂學院流行演唱系,成為他們村里的第一名本科生。
2009 年大學畢業后,吉布小龍和一位藏族朋友組成“青稞蕎麥”組合,去北京、成都、昆明參加音樂選秀比賽,但通過海選后,都沒有下文。最難的時候,他兜里只有3 塊錢,靠著大口大口喝白開水充饑,早上一睜眼,想的是可以去哪家酒吧演出掙錢。
但那也是一段勇敢追夢的歲月。“音樂是我的精神食糧。那時,只有音樂能帶給我安慰,讓我看到前方的那束光。”靠著一把吉他和許巍的《藍蓮花》《曾經的你》,他熬過了一天又一天。
家鄉的風
螺髻山的風,吹不進媽媽的懷抱。螺髻山的風,越不過爸爸的肩頭。螺髻山的風,吹不落天上的雄鷹。慢慢地長大啊,吹痛我的臉……
——《螺髻山的風》
在外漂泊了3 年,2012年,他終于下定決心,回到大涼山,考取了家鄉的教師崗。
頭兩年,吉布小龍在木里藏族自治縣的小學任教。木里縣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端,要去那所小學,他必須先在西昌搭火車,再騎馬上山,單程需要14 個小時。山上信號差,每次和家里通電話時,他都得爬到山頂,反反復復找信號。
看到朋友們還在寫歌、出單曲,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覺只有自己與外面的世界隔絕了。“我時刻在斗爭,是去唱歌,還是繼續當老師?”
在和孩子們日復一日的相處中,吉布小龍找到了當老師的樂趣。生病時,他躺在房間里,孩子們想看望他又害羞,就趴在窗戶外靜靜地注視著。摘了梨子,撿了蘑菇,看到好看的花兒,他們也都像獻寶一樣送給老師。“他們身上有一種清澈透明的感覺,很純潔。”吉布小龍不再想“逃跑”,“我不僅在自己的世界里唱,還可以唱給這些孩子聽。”
之后,他從木里縣回到普格縣,先后在不同學校任教。再后來,他終于組建起自己的合唱團,妞妞合唱團從鄉里唱到縣里,又唱到全國各地。
吉布小龍最難忘的是妞妞們在中央歌劇院的演出。他至今仍覺得像做夢一樣——歌聲、樂器聲似乎穿過了他的身體,震顫著他的靈魂。從前,他和妞妞妞們在荒野中唱,在田埂上唱。那一刻,他和妞妞們站在國家級音樂殿堂,身后是國內頂尖的管弦樂團,“內心感到特別幸福”。現在,吉布小龍很想寫一寫家鄉的風,“小時候,我很害怕風。父母去守山上的羊圈,家里只剩我一個人,風從屋頂刮過,很嚇人。但現在,它給我一種安全感,風吹過來,像擁抱著我一樣”。
風吹啊吹,一代又一代人在山間長大,不同的是,新生一代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排云而上的風,吹起妞妞們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