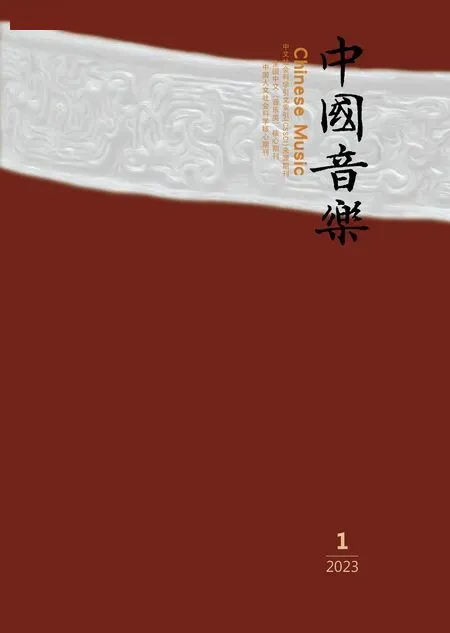“和聲”教學改革及教材編寫綜述
○徐平力
和聲學是音樂專業(yè)作曲技術理論的基礎學科之一,作為一門獨立的基礎學科,它肩負著學科自身建設、發(fā)展的重任,同時還要兼顧和聲與創(chuàng)作、和聲與其他作曲技術理論學科之間的協(xié)調發(fā)展等。
本文擬從中國樂派“8+1、思政+X”課程體系之“和聲”學科建設的角度出發(fā),在課程規(guī)劃及設想、課程特色及創(chuàng)新點以及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西方音樂結合等內容方面作一定程度的剖析與闡述。
一、中國樂派“8+1、思政+X”課程體系建設背景下的教學改革與教材編寫
(一)教材編寫的初衷
2016年年初,中國音樂學院提出“中國樂派”①“中國樂派”即中國音樂學派的簡稱,是以中國音樂元素為依托,以中國音樂風格為基調,以中國音樂家(人)為載體,以中國音樂作品為體現(xiàn),以中國人民公共生活為母體的音樂流派與音樂學派的合稱。“中國樂派”這一概念,最初是由中國音樂學院原院長王黎光在2015年10月首次提出。(參見王黎光:《〈中國音樂大典〉總序》,《中國音樂》,2022年,第5期,第5頁)建設之構想,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中國樂派“8+1、思政+X”②中國樂派“8+1、思政+X”課程體系,是中國音樂學院于2019年春季學期提出的課程體系理念。其中的“8”是指中國樂派8門核心的專業(yè)基礎課,即音樂基礎理論(包括視唱練耳)、和聲、曲式、復調、配器、中國音樂史、世界音樂史、民歌與戲曲;“1”是指包括專業(yè)主課和專業(yè)實踐課的各類專業(yè)課;“思政+X”是指國家規(guī)定的思想政治類課程與人文通識類課程,如英語、體育、第二課堂等共同構成的文化課板塊。課程體系理念,即“以立德樹人為根本,在西方音樂教育體系重視知識和技能的基礎上,從‘8+1’(為樂)、思政+X(為人)兩方面架構,將為進一步構建完善的中國音樂教育體系奠定基礎。”③《中國音樂學院舉行中國樂派“8+1、思政+X”課程建設學術研討會》,中國音樂教育新聞網(wǎng),2021年3月29日。
“中國樂派”的建設,需要人才的培養(yǎng),而人才培養(yǎng)的核心在于課程體系的建設。
中國樂派“8+1”“和聲”課程體系的建設,是在中國音樂學院中國樂派“8+1、思政+X”教學改革的大環(huán)境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原院長王黎光曾指出,音樂與舞蹈學學科建設的核心內容是如何構建中國音樂教學體系,這是中國音樂學院的“初心和使命”④王黎光:《構建“中國樂派”課程體系的學科基礎及實施路徑》,《大學與學科》,2020年,第1期,第25頁。。“中國樂派”課程體系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樂教中“育人”的教育理念,以人才培養(yǎng)為中心,遵循藝術教育規(guī)律,旨在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具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覺、國際視野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中國音樂高層次人才。
本教程⑤這里指中國音樂學院中國樂派“8+1、思政+X”課程體系建設之《和聲》教程。秉承著中國音樂學院“承國學、揚國韻、育國器、強國音”十二字辦學理念,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為發(fā)展目標,在中國樂派“8+1、思政+X”學科建設的基礎上,對現(xiàn)有和聲教材進行整合,同時對我院本科教學進行一定程度的分析與研究形成了這套完整的系列和聲教材。
(二)課程規(guī)劃及設想
本教程為高等音樂院校本科學生必修的一門音樂專業(yè)基礎課。
在音樂學院的教學中,和聲一般分為主科和聲教學(作曲及作曲技術理論專業(yè))及非主科和聲教學(包括音樂學專業(yè)、表演類專業(yè)等)兩大類型。
1.主科(作曲及作曲技術理論專業(yè))和聲教學設計
主科和聲教學分為本科前三年、本科后兩年及研究生教學等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本科前三年平臺課程—集體課(初級階段)
這是面向所有作曲及作曲技術理論專業(yè)同學而設的,它是以本科教學大綱為主,兼以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標準(程度)為前提,同時也為本科后兩年的專業(yè)和聲課學習做準備。學習年限為三個學期(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上學期),具體內容涉及西方大小調和聲、西方近現(xiàn)代和聲及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等。
(2)第二階段:本科后兩年專業(yè)課程⑥這里指凡修畢作曲技術理論(和聲、復調、曲式)A類課程,且考試成績均在85分以上(含85分)的作曲系本科學生,可以在本科三年級末提出申請,于四年級起修讀作曲技術理論專業(yè)。(參見《中國音樂學院本科人才培養(yǎng)方案》2018年版,第13頁“附則”)—個別課(中級階段)
這部分內容在四部和聲寫作方面以對位化和聲寫作為主,同時加入“綜合性和聲分析”⑦綜合性和聲分析,是指對音樂作品中的和聲進行及調性布局等涉及多聲部運動規(guī)律方面的各種現(xiàn)象及由此帶來的結構方面的變化等一系列綜合因素的分析。(參見徐平力:《和聲對位化寫作與綜合性分析》,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9頁),它對于已經(jīng)初步掌握傳統(tǒng)和聲的同學來講,所進行的是進一步的強化寫作訓練及理論方面的拓展。
在和聲理論教學方面,將傳統(tǒng)和聲課的教學內容,適當雙向延伸,擴展到中世紀教會調式和聲理論及浪漫樂派后期的各種調性擴張理論,加強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理論的學習與掌握,為研究生階段的和聲專業(yè)課的學習打下扎實的基礎。
(3)第三階段:研究生教學部分(高級階段)
這部分內容是以個性化、風格性教學為主,根據(jù)學生自身的條件及導師所指定研究的方向,進行論文寫作及相關內容的研究。
在和聲理論教學方面,以中國現(xiàn)當代作品和聲技法研究為主,兼有西方近現(xiàn)代和聲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等,在授課形式上可采用個別課與集體課講授及座談討論等多種授課方式。
2.非作曲(包括音樂學、表演等)專業(yè)和聲教學設計
非作曲專業(yè)和聲教學,其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的和聲思維能力、分析技巧以及對多聲音樂歷史風格的理解力,研究和聲的結構原理、應用以及其(和聲)在音樂作品中的意義的一種知識技能。
非作曲專業(yè)和聲教學與作曲專業(yè)和聲教學在教材上是統(tǒng)一的,但在學習過程中有所側重,如指揮專業(yè)的學生,可以和作曲及作曲技術理論專業(yè)的學生要求相等(如加強四聲部寫作訓練、鍵盤和聲及分析能力等);音樂學(包括音樂教育、音樂科技等)專業(yè)的學生,則注重和聲基礎理論知識的掌握(如側重和聲理論系統(tǒng)及邏輯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知),加強和聲分析能力及對作品風格的理解等,為其將來所從事的理論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對于表演專業(yè)(包括演奏、演唱)的學生則注重和聲聽覺(特別是和聲聽覺的“感性聯(lián)想”⑧和聲聽覺的“感性聯(lián)想”,是指我們在聽音樂時感受到和聲音響色彩的表現(xiàn)力及作品通過和聲這種表現(xiàn)手段所要傳達的某種思想、情緒等。)、分析等方面的訓練(如加強鍵盤和聲及和聲分析等),以便在其日后的藝術實踐中,發(fā)揮多聲部音樂聽覺的優(yōu)勢作用;而對于其他專業(yè)(如藝術管理系)的學生則根據(jù)其專業(yè)的需要,可以靈活掌握教學內容及教學進度。
具體做法:開始時可以進行一定的四部和聲寫作訓練,打下一定的多聲思維基礎。隨著內容的深入,逐漸過渡到以分析為主的學習模式,通過作品的綜合性分析,將學生的注意力引到對多聲部音樂表現(xiàn)力和風格的理解上來。這樣,用相同甚至更少的學時,便可以讓學生掌握更多的和聲知識,為后續(xù)課程“復調”“曲式”“配器”等課程奠定良好的技術基礎,提高公共共同課的教學質量。
(三)教材編寫的基礎
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和聲教研室自1981年學院復建以來,一直承擔著全院和聲專業(yè)課與公共課的繁重教學任務,同時緊扣著學科建設的目標推動學術研究和教學改革,經(jīng)過學科群體40多年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可觀的成績,累計在專著、譯著、教材、文論等方面的出版、發(fā)表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如下:
專著(譯著)教材共計39部;和聲(民族多聲)理論研究(如基礎理論、和聲教學、民間多聲、作品技法等)共計159篇;博士、碩士學位論文25篇⑨徐平力:《中國音樂學院和聲成果一覽表》(2022年10月統(tǒng)計)。。
主辦全國性大型學術活動2次,如2010年4月在北京中國音樂學院召開的全國和聲復調教學研討會;2011年11月在北京“美國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舉辦“音樂理論比較國際論壇暨《劍橋西方音樂理論發(fā)展史》中文版首發(fā)式”。
在教學改革方面,全國范圍內獨有或最早開設的課程(包括課型)有:現(xiàn)代和聲系列講座(1986年、1995年);和聲分析(1994年至今);和聲風格模擬寫作及專題研究,如巴洛克、古典、浪漫等不同時期(2013年);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分析與寫作(2014年9月至今);近現(xiàn)代和聲分析與研究(2006年3月至今)。
本教程以和聲教研室現(xiàn)有成果為基礎,對所授課程進行一次系統(tǒng)的教材編寫工作。
其目的之一:將目前已有的科研成果轉化為教學內容,這方面有許多前人的經(jīng)驗可以借鑒。
目的之二:改變以往“各自為戰(zhàn)”的教學狀態(tài),通過教研室全體同仁的齊心合力,做成一套具有中國獨立設置音樂學院和聲教學水準的、具有中國樂派民族教學特色的較系統(tǒng)完善的本科和聲學教程。
(四)學術交流與反饋
中國音樂學院教育教學中心分別在2020年11月21日及2021年7月18日兩次召開了“中國樂派‘8+1、思政+X’和聲學科評審會”,其間聆聽了我國和聲學界的前輩、專家、學者對教學改革的意見和建議,這對我們教材編寫工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此后,又根據(jù)原院長王黎光多次對于整部教材內容、篇幅等細節(jié)問題的審核要求,做進一步的調整(縮減),由最初的40.8萬字壓縮至目前的30萬字左右。
在教材編寫中我們采納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例如中國音樂學院樊祖蔭教授建議增加有關部分章節(jié)的內容,為此我們重新撰寫了“復合和聲”一章,內容包括復合和弦、復合調式及復合調性。對有爭議的相關概念也進行了修改,如一均(Yun)三宮改為一階三宮等。
中央音樂學院劉康華教授提出如何將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內容更好地融入到整部教材中,我們在相關章節(jié)中,如離調與近關系轉調、遠關系轉調方法、復合和聲、線性和聲與平行進行、縱合化和聲手法等章節(jié)都增加了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內容的比重。
此外,中央音樂學院劉錦宣教授希望留出一定的時間可以充實進一些關于同主音調式交替和弦以及遠關系轉調的部分內容;上海音樂學院張巍教授建議在課堂上能否將教學方法、內容的呈現(xiàn)方式與不同專業(yè)的需求體現(xiàn)出來,以適應不同專業(yè)學習的特點和不同層次的學習要求;沈陽音樂學院王進教授認為本教程很好地體現(xiàn)了“中國樂派”的教學理念,顯示出本次教學改革的前瞻性與民族化特色;上海音樂學院姜之國教授認為本教程的近現(xiàn)代和聲部分內容還不夠豐富,可再增加一些;中央音樂學院陳欣若教授認為本教程對傳統(tǒng)的和聲教學進行了有益的補充與完善,使學生學習的視野得到很大的拓展等。對此,我們在相關內容及篇幅方面也都做了一定(包括較大)的調整。
二、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的創(chuàng)新
中國音樂學院是以中國傳統(tǒng)音樂教育和研究為特色的綜合性高等學府,作為一所以民族音樂教育和研究為主要特色的音樂學院,我們始終堅持以民族多聲部音樂理論研究和教學為基礎,以學科建設發(fā)展為導向,在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等方面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和突破。
(一)繼承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的教學傳統(tǒng),創(chuàng)新、發(fā)展民族多聲部音樂理論
這是“中國樂派8+1”和聲課程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早在20世紀50年代,我系老一輩音樂家黎英海先生就出版了一部對我國和聲學發(fā)展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族和聲方面的學術專著—《漢族調式及其和聲》。這本書是以漢族五聲調式七聲音階為基礎,同時結合西方大小調和聲理論,對當時民族音樂創(chuàng)作等問題進行系統(tǒng)性歸納總結的一部論著。
20世紀80年代以來,張肖虎先生《五聲性調式及和聲手法》(1987年),樊祖蔭教授《中國多聲部民歌概論》(1994年)、《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的理論與方法》(2003年)、《中國少數(shù)民族多聲部民歌教程》(2008年)、《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寫作教程》(2014年)及楊通八教授《調式半音體系與和聲的現(xiàn)代民族風格》(1986年)等論著的相繼出版,進一步加強、鞏固了本學科在民族多聲部音樂教學及研究領域里的優(yōu)勢地位,作為學科基石的最重要的幾部專業(yè)著作,幾乎均出自中國音樂學院教授筆下,就理論建設而言,這些研究已經(jīng)成為該領域最重要的成果與核心內容。
樊祖蔭教授在我國和聲學界與民族多聲部音樂研究領域享有盛名,作為一位橫跨作曲技術理論與音樂學兩大領域的著名學者、理論家、作曲家、音樂教育家,他對中國傳統(tǒng)多聲音樂理論及五聲性調式和聲理論的研究,進行了富有開拓性的探索與實踐,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開拓創(chuàng)新,完成了一篇又一篇較權威、較系統(tǒng)地研究中國多聲部音樂理論方面的力作。其中《中國多聲部民歌概論》被呂驥⑩呂驥(1909-2002):中國著名作曲家、理論家、音樂教育家,第四、第五屆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譽為“是一部填補了有關學科空白的、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開創(chuàng)性論著”?樊祖蔭:《中國多聲部民歌概論》(上、下冊)“序”,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1年,第1頁。;《中國傳統(tǒng)多聲部音樂形態(tài)研究》?樊祖蔭等:《中國傳統(tǒng)多聲部音樂形態(tài)研究》,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20年。則被列為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該項目通過實地采訪、文獻收集整理、歸納、分析、比較等方法,系統(tǒng)地將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的民歌、說唱、戲曲、器樂及綜合性樂種中的各種多聲現(xiàn)象,作進一步深入研究,以求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的多聲部音樂形態(tài)的形成發(fā)展做出全面客觀的論證。
(二)創(chuàng)立“三位一體”?“三位一體”這一概念,最初是由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楊通八教授在其《2008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申報書》中首次提出。的專業(yè)課教學體系,對中西方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和聲理論進行系統(tǒng)、綜合性講解
所謂“三位一體”就是將西方古典—浪漫主義時期的大小調和聲技法、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技法及中西方近現(xiàn)代和聲技法等教學內容視為一體,按照和聲的自然音體系、變化音體系及調性擴張理論體系等三個板塊分別設課,分階段實施。
課程內容之一(大小調和聲部分)強調西方傳統(tǒng)技法的學習與掌握,力求做到訓練扎實、風格純正。
課程內容之二(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部分)是以重點形式開展的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技法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它是此次“中國樂派8+1”和聲課程體系建設的主要標志性內容之一。
課程內容之三(中西方近現(xiàn)代和聲部分)是和聲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也是作曲及作曲技術理論專業(yè)學生在理論應用于創(chuàng)作實踐等方面所必須掌握的和聲技能之一。
在編排順序上,我們采納了中央音樂學院劉康華教授的建議:在自然音體系部分將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與西方大小調和聲以各自獨立的方式分別進入;在變化音體系及近現(xiàn)代和聲理論部分則采用混編的方式進行綜合講述,這樣既保證了不同和聲風格基本內容在章節(jié)上保持相對的完整獨立,同時又將中西方多聲思維理論之交叉互融體現(xiàn)出來,在闡釋中西方多聲思維的差異與交融的同時,使所授課程的內容及進度盡可能做到“難易適中”“循序漸進”。
該體系以本學科的大量學術成果為支撐,立論合理、教學的可操作性強,彰顯國內高層次專業(yè)音樂教育和中國音樂學院的辦學特色。
(三)創(chuàng)新主科和聲課教學內容及教學模式
和聲主科教學與實際創(chuàng)作不可能同步,但是如果距離過遠,就會將和聲這門課變成單純的技術理論課,導致學用脫節(jié)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為此,我們在和聲主科教學方面,將傳統(tǒng)和聲課的教學內容(從古典—浪漫時期的大小調和聲),適當雙向擴展?童忠良:《突破二元 雙向擴展—兼論多元終止式的和聲理論架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第23頁。到中世紀教會調式和聲理論及浪漫主義后期的各種調性擴張和聲理論,同時在習題訓練方式上加入“對位化和聲寫作”?對位化和聲寫作,是指在四部和聲寫作的基礎上加以對位化處理的一種練習方式。(參見徐平力:《和聲對位化寫作與綜合性分析》,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頁)“綜合性和聲分析”“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理論教學及風格模擬寫作”等新的內容,使傳統(tǒng)主科和聲課的教學質量與教學水平得到提升。
(四)注重綜合性和聲分析,強化和聲公共共同課教學目的和意義
和聲公共共同課教學,其目的是培養(yǎng)研究和聲的結構原理、和聲應用以及和聲在音樂作品中的表現(xiàn)意義等知識技能。它以音樂作品為對象,綜合應用音樂形態(tài)學、風格學、分析學等多方面的理論方法,詮釋音樂作品中的各種和聲現(xiàn)象,探索和聲技法與音樂結構、審美及風格等因素的內在聯(lián)系,增進對和聲及相關音樂的理解。
在一般的和聲分析的教材中,往往以音樂作品的片段譜例作為和聲教學的內容的掌握與練習標準,這種孤立的解釋某種和聲技法的現(xiàn)象還不能算作是全面的和聲分析。全面的和聲分析應包括作品的整體結構、音樂內容、旋律音調、織體寫法等諸方面因素,對和聲現(xiàn)象(包括和聲風格、和聲序進、調性布局、和聲的陳述發(fā)展手法等)所進行全面的綜合性分析。通過分析可以從更高、更寬的層面上去了解和聲的魅力之所在及不同時期和聲運用的共同點及區(qū)別等。
(五)中西方多聲思維理論之交叉互融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近五千年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傳統(tǒng)文化就像一棵大樹,始終根植于華夏各民族深厚的土壤里,這與我國多年以來儒家所倡導的“禮儀之邦”“寓教于樂”等文化傳承相聯(lián)系。
儒家音樂思想的代表—孔子,是把音樂、人心、道德、人倫社會、政治等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構成一個循環(huán)的“鏈條”,它們是互通、互動、相互協(xié)調、相互因果,人心是根本,音樂是這一鏈條重要的紐帶。
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一個藝術門類,音樂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大背景下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來,并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古至今,音樂始終保持著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中國傳統(tǒng)藝術等方面的聯(lián)系。
中國傳統(tǒng)音樂(如雅樂?雅樂,是我國古代的宮廷音樂,形成于我國西周時期,它是指歷代帝王舉行祭祀朝會等儀式時所使用的音樂形式,它是當時禮樂制度的產(chǎn)物。雅樂的演奏形式在周代得以確立,它包含了遠古圖騰及巫術等宗教活動中的樂舞及祭祀音樂,也包含西周初期的民俗音樂。作為一種統(tǒng)治手段—禮樂教化的工具,樂舞藝術的地位和作用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參見樊榮:《越南雅樂的歷史》,《中國音樂》,2017年,第4期,第76頁))早在先秦時期就已達到一定的高度。據(jù)史料記載,當時已有多聲音樂出現(xiàn),但至秦漢失傳,以后形成的七聲音階是“奉五聲為骨干的七聲音階”(五聲性七聲音階,五聲由宮、徵、商、羽、角五個音組成,另外兩個則為“偏音”?古時候對五聲以外的音都稱為偏音。),最終被定位為“華夏正聲的五聲”?黃翔鵬:《七律定均·五聲定宮》,《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4年,第3期,第77頁。延續(xù)下來。其和聲、旋法、織體等已形成固有的傳統(tǒng)法則,這就是我國傳統(tǒng)多聲形態(tài)(和聲)建立的基礎,構建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理論體系是我國近代許多音樂家終其一生為之奮斗的目標。
我們知道,大小調和聲理論在我國已有百年的發(fā)展歷史?和聲傳入歷史,大約從1914年由高壽田翻譯過來的日本教材算起。(參見鄧波:《中國1949年以前的和聲與對位教學》,載楊通八、張韻璇、徐平力、劉青主編:《和聲對位教學論壇—2010年全國和聲復調教學研討會論文選》,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488頁)。一百年來,數(shù)代中國音樂家在音樂藝術創(chuàng)作中所做的最有意義的工作之一,就是探索和聲風格民族化的問題。
20世紀20—40年代,趙元任、黃自、青主等音樂家的民族風格音樂的創(chuàng)作,對多聲部音樂寫作風格做了有意義的探索和實踐。
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重慶國立音樂院的師生們對和聲民族化等問題進行一系列有益的嘗試,如對民歌進行收集、整理、編配。當時在此聚集了一大批在國內享有盛譽的音樂家,如江定仙、王震亞、黎英海等。這期間以王震亞所著《五聲音階及其和聲》最為著名,它是一部最早涉及民族五聲調式和聲方面的論著。
20世紀50—70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后,是我國多聲部研究歷史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許多作曲家、理論家(如江定仙、黎英海、吳式鍇、趙宋光等)在和聲民族化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與探索實踐,其中以黎英海《漢族調式及其和聲》為代表,它是我國第一部較權威、系統(tǒng)的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方面的論著,對我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的研究和發(fā)展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在多聲構成方式上,西方大小調和聲與我國傳統(tǒng)多聲思維有本質上的區(qū)別,用樊祖蔭教授的話來講,就是“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樊祖蔭:《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中國傳統(tǒng)多聲部音樂的思維特征與中西多聲結構差異原因之探究》,《中國音樂》,2016年,第1期,第78頁。。
西方大小調和聲是在一個調性框架內,以功能性序進(正格、變格、完全進行)為主,縱向上采用三度疊置,通過橫向的聲部進行來完成的“以協(xié)和的三和弦為中心,四五度關系為基礎的多聲部音高關系體系”?劉康華:《二十世紀和聲的基本結構成分及其衍生的音高關系體系》,載葉小剛、劉康華、黃蜀青主編:《當代和聲理論與教學研究》,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9年,第20頁。。
中國傳統(tǒng)多聲思維則是以橫向為主,各聲部以同一旋律為出發(fā)點,在進行過程中所形成的同一旋律的變體在縱向上的疊合所產(chǎn)生的多聲音響效果,它體現(xiàn)了“分合相間”的中國傳統(tǒng)多聲思維。
本教程所采用的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理論(如黎英海著《漢族調式及其和聲》、樊祖蔭著《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的理論與方法》)則是上述兩者相結合的產(chǎn)物。
《漢族調式及其和聲》是我國第一部以現(xiàn)代音樂理論研究五聲調式和聲的論著,這是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學術專著,它是一部融中西方理論之精粹的學術創(chuàng)新成果,也是當時我國研究五聲調式和聲較為少見的學術成果之一,該研究成果對我國當時乃至現(xiàn)在音樂創(chuàng)作都有一定的影響作用。
該書從所收集的歷史資料及全國各地民間民歌、戲曲作品等實例出發(fā)(結合西方傳統(tǒng)和聲發(fā)展理論),對我國民族多聲部音樂特點做系統(tǒng)、規(guī)律的總結,同時注重其(西方傳統(tǒng)和聲技法)與本民族音樂之間的借鑒、吸收、融合等方面問題,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述:“在專業(yè)音樂創(chuàng)作和教學中,我們要借鑒國外高度發(fā)展多聲部音樂的經(jīng)驗和成就,結合包括民間多聲在內的民族音樂傳統(tǒng),來發(fā)展、創(chuàng)造本民族的多聲部音樂。”?黎英海:《關于研究民間多聲部音樂的幾個問題》,《黎英海音樂理論選集》(二),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4年,第56-59頁。
《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的理論與方法》是一部具有21世紀開創(chuàng)性的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專著,它是在繼承前人(如黎英海、桑桐等人)成果的基礎上,所完成的又一部系統(tǒng)研究中國多聲部音樂理論方面的力作。
樊祖蔭教授作為一位兼有音樂學與作曲技術理論學術背景的著名學者,始終堅持認為:“音樂的民族風格是需要發(fā)展的,因此,在強調學習、繼承我們民族的優(yōu)秀音樂傳統(tǒng)的同時,也應該重視對人類一切優(yōu)秀音樂文化成果的借鑒與吸收,并力求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八十年來的中國專業(yè)音樂創(chuàng)作道路正是這樣走過來的。”?樊祖蔭:《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的理論與方法》,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3年,第297-298頁。
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與西方大小調和聲之間,盡管文化背景不同、表現(xiàn)手法各異,但也存在著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在調式—音階、和弦構成、和聲進行、調發(fā)展等方面均與西方傳統(tǒng)大小調和聲有一定的聯(lián)系?徐平力:《傳統(tǒng)音樂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黎英海鋼琴曲〈夕陽簫鼓〉和聲分析》,《中國音樂》,2007年,第4期,第114頁。;在縱合化和聲手法?縱合化和聲手法(也稱為以音列為中心的寫作手法),最初由桑桐先生在1979年第一屆和聲研討會上首次提出,它是一種有別于三度疊置及非三度疊置結構的一種近現(xiàn)代多聲部縱向結構組織方法之一,它的和弦結構直接受旋律因素的制約。嚴格地說,它是線性和聲思維的另一個分支。這類和聲手法的范圍較廣,涉及三度疊置與非三度疊置和聲,各種傳統(tǒng)的與非傳統(tǒng)的、特殊的與復雜的應用方法等。及綜合調式性七聲音階理論?黎英海先生對于五聲性旋律在發(fā)展中呈現(xiàn)出來的各種調式變化現(xiàn)象,提出了綜合調式性七聲音階理論。其特征是:“在旋律構成中表現(xiàn)為七聲音階內綜合兩個甚至三個不同宮的五聲音階,這里的‘間音’具有另一‘宮’的五聲音階音的意義”。(參見《黎英海音樂理論選集》(一),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4年,第27頁)等方面則與西方近現(xiàn)代和聲中的“泛自然音化”和聲手法?“泛自然音化”和聲手法,是美國著名音樂理論家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在其所著《1900年以來的音樂》一書中所創(chuàng)用的術語,它是指在自然音的基礎上,旋律與和聲均來自其自然音階的基本范疇,并可作各種自由組合:既可以成為三度疊置的三和弦、七和弦,也可以成為非三度疊置的各種縱向組合,但均要在同一自然音體系范圍之內。(參見桑桐:《和聲學教程》,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1年,第369頁)及巴托克的“調式綜合半音體系”?巴托克“調式綜合半音體系”,通常以某一音為軸,將兩個倒影關系的調式音階作縱向復合,所形成的各種不同綜合性調式音階(屬人工音階類),如七聲、九聲、十一聲、十三聲音階等。相近似,甚至在我國民間山歌中的“信天游”、民間戲曲音樂中的“散板”及江蘇民間器樂合奏曲《十番鑼鼓》中,也能看到西方后現(xiàn)代作曲技法中的“偶然主義音樂”?偶然主義音樂,西方現(xiàn)代主義音樂流派之一,指作曲家在創(chuàng)作中將偶然性因素引入創(chuàng)造過程中或演奏過程中的音樂。亦稱“不確定性音樂”或“機遇音樂”。它始于20世紀中葉,在西方有一定影響。偶然性的音樂因素在中國的傳統(tǒng)音樂中早已存在,如自由的山歌、信天游、戲曲音樂中的散板等。“整體序列主義音樂”?整體序列主義音樂,指20世紀后半葉,作曲家不僅把“音高”作為重要“參數(shù)”加以控制,而且還把“時值”“力度”“發(fā)聲法”等其他“參數(shù)”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整體序列控制。整體序列主義中的節(jié)奏序列部分,在我國江蘇民間的器樂合奏《十番鑼鼓》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其中的《魚合八》《金橄欖》就與西方20世紀后半葉的整體序列主義音樂有許多共通之處。的影子等。
正如樊祖蔭教授在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從和聲與旋律的關系來看,各種和聲手法,包括三度結構、四五度結構、二度結構、縱合性結構及各種復雜的近現(xiàn)代和聲手法,都有可能與五聲性調式的旋律相結合,在發(fā)展音樂的民族風格方面發(fā)揮其作用。手法總是越多越好,不同手法的運用有利于拓展五聲性調式的和聲,有利于把五聲調式拓寬為一個開放性的調式體系”?同注?,第297頁。。
三、教學的實踐效果
本課程自2020年秋季在中國音樂學院本科階段的教學中開始實施以來,共經(jīng)過兩輪完整的教學實踐(專業(yè)基礎課與公共共同課),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和實踐成果。具體如下:
1.采用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理論教學及風格模擬寫作—通過學習,使我們了解本民族調式和聲的發(fā)展現(xiàn)狀及規(guī)律特點,在繼承前輩探索經(jīng)驗的基礎上,不斷進取,開拓創(chuàng)新。
2.采用主題發(fā)展式習題寫作—此種練習可以在和聲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之間,起到一定的橋梁作用,為實際創(chuàng)作積累豐富的經(jīng)驗。
3.采用對位化和聲寫作—通過練習使我們在了解和聲的本質(縱橫一體化)的同時,縮短和聲與創(chuàng)作之間的距離。
4.采用綜合性和聲分析—音樂的構成,有賴于各種“參數(shù)”(音樂表現(xiàn)手段)的結合,各種“參數(shù)”相互依存成為音樂作品的整體。通過綜合性和聲分析,使我們了解到和聲的規(guī)則是如何從作品中提煉出來的,同時還可以看到作曲家們是如何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和聲的。
5.通過具體作品創(chuàng)作(西方近現(xiàn)代或中國現(xiàn)當代民族風格的多聲部音樂作品)的實踐,來提升和檢驗本課程的實際教學效果。
綜上所述,本課程解決了和聲課(包括專業(yè)基礎課及公共共同課)中長期缺少民族多聲部音樂風格訓練的問題,通過學習(如采用上述各種不同風格、題材、體裁、形式的練習),使學生比較系統(tǒng)地了解中西方現(xiàn)當代音樂作品中和聲技法運用的特點,同時為學生們創(chuàng)作出具有時代民族風格特征的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礎。
結 語
基礎學科教學系統(tǒng)的建設,歷來被各大音樂院校重視,因為它關系到學院人才的培養(yǎng)及整體音樂素質水平的提高。
中國音樂學院副院長黃虎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的中國樂派“8+1”課程體系建設分四步走的想法(思路)對我們的啟示非常大:首先是教學團隊的組建;其次是教學大綱的制定;再次是教材的編寫;最后是教學法的研究與實踐。
目前,中國樂派“8+1”課程體系建設背景下的和聲教學與教材研究(本教程的教學法實踐研究)也在同時進行,它是中國樂派“8+1、思政+X”課程體系探索與實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該課題擬對我國現(xiàn)有的和聲理論及教材等相關成果進行系統(tǒng)性的研究、歸納、總結。同時,從構建完善的中國多聲音樂理論教學體系的角度出發(fā),對中國樂派“8+1、思政+X”本科和聲教材進行一定程度的思考與探討,并提出進一步研究設想:
其一,在中國樂派“8+1、思政+X”課程理念、目標、方法、特色、實踐與效果等方面的基礎上,突破現(xiàn)有的研究方式,從“我國和聲理論發(fā)展歷史總結”“和聲教學研究”“和聲教材研究”“中國樂派相關研究”等方面入手,結合音樂專業(yè)人才的成長規(guī)律及教育規(guī)律,對現(xiàn)有本科生和聲理論教學與教材做更進一步的研究與思考,進而對研究生階段和聲課程的教學內容進行系統(tǒng)規(guī)劃與補充,同時針對“中國樂派”和聲課程體系建設的一系列相關問題進行分析與探討,以期為中國樂派“8+1、思政+X”和聲教學體系的完善提供參考。
其二,在中國樂派“8+1、思政+X”課程體系建設這樣大的環(huán)境背景下,從我國多聲音樂音高組織理論體系的構建出發(fā),通過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元素與西方不同時期創(chuàng)作技法之間的融合、不斷演變發(fā)展及所形成的個性化差異之間進行比較,對中國現(xiàn)當代作品中的音高組織技術作一定程度的分析和研究,以求得對于我國民族多聲音樂音高組織理論體系的形成、發(fā)展,做出全面、客觀的論證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