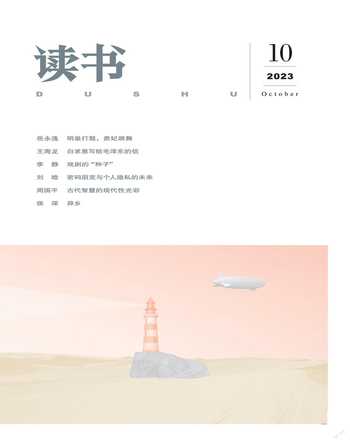被利用的性別
李爾岑
一八0三年,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的危地馬拉城正在進行一場特殊的審判,被控犯有男女同居罪的綽號“LaLarga”(“巨大的”)的胡安娜·阿吉拉爾(Juana Aguilar)因同時與男人和女人同居而受審。審理過程中,對胡安娜性別身份的界定很快成為超越審判本身的焦點——胡安娜疑似為“雌雄同體”。法官將胡安娜的性歧義問題遞交西班牙皇家醫學監察機構(the Royal Protomedicato),該機構委托醫生納西索·埃斯帕拉戈薩(Narciso Esparragosa)對胡安娜進行徹底的檢查,最終出具了一份精心編寫的醫療報告。在這份醫療報告中,埃斯帕拉戈薩指出,胡安娜的陰蒂異常巨大,達到1.5 英寸(約3.8 厘米),在其附近還有兩個橢圓形的腺體,而陰道區域則粘連在一起。他斷言胡安娜并非法庭所懷疑的“雌雄同體”,作為替代,他建立起一個新的“非男非女”的概念來適配胡安娜的性別身份。
受西方世界的“酷兒運動”影響,這場審判近些年受到關注。“酷兒”(Queer)原意“怪異的”,在前現代是所有性異常者的帶有歧視意味的羞辱用語,在現代的“酷兒運動”中,則被性少數群體解構為帶有對主流性別群體的抗拒意味的自我認同。胡安娜的酷兒身份與其遭遇審判的歷史事實使她(研究此案的各學者均稱其為“她”,故沿用)成為探討酷兒歷史,尤其是酷兒與政治關系歷史的一個切入點。拉美史、性別史學者瑪莎·弗(Martha Few)根據這份僅存的醫療報告,深入考察了醫生埃斯帕拉戈薩如何利用“畸形”話語與歐洲關于雌雄同體以及性別差異的醫學文獻相整合,建構起一個與歐洲主流性別差異的醫學框架不同的性別分類。在殖民社會對性行為的嚴密監管下,胡安娜的性異常導致她被懷疑具有與女性發生性關系的能力,埃斯帕拉戈薩對胡安娜的檢查報告則否認了這種可能,由于殖民法庭對“雞奸罪”的定義要求涉案方必須為男性或女性之一,而胡安娜——按照他的結論——是非男非女的,“在性方面是‘中性的,就像一些蜜蜂”,所以他建議法庭應當宣布胡安娜無罪。〔對此案的考察,見Martha Few, “That Monster of Nature”:Gender, Sexuality 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a “Hermaphrodite”in Late ColonialGuatemala. Ethnohistory 54:1 (Winter 2007)。另見Thomas A. Abercrombie,Passing to América: Antonio (Née María) Ytas Transgressive, Transatlantic Lifein the Twilightof the Spanish Empire .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8)。〕由于法庭文件業已佚失,我們今天無法確定法庭是否采納了他的建議,但值得關注的是,對當事人性別身份的界定,成為法庭審判的核心考量因素,醫生利用對當事人性別身份的重構,使一個人看到了脫罪的希望,同時,也使醫生自己確立起一個與大西洋世界迥然不同的醫學性別分類主張。
九年之后,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國,另一個性別成謎的人登堂受審。時值大清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三月,步軍統領吉綸等上奏匯報一起“女扮男裝欲行叩閽”案件。初一日皇帝圣駕自圓明園起程進宮,步軍統領所轄官兵在各處巡查防備,中營守備謝麟在大柳樹地方盤獲一名欲行叩閽之人,名喚劉三兒。叩閽系指民人通過攔住皇帝車駕的方式陳訴冤屈,是古代京控的一種方式。嘉慶朝在整個清代的京控案件歷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嘉慶帝即位時,外部面臨白蓮教危機的擴大,內部則有和珅權傾朝野,他將朝野內外危機歸因于民情無法上達,故嘉慶四年甫一親政,即要求所有京控案件必須奏報,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不得擅自駁飭京控案件(阿風:《清代的京控—以嘉慶朝為中心》,收入[ 日] 夫馬進主編:《中國訴訟社會史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這引起全國范圍內的京控熱潮,面對迅速激增的京控案件,從嘉慶中期開始,皇帝的熱情開始冷卻,大多批回控告人原籍之督撫予以審理,不再親自給出審辦意見。劉三兒亦不例外,經步軍統領衙門拿獲初訊具奏后,即奉旨交直隸總督溫承惠審理。
根據步軍統領衙門的初訊,劉三兒自稱直隸欒城縣女子,年十八歲,父親因沒有子嗣,故自幼將她作兒子養活,有一姐姐二妞于十七歲時嫁牛姓為妻,但因有氣迷病癥,被夫家休回,在二十五歲時病故。劉三兒聲稱,去年八月時族兄劉洛懷同子安老清盜竊她家財物,被她母親看見,還將她母親門牙打落兩顆,導致母親患病,她便在去年九月時來京告狀,被盤獲發至直隸總督解回欒城,卻并未等到知縣傳喚劉洛懷等質訊,而令她父親將她領回,十一月時,縣差衙役馮老修、崔老祥將她父親鎖拿逼詐,導致父親去世,她才于今年二月十八日騎驢進京,三月初一日候在西直門外等候,欲再次叩閽。
步軍統領衙門檢查過往案卷,確實發現去年劉三兒叩閽之事,當時發直隸總督審辦后,該總督已然將審理結果咨回,總督聲稱,實際是劉三兒患有瘋病,曾嫁給牛姓為妻,因病休回,劉洛懷偷竊是真,但被撞遇后,并沒有打落她母親牙齒,而是央求寢息,得到同意。去年劉三兒赴京,并非欲叩閽控告,而是因父母患病,欲赴京求醫買藥,父母勸阻后,她私自改裝為男子,潛行入京,被衙門拿獲后,妄供出諸般冤抑。總督在當時以劉三兒婦女無知,且系患有瘋病,故僅判交生母管束。此番再度進京叩閽,步軍統領衙門迅速發現一些信息矛盾之處,比如去年直隸總督審出劉三兒二十五歲,嫁給牛姓為妻,因病休回之情節,在本次審理中劉三兒則聲稱自己十八歲,未曾嫁人,尚為處女。就此,步軍衙門懷疑本案有不盡不實之處,故奏請轉發直隸總督再審定擬。
十七年六月,直隸總督奏報再審結果,在此次審理中,劉三兒的性別神奇地發生變化,總督聲稱,劉三兒實系“身具二形”,年齡確為二十五歲,也確實是她嫁給牛姓為妻,正因其“身具二形”,所以未能圓房,仍為處女,兼之愚傻倔強,不服管束,故被休回。此外劉三兒所告之處,仍屬全虛,其父母之死均系因病,并無差役鎖拿逼詐之事。總督奏請將劉三兒“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依律收贖。惟該氏身具二形,又復乖張多事,誠恐收贖之后另滋事端,應令該親屬領回鎖錮,毋任復出滋事”。
“身具二形”是傳統中國對于兼具男女性器之人的稱謂,與“雌雄同體”的概念類似。最初應從佛教“二形”概念演化而來,依佛家戒律,“二形”者不能受戒,故佛家對此概念比較重視。在傳統中國的社會觀念中,“身具二形”者同樣受到歧視,以“人妖”或“人痾”呼之。宋代筆記《癸辛雜識》“人妖”條載: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后奸狀不一,遂置之極刑。
僅僅因婢女身具二形,即處以極刑,多少反映時人對性別異常者的厭憎。明代《萬歷野獲編》“人痾”條稱:“晉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此又與胡安娜“雙重納妾”之罪名想象何其相似?
問題在于,劉三兒真的“身具二形”嗎?從步軍統領衙門時的閨中處女,到直隸總督衙門時的身具二形,劉三兒的性別已然成謎。問題的突破口在于步軍統領奏報時透露出的信息:“現經奴才衙門飭令穩婆相驗,據報劉三兒實系處女。”也就是說,在劉三兒交直隸總督審理之前,步軍統領衙門已然派穩婆對劉三兒的性別予以識認,若劉三兒果系“身具二形”,早在步軍統領衙門時即應驗明出來,何以步軍統領衙門所派穩婆驗出處女之身,至直隸總督處卻忽成“身具二形”?其中的奧妙,或許正在于步軍統領衙門對前后兩次審理情節矛盾的揭露上。在前一年的審理中,直隸總督審出劉三兒曾經嫁人,咨送步軍統領衙門存案。而在本年的審理中,步軍統領衙門卻驗出劉三兒的處女之身。于直隸總督而言,如何彌縫“已經嫁人”與“仍系處女”間的矛盾,是他此次再審的重點。恐怕,直隸總督溫承惠正是為彌合兩次審理間的矛盾,借“身具二形”的性別身份,彌補了兩次審理間的情節矛盾,最終更是以此為據,將劉三兒判由親屬領回鎖錮。可惜的是,如此明顯的前后矛盾并未獲得注意,無論是皇帝、總督、統領,抑或刑部,都早已對京控中的雀角細故喪失了耐心,劉三兒的性別,就此以“身具二形”留存于清朝檔案中。而她的真實性別,無人在乎。
這誠然是個有趣的歷史巧合,世界的兩端,相近的時間,兩場關于性別的審判。兩場審判中,兩個人的性別成為他人利用的資源,一個成為闡發醫學主張的根基,一個成為應付詰審的托詞。歷史、文化均迥然不同的兩地,對這兩場審判進行褒貶顯然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是這兩場審判使我們在晦暗的過往瞥見了兩位成為“話語”的酷兒,他們的性別身份被制作、利用、審判,他們的命運、他們的人生則淹沒于漫漫歷史長河中不再浮現,僅存這兩朵小小的浪花,使我們了解到其人生中浮光掠影般的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