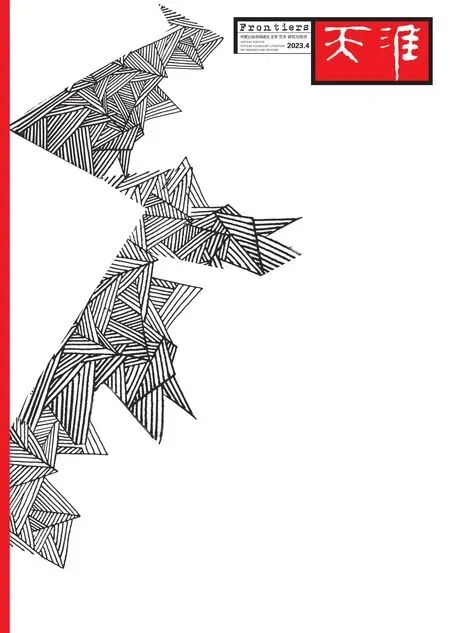想念之河
習習
一
小時候,夢見母親死了,我抱著母親哭得喘不過氣來。第二天,眼睛一刻不離追著母親,眼淚終于蓄不住了,嚎啕大哭,母親問我怎么了,我給她講夢里的事。母親說,夢是反的,你的夢是在給夢里的人添壽。
現在我很想做這樣的夢,但很難做到。不過有一天我確實夢見她了,夢里,母親要我在一本印滿字的書上寫下身高、體重、喜歡吃的東西……她要做什么?我詫異地回憶起寫下的是我孩提時的身高、體重,我孩提時最想吃的油條。我順著逼仄的空白寫了一溜兒,像在書本里擠進了一條歪歪扭扭的長隊。母親拿過去,像老師檢查作業一樣,拿起一支筆要批閱。但她握不住筆,只是不受控制地在我的字跡上畫了個符號,一個很奇怪的符號,我最終沒能在夢里記住它。
二
我現在的年齡是母親離開家時的年齡。現在,母親病了,他們還回一個生了重病的母親。
母親一生有兩個階段、兩個家。對我來說,母親一直是我小時候的母親。母親自己記得最清的是她的第二個家,她和他們說、笑、哭。我倒像個老人,想到的、能說的全是過去的事情。我藏匿在往昔不能自拔,像個隱形人,心里默念的都是淵源。我想告訴他們一切都有來路,哪怕再彎彎曲曲,但沒人關心來路。我看到的是母親的根,他們看到的包括母親現在看到的都是新生的枝葉,以及新生的衰朽的枝葉。根在地里沉默,我黯然不語。
對我來說,母親也是兩個階段的母親,一個是我年少時的母親,另一個是現在被病魔纏住的母親。我總是力圖在二者之間畫出來龍去脈,但畫到中間常常虛茫到沒有著落,于是又趕忙回到現在。現在,母親甚至記不清我的名字,她呆呆看著我,很努力很辛苦地尋找記憶。現在,她馬上把自己也要忘了。我還深記離開家幾十年后母親第一次看到我們時一臉狐疑說的一句話,我的娃們怎么都這么老了啊!這是和我們每個人命運相關的事件,板結得十分厲害,滲透各種悲苦,母親無力看穿它。她讓我們流浪了那么久,她記得的當然是我們年輕時的樣子。
三
母親的紅高跟皮鞋藏在我家放雜物的柴房子里。那是個象征,象征母親蟄伏起來的理想。雜亂的柴房子是藩籬,紅高跟皮鞋和柴房子是反義詞、是對抗,它們在我家小院暗暗絞殺了那么多年。那是母親少女時跳交誼舞穿的鞋。母親偶爾拿出來,擦干凈再小心翼翼地放進柴房子里。母親拿出那雙紅高跟皮鞋的樣子我深深記得,我甚至還能描摹出她臉上的神情。那是我少女一樣的母親,是生過三個孩子后藏起來的另一個母親。高跟鞋流光溢彩,高跟鞋跟著節奏旋轉、起舞,三步、四步,快三步、慢三步。母親最愛跳快節奏的三步舞,嘣嚓嚓,嘣嚓嚓,鳥兒一樣飛啊飛,忘了地面。“藍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樣,寬闊的大路上塵土飛揚……”后來,那個藏起來的母親義無反顧穿著她的紅高跟皮鞋離開我們了。
四
甚至都來不及把時間延伸過來,把這根硌人的粗麻繩捋直,看看它在哪里打結,在哪里藏進了時間,何時開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比如,母親都未曾問到我的弟弟后來怎么樣了,作為家的屋子怎么樣了,屋里那個裝滿她衣服的大衣柜怎么樣了,窗戶上她設計的窗簾怎么樣了,廚房里的大水缸怎么樣了,我父親親手做的高低床怎么樣了,鑲了一圈亮閃閃的泡泡釘子的格子沙發怎么樣了,那根長長的搟面杖怎么樣了,那個可以燒得通紅的鐵疙瘩烙鐵怎么樣了……
他們吵吵嚷嚷,講現在的母親,我突然對著一臉茫然的母親插進一句莫名其妙的話,媽,那個鐵皮的小針線盒我還存著。
那是個用馬口鐵做成的小盒子,盤花鐵扣,外表的漆快磨光了,里面還放著很多母親用過的針線、零零散散的各色扣子。那個時候的縫衣針很剛硬,再細都不彎折。那個時候流行子母扣,子母扣扣起來很親,名字也很甜蜜。
五
母親現在是我的孩子了。
背母親去廁所,背母親到床邊,背母親到椅子上。母親說不出話了,她的眼睛也空洞得說不出話了。起初她聽別人說話時,總是不斷點頭,不管別人是不是對她說的。后來我看出她點頭時有些懊惱,因為她實在不知道別人說的啥。現在她不懊惱,格外安靜。我說,聽話哦。我把母親臉頰上的頭發捋到耳朵后面。我不停地看她的臉,我想把多年沒看到的母親都看回來。我坐在她的腿旁,摸她的手,搓她手指上彎曲的骨節。這手受了多少苦啊,但她后來的苦我已經無法知道。我不注意時,母親歪在凳子上睡著了。
從此以后,我將是我自己的母親。
六
我有個名字,這個世界上只合適母親呼喚。“蛋娃”“蛋娃”“我的蛋娃”,母親用我們的方言這樣呼喚。母親上午班、下午班的時候,我懶在炕上不去幼兒園。快到中午了,母親圍著圍裙要和面時,才喊:“蛋娃,蛋娃,我的蛋娃起床了”。母親把我抱到窗臺的小凳子上曬太陽。
母親上午班、下午班的時候,我家小院的天總是晴的,太陽特別好。

七
母親那時黑瘦黑瘦的,總是很困倦。工廠三班倒,上完早班回家的路上,她得在半途坐坐才有氣力走回家。做晚飯前母親總要先和衣睡一覺,我們誰都不能吵,連翻書的聲音都不能有。有一次,我和姐在炕沿下抓杏核,吵醒了母親。母親一伸手,扔下掃炕的笤帚,芒刺扎到我腳面上。我哭了,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哭一定不是腳疼,是覺得母親心狠。晚飯后,母親沖了兩碗白糖水,悄悄給我一碗糖多的,我和母親會心一笑。父親打我,我的反抗是飲泣,忍著不哭出聲。母親不小心打著了我,我哭得驚天動地,就是要母親聽見,她打了她的蛋娃,她把她的蛋娃打哭了。
那天,我看見母親哭了,是身體條件反射出來的哭。她起身那一剎那,彎腰那一剎那,身體折住的時候,像嬰兒一樣皺眉、哭,眼角滲出淚來。是疼嗎?她現在疼也說不出來。她現在的哭和她的心也沒多大關系。一棵老樹,病了,疼了,流出了汁液。
八
母親的工作是織襪子。那正是尼龍襪子流行的時代,尼龍多么好啊,它幾乎成就了母親所在的襪子工廠。尼龍襪子有彈性,花色豐富,顏色不掉還不容易破。抹了香噴噴的雪花膏和頭油的女工們進出工廠,她們在我心里就和母親一樣,真的像花兒。女工們站在一排機車前面,圍著白圍裙,戴著白帽子,一針一針把襪筒戳進鏇子上細密的牙齒里,頭頂各色尼龍線飛舞,機器下面,吐出一截一截漸漸成形的襪子,襪子下面墜著一個大鐵疙瘩。假如誰要站著打瞌睡,鐵疙瘩就會跟著織出的襪子剛好重重砸到腳面。母親說起那個稱砣一樣的鐵疙瘩時,常常如釋重負,因為她的腳始終沒被鐵疙瘩砸中。白圍裙上,“為人民服務”四個字彎成一個紅色的半弧,剛好在胸前。女工們的白帽子邊上露出的劉海落著一層毛絮,那層輕輕的毛絮我覺得也很好看。尼龍襪子結實,但最怕火,冬天,即使第二天著急穿,也不敢把它放在爐子上烤。每年快過年,女工們會分到一打襪子。一打是12 雙的意思,我從小就知道。12 雙襪子對應12 個親人,數量剛剛好。隨機抽的一打襪子,男女老幼的都有。運氣好的,抽到的都是大人的襪子。我們一家,還有姥姥、舅舅、舅母和姨娘,少一雙都不夠。襪子大了,把尖兒折過來縫上,等腳長大了再拆開。我最喜歡鮮艷奪目的尼龍襪子,但多半都不能如意。母親老是說,我的蛋娃其實穿素色最好看。穿衣服也是,即便到了過年,母親還說,蛋娃還是穿素色吧,穿素色的衣服好看。母親總說這話,這話就成了一個暗示,暗暗形成一股力量。母親離開家的這幾十年,我很少穿艷麗的衣服,包括對很多事物和事情,都有了這種傾向。素色不喧嘩,和大部分時候的我一樣。但母親不是這樣啊,愛穿紅高跟皮鞋的母親,一直穿各色鮮艷的衣服。幾十年來沒看見的母親,我們在她的新相冊里看到了。五彩繽紛的母親,歡樂著,笑著,艷麗的母親依偎著別人,像小鳥一樣。
這朵用白尼龍編織的精致的小花和母親喜歡的鮮艷形成反差。一朵在1976 年反復用過的小白花。那一年人們不斷悲痛、流淚。只有織襪廠的家屬們擁有這樣一朵別致的小白花。用別針把小白花別在胸前,在針織廠隔壁的大禮堂里,在耳郭里終日回響的哀樂中,跟著緩緩前進的隊伍,緩緩地進入禮堂參加祭奠,再緩緩地走出,緩緩地走在大街上。人們表情凝重。那一年,哀樂不斷響起,以至于我們玩耍時,嘴里哼哼的都是這樂曲。這朵尼龍小白花勾起的回憶里,除了反復悲傷的人們,里面最鮮明的還是母親的影子。母親所在的織襪廠,機器轟鳴,漂染車間上空,終日蒸騰著白色的云朵。女工們整齊地站在一排機床前,母親就在她們中間。機器有節奏地轟響,女工們喊著說話。母親說機器的聲響很容易叫人打瞌睡,所以鐵疙瘩才不斷砸到女工的腳上。夏天酷熱時,我們能喝到工廠發給工人們的彩色汽水,滿滿一大搪瓷缸子,鮮艷的汽水非常甜。
母親的白圍裙和這朵尼龍小花我都存著,白色的尼龍小花還雪白如初。
九
我能憶起的生命里和母親相關的最早的情景是,躺在母親的肚子上玩。母親那么瘦,我那時該多小?我上中學時,和母親睡一個炕。臨睡前,關了燈,和母親在被子里說話,基本都是我講母親聽,一個白天的事,拉拉雜雜,一口氣講不完,講學校、講老師、講班上的男同學,我可能害羞了,在被子里扭捏,母親總說:“你的樣子,怎么跟個蛇蟲子一樣。”
母親有海綿般溫柔的天性,她可以一直耐心地聽我說呀說,從不批評我。她總是很困倦,我知道有時候她只是做出聽的樣子,其實已經睡著了,但這有什么關系呢?
十
大白天,在炕上做夢,夢里的東西在長,越長越大,大到天上,這樣的夢一來,母親就說我又發高燒了。小東西們長啊長,長啊長,大得嚇人,被它們擠著,迷迷糊糊總睡不醒。我成家之后,有一回,又被夢里長大的小東西們擠住了,醒不來,但清晰地聽見母親坐在床邊拿蓖子蓖頭發,唰——唰——唰,一下又一下,我都能想到母親蓖頭發的樣子,然后又聽見地里的小蟲子在叫。最先,在大院的土坯房里,我能聽見屋里泥地下的蟲子叫,母親不信。我家樓房的水泥地里,也有小蟲子叫。這是很難形容的叫聲,又遙遠又清晰,又微渺又明確,但確乎是小蟲子的叫聲。掙扎著醒來,就我一人病在床上,環堵蕭然,母親早幾年就離開家了。
我還想起小時候,半夜總聽到碗柜子里碗碟的聲響,母親說先人們來找吃的了。那時候先人們也總挨餓嗎?母親說娃娃里就我眼睛亮,所以身體最弱。我的尕爹,一見我,就說,這個娃能長大嗎?他抓著我的胳膊比畫著說,和柴棍棍一樣細,一撅就折了。我高燒不止時,母親倒碗清水拿把筷子到屋門口,嘴里念念叨叨,那把筷子就端端地站到了碗里,這時,母親很生氣地拿刀背把筷子一下砍出去,大聲說:“哪里來的到哪里去!再不要靠近我的蛋娃了!”
十一
母親的單位三班倒,母親下夜班回家,天還沒亮。我在被子里偷偷聽她是否掏出了鋁飯盒,是否把飯盒放在了桌子上。母親去睡覺了,我們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打開飯盒,看里面是否有好吃得要命的油條。油條太香了,可以和肉媲美。一根油條切成三截,我們姐弟一人一截。油條真是與眾不同,每一截臉對臉還可以分成兩塊。我舍不得一下子吃掉好吃的東西,兩塊油條可以吃許久,像吃水果糖,把它放在玻璃糖紙里咬成很多碎塊兒,這樣就能在嘴里斷斷續續含一天。
母親上早班后,我能繼續睡個長覺,起床后,時常看到母親給我的零花錢壓在透明玻璃杯下面。
母親的溫暖是持久的,線形的柔緩的溫暖,從來沒有中斷過,即便她離開了我們的家。那溫暖一直長進了我的時間,延伸到了現在。那溫暖里不僅有單純的母愛,還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內容,如同切面的寶石,每個棱面都折射光亮。
十二
一條老舊的不長的街道,就在我們一直生活的城市里。它像一個破折號,連著兩個時空,一頭是過去,另一頭是現在,一邊是多少年未見的母親,另一邊是我們。我們曾在大街小巷,嗅著蛛絲馬跡無望地找尋她。很難想象,幾十年里,就在同一個城市,我們如同近鄰。我們被同一天的雨打濕過,同一天的太陽和月亮照過我們。我們或許還有過小小的失之交臂或者摩肩接踵。但無論如何,幾十年后,我們才看出這個破折號的存在。幾乎和成千上萬條破舊的老街一模一樣,我第一次去母親現在這個家的時候,竭力用眼睛默記著街上的一切,唯恐把這個地方再弄丟。母親第一次出醫院時,還有模糊的意識,在靠近這個破折號的時候,看著車窗外一掠而過的街景說,這家的面好吃,那家的點心好吃。
多么殘酷,這家的面我們吃過,那家的點心我們也吃過。
十三
我和母親住在郊區的表姐家。花花表姐,大舅的女兒。表姐家靠近黃河,地里種茄子、辣椒、西紅柿、黃瓜。我跟著母親,在菜蔬快長起來的時候,幫表姐在架子上扎西紅柿和黃瓜的藤蔓,用的就是母親所在的織襪廠廢棄的線團。那個晚上,睡在表姐家的大炕上,關了燈,我第一次感知到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在我們生活的大院,晚上關了燈,也有工廠的燈光映入窗簾。像被巨大的黑色翅膀罩住了,我無法呼吸。幸好又斷斷續續響起母親和表姐拉家常的聲音,然后,又聽到遠處地里的青蛙在叫,心緒立刻平緩了。傍晚下了陣急雨,青蛙的叫聲一下子把雨淋過的黑夜拉到很遠。黑暗和寂靜有著類似的品質,它們一旦結盟,叫人孤單到不知所措,幸好有母親在身邊。
花花表姐活著時,總說我不好好吃飯。我抗拒那時的湯面,很不喜歡碗里漂著的油熗過的蔥花。表姐見我不好好吃飯,會和母親說,你看尕蛋,又用舌頭數著面條子呢。
母親已無法知道,她疼愛過的那個侄女很多年前就去了另一個世界,她也不知道,我在這個世上點點滴滴認知的長河,很生動的一部分發源自她那里。
十四
上小學時,我個子小,排隊總在第一排。課間操結束后,班主任給同學們訓話,習慣把交疊的雙手放在我頭上,我幾乎緊貼著她微微隆起的腹部,我喜歡這樣,一動不動,用頭認真地支撐著她的手。她問,你頭發上抹的啥?我說,發蠟。她接著問,誰給你抹的?我說,我媽。母親那時很喜歡在頭發上抹香香的東西,先是玻璃小瓶里的頭油,后來是發蠟,軟軟的發蠟裝在鐵皮圓盒里。母親那時很瘦小,開家長會時,班主任總以為她是我姐。我告訴母親,老師說她是我姐,母親很高興。我的短發是母親剪的,一直到上中學。我的頭發又硬又燥,稍微長一些,脖子后面就撅起一條尾巴,大家都叫我公雞頭。母親給我抹發蠟,多半是為了制服那條燥亂的公雞尾巴。我告訴她,人家叫我公雞頭,不知為何。母親聽后,總要笑啊笑,前仰后合,笑出眼淚。
十五
大雨如注,沖刷著窗玻璃。我說,媽,下大雨了啊。母親定定地看著窗戶,仿佛世界的變化和她無關了。
這樣大的雨幾十年前的一個夏天也下過一次,晚飯后,我去同學家玩,一直等到突如其來的大雨停歇。回到家,我看見穿著短褲和二指背心的父親滿臉怒氣坐在樓道臺階上。他倒垃圾時,風把門鎖上了。我也沒帶鑰匙,我們在臺階上坐到很晚,一直沒等到下班的母親。我跟著父親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游走,父親一刻不歇地在斥罵我。后半夜真冷,我們躲進醫院急診室,像病人一樣,我虛弱不堪地在長條椅上半躺著,繼續聽父親的斥罵。天快亮時,我去母親單位門口等她,遠遠看見母親和幾個女工走來,我顧不得害羞,跑過去放聲痛哭,攢了整整一夜的眼淚啊。雨水淹壞了馬路,沒有公交車,母親沒辦法托人帶話,她當時住到了一位女同事家。我拿到鑰匙回家,父親還那樣坐在樓道臺階上,一夜沒合眼的他,依舊目光咄咄。我身心俱疲,躲進小屋里飲泣。父親所有的斥罵,都不像在罵自己的女兒。整個夜晚,我跟著他孤苦游蕩,幾乎聽完了他搜刮盡的人世上所有可以罵人的話。
現在我知道了,一切都有淵源,那個大雨之夜,是個跡象。父親不是在罵他的女兒,他把所有對母親對女人的怨恨全都像暴雨一樣潑到了我身上。
其實那天夜里,孤苦無依的不單是我,還有獅子一樣強悍的父親。
十六
“一天,娟娟正在吃西紅柿,西紅柿的汁不小心掉在了白襯衣上……”這是我小學時站在講臺上給同學們講的一個小故事,老師布置的作業。母親從報紙上找到這段文字,抄到筆記本上叫我背熟。我還記得母親教我的動作,伸出食指,歪著頭,開始講:“一天,娟娟正在吃西紅柿,西紅柿的汁不小心掉在了白襯衣上……”這個故事其實是普及一個小常識,怎么洗掉掉在衣服上的西紅柿汁。那時水果少,西紅柿既可以當菜又可以當水果,我想,這個小故事對當時的同學們很有用。母親的字跡,纖巧又倔強,里面夾雜著好幾個繁體字。在紅色塑料封皮筆記本的最后幾頁,母親把這篇題為《醋能去掉果汁的污染嗎?》的短文抄了三遍,后面打了個括號,括號里是我的名字。是的,藏在本子里的我的名字,和母親在筆記本的那一角的字跡相會。
十七
還是這個紅色塑料封皮筆記本,扉頁上,母親寫了這樣幾行:日記我來記/里面有秘密/誰要看日記/必須我同意/我要不同意/那你別生氣。
塑料封皮已經破損,無需打開,遠遠看著它,往昔就從那里撲面而來。
本子里夾著很多發黃的零散紙片,有一張發票,我反復看過多次。
一副茶晶眼鏡,四十元整,開票時間是1983年6月21日。這是我們全家熟知的一小截歷史的開頭——父親在一家眼鏡店買回這副茶色鏡片的茶晶眼鏡,結局是這個眼鏡在不多年后以誰也預料不到的方式遺失了。那時,父親常說,茶晶眼鏡的鏡片是水晶磨成的,水晶里有活水,女人們萬萬摸不得。他對這副昂貴的眼鏡倍加愛惜。那天,酷愛看電影的父親戴著這副心愛的茶晶眼鏡去看一部外國電影,不知是哪部片子,父親說電影故事情節很緊張,所有人從頭到尾眼睛都顧不上眨巴。回到家,父親才想起看電影時把茶晶眼鏡放在了腿上,父親一直在電影情節里沒回過神來,等他發現眼鏡丟失再跑回電影院時,下一場電影已經開演。丟了心愛的茶晶眼鏡,父親多年不能釋懷,他總說那副茶色的水晶眼鏡,好到世上無雙,即便攢足了錢,也再遇不到那樣的好鏡片。父親就是這樣啊,一輩子喜歡反反復復說那些叫他愁悶又無法更改的事實,而且,他愁悶的時候,也要別人跟著他一起愁悶。
筆記本里還有保健站給母親開具的一張請假條。母親生弟弟時難產,失血過多,身體虛弱,保健站建議母親多休息三周。弟弟生于那天的上午八點,母親那年二十七歲。
舊物藏在本子里連點成線,叫人遐想,又叫人心碎。我再次拿出那張黑白照片的底片。
那天的情景歷歷在目,父親背著好幾個白蘭瓜,我們一家人過了黃河鐵橋,到北山上的公園游玩。那是記憶中唯一一次我們的全家游,我借了同學的相機,那天我們拍完了一卷膠卷。
時間停在膠片上,帶著沒有被它改變的寧靜和單純。
沒有人能預知后來的生活。那天我們暢快游玩后,半夜下起大雨。我們干燥的城市,在盛夏過于燠熱的一天,總會醞釀暴雨,那天半夜,屋頂漏起了雨,父親和母親拿來盆盆罐罐放在炕上,雨水滴滴答答響成一片,我們全家只能橫七豎八地躺在炕上干燥的地方。
那是一張合影,父親和弟弟。那時的白蘭瓜能甜到蜇疼舌頭。父親和弟弟,都端著一牙瓜,望著鏡頭,笑得那么開心。我拿著這張底片在燈光下反反復復看呀看,父親和弟弟的眼睛笑成了一模一樣的白月牙。底片里的世界,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那真的就是另一個世界呀,他們在里面那么真實地望著我,他們吃著能甜疼舌頭的白蘭瓜,笑得好生歡快啊。
十八
他們說,你媽愛吃蝦。這些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沒吃過蝦,我們最常吃的是湯面。
我第一次見別人吃蝦,是跟著母親在買帶魚的長長的隊伍里。有一刻,透過人縫,我看見那個穿黑膠皮圍裙的售貨員,從泥灰色的帶魚堆里抓出一只蝦,是一只和泥灰色帶魚顏色一樣的蝦,他迅速脫下手套,剝了蝦殼,把雪白的生蝦一口塞進嘴里。這個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叫我很吃驚,我悄悄對母親說,那人把一只生蝦剝殼吃了,都來不及嚼。母親說,他大概餓了。我堅持說,不像餓,像饞死了的樣子。
母親總說我說話像大人,我不明白。我奶奶也這樣說。有一回,奶奶讓我唱《紅燈記》里的“我家的表叔……”,我學著鐵梅的樣子,用手摸著胸前毛線編的假辮子,轉過身,一邊唱一邊做出眺望的樣子,奶奶樂不可支地用她的狀似粽子的小裹腳在我屁股上踢了一腳,說:“你們看這個尕大人!”屋里的人哄堂大笑,我跑出屋,難過了許久,我覺得奶奶和屋里的人,包括母親,都傷了我的心。
他們說,你媽愛吃辣。是的,那時候母親就愛吃辣味的食物。我們小時候吃的最辣的是釀皮。母親在低矮的廚房里蒸釀皮,我們在廚房外的燈影下眼巴巴守著。做釀皮比平時的湯面工序復雜得多。辣子、蒜、醋、芥末都已備好,釀皮好不容易涼了,叮鈴鈴,自行車鈴聲響了,又是小舅來了。小舅吃了一大碗釀皮,我們不敢當著他的面說我們才吃了那么一點兒。母親說,你們小舅有口福,做了好吃的,他能聞到。小舅吃完釀皮還愜意地咿咿呀呀拉了一陣子我的小提琴。我那時好不容易懇求老師讓我進了學校的樂隊,每天可以神氣地背著小提琴回家。其實到最后我都沒學會拉小提琴。小舅也沒拉出哆來咪發唆拉西,母親說,來,蛋娃,你給我們拉個《我愛北京天安門》,我轉身跑出去玩了,直到天很黑,小舅的自行車鈴聲遠到聽不見才回家。其實,母親早看出我不會拉琴,但她還是給我買了一張畫貼在炕邊的墻上,畫中是個拉小提琴的女孩。
母親能看穿很多事情,甚至能看到事物的背面。她用天性里的柔韌對尖銳的事物溫柔以待,她的安靜流淌著的涓涓小溪般的小歡樂,讓我們的家常常東邊日出西邊雨。后來,樂隊老師堅決收回了我的小提琴,母親問我原由,我打開成語詞典,翻出“濫竽充數”給她看,她又差點笑出眼淚。
十九
母親說,生我的前一夜,她夢見了一只青蛙,一只綠身子紅嘴唇的小青蛙。母親說,生我弟弟的前一夜,夢見的是一條蛇。
我還沒到這個人世上的和我相關的事情,我不厭其煩地叫母親講給我聽。但我想起母親夢里的那條蛇,心就生生地疼。
二十
小學運動會,我跳遠第一名,獎品是一個鐵皮鉛筆盒,到主席臺領獎,校長很驚訝。母親想不明白又瘦又小的我怎么能跳得最遠,我說,我是青蛙呀。晚上睡了,母親在蠟燭下給我縫褲子,縫完褲子,我聽見她說,給我蛋娃的褲子兜兜里裝顆糖,母親一定知道我沒睡著,如果她知道我真睡了,就會一聲不響地把糖裝進我的口袋。
我想到燭花,蠟燭的捻子突然迸出的小花,奇異地懸在火焰邊,一朵明亮的搖曳的小花,讓屋里奇異得熠熠生輝。我想到一些類似的細小的事情,母親說,蠟燭結出花朵,家里會有好事。母親說,做了不好的夢,早晨一睜眼,別說話,先把壞夢變成唾沫吐三下。過年炸油果子,母親一再叮囑我們不能把鍋里的清油叫油,一定要叫水,叫它水,鍋里的油用起來才不費。眼角長了小疙瘩,母親讓我們在門框上蹭。脖子落了枕,要叫院里懷了娃的婆娘拿搟氈搟。
母親的左腳費襪子費鞋,我也是。母親腿上有塊胎記,我也有。我現在炸油果子,把鍋里的油也叫水。我縫衣服也像母親那樣不知所以地把針先在頭發縫里刮一下。我身上流淌著母親的習性。
他們說我和母親很像,樣子還有性情。我想起母親離開家后,有一次去多年未去的舅舅家,走進小巷,遠遠見舅舅一家面露驚訝,他們說,仿佛看見了我的母親。
二十一
那一年,我第一次知道地震。電影院正片放映前的假演里宣傳各種地震知識,地震前的預兆、如何自救,等等(那時,我們把電影院放映的故事片叫真演,把真演前播映的紀錄片、宣傳片叫假演)。對周圍的一切仔細望聞問切,似乎到處都有異兆。深夜里如果有瘋狗吠叫,會叫我心驚膽戰,大雞小雞們追逐亂竄也叫人瞎想,更別說刺眼的電閃和刺耳的雷鳴。母親炒了炒面,包在包袱里,放在最順手拿到的地方。我問母親,家里什么最貴重?母親說,就鬧鐘吧。我無數次在腦海里想象地震時的場景:飛快抱起鬧鐘,穿過大院,奔跑到馬路邊,抱緊一棵道旁樹。
那個鬧鐘的玻璃罩下面是蔚藍色的底子,金色的夜光針一長一短,鐘里有兩只小黃雞常年累月一刻不停地低頭啄米。父親給鬧鐘做了一個木屋子,前面剛好露出鬧鐘的臉盤,后面有個小門,門上有個金屬小門閂。對于一輩子分秒不歇地趕路,又一輩子不會走遠一步的鬧鐘來說,這個上了門閂的小木屋再合適不過了。
二十二
綠色的綢緞窗簾,嶄新時,翠色欲滴。對開的兩條窗簾,白天挽在窗戶兩邊,夜晚把它放下。其實,窗戶已被父親用塑料封死,再炎熱的夏天也打不開。翠綠色的窗簾掛在窗戶上,叫人覺得窗戶不再是個布景。很多年后,那個老舊的家已空無一人,路過時,我仰頭看著窗戶,仿佛還能看見翠綠色的窗簾。我和母親臨睡時把窗簾放下,第二天再挽起。我們好像在日復一日地為我們家徒有其表的窗戶完成一個儀式。
那時很甜的葡萄酒,過節時,母親喜歡用透明玻璃杯給每人倒一點兒。
母親用海娜花給我和姐姐染紅指甲。晚上臨睡前,把海娜花放在蒜缽里搗成泥,加點兒明礬,把花泥裹到指甲上,再用向日葵葉子把手包嚴扎緊。一夜不敢亂動,第二天一早拆向日葵葉子時,我非常緊張,因為有時候染出的指甲是紅的,有時候是發黃的。母親說,指甲染黃是夜里給屁熏的。
只染八個指甲,兩根小拇指的指甲不染,母親說,染紅了會遇到狼。
多虧母親給我們染的指甲都是紅紅的,紅艷艷的指甲一直不掉色,除非它長啊長啊,不能再長的時候,只好把紅指甲剪掉。
母親教我們用鉤針鉤織一片片太陽花苫簾,苫被子、枕頭、茶盤和箱子,還有花瓶里常年不敗的鮮艷的塑料花、炕邊墻上圍的一圈母親精心挑選的花布墻圍子。
那些看上去仿佛無用、多余的事物和事情,多么可愛。
二十三
后來,我們搬進了樓房。母親愛跳交誼舞,街坊近鄰都知道。我家買了唱機,有些陌生人到我們家局促的客廳里跳舞。
我深愛那個奶油色的唱機,一曲完了,趕快提起唱針,輕輕地把針腳放入另一張唱片的滑槽。那是我長久不能解釋的原理,聲音如何藏進那些滑槽,唱針怎樣喚醒它們?唱針有時會崴了腳,唱機的聲音歪歪扭扭像要被風吹走。“天涯呀海角,覓呀覓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們倆是一條心……”周璇的歌聲最適合唱機,聲音抖抖的像是要飄遠。有各樣顏色的塑料唱片,貴一些的是厚硬的黑膠唱片。那時,看大人們跳交誼舞,我知道了不少世界名曲,《藍色多瑙河》《春之聲》《溜冰圓舞曲》《培爾·金特》……還有不少外國電影的主題歌,《孤獨的牧羊人》《雪絨花》《友誼地久天長》……我滿腦子旋律,有時心里想著某個曲子,用手指敲著節奏給母親看,讓她猜我心里想的是啥曲子,母親笑我,心里的事,別人怎么知道?是的,母親藏在心里的事,我們沒人知道。
我跟著母親去過幾次街面上的舞廳,新曲子一響,人們紛紛搜獵舞伴,母親一曲不落。奇怪的熒光燈跟著新曲子亮起,牙齒和白襯衣像被X 光探照一樣,變得瑩白,女人們白襯衣下面胸罩的輪廓一清二楚。
父親那時最厭煩母親和別人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慢四步,動作緩慢,緩慢里似乎會生出很多不一樣的東西來,那些東西又不屬于他。那時,我也恨這個曲子,我惡狠狠地唱到半音階的那句“我想對他講……”就覺得聲音失重得像要從高空跌落下來一樣。放學后看到跳舞的男人和母親在屋里聊天,那人給我掏出一把亮晶晶的水果糖,我像厭煩那個半音階一樣厭煩那些糖。
二十四
母親用普通話和我們說話,她后來到了一個說普通話的家里。她和他們不一樣的是,她的普通話里夾雜著方言。
后來,她用普通話說出的話是反的。她不想在床上躺,想坐起來,一個勁兒扶著床邊用普通話說要躺要躺。在醫院,姐姐要送飯過來,她一直把姐姐的名字叫成我的名字。那天出院,外面下著雨,我用輪座把她推到露臺上,她說,天怎么又曬了啊?母親用普通話說的那個“曬”字,特別叫我心疼。
出院前一天,她在病床上躺著,一天都不說話,他們來了,她突然痛哭起來,我退到門外,看著他們哭,母親突然清醒了似的,說,我們的家以后怎么辦啊?
是啊,他們的家。
他們說,幾十年了,第一次見你母親哭。
二十五
河邊,雪白的月季長得都高過我了,這條母親也曾熟悉的大河,流得多像時間呀,它又快又慢,分秒不歇,老天也留它不住。
二十六
那么,我們有過多少個家呢?
我們一直在流徙。
我們第一個家在大雨里破了,電閃雷鳴中,我們家的后墻坍塌。那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們三個孩子,我們逃出屋子,一院子的鄰居在大雨中排隊傳遞我們的家什。那晚,我住在大院里的蘭蘭家,第二天,我看見我們家變成了油毛氈苫著的一小堆家具。
很多年,我反復夢見工廠大院角落里那個被雨水泡塌的家。一棵臭椿,顯示著我們家可愛的獨立,如果立一面墻,我們的小院便可自成一體。但院里的眾人不允許我們獨立,父親做了一道木柵欄,因為攔住了隔壁家隨意走動的小雞,便有了唯一一次鄰里之間的吵架,眾人圍觀,木柵欄被拆了。就在那個小院,母親把偷懶不上幼兒園的我抱到窗臺上曬太陽。母親在低矮的廚房里蒸釀皮,母親叫我蛋娃。母親在小院里踢毽子,能連著踢十幾個。母親雙腿騰空,辮子揚得好高,我和姐姐誰都踢不過母親。我和姐姐跳皮筋,缺一個人,臭椿在一邊替我們撐皮筋。木匠父親給弟弟做了一個木頭推車,推車外面掛著父親給弟弟做的木頭刀。
后來我們借住在一個親戚家,一個四合小院里的一間小屋。四合院里,北屋人家喇叭花盛開。菊花夜夜尿床,她家早晨開門第一件事是到花架下曬洗過的尿褥子,菊花能在她家屋墻上倒立很久,還能騰出一只手挖鼻孔。對面一家的三個兒子做賊,警察到他家搜出很多贓物擺在院里,我縮在姥姥身邊,從姥姥小心翼翼拉開的細細的窗簾縫往外張望,很長一段時間,我像做了賊一樣,見到警察就會瑟瑟發抖。那個小院離學校很近,小院所在的巷道對面是長途汽車站,樓頂是城市里唯一一個會報時響音樂的大鐘。中午十二點,《東方紅》的音樂和鐘聲還沒響完,我已經從學校飛跑進了家門。有一天,久久不回家的四五歲的弟弟被父親在長途汽車站找到,不善言談的父親那幾天逢人就說,找到弟弟時,弟弟手里捏著幾塊奶油糖。現在,我寧愿我的弟弟那時被騙走,這樣的話,他或許還活在這個世上。茅廁在四合小院的院角,每次上廁所,北屋菊花家的小公狗就尾隨而來,我便早早解下皮帶,上廁所時,把對折的皮帶抽得啪啪響。
后來,我們搬進織襪廠的會議室,大約七八家擠在一起。用裝襪子的大紙箱板子隔開的家,十分奇特。家家難藏秘密,主席臺上住的是一家上海人,趁他家沒人,我們偷偷進去研究人們常說的上海人用的馬桶。家家用軍綠色的煤油爐子做飯,誰家的好吃的都躲不過每個人的鼻子。我的床由兩條長椅對拼而成,床頭放一個兩頭拆開的大箱子,睡覺時,把上半身鉆進去,那里成了我的私人領地。
后來我們和幾家人從會議室搬進一片廢墟上孤立的幾間舊屋。屋子對面,機器轟鳴,工人們夜以繼日地破舊立新;屋子這邊,是被我們利用的一大片廢墟。我時常到廢墟里搜尋,曾經找到一個寫了幾頁字的日記本。扉頁上抄有一段文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我在那個本子上做作業,班主任問我,這段話是誰抄的?我言之鑿鑿地說:“我。”老師沒有戳穿我。后來我才知道陌生人在本子上抄的是魯迅先生的文章,我也常常想到這個人何以愛上魯迅的這段文字,而且那筆觸,像是用鋒利的蘸筆刻到紙上的。
晚上,我和姥姥早早睡了,沒有窗簾,可以看到廢墟對面嶄新的樓上無數個燈光明亮的窗戶,像一塊在夜色里打開的巨大的屏幕,里面人影幢幢,輝煌怪魅。弟弟非常漂亮,人見人愛,姐姐和他追著玩,他的額頭撞在工地的軋機上,流了很多血,額頭上從此留下一個永久性疤痕。姥姥養的下蛋雞不見了,我們尋遍工地,在一幢新樓的樓道前發現了一堆雞毛。后來,巨大的廢墟場中間漸漸拱起一個巨大的廢墟堆,像在我家門前聳立了一個巨大的墳塋,里面埋著很多人林林總總的時間和記憶,也有我的。
后來呢,我們搬進樓房,有了光滑的水泥地面。陽臺上的花盆里,母親種了牽牛花、喇叭花、吊金鐘、金錢樹、臭繡球,它們都是些窮人家的花兒。父親種了滿刺的仙人掌、仙人球、劍蘭,它們都是些能忍饑挨餓的花兒。一年四季,如果沒有父親漚的肥料作怪,我們的陽臺可以說花香四溢。屋里有了唱機,陌生人到我家跳交誼舞,我家也可謂歌舞升平。我和母親的小屋,徒有其表的窗戶掛上了翠綠色的綢緞窗簾。我上中學時,一溜煙跑下小山坡,和同學像鴨子一樣,張開膀子,一人一根鐵軌,比賽誰走的時間長。再后來,家里沒母親了,也沒父親了,只留下我們陪著重病孤苦的弟弟,我們做他的姐姐,也做他的媽媽和爸爸。
流徙一再加重著生命的無力感,也顯現著一個家叫人難以置信的生命力,只是有些過往怎么都難以掌控,我們只能堅韌地跟著時間前行。
這就是我們史詩一樣的家。只是,母親同史詩一樣的人生,有一半流徙到了我們的家外面。
二十七
現在,母親已走完這個世上的路。我們的生命交疊了半個多世紀。深夜,我眼前總是出現她最后一刻的樣子,時間在那一刻滯留、徘徊。那一刻,記憶和想念循環往復,時間如大海般幽暗深邃。